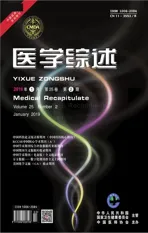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细胞癌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2019-01-24欧阳福杨丽莎
谭 萃,欧阳福,杨 怡,杨丽莎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广西 桂林 541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除外饮酒和其他肝脏损害因素所导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NAFLD在组织学上可分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两种类型。非酒精性脂肪肝存在肝脏脂肪变性,但无肝细胞气球样变等肝脏损伤。NASH指肝脏脂肪变性,存在肝细胞损伤,伴或不伴纤维化。NAFLD涵盖单纯性脂肪肝、NASH、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等范围广泛的肝脏改变[1]。
随着亚洲人口老龄化进展,NAFLD患病率普遍上升,已从2005年的15%上升到2010年的25%[2]。在接受肝活检的NAFLD患者的荟萃分析中,估计NAFLD患者NASH的全球流行率为59%,而一项对全世界人口的荟萃分析中,NAFLD患者的HCC年患病率估计为0.44/1 000,相比之下,NASH患者的HCC年发病率为5.29/1 000[3]。由此可见,对NAFLD相关肝细胞癌(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NAFLD-HCC)发病机制的研究尤为重要,现对近年来NAFLD-HCC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代谢综合征与NAFLD-HCC
NAFLD作为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与肥胖、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与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诱发肝/全身IR,并导致多种促炎细胞因子、血管活性因子和促氧化剂分子的增多,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通过促进肝细胞生长和抑制细胞凋亡等途径来促进HCC的发展[4]。目前,慢性肝炎感染的发病率降低,但HCC发病率却不断增加,可能与代谢危险因素有关的NAFLD和NASH发展为HCC数量增加有关[5-7]。
1.1肥胖症 低度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增加是肥胖症的特征,可损害细胞成分,并在由代谢改变引起的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NAFLD的发展与活性氧类介导的肝细胞损伤有关[8]。肥胖症的营养过剩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抑制细胞凋亡,产生活性氧类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受损,癌细胞代谢失调,最终促进癌症进展[9]。
Fujiwara等[10]发现,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2下调诱导脂肪酸β氧化的抑制,可解释HCC的脂肪变化。肥胖导致的HCC中,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2下调使HCC细胞逃脱脂毒性,并促进HCC发生。肌腱蛋白C是一种在纤维发生和肿瘤发生中起作用的细胞外基质蛋白,饮食诱导的肥胖HCC动物模型中观察到,肝星状细胞衍生的肌腱蛋白C和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表达增多,促进免疫细胞和肝细胞的炎症反应,肝细胞转化和迁移,从而促进HCC的发生[11]。因此,减轻体重而抑制肌腱蛋白C和TLR4表达可能会抑制HCC的发生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有助于肥胖相关HCC的发生。补充二十碳五烯酸的高脂肪饮食组小鼠致癌物诱导HCC的发展显著低于仅高脂饮食组小鼠,二十碳五烯酸几乎不影响与肥胖相关的炎症,但可抑制致瘤性IL-6效应子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的激活,有助于抑制肿瘤生长[12]。二十碳五烯酸具有比二十二碳六烯酸更强的三酰甘油还原作用,而二十二碳六烯酸比二十碳五烯酸对致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肪饮食诱导的肝脏炎症和活性氧类产生具有更大的抑制作用,但致纤维化作用无明显差异[13]。
1.22型糖尿病和IR 有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是HCC的独立危险因素,2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肝纤维化的风险[14-15]。IR是一种慢性炎症,可导致脂毒性、内质网应激和自噬受损,最终导致肝脏炎症、肝星状细胞活化和进行性纤维化的肝细胞损伤和死亡,从而推动疾病进展。肥胖和胰岛素作用的损害导致脂肪细胞脂解抑制,脂肪细胞应激,随后释放肿瘤坏死因子α、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抵抗素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等促炎脂肪细胞因子,这些促炎脂肪细胞因子通过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和c-Jun氨基端激酶途径破坏胰岛素信号转导,并在其他胰岛素敏感组织中促进IR[16-17]。
NAFLD患者一般也存在IR,IR与脂肪肝和低度慢性炎症共同为肿瘤生长提供条件。IR和高胰岛素血症促进激素失衡,导致炎症、氧化应激、脂毒性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1轴的过度刺激[18]。IR损害胰岛素抑制葡萄糖的产生,并可能通过促进细胞增殖、抑制凋亡和刺激肝脏新血管形成而直接加速HCC发生[19]。一项研究显示,NAFLD的IR与增加的氧化应激相关[20]。
IGF-1受体在体外和HCC动物模型中过表达证实,IGF配体通过IGF-1受体对HCC细胞发挥作用,通过提高有丝分裂活性参与癌前病变的恶化[5]。高胰岛素血症导致IGF-1的产生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的肝脏合成减少,同时可增加IGF-1的生物利用度,进而促进诱导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亡过程,并在HCC发展中起重要作用[21]。二肽基肽酶4在肝脏中的表达升高促进了NAFLD和IR,这与活性胰高血糖素样肽1水平降低有关,也与二肽基肽酶4对肝脏胰岛素信号的自分泌和旁分泌效应有关[22]。
HCC中miR-190b通过调节IR发挥作用,NAFLD患者肝组织中miR-190b的表达较正常组织显著增加。此外,miR-190b在高脂饮食NAFLD小鼠模型和非酯化脂肪酸诱导的NAFLD细胞模型中均上调[23]。
2 肠道微生物与NAFLD-HCC
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在NAFLD-HCC中起关键作用。NAFLD-HCC进展过程中,肠道微生物发生相应改变,厚壁菌门和放线菌显著增加,而类杆菌和变形杆菌显著减少。肝脏脂肪变性阶段可观察到肠道微生物群的显著改变,并持续整个肝脏疾病进展过程[24]。NAFLD患者和小鼠模型中可见细菌过度生长和肠道通透性增加,这与肠道细菌产物脂多糖水平密切相关,脂多糖通过TLR4依赖性上调的细胞内机制引起肠渗透性增加,脂多糖通过门静脉到肝脏,从而激活TLR4[25-28]。小鼠模型中,TLR4激活肝星状细胞导致CXC趋化因子配体1(IL-8的同源物)的分泌,引起中性粒细胞募集至肝脏[29]。TLR4缺陷型小鼠肝脏中CXC趋化因子配体1的水平下降,中性粒细胞计数也随之下降,而肠道微生物群的消耗模拟TLR4缺陷表型,即减少肝脏中的中性粒细胞计数[30],使肝脏的炎症反应减轻。Achiwa等[31]研究发现,胆碱缺乏型高脂饮食小鼠在使用葡聚糖硫酸钠治疗时显示出脂多糖的全身性易位,高水平内毒素血症的存在导致门静脉高压和肝细胞损伤,促进NAFLD向HCC的进展[32]。

3 基因因素与NAFLD-HCC
PNPLA3、TM6SF2、GCKR、NCAN、LYPLAL1和MBOAT7被证实与NAFLD相关,而PPP1R3B和MBOAT7可能影响NAFLD的严重程度[39-40]。PNPLA3是NAFLD发展中最重要的基因之一。肝脂肪变性的进展与携带PNPLA3多态性rs738409的等位基因G有关。基因型GG rs738409 PNPLA3的NAFLD患者比杂合子和无G等位基因患者的肝脂肪变性更严重[41]。PNPLA3多态性参与HCC发病机制可能与PNPLA3在肝星状细胞中视黄醇代谢中的作用有关,但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其相关性[42]。研究发现,E434K可降低PNPLA3的表达,减少I148M变体对脂肪变性和肝损伤的影响,并通过阻碍其在脂滴上的积聚来减少I148M变体的负性作用[43]。
TM6SF2的过表达通过减少载脂蛋白B的分泌,导致其在内质网的积聚,从而调节肝脏脂肪积累,而MBOAT7多态性与纤维化有关,PNPLA3多态性则赋予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增加的风险[44-45]。PNPLA3和TM6SF2在校正IR后也能增加NASH和显著纤维化的风险,并产生累加效应[46]。TM6SF2 E167K变体可部分通过改变TM6SF2和微粒体三酰甘油转运蛋白的表达,从而促进脂肪变性和脂质异常,而对纤维化的影响较小。尽管肝脏脂肪含量明显增加,但TM6SF2 E167K变体对脂肪分解、肝葡萄糖产生和缺乏高三酰甘油血症仍保持胰岛素敏感性[47-48]。
4 促炎细胞因子与NAFLD-HCC
NASN以广泛的肝细胞单核细胞浸润为特征,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在调节疾病演变中具有重要作用,NASH进展期肝巨噬细胞内脂肪积累促进了影响肝炎症反应的抗炎介质的产生[49]。脂肪酸结合蛋白4在肝星状细胞中的过度表达可刺激NF-κB信号转导途径,其中炎性趋化因子的表达水平通过NF-κB的核易位上调,导致巨噬细胞募集。可见,脂肪酸结合蛋白4在肝星状细胞中的过度表达可能通过调节炎症途径促成具有代谢危险因子患者的HCC发生[50-51]。
高脂肪饮食诱导的NAFLD模型中可检测到促炎细胞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1的早期和持续升高,它的上调是双通道修饰上调,转录后被miR-200家族调控,特别是miR-429[52]。
通过给予小鼠甲硫氨酸和胆碱缺乏饮食模拟NASH发现,NASH不仅增加总肝脂肪酸和胆固醇,还可明显升高C18/C16比例,从C16到C18的脂肪酸延长可促进肝脏脂质积聚和炎症,并发现介导C16脂肪酸延长的超长链脂肪酸延伸酶6在人NASH和NASH相关HCC中升高[53]。
5 脂肪细胞因子与NAFLD-HCC
脂肪细胞因子(脂联素和瘦素等)在NAFLD及NAFLD-HCC中发挥重要作用。脂联素具有抗炎、抗糖尿病和抗肿瘤作用,几乎全部由脂肪细胞产生[54]。研究发现,脂肪组织中介导脂联素分泌的常规驱动蛋白重链的选择性缺失可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症及其相关代谢紊乱产生加剧作用,而脂联素的过度表达可阻碍肝微粒脂肪变性的进展[55]。除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调节肝脏脂肪代谢外,脂联素可通过抑制NF-κB的活化及肿瘤坏死因子α的表达来减轻炎症反应。此外,降低的脂联素水平可能有助于NAFLD坏死性炎症的发展[56]。瘦素由脂肪细胞以外的多种细胞产生,可抗脂肪变性,具有调节T细胞和免疫、促炎症、促纤维化的作用。瘦素在NAFLD相关HCC中的表达下降,与脂联素具有相反的作用[54,57]。血清瘦素水平的增加也与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瘦素水平升高而脂联素水平下降可促进NAFLD疾病的进展[54-55]。脂联素和瘦素在NAFLD-HCC中的作用还不完全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6 自噬与NAFLD-HCC
自噬是脂质分解代谢的主要途径,可调节胰岛素敏感性、肝细胞损伤、先天性免疫反应、炎症、纤维化和癌变。有证据表明,自噬有助于NAFLD的进展[35,58]。NAFLD发展与免疫相关的GTPase家族M基因(自噬相关基因)变体有关,GTPase家族M可能通过改变肝脏脂质代谢通过自噬途径促进人类NAFLD的发展[59]。
自噬可保护肝细胞免受外源性凋亡途径,自噬的肿瘤抑制功能通过降解致癌自噬底物和维持健康线粒体减少氧化应激和DNA损伤[60]。具有肝细胞特异性剔除转化生长因子β活化激酶 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activated kinase 1,TAK1)的小鼠易发生自发性HCC,若肝细胞缺乏TAK1,可抑制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靶基因和调节肝脂质降解的β氧化,表明TAK1诱导的自噬可能抑制脂肪肝相关的HCC生长[61]。
7 小 结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抗病毒药物的使用,病毒性肝炎导致的HCC逐渐减少,但是NAFLD-HCC患病率逐渐上升。肥胖症、2型糖尿病和IR的代谢综合征和促炎细胞因子以及脂肪细胞因子等细胞因子疾病在NAFLD-HCC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目前,针对肠道微生物、基因因素和自噬的研究尚未深入,仍缺乏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持,已成为研究热点。NAFLD-HCC发病机制多样,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可为NAFLD-HCC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