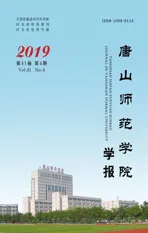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唐代乡村治理转型初探
2019-01-20胡瑜锴
胡瑜锴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50)
唐代是古代中国最为辉煌的朝代,诸多制度在此时形成,而乡村治理制度也在此时产生了重大变革。
唐中叶开始的乡村治理转型是渐进式的,乡村与国家的互动和博弈是其中重要的主线之一,二者之间冲突与碰撞导致了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变化。如何吸收唐代乡村治理经验,从而实现当代基层社会有序稳定地运行,这正是本文重点。
一、乡官制的构成
唐初乡官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而设立,里正亦以其为依托,故乡官制与均田制乃是荣辱与共的关系,实际运行时亦呈现大体一致的走向。
唐代“乡”制的改革,里正成了实际掌权人。统治者一方面提高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予以厚待,里正成为唐代基层管理人员而备受欢迎。《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七》载:“每一员阙,拟者十人。”[1,p4166]这既是大一统社会对乡村基层管理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所致。
当时的里正需要依律典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否则就会被处以刑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2,p251]
由上可见,乡官制的核心在于里正。但是唐代中期以来,由于土地兼并问题逐渐凸显,导致均田制下的小农阶层解体,从而出现了大量流民,从根本上打破了唐初设立的乡村管理体制。里正的原有权威与管理职能日渐衰微,此种变化昭示了乡官制渐趋衰微。究其根源,便在于均田制的衰败,原先流畅运行的治理体系在此环节上出现问题,导致土地还授机制受到了极大冲击,且状况不断恶化,而这又进一步促使里正的弱化。实际上,里正仅是国家掌控乡村的工具罢了,其本身并无可能超越其所在阶层的局限,但从里正的衰落,也能看出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权力的流失与王朝的衰落。
(一)乡里制及里正
“乡”最早出现于周代,当时称之为“乡遂制”;春秋时期,奠定了乡里制的基调,此时“乡”下沉为基层行政单位;秦汉时期推行乡里制,奠定了“乡”的地位,成了后世沿袭的基层组织;汉代,“乡”乃基层权力之中心,全面管理所在区域的各种事务,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两晋仍采乡制,至北魏拓跋氏当政,创立三长制,乡制被废止。隋至唐初期,重新设立乡制,然其并未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导致乡级行政人员终被废止。乡正废止后,其具体职掌由里正接管,这也是唐代乡村的一个重要特色。
唐代乡级行政建制则是政权组织结构中重要的一环,亦是行政区划和赋税征纳的基本单位,承担具体事务的组织、监管、实施等职能。另外,皇帝大赦天下、授予封号时,乡也是一级封授单位。
而“里”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组织,出现早于“乡”。东周出现了乡里并称的趋势,这一时期管仲所创的乡里制较为成熟;秦汉时期则进一步简化,“里”成为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唐代规定则较为合理:“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3,p63]
在唐代乡村建制中,乡是基层行政中心,其实际执掌人员是里正,凡是县府所下命令,均由里正承接,负责执行。而在“村”制度确立后,里正直接处理村务,形成里正为主、村正为辅的格局。
里正设置历史悠久,战国时一里之长“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3,p195]。
其一,按比户口。《唐律疏议·户婚律》载:“里正之任,掌按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2,p251]也就是对人口户籍的管理。
其二,课植农桑。侧重于农业生产的组织督导,及各项相关制度的执行核查。若遇上灾害,里正则应当按实上报,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考,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若致枉有所征免,赃重者,坐赃论。”[2,p252]
其三,检查非违。里正要对辖区内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察、上报;对于外来人口,必须及时核查上报;对于从其它地方逃亡来的浮浪者,唐律严令禁止予以收容。此外,里正还需要协助军方检查军人违法状况。
其四,催驱赋役。即征收税赋,驱使劳役。
唐初政府废弃乡正而提升诸里正职权,由其共掌乡务,既达到分权的目的,也可使诸里正相互制衡;唐代中期里正势力渐大,政府为保证中央权力,设置村正分权,从而削弱里正。这也是里正衰落的一个原因。里正的衰落也反映了直接依靠政府权力进行治理仍有较大缺陷,故而其后转变为以自治为主的户役制。
(二)村制及村正
隋朝在继承前朝乡里制基础上并加之改造,村落发展基本成熟,《隋书·食货志》载:“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4,p680]
“村”正式成为国家行政的一环是在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5,p2089]。
“村”制度大致创设于武德年间,其行政首脑称为“村正”。谷更有认为,“村正”设立于废除乡长、佐以后[6,p7]。
开元时期,国家制度建设已较为成熟,承唐初之设计,唐政府于基层组织的规制已大致定型。与秦汉不同的是,“里”的地位提升,而“村”“坊”则取代“里”成为基本行政单位。随着村落普遍化,原先行政设置已不能实现有效管理,故唐政府顺势应变,正式确立“村”制度,“村”成为国家基本治理单位。
里正工作的履行需要直面“村”。政令榜示于“村”,便可直接迅速地布告广大村民。而具体执行中,里正需要直接与村民接触,故为履行职责,里正必须频繁活跃于村落,方能及时掌握和应对各种情况。
里正是乡村事务主导者,村正则为助手。村正职能为“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3,p63]。其主要负责村内治安,同时也负责思想教育工作,包括防盗捕贼、处理突发事件、核查上报外来人口、禁止邪教等。相较里正,村正于村情更为熟悉,故政府赋予其职责亦在情理中。实际上,保持乡村稳定从而汲取乡村资源,乃一切乡村管理方略之根本出发点,村正之设立及其职责,即国家加强对“村”控制的方略之一。
因此,无论里正之调整,还是村正之配置,均是政府为有效掌控“村”刻意而为的措施。唐代“村”的强化是统治者加强基层控制的必然结果,而乡村中里正、村正的设置规范则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表征。
而其设立之考虑便在于如何管理的问题,故有无村正乃是否为行政村的标准。
由于村正熟悉村情,故为乡村的主要掌权者,对于村内的管理问题应当及时上报,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其职责包括对外来人口的稽查和乡里纠纷的司法。此外,对于县政府临时诏令,村正也必须遵守执行。
但随着村务逐渐繁杂,村正也逐渐突破了原先职能的限制,政府赋予其更多的职责,如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征纳赋役也是其一。《王梵志诗校注·贫穷田舍郎》载:“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恶骂,啾唧搦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赔。”[7,p651]由此文可知,村正与里正共同行使税收的职责。
村正与里正同是唐代乡村的掌权人,故《唐律》中于二者的职责规定,也大致相同,但就其本身特性而言,仍有着较大区别:
其一,行政职能。里正乃事实上的乡官,故其职能包括所有乡村之事,而村正职责虽不限于治安管理方面,但范围仍在一村内。
其二,选任条件。里正选任条件明显高于村正。而实际选任中,里正均出身白丁以上,但村正多为中男,从而与唐制标准保持一致。
其三,任职待遇。按唐制,里正可免除课役,即租、庸、调、地税等;村正免除的则是杂徭,其多于本州县服役,如水利设施修建。
由此可知,里正、村正虽同为乡官,但在职能权限、选任标准、任职待遇上,村正地位都明显低于里正,故在处理乡村事务时,里正为主、村正为辅的格局也是合理的。
二、户役制的萌生
唐代中期,逃户数量巨大,“安史之乱”引爆了积累颇深的社会矛盾,导致唐王朝的衰败。平叛之后,乡村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定型,富户阶层开始崛起,基层力量增强,农户则成为雇农或佃农,均田制名存实亡,唐代政府因之陷入财政危机。
在此背景下,两税法被提出,“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8,p7556]。资产代替了原先的人丁,成为缴纳税赋的标准。纳税者按照田亩资产征税,改变了以往税赋不均的现象。两税法的实行,宣告了均田制的废止,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乡村现有资源分配格局的认同。于是,两税制取代了均田制,而以财富多寡为征收标准,说明富户阶层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里正在面对实力强大的富户时,由于其实力不足而无法取得税款,常常需要其代垫,里正之衰败一至于斯。故而,唐政府转而同富户进行合作,努力将其纳入国家利益中来。富户阶层从而掌握了税赋收缴、户口监控、司法诉讼等权力。至此,户役制取代乡官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制度。
(一)富户阶层的兴起
唐代中期以后,“富民”的实力逐渐增强。但纵然商人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仍然将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产,大量的资本投入土地,故而大量的乡村富民阶层兴起,成为基层社会强大的力量。
在资本大量投入土地的背景下,原先均田制下的小农阶层受到巨大冲击而逐渐瓦解,一部分成了富户,但更多的沦为了佃户、贫农。富户阶层的概念在玄宗时期也逐渐明晰,“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如有嘱请者,所由牧宰录名封进,朕当处分。京都委御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隐蔽不言,随事弹奏”[9,p385]。
富户成为相对于官吏、豪强的另一股地方势力,其崛起也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故而在乡官制衰落的背景下,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户役制被提出:“宣宗大中九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炼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10,p127]
富户阶层兴起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均田制本身所具有的不公平性,《通典·食货典》载:“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3,p29]田地不仅因种类而有所区别,重点在于官员豪强所具有的特权,这埋下了均田制崩溃的种子。到了玄宗时期,唐初均田制下的小农阶层瓦解,少数农户成为富户阶层,成为乡村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权贵工商以其财富和权力,掌握了大量乡村土地资源,亦为富户阶层。其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由于隋唐科举制的兴起而逐渐没落,大量寒门新贵崛起,成为新的乡村力量。许多官吏退休后,大多选择在乡村置办田产,从而形成诗书耕读传家的传统,良好的乡村—城市互哺循环渐渐成形。而那些入仕失败的读书人,往往也选择在乡村教书育才,使得乡村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教育上都能够自给自足,不断涌现优秀人才。其三,唐代商品经济发展,农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优胜劣汰的规则下,少数富户脱颖而出,成为乡村资源事实上的掌控者。
总而言之,在社会阶层流动活化的情况下,富户阶层的兴起是合乎发展的,这也昭示乡村自我治理的强大能力。
(二)乡村资源的重组
唐初均田制的制定,产生了大量的乡村小农阶层,但随着土地兼并和中央实力减弱,富户阶层渐渐取代了小农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贫富差距一步步扩大。玄宗朝为限制土地兼并,多次下诏。
通过政治的力量来干预土地买卖,从而保证乡村社会的稳定,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10,p48]
可以发现,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导致了小农阶层的生活无以为继,恶性循环之下土地都被富户所把持,国家和底层民众都遭到了巨大创伤。
富户阶层的兴起正是在这种剥削体系下发生的,而唐代统治者为了抑制富户,也出台了相应政策:“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人,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公钱未益于时须,禁法不当于世要。其恶钱臣望官为博取,纳铸钱州,京城并以好钱为用。”[9,p2828]
政府把劣质钱币的流通归咎于富户阶层,并意图借此打压富户,从而取得充足的税赋。但效果并不明显,仅仅在名声上抹黑了富户阶层,而乡村资源仍旧掌握在富户手中,故而统治者也不得不依靠富户进行乡村治理,户役制应运而生,基层社会也由国家直接管理转变为乡村自治的模式。
(三)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
唐初,统治者就开始表现出对富户的重视,“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5,p32]通过政策强制富户帮助贫困人群,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富户对当地乡村的掌控,但也有利于乡村基层的稳定。
到了玄宗时期,随着富户阶层兴起,政府也逐渐尝试给富户摊派事务,并且兵役也多由富户承担:“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5,p2086]税、役都由富户负责,看似加大了富户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将权力交到了富户的手中。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对乡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断层,富户阶层趁机掌握了大量的乡村资源。而政府为了迅速平叛,增加了南方小农阶层的税收,从而进一步瓦解了均田制,也使得其财政彻底陷入瘫痪状态,而乡村社会则彻底被富户阶层所掌握。
面对困境,政府开始了全新的财税政策即两税制,有效改变了赋役不公的状况,大大减轻了贫农的负担,保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故而,两税法取代了均田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制度。此后唐代统治者亦多次下令,重申两税制:“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8,p8056]通过禁止人口买卖、叫停苛捐杂税、打击宗教势力等手段,政府有效地维护了乡村基层的秩序。
而在两税制的背景下,富户成了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既解决了乡官制下里正没有足够能力收取赋税的缺陷,也有效保证了贫农的基本生存,故而富户阶层最终成了政府在乡村的代理人。
至此,乡官制被废除,富户轮差的户役制兴起,唐代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可以看出,完全的基层自治是不可取的,国家应当运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来防止基层力量过于膨胀,在法律的框架下赋予基层社会一定的自治权利,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一切的历史都是整体的历史。唐代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官制到户役制的转变,既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同时此项转变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总的趋势,就是国家权力从中央走向了地方,这一方面加强了地方自治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乡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唐王朝无法解决也没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从而走向灭亡。
在当前基层社会中,虽然不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但如何治理仍旧需要从唐代的制度变化中吸取经验,一方面要警惕国家对基层干预太多导致的僵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基层尾大不掉、侵犯民众权利现象的出现。
首先是要充分发挥基层能动作用,形成基层自治,一方面可以通过居(村)委会调解的方式将一些矛盾化解,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邻里作用,从而实现守望互助;其次,应当以法律为基准,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实现基层自治,避免“土皇帝”的出现,既可保证公民权益,也能维护国家力量;再次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新道德,避免传统糟粕思想和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最终,实现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治理,形成以德治为标杆、法治为根本、自治为动力的全新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