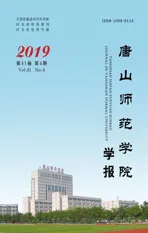明治大帝像的三个侧面及其阴影
2019-01-20崔祖祯刘豫杰
崔祖祯,刘豫杰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彼得·伯克认为,大多数所谓伟大君主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有意识的人为建构[1,p100-103]。在《制作路易十四》一书中,作者更是将“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比作是一场“17 世纪的造神运动”,即臣下利用诗歌、雕塑、油画等艺术形式对国王进行“包装”,国王本人则通过在一系列节庆仪式中“表演”来宣扬自我。事实上,“伟人塑造”这一造神传统延续至今:“17 世纪君主与20 世纪领导人间的对比,并非虚饰与真实间的对比。只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虚饰之间的对比。”[2]
那么,以此种方式解构所谓的明治大帝,还原其历史性的本原形象,这对剖析“明治的伟业”应当不无裨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及语言的差异,“西味”浓厚的大帝一词显然并不是明治天皇的专属,实际上在明治天皇逝世后正是欧洲媒体率先赋予其大帝的称号并将其视作是与俄国彼得大帝相比肩之人物,而日本原产的“圣帝”与“圣徳”的前缀仿佛已不能完美地叙述其历史性之地位[3,p11-13]。因此,明治大帝这一西式称谓不啻为自明治维新始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了解到这一点便是进行解构作为大帝的明治天皇这一工作的起点。
当然,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完全同质的群体并不存在,“缔造者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向人们表达了太多的信息,而每当追随者试图去诠释缔造者的信息时,潜在矛盾便暴露出来了”[1,p116-117]。这一点也就是大贯惠美子所说的意义域之转化的问题,而这一点在国体明征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明治大帝的形象图示并不统一,而本文中所提的解构工作乃是基于抽象出的明治天皇形象的三个侧面,以及建构这三种不同维度的不同方式。
一、万世一系的现人神
自平安后期藤原氏掌权后,古代天皇制下天皇的权威便被摄关政治逐步消解,步入武家社会之后,天皇在政治上的实际作用更是渐趋为零。而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本由皇室承担的诸多礼节性仪式、祭祀也索性被幕府接管。甚至当时的朝廷一词乃是对幕府的指代,京都仅被冠以“禁中”“禁里”的称呼;与此同时,天皇本人不仅足不出户,专于文艺,在光格、仁孝两代以前,天皇更是仅被称为“某某院”[4]。天皇朝廷除了权威扫地,其形象也几乎消失于百姓的视野之中。
直至德川幕府后期,逐渐兴起的国学与后期水户学才扭转了这一局面,前者假托记纪神话构建出天皇家的神话谱系,后者则凭借宋学中的大义名分论强调出天皇家的绝对权威。尽管在宝历、明和事件中,幕府对于尊皇意识的抬头严防死守,但上述两种不同源流的尊皇意识的合流却在幕末激起了巨浪,万世一系的理念亦由此辐射而外并附着于尊王攘夷的口号,深深植根于幕末草莽志士的意识之中。安丸良夫所说的近代天皇制的第一个要点便由此脱胎而出[5,p10]。
如果说国学、后期水户学两派知识分子关于以天皇为顶点的宇宙论的精神建构尚属一种早期的、被动的建构,那么以幕末为拐点,京都朝廷则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事实上在整个德川幕府时期,由于与朝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关联,京畿周围的民间社会一直延续着对于朝廷的神话式尊崇[5,p66-67],只是这种神话式尊崇的对象并非只局限于天皇一家。然而自孝明天皇始,这种所谓“天皇和贵族共有禁中”的“传统神国思想”逐渐崩弛,摄家等贵族家系被清理出门,“唯有天皇才是神武天皇以来继承‘万王一系’的‘贵种’”的“新神国思想”得以确立[6]。不仅如此,由于孝明天皇出身于血统并不高贵的闲院宫家系,为了抵消其它宫家以及以鹰司家为代表的摄家的压力,这种神话式的自我建构便具有了相当成分的现实政治的考量。可以认为,尽管孝明天皇的诸多行为与“维新的伟业”常相龃龉,但他重塑天皇权威的运作却造就了一笔丰硕的政治遗产,明治新政府正是藉此拥立起仍是冲幼少年的明治天皇,假借他的“祖传权威”发号施令。因此,可以将塑造明治大帝及其权威的起点置于孝明天皇时期。
除了具备上述的先验性的权威以外,明治天皇亦通过“六大巡幸”①等举措强化相关的神话式权威建构。实际上,此前的行幸江户就可视作这一系列“表演”的先声,特殊的是,1868年的行幸江户还隐藏着迁都的意图。正是这第一次的行幸,使得明治天皇完美地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有意识地将天皇作为全日本国的精神联结。正如多木浩二的研究指出,天皇东幸既将天皇的威权视觉化,也向全社会彰显了新政府的国家权力[7,p17-18]。其后的多次巡幸同样如此。比如在东北巡幸中,天皇不仅参拜神宫,赐予百姓,抚慰戊辰战争的创伤[8,p44-45];在北陆巡幸时还赐金给民众治疗眼疾[8,p51],在其他巡幸中甚至还通过“御触”为百姓治病。这一整套的“表演”使得天皇在重回人间的同时,也让天皇再度归于神位。通过这一系列的巡幸,早先曾撕裂德川幕府权威的地方民俗与信仰被整合进以明治天皇本人为顶点的国家神道秩序之中;或者说新式的天皇崇拜已然植根于民俗传统的宗教观念之中,二者融为了一体[5,p176-178]。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众在夹道膜拜天皇时还只是静默肃立。到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的1889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策划下,人群中第一次对天皇爆发出了“万岁”的呼喊,这一场面的出现再一次有力地确认了天皇的神之地位。此一时期,官方的塑造、天皇的表演首次与民间的回应形成了一种即时互动,演员与观众各就各位,“剧场国家”②呼之欲出。
明治天皇大帝形象的第一个侧面就是如此制作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意识形态的灌输,亦有接受主体的反馈。由此可见,昭和时代流行的、近代天皇制下的天皇崇拜只是幕末以来被人为塑造出的一种伪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9]但是,这种虚构的传统却并不缺乏力量,一方面它给明治新政府提供了推翻德川幕府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创造新政府权威的源泉,最关键的是,它还给明治国家刻上了封建性的烙印。
二、超脱政治的施政者
将现代政治话语中的国家——这一支配性名词剖开来看,它便具有等级(estate)、辉度(stateliness)与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的内容[10]。其中的辉度与治理,显然是指权威与权力两种支配类型。由此出发,丸山派和讲座派关于近代天皇制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得到了解决,即前者强调天皇在精神结构中的权威,后者突出天皇在制度设计里的权力[5,p16-17];权威与权力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二者并不矛盾。前文已经论述了关于明治大帝现人神的超权威形象的建构,接下来将厘清其权力形象的重塑过程。
这一重塑过程早在明治政变时就已开启。在1867年12月9日于京都宫中召开小御所会议时,萨、长二藩及激进派公卿坚持要求给予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处分,而以松平庆永和山内丰信为代表的合体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抗议。相持之下,山内称天子冲幼,尚无领导全国的能力,而岩仓具视却就此怒斥山内无礼,称睦仁乃不世出之英才。及至翌年3月,少年天皇更是率领百官对神祖盟誓,宣读五条誓约,俨然实际领袖。于是,数百年来与现实绝缘、遭武家轻视的天皇,首次在国家高层政治活动中化身为最高权力的代表,一个十五岁的懵懂少年,就此成了日本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玉”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但这一系列事件绝对是近代天皇制与明治大帝形象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王政复古后,新政府领导集团又多次发布“告谕”,着力在民间竖立起明治天皇的最高施政者之地位,如1869年2月3日,京都府发布《京都府人民告谕大意》;2月20日,行政官发布《奥羽人民告谕》。虽然告谕的发布地点不一,其宣传的意图却同,比如赞美日本作为神州,王政传统、礼仪风俗优于万国;又声称天皇乃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主人,百姓无一例外都是天皇的臣民[11]。如此一来,天皇作为万民之主的神统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对于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告谕中的深奥文字也有可能难以理解,这将限制民众对于明治大帝的个人想象;因此,新政府采取了更加视觉化、更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而这一方式的中心媒介就是御影——明治大帝的相片。供奉明治天皇的御影并进行礼拜是从1873年的各个官厅开始的;《军人敕谕》颁布以后,天皇御影走进了军营;而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颁布后,御影更是被下赐到全国各中小学,每逢节庆,师生们都要面对御影施“最敬礼”并奉读《教育敕语》[7,p201-202]。由此,天皇作为最高施政者的形象渗透进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润物无声地塑造着每一个日本臣民。
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则更是将天皇的当权者、主权者之虚像强化到了极致。关于宪法的制定,最初是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普鲁士派击败了以大偎重信为首的英吉利派,甚至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大偎几乎性命不保[12]。而他们两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君主之地位。伊藤等人认为,大偎的提案将把天皇作为“虚器”,国家的所有权力都将集中于政党,这样的一种操作显然威胁到了萨长藩阀的政治生命;他们也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版图中,作为虚像的天皇权威也将受到议会与政党的消解。但是伊藤等人也并未计划让明治天皇掌握实权,在制作普鲁士式宪法时,他们否决了法律专家罗埃斯勒的提议,即把明治天皇置于德皇之同等的实权地位。于是,“天皇实际上成了统而不治的皇帝,但又有宪法规定的无上权力”[13,p228]。很明显,藩阀政要的终极诉求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天皇政治权威。尽管如此,《大日本帝国宪法》仍旧制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君主的虚假形象:明治大帝在成为全日本国之大家长的同时,“其个人意志有可能被‘封印’在天皇权威这一抽象概念之中”[14],正如以侍补运动为表象的天皇亲政运动[3,p105-114],甫一出世便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可见,在明治大帝第二个侧面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而只有掌握政局的一方才有权规划天皇形象的制作。积极地看,它是高层政见分歧的最终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同时它也有效预防了天皇的个人滥权,将天皇置于统而不治的地位。然而,它给胜利者的政治行为注入合法性,既允许藩阀政府长期存在,也无法干涉山县有朋将统帅权独立。因此,明治天皇的超然形象正是明治时代元勋专权的生动诠释,充分显示了明治国家的专制性格。
三、文明开化的引导者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道路上曾树立起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的三大口号。在“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追赶过程中,从机械器物到政治制度,无一不是全速引进、全速吸收,以至于“东洋道德”竟好似明日黄花。但“政治、经济等诸多新设施,大部分不外乎是文明开化的表现”[15,p401],内在的人心如若不能更新,智德未能提升,社会的风气便只能是因循守旧,一国文明的实质自然也是无法达到。正如福泽谕吉所说:“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16,p45],而且,“要想知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16,p45]。此般见解可谓鞭辟入里。从历史来看,尽管日本在文明开化的道路上亦走过所谓鹿鸣馆时期的弯路,但客观来说,千万个笼子里的人结为了一体,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也得到了废除,文明开化之功何需赘述。而作为文明开化的引导者,明治大帝在这一过程中更是扮演着“主角”的角色。
就作为“社会风气”的表象——着装、打扮而言,明治大帝无疑是全体国民的楷模。尽管新政府早在1871年便颁布废刀令,同时鼓励剪短发、穿西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旧士族拒绝接受诸如此类的新时代风尚。萨摩藩的岛津久光更是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十四条质问书,以此表达自己对于政府开化政策的不满[15,p402]。但在1873年3月,明治天皇剪掉发髻,蓄西式发型;当年10月,天皇更是身着法式军服坐在洋式座椅上两手抚剑,以此种形象制作了一张御影,此御影既被悬挂于驻外公使馆,也被下赐到各县官厅以供官民礼拜。天皇亲自带头的示范作用自然是效果极佳,自此之后,官员百姓纷纷断发,发式的转变也被称作“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8]。当然,从明治天皇对于西餐以及诸多西式礼节的私下不满来看,明治天皇本人并不是一位“文明开化”人士。既然如此,这一系列行为的“表演”性质便不言自明了。正如飞鸟井雅道所写:“天皇的衣食住行完全是双重生活”[3,p18-19]——无论是工作还是外出,天皇衣着的标准配置始终是大元帅服;如果是在公众场合进餐,那么必然是西餐。而事实上,明治天皇喜食日本的料理,爱喝日本的滩酒,回到宫内总会变回传统的和式装束。因此,百姓眼中“文明开化”的天皇形象根本只是一种交织着表演与想象的奇特混合物。
与军队有关的场合亦是明治大帝进行表演的重要“前台”。明治大帝不仅身着军服检阅军队,也亲自出席甚至是指挥军队的演习,然而这些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相当欧化的,明治大帝显然是想借此模仿欧洲的君主,展示亲率军队的一种姿态。除此之外,明治大帝还通过参加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来强化与军队间的联系;从1874年开始,明治大帝还主持了授予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联队旗的仪式[17]。这一系列的表演与仪式,将军人对于天皇的效忠意识具体化、视觉化,演员与观众之间显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当然,这些表演中最富夸张色彩的当属天皇的“御驾亲征”。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临近爆发前的6月5日,日本就设立了以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负责人的、直属天皇的大本营;战争爆发后的8月5日,大本营转移至宫内,随后在9月再次迁往广岛,与此同时,明治大帝亦开赴广岛[18]。尽管战争的进行以及最后的胜利与天皇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但这一系列“表明天皇亲征的姿态”的“大型表演”,仍旧使得日本国民沉醉于明治大帝的勇武与英明。
一般来说,文明开化与军事性事务之间不仅毫无联系,甚至还相矛盾。但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二者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在彼时诸多日本人的意识思维里,殖民侵略本就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日本在“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文明开化的同时走向侵略扩张也就具有了高度的合理性。因此,明治大帝与军队间的紧密联系,也就使得明治大帝的文明形象愈加文明。此外,这种构建既然是明治政府高层的活动,那么这一近代化的形象在支撑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之同时,也有力地构建出明治日本文明国度的幻像。潜藏于其中的、天皇与军队的关系正是问题实质之所在,即近代化大帝像背后的明治国家的侵略性格。
四、余论
汇聚于明治天皇一身的不同形象,看似矛盾,实则有其内在之逻辑;明治国家内在的矛盾性格亦是这般。鼓吹天皇乃“万世一系的现人神”,一方面使得明治新政府在推翻德川幕府的过程中获得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假借天皇背后的神国思想创造出虚幻的国家优越性,并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国内统治。从这一点来说,明治天皇的“大帝”像中无疑充斥着前近代的不合理成分,此一点在明治国家性格中的反映就是强烈的封建性。至于“超脱政治的施政者”,起先是给藩阀政府创造出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宪法颁布之后则完全堕为宪政幌子下装饰日本帝国的一个工具,这无疑是明治国家专制性格的绝佳体现。而“文明开化的引导者”这一“大帝”像则更是明治政府高层的人为制作。突出表现天皇本人的西化态度,既可以为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寻求支撑,也可以塑造出西方认同的文明君主形象,间接标榜自身近代国家的属性。尽管天皇本人的生活喜好也证明了这一形象的虚构性,但天皇与军队之关系才是最大的隐患,这一联结成为合理化乃至是美化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最佳借口。这一形象充分展现出明治国家的侵略性格。
可以看出,明治天皇作为“大帝”的复杂形象与明治国家的内在性格之间存在着高度重合,美化明治天皇的个人形象,也就是为近代日本的封建性、侵略性与专制性作辩护。虽然日本是第一个非西方的近代国家,明治天皇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此一点基恩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天皇驾崩时来自西方媒体的评论③,但并不可就此忽视明治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重新解构、审视其大帝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分析近代日本两面性的一种路径。
[注释]
①见《明治天皇行幸年表》(明治天皇胜迹保存会编,大行堂,1933)。
②剧场国家的概念来源于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尼加拉:19 世纪的巴厘剧场国家》,在第12 页的一段中有关于这一概念的一段精彩论述,概括来说即“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彼得·伯克也用这一概念描述过17 世纪的教皇国,见彼得·伯克《制作路易十四》(麦田出版,1997)第17 页。
③见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1852-1912[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81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