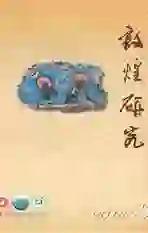采他山之石 筑学术津梁
2018-12-20冯小琴金琰
冯小琴 金琰
内容摘要:杨富学教授推出的《回鹘学译文集》《回鹘学译文集新编》收录了国外学者研究回鹘学的论文52篇,内容涵盖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语文学、文化史等多个学科领域,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回鹘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沟通国内外回鹘学界的联系起到了津梁作用。
关键词:回鹘学;回鹘文写本;敦煌吐鲁番文献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5-0137-04
Abstract: Prof. YANG Fuxues new work entitled“A Collection of Translated Essays in Uigurica”and its sequel collected a total of 52 articles concerning Uighur Studies by foreign scholars that cover many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philology, history, relig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se books are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Uighur Studies, but also for playing a role as a bridge link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ircles of the discipline.
Keywords: Uighur Studies; Uighur manuscripts; Dunhu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近年来,“回鹘学”一词的出现频率逐步见高,用于指代以回鹘(前伊斯兰时代)及其先民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问。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始于杨富学博士的《回鹘学》一文,是杨先生受南京大学名宿卞孝萱先生所邀,为其主编的《新国学三十讲》而撰写的。文中对回鹘学的对象、范围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回鹘学涵盖了前伊斯兰时代维吾尔历史文化(也可称“维吾尔学”)研究的各种领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考古、文献、文学、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哲学、科技、民俗、建筑等,但不包括伊斯兰化之后,仅限定于回鹘先民、漠北回鹘及西迁回鹘,而以唐宋元三代为主[1]。回鹘学研究的一个集中代表或典型特征,就是回鹘文的使用。需要说明的是,回鹘文流行的最大中心原本为西域,但由于各种原因,当地回鹘人自10世纪以后,相继皈依伊斯兰教,放弃回鹘文而采用阿拉伯文字。由于西域地区回鹘文失去了传承载体,至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回鹘文在西域便成为“死文字”,但在河西地区,回鹘文一直流行至18世纪。20世纪初,酒泉文殊沟发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抄寫于敦煌,长期被视为时代最晚的回鹘文文献[2]。近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又发现了时代比之更晚的回鹘文题记,在纪年清楚的题记中,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最晚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外尚有万历十五年、万历二十年、万历四十二年、顺治八年、顺治十五年和康熙十三年等[3]。文殊山一带发现的回鹘文字遗物表明,最晚到清康熙朝后期,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成为回鹘佛教与回鹘文化的最后家园[4]。这一段历史与相关回鹘文文献,既是“裕固学”的组成部分,同样也应该归为“回鹘学”的一部分。
在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有Уйгуроведение一词,指的是“维吾尔学”[5]。十月革命后,苏联确定以“苏联维吾尔学”作为固定名词使用。1979年,苏联维吾尔学者齐聚阿拉木图,就苏联维吾尔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研讨,会后出版《苏联维吾尔学面临的迫切问题》一书,对“维吾尔学”的概念、内涵、外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1}。本文所谓的“回鹘学”即是“维吾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概念,在欧美、日本学者中较少使用,他们对维吾尔的研究,有相当部分都集中于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古代回鹘文文献的解读、刊布与研究。本文所谓的回鹘,在西方学者的笔下,多称作“古维吾尔”或“古突厥”,尤以后者最为常见。
“回鹘学”之概念自2011年系统提出并得到论述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与重视,兹后,“回鹘学”术语开始多见。最近,杨富学教授更是推出了以“回鹘学”为名的译文集及其续编。
作为《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回鹘学译文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8月推出,收录国外学者研究回鹘历史文化的论文22篇,大多由杨教授独自译出,也有部分与他人合译。3年之后,《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收入译文30篇。二书集中收录了近年国内学者译出的各种论文52篇,就学科分类言,以文献学研究最多,有19篇,内容丰富,研究对象包括回鹘文《罗摩故事》残卷、回鹘文医学文献《医理精华》、吐鲁番出土回鹘语摩尼教写本、新疆与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敦煌出土的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巴米扬发现的一件回鹘文残卷,为学界所未知,首次刊布,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敦煌出土的西夏语佛典中夹杂回鹘文杂记,反映了回鹘与西夏的密切关系;吐鲁番葡萄沟出土的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文献,是元代基督教在吐鲁番一带活动的有力证据。匈牙利学者马尔丁奈兹对阿拉伯旅行家迦尔迪齐所著《纪闻花絮》中所论述突厥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弥补了巴托尔德刊布的缺失,堪称目前最值得参考的校订本。
其次为宗教学研究,计有12篇,内容涵盖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内容。再下依次为历史学研究(10篇)、语言学研究(5篇)和文化史研究(4篇)。这一分布情况也大体符合国际回鹘学研究的基本特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介绍。
总之,二书原文的原作者分别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瑞士、匈牙利、土耳其、韩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中国,基本涵盖了世界回鹘学研究的主要国家,其中以德国学者论文最多,有20篇,其次为日本,有11篇,再次为美国、俄罗斯、匈牙利、英国,分别为6篇、4篇、3篇和2篇,大体反映了当前国际回鹘学研究力量的分布现状。
就原作者个人而论,以德国学者茨默论文最为集中,一人独占14篇,体现了茨默先生在回鹘学领域地位的重要。茨默长期就职于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对接触与研究回鹘文原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系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回鹘文文献刊布者,先后曾发表过众多研究回鹘文文献的著作,其篇目之多,不胜枚举。特别要说的是先生所著《佛教与回鹘社会》,已由桂林博士和杨富学博士合译为汉文,于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刊行,备受国内回鹘学界关注。茨默的研究,对中国乃至国际回鹘学都有重要影响,而此次译文集收录的文章也多为先生之新作,势必会增进国内学术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进一步了解。此外,德国学者葛玛丽、克林凯特,俄罗斯学者克里亚施托尔内、吐谷舍娃,日本学者护雅夫、梅村坦、森安孝夫,英国学者克劳森,美国学者孟赫奋、克拉克,瑞士学者孟格斯等,都是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名宿。择其要者汉译出版,意义重大,乃当下国内研究“回鹘学”之亟需。
耿世民先生曾言:“没有哪一门语文学能像突厥语文学那样多地受益于新疆出土的文献。”[6]杨富学先生进一步言道:“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鹘文化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7]这都道出了出土文献对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20世纪以前,世人对回鹘历史文化的了解甚少,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较多而且较为系统外,学界对回鹘文化的认识常常局限于穆斯林文献中一鳞半爪的记载{1}和传世的几件回鹘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争赴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险的热潮,大批回鹘文写本与刻本残卷相继出土,为回鹘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
由于历史的原因,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献主要收藏于外国,尤其以德国的收藏最为丰富;百余年来,德国回鹘学界得益于这批文献,孜孜矻矻,研究不辍,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专家,最早的如缪勒(F.W.K.Müller)、勒柯克(A.von Le Coq),继之有邦格(W.Bang)、葛玛丽(A.von Gabain),再到第三代传人茨默(P.Zieme)、罗伯恩(K.R?觟hrborn)、劳特(P.J.Laut)等,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国外维吾尔学研究历来都以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为重点,尤其是对前伊斯兰时代回鹘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的发现、研究为先导的。
比起欧美日本,中国回鹘学起步较晚,发轫于本世纪50年代,而斯时国际回鹘学即已相当成熟了。《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于学习他人之长,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对中国学术而言,通过翻译,掌握国外收藏、刊布的回鹘文原始资料,借鉴国外的先进学术成就,提高国人的研究水平,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回鹘学尤其如此。诚如牛汝极先生所言:“维吾尔族在中国,维吾尔学在世界。要加强和促进我国的维吾尔学研究,必须时刻关注国外维吾尔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我们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取决于我们对中外研究情况的掌握和研究成果吸收的程度。”[8]
国人对国外学术进展情况的了解与把握,翻译可以说是最佳途径,但并非易事。众所周知,翻译是最高程度的阅读,有相当的难度,回鹘学著作的翻译就更难,对专业的要求极高;其中,最难的莫过于语言的复杂性。翻译过程中不仅随时会遇到诸如古突厥-回鹘语、梵语、粟特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吐火罗语、古叙利亚语、于阗塞语等古典语言,而且还经常面临用英、法、德、俄、日、土耳其、匈牙利、朝鲜等多种语言撰写的研究著作,最为繁杂的是,西方学者研究著作中经常会直接大段引用来自不同文字的著作,势必给翻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国外学界研究回鹘的著作被译为汉语者并不多见,不仅不利于国人对欧美、日本学术信息的了解与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回鹘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杨富学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在回鹘文方面造诣颇深,拥有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仅在回鹘学领域就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甘州回鹘史》《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等多种著作,在西域宗教、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西夏研究等多个领域亦有独到的研究,始终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优势对翻译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回鹘学译文集》和《回鹘学译文集新编》精选的52篇论文,尽管选题不同,但每篇都有其独到之处,不仅资料扎实,内容丰富,而且学术观点新颖,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准,他们的汉译出版,有利于国内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与了解,促进国内回鹘学的发展,同时有利于沟通国内外回鹘学界的联系,可谓起到学术津梁之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富学.回鹘学[M]//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75-300.
[2]W.Radloff,S.E.Malov.Suvarnaprabhāsa(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Vol.I-III[C].St.Petersburg,1913-1917.
[3]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C]//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4-106.
[4]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J].河西学院学报,2012(6):1-7.
[5]魏良弢.对于深入开展维吾尔学研究的几点建议[C]//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9.
[6]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65.
[7]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
[8]牛汝极.维吾尔学系统工程构想及国外维吾尔学研究的最新情况[C]//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