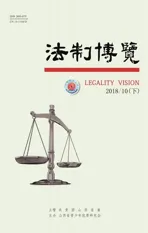信息透明化视角下的高校法治化建设
2018-10-30周学文
王 普 周学文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论阐释和战略部署。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①该项要求中提到的“一体建设”表明法治建设是国家的系统性、全局性工程,法治的精神、理念应辐射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换言之,所有行使权力或享有权利的主体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之内明晰自己的定位,规范自身的行为,最终使整个系统的法治状态得以完满。
高校作为“法治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权力亦需在法治建设的格局中运行。作为一种公共组织,高校的法律地位具有特殊性。其一,当前有法律、行政法规授予了高校以行政权能及相应权限,其可以“行政主体”的姿态处理各类公共事务。②;其二,高校自身依然保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其可对上位法授权高校自主决定的事项或未作规定的事项自行做出安排,以达到内部管理的目的。③由此二点可推知,所谓高校的法治化,应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行进。对于前者,高校必须遵守“依法行政”原则,自不必多言;而对于后者,高校虽无直接管理依据,其权力行使亦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因为,虽然高校的法治化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但其实存在着相同或相类似的机制、手段服务这一法治化进程。因为在此二种面向下,法治的理念依然是共用的,故而制度安排背后的价值取向、公平观念也大多是相通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共用法治理念”的大前提。具体而言,高校作为行政主体时,其须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或主动或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及时、准确地公开相关信息,以保障公众或相对人的知情权。而当高校作为内部的自主管理者时,其是否也应当实现其“信息透明化”,以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和其他相关权益?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即在于其内部的管理过程同样要遵循基本的法治理念,具体即基本的法律原则、精神,以支撑其管理的合法性、正当性。本文即结合当前“信息透明化”的理念,阐述和探究“信息透明化”对高校法治化建设的功能和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这一方式去实现高校的法治化。
二、“信息透明化”机制概述
(一)机制法理
信息保有者将信息向不特定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的审视,此为“信息透明”,而当这种公开成为一种常态时,便成为“信息透明化”。为什么要使信息“透明化”?“透明化”能带来何种效果?这些问题涉及到信息透明化机制本身的原理,搞清楚这些问题,方能明晰信息透明化的必要性以及进一步解答信息应该怎样“透明化”。
信息透明化即实现信息公开,而信息公开的首要动因是实现公众的知情权。从宪法权利角度透视,“之所以公民有知道与国家权力行使有关信息的基本权利,是因为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公共财产’,属全体公民共同所有,不是国家机关的‘私货’,且借助于这些信息,公民可以有效地监督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④可见,在宏观层面,信息公开与权力的行使密不可分,一方面,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知悉权力源于何处,它如何运行,它的作用效果怎样等等与权力本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知悉了前述这些与权力有关的信息后,公众才能对照法律去评判该种权力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监督权力行使的目的。对于高校而言,其本身拥有着一定的自治权力,也就当然地会涉及到权力行使的问题,故此机理也同样适用于高校的信息公开。因此,高校信息公开的首要原因即在于保证学生、教职工清楚高校自治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而使权力受到监督。
(二)机制功能
信息公开保障知情权的机制初衷可进一步衍生出其他功能。最重要的即为前述的权力监督功能,对于该项功能,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此外,信息公开另一重要衍生功能即在于为学生、教职工参与高校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契机。传统上,高校一般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者,其与被管理者师生、职工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明显不平等的隶属型关系,该种不平等关系从公法理论上可被称为“特别权力关系”,亦即高校可按自己的意志管理内部事务,无需听从被管理者的意见,被管理者处于一种绝对服从的地位。当前,随着交流协商、合作共赢理念在法治领域的渗透,地位上处于不平等的一方也拥有了一定的与管理者对话、协商的权利,从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该种对话权利行使的重要前提即是管理者对信息全面、无误的公开,否则,被管理者无从获悉管理者的决策依据、决策意图,也就无法平等地、实质性地与管理者展开对话。因此,高校信息公开机制是高校师生、职工了解高校管理、决策的重要窗口,此窗口的开放才能够进一步打开参与高校公共事务管理的大门。而该机制对于高校这一管理者来说,也起到了及时获得反馈以修正决策、提高管理效率的功能。
此外,信息透明化因其保障知情权实现的功能,可以在高校法治化建设中起到一定的“预防性”作用,即有助于防止或者提前消解高校与师生之间的误会、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当高校内发生某些重大事件时,校内舆论引发的种种议论、猜测甚至质疑。如果高校不能及时回应这些声音,澄清事实,舆论的发酵或将愈发不受控制,最终将导致高校公信力的下降。因此,高校在日常行政管理中,对于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应事先发布相关信息,以保障师生的知情权,使师生了解真实状况,扶正舆论导向,防止因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而产生误会、矛盾。
三、“信息透明化”在高校法治化建设过程中的运作方式
高校信息透明化机制本身即是高校法治化建设的一部分,它与其他法治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可以构成一种手段与目的的联系,而在不同环节,该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存在差异的,但可以明确的是,高校法治化建设应当浸染在信息透明化机制的色彩之中。总体上,与信息透明化关联最为紧密的当属高校决策行为以及个案处理行为。
(一)决策过程的信息透明化
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拥有对高校制度、政策等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决策权的行使主要表现在制定各类校级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有高校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设置了必要的听取、交换公众意见的程序,如听证程序,尤其当该文件关涉到师生的重大权益时。⑤这实际上也是吸收上层法律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原则的表现。
无可否认,诸如听证等为校方与师生间搭建对话平台的程序使师生间接地成为了高校规范的制定者,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然而,使得该种程序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前提条件之一应是以供决策的信息应当全面公开,否则,信息不对称状态的下的“公众参与”很可能将沦为形式。“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应当是以所涉决策的相关信息充分、透明为基础,信息大量缺失不仅会伤害参与热情,更使得参与变得盲目、徒然,所提意见没有意义,也无法展现参与能力,错误的、有偏向的信息会误导参与。”⑥
信息透明化机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知情权,而实现真正“公众参与”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师生的知情权,使师生能够全面、快捷地获取高校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包括决策前已经调查掌握的信息,决策期间产生的信息以及决策产生后形成的规范性文件本身和其他相关信息。当然,该信息透明化的程度应视事项的重要性程度而有所区别,对于关涉师生重大权益的事项的决策信息透明化程度应高于一般事项。
(二)个案处理的信息透明化
高校在处理公共事务、实施决策的问题上须向广大师生公开相关信息,相对地,在个案处理的情境中,就现行的法律制度而言,只在高校对学生做出不利处理决定时,设定了高校对被处理学生的“告知义务”。⑦此种告知义务与其说是一种信息披露义务,毋宁说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必然要求。那么,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是,高校在此种情境中,是否亦有向其他公众披露信息的义务?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高校对学生所作出的在授权范围内的处理决定,可视为授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这一点上,近年来的许多司法实践也给予了回应。此类可诉行为包括:学生招录行为、学籍管理和纪律处分行为、授予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⑧如果将此类行为视作高校的行政行为,则其必将与行政法上的行政公开原则产生密切联系。“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到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通过行政公开行政相对人可以有效地参与行政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民众因此可以通过行政公开,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⑨可见,行政公开原则不但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向行政相对人公开有关信息(集中体现在理由说明制度上),同时也要求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通过公众的监督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虽然在我国现行法上,行政主体并无向社会公开有关行政行为信息的要求,但对于高校,基于其相对封闭的内部行政管理空间,其权力(包括作为行政主体时的行政权以及内部自治时的自主处理权)的行使过程不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调整,故权力不当使用、滥用的可能性较高。此外,基于高校处理行为的示范、警示作用,对于高校的其他公众来说,他们都是潜在的可能被处理者,就应当享有知情权去知悉校方在某事项上的处理方式、过程是否公正、妥当,处理依据、理由是否正确、充分。因此,在高校在对学生作出上述各种不利处理决定时,应受到完整的行政公开原则的规制,除了向被处理学生本人外,至少也要向校内的其他公众公开其在个案中职权行使的相关信息,促使高校的权力在公众的监督下运行,以遏制其不当使用、滥用权力的倾向。但应当注意的是,此种信息公开的程度并非没有上限,只要在现有信息足以澄清事实的情况下,便可认定高校已尽到了必要的公开义务。
实践中,高校在对学生作出不利处理决定之后,通常都会在校内以通报等形式公布处理结果,但这仅属于结果的公开。虽然通报中也会或多或少地陈述处理经过,但并不能完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更无法起到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个案处理中的信息透明化应立足于处理理由的透明化,即除了向被处理者说明理由外,也要面向公众公开处理理由。从行政法理论上的理由公开制度的原理上看,由于理由公开的对象是公众,所以它还会放大理由说明制度的核心功能——控制行政裁量权。在行政裁量的理由不仅要告知相对人,还要公之于众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无疑会更加谨慎,更加注重科学合理决策。⑩
实际上,听证制度就是实现个案处理理由公开的最好平台,建立完善的高校听证制度是实现个案处理信息透明化的重要路径。然而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听证程序没有任何规定,这意味着学生即使面临开除学籍的处分,也并无要求听证的法定权利。当前我国有高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校内听证制度,且实施成效可观。国外也有部分公立高校赋予了受到不利处理学生的听证权,并专门设立了听证机构,规定了详细可操作的听证程序,○11其有益之处可供借鉴、参考。
四、结语
高校的法治化集中体现于高校权力的“依法”行使,故信息透明化机制在高校法治化建设中的运作应着眼于对权力的监督上。具体而言,信息透明化机制实现公众的知情权,从而衍生出对权力的监督功能。而高校的权力从行使的目的、效果上可划分为决策权和个案处理权,信息透明化机制的监督功能在此二类高校权力的行使上均有用武之地。对于决策行为,信息透明化机制应关注决策的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而对于个案处理,信息透明化机制应关注处理的理由公开。当前,我国高校可围绕该两类权力的行使,结合信息透明化机制的作用,加快高校法治化的建设进程。
[ 注 释 ]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②如高校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属于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参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3、6、10条.
③如学生留级、跳级的条件,可由高校自主规定.参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5条.
④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03.
⑤朱振岳,王汝菲.依法治校的创新实践——<浙江工商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听证会侧记.http: // www. jyb. cn/ high/ gdjyxw/ 201305/ t20130502_536275.html,2018-6-26.
⑥骆梅英,赵高旭.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生成中的角色重考.行政法学研究,2016(1).
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规定:“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决定之前,学校应当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⑧何海波.行政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0.
⑨章剑生.论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公开原则[J].浙江大学学报,2000(6).
⑩蒋清华.从理由说明到理由公开:行政治理透明之道.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6卷)[M].法律出版社,2014:26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