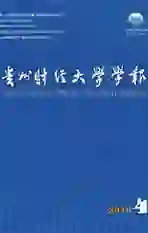外部冲击影响下的农户家庭决策与制度调整
2018-10-10贺娜
贺娜
摘要:农户家庭是现在及未来很长时段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以家庭为单位作业,易受自然资源、技术条件、劳动供给、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秩序乃至地理天气等外部条件影响,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近期外部要素变化对农业经济冲击可谓喜忧参半。贴合经济生活原型,纳入风险要素并构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可为政府反馈农户经营信息、评估家庭微观经济行为和构建有效制度提供实证依据。目前,农户家庭经营主要面临系列制度障碍,因而应加快推进涉农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激励和保障功能,以降低农户风险和成本,提高农业经营业绩。
关键词:外部冲击;农户家庭;不确定性;经营组织;技术变迁;决策模型;制度调整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4-0080-10;中图分类号:F3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后,“个体农户”取代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成为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充分调动,农业经营活力充分释放。此后40年,受政府制度优化、政策扶持和农民群体自我创新机制驱动,组织形式处于不断演化和升级之中,农业经营在个体小农基础上,逐步衍生出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或混合组织等多种新型组织形式。[1]但农户家庭依然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微观单元。至2012年,我国农户总数26802.32万户。① ①见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 2016年末,我国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组织总数约280万个,职业农民总数超过1270万人。家庭农场87.7万家,经农业部认定的有41.4万家。依法登记合作社达179.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4.4%。其中,国家示范社达8000家、县级以上各级示范社达13.5万家,联合社7200多家。农业产业化组织38.6万个,其中龙头企业达到12.9万家。② ②见农民日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达280万个”,2017.3.8 前后加以对比,2016年各种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约相当于2012年农户规模的1.04%。现行涉农体制、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约束下,庞大农村劳动力群体就业压力及农村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必然使“个体农户”为主、“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种新型组织协同发展格局,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段内农业经营组织的主要结构形态。
农户家庭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主要的微观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作为基本单元,它是其他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的基础。当前农村许多农户已经和各种新型经营组织充分融合,经营活动亦渗透到组织系统内部。个体农户或者和这些新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农户家庭扩大再生产超过一定边界后,即成为家庭农场。农户家庭、服务组织和涉农公司等组织形式相互联合或再联合,以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形式缔结合作组织,即可确立农业合作社或联合社。农户家庭来料并提供劳动力,企业进行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生产,可推动实现农业产业化。现阶段个体农户和新型农业组织间彼此融合和交互影响,农户家庭经济兴旺和活跃,有益于经营组织培育和成长,有益于乡村整体振兴和发展。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本年要實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把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且上升到中央重要文件高度,是政府高层对理论和实践领域涉及农业和农村发展前景重大命题的紧密关注和热切回应。笔者以为,要促进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仍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现实。毕竟,2亿多户的个体农民家庭经营才是目前农业生产的普遍现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决策会形塑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调整亦会影响农户经营选择和农业绩效。分析受不确定性影响的农户家庭决策和行为,对政府相关信息反馈及后续制度构建和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该领域相关命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加以归纳和梳理,可分为:一是关于农户决策和行为的理论研究。国外最早关于农户行为系统性研究的是俄国学者恰亚诺夫。他的基本理论主要有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论以及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恰亚诺夫(1925)通过对1930年集体化前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认为小农生产的目的并非是追求利润最大,小农决策是基于生存需要的,最优化选择是在消费满足和劳动辛苦程度间实现均衡。认为小农经济既非集体化、也非市场化,而是合作化。[2]斯科特(1976)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从不确定性和风险角度进行分析,强调小农生产的首要目标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而不是平均收益最大化。他们的研究都突出农户的生存需要,故被称之为生存小农理论。舒尔茨(1965)把小农看作是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的理性经济人,有进取精神,追求利润最大化。指出要在保持家庭农场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改造传统农业,使用先进技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3]波普金(1979)则指出,农户是理性的个人和家庭福利最大化者,能够最大化期望选择。理性经济人分析是这两位学者共同特点,因而把其归入理性小农理论。
华人或国内学者也有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美籍华人黄宗智(1985)通过20世纪30—70年代的中国农户调查研究,构建折中的“商品小农”理论。他认为,中国农户既不是完全的生计小农,也不是追求利润的理性小农。提出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认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温铁军和杨帅(2016)指出传统农业经济领域的两大理论派别——“理性小农”和 “生存小农”——对中国当代实践的解释困境,认为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及随之而来的产业资本扩张,是“三农”和“三治”问题的本源。
二是关于农户决策模型研究方面。相对于理论研究的前行速度,实证模型化的分析推进要更快一些。Becker(1965)关于家庭内劳动配置的研究引入了家庭效用函数,分析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效用不仅可以从市场商品中获得,而且可以从生产的最终消费物品中获得。[4]Dimin(1971)将期望效用引入农业生产领域。Barnum & Squire(1979)建立的模型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5]McElroy & Homey(1981)将博弈论引入集体模型,并提出独立地位模型,以说明农户家庭成员的联合生产行为。[6]Iqbal(1986)引入储蓄、投资和借贷变量,将时序扩大到两个生产周期,把农户决策和政府宏观政策关联起来,实现了分析的动态化。Singh,Squire & Strauss (1986)在农户模型中包含了利润效应,分析农户经济行为。[7]Quiggin(1991)对EU理论的实用性进行了有益地探索。[8]Bourguignon,Chiappori & Kirn(1992,1997)认为非协作博弈模型的假设是:家庭内部成员有不同偏好,且根据自身条件进行选择。Knight(1997)指出应该使用不确定性表述决策過程的条件,用风险表述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Abdulai,Huffman & Kimhi(1999,2006)对基于单一效用函数的单一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研究不同外部制度环境下农户劳动力就业问题。[9]Silva, Alexandra & Berbel (2015)基于多标准模型模拟奶农的行为。结果表明,决策过程似乎有三个相冲突的目标: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劳动力的季节性和风险最小化。此外,农场目标取决于放牧系统的强度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农民的行为并不总是由利润来解释。[10]Donoghue (2017)发展了一个行为选择模型。受限制模型表明,爱尔兰农民的行为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通过农场收入和AES付款消费。不受限制模型表明,农民参与效用最大化行为的AES参与决策是复杂的,随区域和时间发生变化。[11]
国内学者近期构建模型对农户行为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方松海(2008)提出“劳动负效应”和“要素纯收益”工具,重新构建农户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拓宽了农户家庭理论体系。梁义成、李树茁等(2011)构建了非农参与下的农户决策模型,侧重分析决策对农业效率的影响机制。彭军、乔慧等(2015)将劳动和健康内化于农户模型,分析农业生产中的“一家两制”现象。[12]王岱、万相昱等(2016)再建基于Agent的农户模型,从现代经济学的适应性假设出发,分析异质化的农户行为,构筑仿真农业经济系统,为粮食安全提供系统化和动态化的建模机制。张治霆、朱烈夫等(2017)运用最优控制论和Bellman方程分析农户在动态生产过程中的选择行为,认为农户的专业化生产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路径,而失业风险是主要限制因素。[13]
如上文所述,农户家庭决策和行为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生存小农”“理性小农”和“商品小农”视阈范围。而理论模型由于多视角、多方法研究,结构比较复杂。有效用同质的单一模型,亦有效用异质的集体模型;有静态模型,亦有动态模型;有同一评价标准的模型,亦有多标准模型。[14]但相关模型化构建中,对农户事前行为研究,纳入不确定性条件加以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结合国内农业经营状况的分析就更为有限。笔者计划引入风险要素,对Barnum-Squire模型稍作拓展,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农户决策和行为,强调在最优数量规划决策效应下,政府信息反馈及制度调整方向。
三、农户家庭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
农业生产经营通常会受自然资源、技术条件、劳动供给、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秩序乃至地理天气等外部条件影响。这些外部要素并非总是处于稳态,当受制环境、因素和机理变化后,它们的现存状态或迟或早会发生演化。有的变动会释放较大冲击波,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经营活动。外部要素冲击效应可为正,亦可为负;影响方向和效力大小取决于要素本身特质,也会和经营主体应激反馈策略及程序相关联。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外部条件变化喜忧参半。此处仅考察可评估的能够对全局形成重要影响的代表性要素变动情况。先看不利变化:一是近期国际市场上,出口农副产品面临的经济形势和贸易秩序不容乐观。美国次债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风波后,几大发达经济体尚处于调整中,经济增长趋缓。发展中国家经济亦面临诸多阻滞,继续发展大都困难重重。相对不景气的经济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和制裁频现。我国对外输出的传统农副产品,在价格、品种和质量等方面本就不具备显著比较优势,受此贸易秩序影响,大宗农贸品交易额明显放量收缩。2015年2月至2017年1月间,农产品进出口持续性贸易逆差,且多数月份逆差额超出30亿美元,期间最高水平月份2015年7月突破60亿美元。和2016年1月同期相比,2017年1月重点大宗商品前三大市场出口的肠衣、大蒜、豆粑、蜂蜜、柑橘、苹果汁、食糖、烟草和中药材等多类农副产品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出现大幅下降。① ①见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数据。 二是国内农地资源方面,数量基本逐年减少,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数据,2012年全国农业用地64646.56万公顷,至2015年降为64545.68万公顷,四年间降幅达0.16%。2010—2016年间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耕地面积均在降低,由13526.83万公顷降为13495.66万公顷。期间政府部门确在加大农用耕地保护力度,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耕地改造和维护。2015年中央累计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等资金212.8亿元,全年开展并验收土地整治项目9535个,土地整治总规模为161.23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15.68万公顷。2016年总投资则增为618.75亿元。开展并验收土地整治项目13406个,建设总规模为333.73万公顷,新增耕地17.58万公顷。但由于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基本都超出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方式增加的面积,所以农地面积整体仍呈现收缩态势。在我国农地资源本就相对不足、可耕地数目有限及家庭人均拥有量严重低下的背景下,土地流失将会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及农业经营压力。
再看有利变化:一是农业装备方面,机械化程度和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农用拖拉机、排灌机、联合收割机、机动脱粒机拥有量逐年递增。2010年农用拖拉机21779644台,2016年增长为23169695台,增幅6.4%。2010—2015年间,排灌电动机、联合收割机和机动脱粒机分别由11761542台、992062台和10167963台增长为13029600台、1739000台和10618000台,增幅分别为10.8%、75.3%和4.4%。水旱灾害装备和防治技术也得到强化,2010年受灾面积30784千公顷,2016年降为18404千公顷,降幅40.2%。单从理论上看,农业生产和治理装备层次的提升,增强了防护能力,降低了农业风险,节约了劳动时间,强化了生产效率。但实践环节更复杂,要审慎分析一些技术变迁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及相伴的适应性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下,多数农户仍是家庭内相互帮扶的小户作业。户用耕地面积小,且田间分界明确。小规模耕种机械取代劳动在成本上相对不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小农相对理性的选择或是固守传统,不乐于接受机械化的推广,或是淡化土地经营重要性,以外出务工更高额的劳动回报补充成本支付,扭转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对比,这一情况下土地精耕细作便难以延续。二是劳动力资源方面,农业劳動人口规模正在收缩,但与庞大基数相比变化不大。以受教育程度衡量劳动力质量,群体素质有所提高。1996年农业从业人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0.73%,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占比43.11%,小学教育程度占比42.15%,未上过学人口占比14.01%。2010年研究生学历占比0.019%,大学学历(包括本科和专科)占比2.04%,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占比52.63%,小学教育程度占比38.06%,未上过学人口占比7.25%。相对比可见,农业文盲劳动力比例下降明显,占比约为1996年的一半;中学以上教育程度劳动力比例逐次上升,尤其是大学学历以上劳动力增幅不小,约为1996年占比的2.7倍。① ①由于缺乏同口径数据,1996年受教育情况使用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2010年受教育情况使用人口普查数据,两者口径稍有不同,可做大体对比,不影响分析结论。 家庭经营视角下,农户是农业经营主体,是家庭经济的内部要素。若从整体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人口规模和层次结构则具有外生性。很难判断当前农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到转化为应用知识的时间表,但知识储备增加和认知力提升的乘数驱动效应是明确的。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成长周期和中间转化机制的配套状况,教育对家户经营产生影响乃至普遍效应显现,应是不断强化的渐进递推过程。三是科技前沿应用方面,人工智能、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同农业经营的充分融合,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智能农业集成依托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音视频技术、3S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专家智慧与知识,在部分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实现可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灾害预警等职能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形式逐步兴起,淘宝村保持高速增长势头,2015年全国淘宝村规模同比增长高达268%② ②见《2016年度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速高涨,2016年第二季度农村网络零售环比增速比城市高4%。③ ③见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5—2016)》 科技新成果在农业经营中的应用和推广,势必会冲击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和业态,基于生计需求的早期家庭意义上的稳定和保障功能正在退化。农户谋利诉求的凸显和增强,将会助推未来经营组织形式的不断演化和升级。
四、农户家庭决策及制度构建的微观基础
(一)农户家庭决策模型
Barnum-Squire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农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可分;农户要出售部分农业产品交换非农业消费品;农户在产品和闲暇组合间寻求效用最大化;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户可以雇入,也可以雇出劳动力;耕地面积不变;农户家庭不考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行为。
不确定性条件下,当前国内农户家庭行为选择必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尽可能规避各种风险。故本文以折中的“商品小农”理论为依托。纳入农业经营中的风险要素,重塑Barnum-Squire模型中微观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假定农户经营目标是不确定性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且效用最大化。在模型原假设基础上,做补充追加:假定农户面对的是完全竞争市场,无价格谈判力。农户生产两类产品a和b,一类是价格Pa i 相对稳定的基础品,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一类是价格Pb i 波动幅度较大的农副品,如绿豆、大蒜和鸡蛋等。考察T1和T2两期,做比较静态分析。T1期两种商品价格分别为Pa 1 和Pb 1 。T2期第一类商品价格基本不变,即认为Pa2 = Pa 1 ;第二类商品价格Pb 2 变化方向和幅度具有不确定性,Pb 2 = Pb 1 (1 + Δ ),Δp为随机变量。分两阶段构建农户模型和求解相关函数如下:
1.风险规避且效用最大化的条件
(二)农户家庭决策分析为制度调整提供实证依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见,农户产品供给,净利润及消费品需求,均是自产品预期价格、要素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函数。自变量的变动,会通过特定传递机制冲击农户决策,引致农户选择和行为的改变。诸变量变化的经济效应中,价格不稳定产品的影响相对更主要一些。农户家庭第二期产品生产、利润实现及对其他消费品的购入情况,很大程度要受第一期末产品组合预期价格的影响。当预期价格上涨时,容易满足E′(Pb 1 ) > 0,农户会相对增加自有产品生产,获取更多利润,进而购入更多消费品。但农户不会无限增加劳动投入,会在劳动和闲暇间做出权衡,以保证预期效用最大化。反之,按照预期边际效用为0的风险规避原则,农户则会进行逆向调整。
能够看到,农户家庭生产和消费决策,实质是相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规划求解问题。小农经营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理性选择不仅要考虑常规的效应最大化目标,也会审视农业经营风险和冲击效应。农户会根据风险状况、约束条件和关键变量的影响,更新决策和调整行为。实证层面解析农户家庭微观行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其决策模型的模拟研究,为政府信息反馈和制度调整提供依据。市场化环境下,农户感知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做出适应性选择。由于农产品市场不完善、小农判断的主观性、滞后性及家庭功能有限性,单个家庭即使非常审慎决策和应对,亦不可能化解所有风险。政府部门要积极寻求防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农业利润空间的应对思路和工具。考虑到当前农户家庭弱质性和农业发展现状,制度调整和优化应首当其冲。
五、制度作用于农户家庭经营的形式和路径对比
(一)制度作用于农户家庭经营的两种形式
制度总处于或快或慢的变动中,以保障利益主体潜在获利机会的实现。[15]根据调整主体和程度差异,可将制度变动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指令、法规和政策强制确立和实施。由于政府部门高度的垄断性、覆盖性和权威性,这类形式变迁速度快,由此确立的新制度稳定性高,推行效力强。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个体或团体自愿倡导和自发创立的制度安排。该类制度变迁往往具有较高的弹性和灵活性,初始发生范围一般不大,推动速度也相对缓慢。市场实践后,如反馈良好制度绩效,则会在社会范围自然传播和渐进推广;如绩效不高,则会自我改良升级或被逐步淘汰消亡。
强制性变迁对象一般是与农业经营相关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法律法规、政策条文等正式约束。首先分析体制层面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从小范围放开市场,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农民家庭构筑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体制环境。其次分析发展战略制定情况。党的十九大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再次分析法律层面的制度变动。有层级最高的《宪法》,有《国家安全法》《城乡规划法》《农业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普通法,还有一些重要的特别法,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和《种子法》等。这些法律有些新近首次修订,有些则经历多次重订或修订。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重订和修订各四次,其中1993年修宪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更替“人民公社”。从“人民公社”到“家庭”组织形式的回归既是制度对农业经营组织的形塑,也是政府为主导的农业组织形式变迁对体制环境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近期首次大修则体现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体现了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及对政府制度调整以维护相关权益的客观诉求。“2017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將于2018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取消同类限制,扩大法律调整的范围。为适应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行发展,在专业化基础上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农民对各类合作社提供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① ①见第一财经内参(微信版).“保障乡村振兴,全国人大做了这些立法工作”,2018.2.14 最后分析惠农政策及配套条文等制度变化。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配合制定和实施各项惠农政策和条文。加以梳理,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直接面向农业生产经营补贴政策,如对大型农机具购置、良种、粮食作物收购、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财政补贴。二是涉农生产经营的减费降税政策。三是用于农业经营相关联的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四是农村教育、农技培训和推广的财政支持政策。五是促进融资的信贷支持政策。
诱致性变迁多适用于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传统习惯和常规惯例等非正式约束。当然,也有一些非正式规则逐步演化和升级,得到政府部门认可和批准,最终确立为正式制度。和农业经营关联的非正式约束通常带有地域性特征,以在特定区域和范围适用的行规、传统及惯例为主。以笔者考察的豫西地区灵宝市果木和干果类经营为例,灵宝市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地表由山地、土原、河川和阶地组成,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降雨适中,盛产多种水果和干货,尤以苹果、大枣和核桃著称。改革开放初期,果木种植主要是小型农户作业。近年来,农业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在农业经营稳步发展中,家庭农户出现了专业化和兼业化趋势。一方面,分工细化和专业化,推动农业向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一些最初仅是满足基本生计的个体农户逐步成长为现代家庭农场;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多元化提供了多种经营选择,农业兼业化趋势不断强化,多类别和多领域生产经营充分融合。随着农业经营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客观需求新的组织形式,以分化市场风险,促进信息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加快产品销售和资本周转。农业经营需求推动组织创新,在“家庭农场”之外,出现了“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经济”及“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多种新型经营组织形式。在多种新型组织形式出现的同时,也衍生出用于规范经营行为的非正式约束体系。该市焦村镇纪家庄村红缇种植经营,以“中小型家庭农场+合作经济”型组织为主,地缘、熟人关系和亲缘为依托的传统和惯例发挥重要作用。果苗集中于陕西和山东农科院采购;劳工雇佣是基于信任基础的村民,闲时帮扶除草、施肥、灌溉和采摘,既可降低偷盗和毁损率,又可稍作延期付款,缓解资金周转;销售方面由中间人或合作社牵线,引入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地采购商,叫作“引客”,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批量采购,货款不需即时结算,可以“客商”银行支票账户和“中间商”信用担保,约定后期支付。这种在约定俗成的规定和惯例下自觉有序组织生产和交易的行为,在该市其他村镇也普遍存在。显然,诱致性变迁下形成的非正式规则,正在成为涉农经营领域正式制度安排的有益补充。
(二)制度作用于农户家庭经营的路径
农户家庭是和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者和承受者,制度变迁会形塑农业经营外部组织形态和内部运作机制,引致组织创新以适应制度变迁需求。[15][16]如图1所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下,农户家庭是制度变迁的承受者。外部组织形式逐步升级,内部运作策略和技巧亦做出调整和优化,被动呼应外部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制度自上而下推行,组织由外而内做出反馈。改革开放前,农村经营组织从农民家庭→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逐次演化和升级,就是组织形式对当时特定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的匹配式变动。诱致性制度变迁下,农户家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新制度创立者,又是新组织缔结者。新规则在已有制度环境下设立,不能违背基本制度。组织通常自下而上游说或呼吁政府,以寻求对新规则更多的维护和支持。组织内部自觉设计运营策略,主动匹配新确立的外部规则。
六、现时制度瓶颈的存在束缚农户家庭经营
(一)经济体制内在机制不成熟,制约农业生产经营
我国农产品市场尚处于成长中,体系不完整,市场层次低、结构单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主体地位仍不突出和不明确,农业经营中各种行政管制和干预现象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频发、区域条块分割明显,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受阻。涉农土地、技术和融资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尚处于幼稚阶段。产品市场以传统作物和种属市场为主,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市场化水平低,交易量有限,后期配套服务不充分。产品流通链条不畅,流通渠道狭窄,周转环节多,成本较高。信息市场规模小,覆盖面有限,农经信息量少,更新和传播缓慢。农业经营以“个体农户”为主,组织规模小,相对分散。大市场和小农户格局下,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较为普遍。
(二)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维护和激励功能有限
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调整相对迟缓,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维护和规制功能。《宪法》第八条对农村集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规定,界定了互作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认为“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和该法律约定匹配的经济状态应是纯粹的集体经济主体,及高度统一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当前农村承包权和经营权显著分离已成事实,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属范围做出约定,显然覆盖面不足。[17]《农村土地承包法》虽提及农地承包后的流转形式和环节,但对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后的权属界定和保障并未涉猎。相关条款需要尽快调整,以规范农村集体经营中的“三权分置”问题。[18]《土地管理法》确立于1986年,此后虽历经三次修改,但2004年最近一次修订距今已14年。订立于经济转型期的法律条文行政管制色彩浓厚,一些规定和经济发展新形势相去甚远。近年来由于生产生活需要,追加开发的土地有增无减,土地稀缺性和交易价格逐年上升。该法律第五章四十七条对耕地征用以市场价较低的农地产出物为基础确定补偿标准,明显不合理,并且扩大倍数小,补偿标准偏低。《农业法》第三十八条在规定各級政府预算内资金安排于农业相关领域时,没有明晰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利和责任。在财政体制不健全背景下,事权极易下行,最终或会导致下级地方承担过高的支出责任。
(三)政策条文不完善,绩效水平偏低
各种惠农基础设施投资、税费减免、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政策数目纷繁,出自多个部门,相互间协调和配合度差。一些文件条款交叉堆叠,有的已不合时宜,甚至彼此相互冲突。2018年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但《农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则指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直接发放给农民)”;农业部和财政部2017年重点强调惠农政策,亦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限定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现行农民从业领域高度分化,一些已不再专注于农业经营。土地流转给其他经营户后,有利于推动规模化生产,提高经济绩效。这两处制度安排的补贴对象,却把拥有经营权的种地农民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排除在外,显然和十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动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的发展方向相冲突。不利于培育和壮大新型职业涉农经营主体,也不利于农地有效维护和农业快速发展。
(四)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主体价值体系滑坡,约束力弱化
文化传统、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约束,往往受地域条件限制,在地缘和亲缘为依托的熟人关系圈,约束适用性强、效力高。但拓宽市场范围后,容易与外圈非正式规则发生碰撞和冲突,稳定性和权威性不足。一旦远离熟人群体,制度效应维系很大程度将取决于盛行社会风尚。如果社会主流文化和道义水平偏低,以传统和惯例约束经济决策和行为,失败概率很高。改革开放后,“利益至上”西方经营观念开始渗入国内,强烈冲击甚至压制和重塑本土文化。传统礼仪、仁爱、诚实和守信社会价值体系下沉和毁损,农药和肥料造假、违约拖欠和拒付货款等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和成本。
七、制度优化以促进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机制配置农业资源效率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持续增强农业领域市场功能。明确和强化新时代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主体地位,农户加入和退出农业组织、从事农业经营范围和种属及购买所需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业产品,均需遵循自愿互利原则。取消和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宜的过多行政管制,严禁强行组织和安排农民加入各种社团或组织,严禁强行限制农民各种正常经营选择的行为,严禁强行向农民兜售种子、农药、化肥和农机具与低价收购农副产品行为,保障和提升农民合法权益。简化冗繁行政程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轻农业经营中行政成本负担。降低农业经营市场准入门槛,破除各种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促使农业生产要素跨区域和行业流动,提升农业和其他相关产业部门的结合度和融合度,延长农业经营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19]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优化市场结构和布局,营造良好的农业经营外围市场环境。促进面向农业和农民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鼓励涉农融资技术和工具不断创新。引导外资、社会资本积极进入农业领域,不断拓宽融资渠道,扶持多种融资合作形式,逐步建立灵活顺畅、兴旺活跃及安全充裕的涉农融资体系。[20]保持各类农产品市场协调有序发展,依托即有市场资源,加强流通设施建设,构建辐射力强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健全产销衔接机制,推广电子商务、“互联网+农业”等现代农产品流通模式。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压缩周转链条,节省流通时间和流通成本。建设和完善农产品信息市场,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升级传播技术,及时更新、全面覆盖,以解决信息不畅所引发的系列农业经营问题。提高农业经营社会保险力度,丰富涉农商业保险业务,增强农业生产经营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健全涉農法律体系,有效维护农户合法经营权益
制度完善和优化是组织创新和绩效提升的基础,在各类制度安排中,法律制度具有高度严肃性、权威性和约束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规范农业经营行为,保障经营权益,激励经营创新,促进农业发展。必须“立法先行”,构筑起健全的法律体系。要结合当前农业发展形势及前景,尽快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草案,及时调整更新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首先是《宪法》相关条款要做出调整。《宪法》是根本大法,勾勒了法律体系整体框架,是其他法律和法规衍生的基础,也是农业和农村治理与安定的基础。农业生产经营中“三权分置”现状和趋势已成既定事实,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间权属关系需要在《宪法》中加以界定和规范。涉及同类事项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法规的对应部分也要分别加以修整。要取消和修订相关法律条文中过多行政干预和管制,真正从法律层面为农业和农民松绑。结合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土地管理法》中耕地征用补贴办法要加以改进,补贴标准要加以提升。《农业法》中财政支农力度要适度加大,各级政府支出责任要明确界定。一些重要支出要指数化,并划定下线。
(三)整合和优化惠农政策结构,激励农业经营组织积极创新
为推动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各项惠农和支农政策相继出台。政府对农业和农民支持以宏观经济政策为主,大体可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类。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补贴、减费降税及社会保障支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要涉及发改委、财政税务部门、科技部门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农业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制定和实施则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财政政策资金来源基本是财政预算。当前许多政府部门尤其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紧张,支出项目繁多、支出压力较大。对于现有惠农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要加以调整和修正。存在重复堆叠的,要清理归并加以整合。以优化政府惠农支出结构,节约财政资金。对于预期即将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农业部要紧密会同所涉及的相关部门,明确和落实各自职责。部门间应加强沟通和配合,订立政策要有明确针对性,防止政出多门、交叉支出。各项政策要相互协调补充,落实到位,真正发挥扶持农业和农民,激励农业经营主体创新的作用。
(四)塑造和宣扬良好社会价值体系,维护农业经营的稳定性
社会风尚和价值体系会依托心智构念形塑公众理性。社会信用和道德状况良好,易于促使行为主体正向内在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稳固。在涉及利益冲突时,能够激励或约束个体决策,较少做出和他人利益相悖逆的选择。基于熟人关系确立的规则和惯例约束力有限,不能满足大市场格局下农业生产经营跨地域扩张需求,应当继承和宣扬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崇优良社会道德风尚和诚实守信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正面价值体系主导和覆盖下的伦理关系网络。以保障和提升非正式规则的制度效力,维护和稳定农业生产经营秩序,促进农户家庭经济活跃发展,农村经济兴旺发达,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参考文献:
[1]王国刚,刘合光,等.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变迁及其影响效应[J].地理研究,2017(6).
[2]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中国编译出版社,1996:252.
[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2010:11.
[4]Becker,G.S.,“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momic Journal,Vol.1965,pp75.
[5]Bamum,H.N.,and L.Squire,“An Econometri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Farm-househo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1979,79-102.
[6]McElroy, M.B., and M.J. Homey,“Nash 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7,1981,pp.333-350.
[7]Singh,1.,L.Squire and J.Strauss.,“Agriculture Household Models:Extensions,Applications and Policy”,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MD,1986.
[8]Quiggin,J,“Comparative Statics for Rank-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Theor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4(4),1991:339-350.
[9]Abdulai,A.,and W.E. Huffman,“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Rice Farmers in Northern Gha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forthcoming).,1999.
[10]Emiliana Silva,Ana Alexandra Marta-Costa and Julio Berbel.,“The Objectives and Priorities for the Azorean Dairy”,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e of the 21st Century ,2015,pp137-156.
[11]Cathal ODonoghue,“Behavioural Microsimulation Modelling: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Farm-Level Microsimulation Modelling , 2017,pp.215-239.
[12]彭軍,乔慧,等.“一家两制”农业生产行为的农户模型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5(11).
[13]张治霆,朱烈夫,等.农户模型中生产专业化的动态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7(12).
[14]张丽丽.非完备劳动市场下农户均衡的实现——基于农户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J].农村经济,2013(6).
[1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8.
[16]诺思,戴维斯.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27.
[17]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和关系合同[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119.
[18]傅晨,陈漆日.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17(3).
[19]罗必良.农地确权、交易含义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科斯定理拓展与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11).
[20]温铁军,刘亚慧,等.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
Abstract:the family is now and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main organization form. The family as a unit, easily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such as natural resources, technical conditions, labor supply, political situa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and even geographical weather, will face various uncertainties. The external factors change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impact is mixed. It can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eed back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f farmers, evaluate the family microeconomic behavior and build an effective system by incorporating the economic life prototype, incorporating the risk factors and constructing the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model. The family management of farmers in the near future is mainly faced with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herefore,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e related system, improve the system system, strengthen the system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functions,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and cost of farmers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Key words:external shocks; household; uncertainty;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decision model; system adjustment
责任编辑:萧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