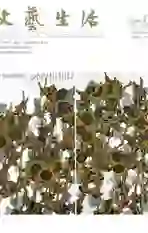一缕情思系家国
2018-05-03李肖肖
李肖肖
摘要:《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反映了那个时代贵族间的政治婚姻。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王室贵胄们以婚姻为纽带,来壮大自身势力,维护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稳定。在上层婚制和成长环境的双重规约下,贵族女儿们的人性诉求被政治利益无情吞没,以至于她们的婚姻观念中没有爱情的概念,有的只是男权政治反复灌输强调的家族、邦国利益。从家族利益出发考虑一切,既是家族规约的要求,亦是她们在生活环境影响下,意识中朦胧存在的本位观念。
关键词:贵族联姻;利益联结;贵族女儿;婚姻观念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06-0001-02
一、引言
《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反映了那个时代贵族女儿的婚姻状况,这些诗篇有的描写了贵族女儿婚嫁时盛大华丽的媵婚场面;有的透露了贵族女儿婚嫁后归宁不得的邦家之思;还有的展现了她们被抛弃后的精神世界。由于上层礼法和成长环境的双重禁锢,这些贵族女儿对爱情的本能需要被淹没,在她们的婚姻观念里充斥着的是邦家宗族的观念。本文以政治联姻这一在《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贵族婚制为背景,结合先秦婚姻礼制,重点分析《诗经》中的《鄘风·载驰》、《小雅·黄鸟》、《小雅·我行其野》三首诗,来透视先秦时期贵族女儿的婚姻观念,以期明晰贵族婚制的潜规则对这些贵族女儿意识形态和婚姻趋向的影响。
二、《诗经》中的贵族婚恋诗及其政治功能
在《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合二性之好的贵族婚姻,如《大雅·绵》中记载了周之大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在迁往岐山之下的过程中娶了姜姓女子为妻。姜姓是远古部落中的大家族,其与大王姬姓家族的结合无疑促进了周部族的壮大,因而周族人得以在岐山之下稳固发展。在《大雅·大明》中记载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与殷商的近畿国家挚国任姓的女子联姻,大任生文王,文王又与商朝有莘国姒姓女子结为婚姻。《史记》载:“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大姜、大任与大姒作为周室三母,亦是贵族女儿,其与姬姓周部族的联姻在保障几大氏族间安全稳固,促进彼此发展壮大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司马迁日:“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也。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以褒姒。”即充分肯定了贵族联姻与夏、商、周三代王朝兴亡之间的紧密联系。《礼记·郊特牲》中说:“夫婚礼,万事之始也,娶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娶异性女子是为了让远者归附,以姻亲的形式将异族纳入本部族的势力范围,来维护彼此邦家之间的安全稳固。就周代社会而言,统治者实行的是分封制,要想使诸侯归顺,远国来附,周王室自身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而这种实力的建立与巩固则需要外援,取得外援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政治联姻,结成甥舅之国。由此来看,在整个先秦时代的政治建构中,政治联姻是固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娶妻助祭宗庙、繁衍子嗣的时代主题下,这些贵族女儿们还要担负起联结异族,维护邦家利益安全的责任。所以那些在当时被评价为贤德后妃,贞顺之妇的贵族女儿,这些赞誉也都是从其为家族利益带来的好处角度所给出的。“女子,从人者也。”这极其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封建社会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人”。“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家庭和婚姻限制了她们全部的生活范围,禁锢了她们的一举一动,也侵蚀了他们的意识观念和精神世界。
三、成长环境和上层婚制规约下贵族女儿的婚姻观念
(一)贵族女儿婚姻观念中家国意识的成因
在《诗经》时代的婚约习俗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正如《齐风·南山》中所歌:“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在世代沿袭的婚约习俗下,绝大多数的女子只能无条件地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政治联姻在稳固邦家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贵族女儿们比起下层妇女,还要担负起为家国利益考虑的责任。虽然在男权社会里,这些贵族女儿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她们有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判断,她们之所以甘心做家族之间政治利益的牺牲品,除了父权和礼制的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则在于这些贵族女儿们已经不自觉地将家国利益置于自己婚姻的首位。分封制体系下的弱肉强食,使得这些贵族女儿不得不为邦家的安全稳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她们不得不奉献出自己的人生幸福,在别国充当贤德、贞顺的妻子,以扮演好维护邦家利益的角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贵族女儿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高度,甚至可以说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只是在生长环境和正统观念的浸染下,不自觉地拥有了这种备受家族重视的婚姻观念。
(二)由《鄘风·载驰》、《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黄鸟》透析贵族女儿们婚姻观念中的家国意識
在《诗经》所涉及的贵族婚恋诗中,最能体现贵族女儿“一缕情思系家国”的莫过于许穆夫人。《列女传》记载: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
历来对许穆夫人的评价,都集中于说她是一位有政治眼光的爱国女性,但很少有人解析这一政治眼光得以形成的现实环境。在壁垒森严的男权统治下,许穆夫人的这种政治洞察力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她从小所接受的教育:“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她之所以对当时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根本原因也在于她所成长的现实环境,在于她生命意识中的家邦本位观念,因而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中,她能有如此的眼界和想法。毫无疑问,在许穆夫人的婚姻观念里,家国利益是她考虑的首位。因此,在得知自己的宗国被灭时,她不再畏惧夫权的淫威和当时的礼制,毅然奔赴漕邑吊唁卫侯。面对家国沦丧的现实,这意味着她一度置于生命本位的精神支柱倒塌了,所以她无暇顾及“既嫁从夫”的教条,为了挽救宗国,这位卫国女儿毅然冲破了经圣藩篱,在男权统治的时代里,高度凸显了她的家国情怀。
在《小雅·我行其野》中,同样表现了这位贵族女儿婚姻观念中的家国意识。尽管这是一首弃妇诗,但其语词风格不同于《邶风·谷风》、《卫风·氓》等弃妇诗中下层妇女的悲吟。在这首诗中,这个被抛弃的贵族女儿讲到的是:“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由于庶民女子嫁到外邦去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且《诗经·小雅》中的作品多为贵族所作,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贵族女子,嫁到异邦诸侯之国而遭弃的自述。郑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娶之月。妇之父,婿之父,互谓婚姻。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孔颖达解释说:“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信之恶夫。既得恶夫,遇己不善,乃责之言:‘我以我父之婚,尔父之姻,二父敕命之,故我就尔而居处为家室耳。我岂无礼而来乎!而恶我也!你既不我蓄养,今当复反我之邦家矣。”这一贵族女儿秉承父命,为自己的家邦而婚配异邦,在被抛弃后,支配这一贵族女儿生命意识的依然是自己的邦家。可想而知,这些贵族女儿们从小就被禁锢在正统礼制的藩篱中,所受的教化便是要在以后成为贤德后妃,守礼贞妇,事事从邦家利益出发,扮演好巩固异族大邦关系的婚姻角色。
从这一政治背景来解读《小雅·黄鸟》这首诗,则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贵族女儿婚姻观念里根深蒂固的家国本位观年。郑笺云:“妇人自为夫所出,而以刺王也之由。刺其以阴礼教男女之亲,而不至笃联结其兄弟。夫妇之道不能坚固,令使夫妇相弃,是王之失教,故举以刺之也。”孔疏云:“兄弟谓婚姻嫁娶,是谓夫妇为兄弟也。夫妇而谓之兄弟者,《列女传》曰:‘执礼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国安危可否,兄弟之义,故比之也。”胡承珙在《毛诗后笺》中云:“此诗自传、笺以后,人人说殊。王氏、苏氏以为贤者不得志而去;吕记、严辑以为民适异国,不得其所之诗。然以经文证之,此言‘复我邦族与《我行其野》之‘复我邦家正同。彼明言‘婚姻之故而与此诗相次,则此诗自亦为室家相弃而作。毛郑之说,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黄鸟采菜,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焦氏正用毛义也。”因而胡氏认为这是一首贵族弃妇之诗。
从诗的内容来看:“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以及“此邦之人,不可与明”郑笺云:“‘明当为‘盟。盟,信也。”这首诗涉及的应是两大邦族之间的政治联姻。这两大邦族结盟为誓,约为甥舅之国,来保障彼此之间的利益,而这种男权社会的外交策略也深刻影响到了成长于斯的贵族女儿,以至于她深明自己的婚姻属性,所以在被抛弃后,受生命意识中家邦观念主导的这一贵族女儿的话语中充斥着的是“复我邦族”。正因为清楚自己的婚姻是两大邦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所以她才反复提到“此邦之人”以及“归我邦族”。由此来看,受正统礼制严格制约下的贵族女儿,她们的人性诉求早已被贵族政治扼杀在摇篮里,成长环境使得她们的婚嫁观念总是不自觉地含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与家国利益相联系。
四、结语
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意识形态都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先秦时期分邦建国的政治体制规约了那个时代的礼乐制度。贵族联姻制既是巩固王室地位的需要,也是各诸侯国保障自身安全稳固的需要。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也就直接决定了贵族女儿们的婚姻走向并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她们的婚姻观念,使得她们在被动接受的婚姻中只知有家国的存在,不知有爱情的存在;只知自己的婚姻关乎邦族利益,却不曾意识到自身的情感需要。这种贵族联姻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联姻都普遍存在着,即使是在思想高度解放、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今天,名门望族间的政治联姻也依然为数不少。
时代在前进,文明在演进,我们依然需要反思当今社會的婚姻制度。毕竟爱情才是婚姻中的天然因子,所以男女双方应该以自己真实的情感需要作为缔结婚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