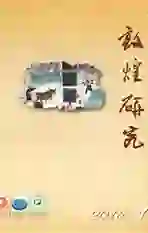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髡发人物
2018-03-20李金娟
李金娟
内容摘要:髡发是将头顶头发剃光、留周围头发的一种发式,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发式,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第346窟、第97窟等洞窟中可以看到若干髡发人物,反映了佛教艺术在流传过程中对当地和周边民族风俗习惯的吸纳,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
关键词:髡发;敦煌石窟;佛教艺术;辽墓壁画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1-0107-06
On the Figures with “Kun” Hair Styles in the Mogao
Murals at Dunhuang
LI Jinjuan
(School of Ar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Kun” is a type of hairstyle for men who only shave the top of their heads and keep the hair surrounding the crown. As a traditional hair style of nomadic ethnic groups in north China, this kind of hair style can be traced as far back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lthough Buddhism arrived in China from India, many paintings of Dunhuang caves show figures with the “Kun” hairstyle, such as those in caves 285, 97, and 346. This demonstrates how Buddhism absorbed the customs of local ethnic groups as it was disseminated eastwards, indicating in turn how Buddhism was Sinicized.
Keywords: “Kun” Hair style; Dunhuang caves; Buddhist art; Liao tomb painting
髡即剔、剃之义,髡发专指剔除头顶发而余留侧面头发的一种发式。髡发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发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髡发习俗。敦煌莫高窟西魏洞窟、五代洞窟、沙州回鹘洞窟都可以看到若干髡发人物像,既反映了佛教艺术在流传过程中对当地和周边民族风俗习惯的吸纳,也是民族大融合的体现。
一 第285窟髡发飞天
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开三龛,南北壁各开四个禅室。北壁有西魏大统四年(538)、五年(539)题记,由于正值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时期,一般推测此窟即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元荣所开“一大窟”。该窟内容丰富,西壁正中大龛内塑倚坐佛,两侧各开一小龛,塑禅定比丘,龛间主要画大自在天等印度诸神。窟顶四披主要画伏羲、女娲、雷神等中国神话诸神。东壁门两侧各画一铺说法图。南壁画五百强盗成佛缘、度恶牛缘(以上为因缘故事画);沙弥守戒自杀、度跋提长者姊(以上为戒律故事画);施身闻偈(本生故事画)等5组故事画和一铺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图。
南壁西侧释迦多宝说法图的华盖两侧各画一身飞天,髡发,身体全裸,双臂环绕一条飘带,双手合十,从空飞下;身体修长,双腿相错,宛若游泳姿势。画工用白色颜料涂抹人物身躯,配以蓝色飘带,使飞天形象更加醒目(图1-1、图1-2)。
佛教有二十八天之说,据失译名者今附东晋录《般泥洹经》卷上记载,从依附须弥山的四天王天向上方天空延伸,最高一天是第二十八天不想入天。诸天实际上是净土世界,佛教艺术中的飞天是指佛说法时诸天的天神前来赞叹供养,多数飞天穿长裙,戴宝冠。此窟20多身环窟四壁上方的持乐器飞天也长裙裹脚,唯独释迦多宝说法图华盖两侧的飞天为裸体,其髡发应该是西魏拓跋族的发式。画工这一突发奇想用现实社会中的髡发人物来表达飞天,又以裸体来表达飞天的天神身份,給洞窟增添了一丝浪漫色彩。尽管少数民族艺术往往不忌讳裸体,但敦煌石窟艺术的主流仍然是汉风,所以裸体在西魏、北周洞窟多有所见(北周第428窟也有,但不是髡发),而隋唐洞窟中却罕见其踪。第285窟髡发裸体飞天体现了北朝洞窟的民族风格。
二 第346窟髡发射手
敦煌莫高窟第346窟实即第345窟前室南壁。第345窟原建于武周时期,经五代、宋(或西夏)重修,主室西壁开一敞口龛。主室南壁、北壁、东壁宋画千佛,窟顶藻井中央宋浮塑团龙,四披宋画棋格团花图案。
主室龛内主尊背光为武周时期原作,主尊须弥座有三面武周时期绘菩萨坐像各一身,技艺精湛,北侧弟子塑像的裙摆也为武周时期原作{1}。多数洞窟在后来重修时并没有彻底毁掉全部壁画,而是在旧有壁画基础上再抹泥层后绘制新壁画,因此第345窟南壁、北壁、东壁底层应该还存有武周时期的壁画。
窟顶、东、南、北壁均为宋重绘壁画{2}。
甬道顶绘五代佛教史迹画,南壁画五代供养比丘三身,上方为垂幔,北壁仅存上方垂幔。南壁三身供养比丘存部分榜题。西起第一身双手持长柄香炉,榜题:“囗囗(官)报恩寺首座尊宿囗(沙)门慈惠供养”;第二身双手捧手香炉(无柄),榜题:“社子释门法律知应管内二部大众诸司都判官兼常住仓务阐扬三囗(教)法师临囗(坛)大德沙门法眼一心供养”;第三身双手捧花盘,榜题:“……囗(知)福田囗囗囗(司判官)阐扬三囗(教)……临坛大德沙门慧净一心供养”[1]。
前室东壁毁,南北壁宽度约5.8米,地面距离窟顶约4.5米。窟顶西侧存七个佛座及部分七佛壁画;南壁残存一块五代时期壁画,高1.1米,宽0.9米,为保护这块壁画而修建了一门,编号为第346窟{1}。
第346窟壁画为一身力士,双腿膝盖以下部位,腿部肌肉刚劲有力,由于壁面有4.5米高,完整的力士像应该有3米多高。力士双腿之间画一射手,保存完整,高与宽均0.65米。射手头缠红色头巾,髡发,左侧头巾附近露出短发,着毡靴;左腿跪于地,右腿半支,腰插二支箭;右手伸直握弓,左手拉弦上箭,满弓待发状(图2-1、图2-2)。由于保存完整,形态生动,为敦煌壁画中的名品,频见各类图录:
1.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第86图,时代定为五代晚期,图版说明是:“此窟即第345窟露天的前室南壁。残存壁画中,天王与夜叉脚下的这身射手形象保持完整。射手头扎红布头巾,身穿紧袖交领长衫,腰束菱纹花革带,带上斜插羽箭两枝,足登长统战靴,胡跪在地,仰面引弓搭箭,瞄准待发。壁画画在麻筋石灰抹面的壁上。可能是在五代末年前室顶及南壁又经历了一次大崩塌,仅存留了这块残迹,又在宋初重修时被封闭。本世纪四十年代才将此画清理出来,因此线描保持清晰,色彩鲜艳如新。”[2]
2.《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之《中国壁画全集·敦煌·9·五代宋》第102图,图版说明是:“这是天王左侧药叉脚下的射手,浓眉大眼,唇上有八字髭,头系红巾,身穿左衽缺袴衫,腰系饰有宝石的革带,腹前插两支羽毛箭,脚穿尖头靿战靴,完全是西域人的装扮,昂首胡跪,紧拉弓弦,好像屏息着呼吸瞄准前方,伸直的臂腕和弓的两翼几乎拉成平行线,显示出放矢前的力量,造型比例准确,线描挺劲有力,面与手的晕染恰到好处,加强了形象的真实感。”[3]
3. 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第213图“吐蕃射手服饰”,将图版排在第61窟之后(第61窟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据S.2687《大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翟氏舍施疏》,推定该窟建成于947年),图版说明是:“射手头束红抹额,身着左衽交领半臂衫,有臂鞲,腰束花纹革带,束绑腿。从额饰看,射手似为吐蕃族。”[4]
力士是佛教守护神,射手位于力士的下方,似乎应该隶属于佛教神灵,但这身射手的形象和装束却具有鲜明的世俗与民族特色。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2号墓是一座较为重要的辽代壁画墓,发掘于1974年,墓道南壁一位男人蹲在车轮跟前,髡发,穿毡靴(图3-1、图3-2){1}。这身髡发侍者与莫高窟第346窟射手形象比较接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1998年,杨富学、杜斗城发表《辽鎏金双龙银冠与敦煌佛画》一文,指出:“在敦煌莫高窟五代时期的壁画中,我们甚至可以见到契丹人的画像。莫高窟第346窟内现残存有一幅射手图,为五代时期之遗画。射手髡发,头扎红布头巾,身着紧袖交领长衫,腰束菱花革带,带上斜插羽箭两支,足蹬长统战靴,胡跪于地,仰面前视。箭在弦上,引弓待发。其装束和发型与辽代内蒙古库伦2号壁画墓墓道南壁屈膝席地而坐的髡发青年驭者极为接近,可明显看出契丹服饰与髡发之俗的影响。”{2}2006年,沙武田先生发表《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引述了前揭杨富学、杜斗城的观点:“莫高窟第346窟壁画中的射手则与内蒙古辽代库伦2号壁画墓的青年人物,在服饰特点上十分相似”[5]。第346窟射手髡发,头顶剃光,但侧面头发不长,并没有垂至颈项。
五代、北宋时期,敦煌与辽代存在密切的关系。《辽史》记载与敦煌有关的资料多达10余处,《辽史》卷3载天显十二年(937):“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贺。”[6]这是敦煌与辽代关系的最早一条有具体纪年的资料。同书卷4记载会同二年(940)“十一月丁亥,铁骊、敦煌并遣使来贡。”三年(941)“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6]46-47使者献舞,似乎是一种侮辱行为,但此后100年间敦煌一直与辽朝有来往。《辽史》卷15、16记载开泰三年(1014):“四月,沙州回鹘曹顺(曹贤顺,一作曹恭顺,避辽景宗耶律贤讳而省改)遣使来贡。”八年(1019)“春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九年(1020)“秋七月……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遣使来贡。”[6]185-187据李万《韩橁墓志铭》(全称《大契丹国故宣徽南院使归义军节度沙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壹佰伍拾戶韩公墓志铭并序》),开泰八年(1019)到敦煌宣布册封的是韩橁,韩橁卒于重熙五年(1036),墓志铭立于重熙六年,墓志铭未提到韩橁生年。韩橁墓志显示他有“归义军节度沙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官职,表明敦煌与辽代的密切关系{1}。《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条记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59个“属国”中,与敦煌有关的有3个:“敦煌……沙州敦煌……沙州回鹘”[6]429-433。虽然杂乱,仍可见敦煌与辽代存在隶属关系。
五代时期敦煌佛教得到空前发展,新建了一大批洞窟,窟形巨大的洞窟很多,另外还对整个崖面进行彩绘,至今崖面露天位置上仍存留部分壁画,第346窟力士与射手壁画即绘于五代时期。从莫高窟洞窟营建史和壁画风格上看,第346窟髡发射手图绘于五代大致可信。结合前揭《辽史》关于937年、940年、941年敦煌“遣使”辽朝的记载,第346窟髡发射手与辽代风俗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 第97窟髡发飞天
回鹘在五代时期就活动于敦煌一带,西夏占领敦煌前夕,沙州回鹘势力很大,参与抵抗西夏的战争。由于藏经洞在11世纪初封闭,此后的敦煌历史资料匮乏,沙州回鹘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属于一支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并存的部落。一般认为西夏在1036年占领敦煌,敦煌归于西夏版图。有一些学者则认为1036年之后的30多年间,敦煌由沙州回鹘统治,1067年西夏才统治敦煌地区{2}。
沙州回鹘信仰佛教,但在莫高窟没有新建洞窟,只是在第237窟、第409窟等一些前代洞窟中绘制了回鹘国王像等。第97窟修建年代比较复杂,可能于唐代始建,沙州回鹘时期重新抹上泥层,在东壁、南壁、北壁绘制了十六罗汉,是一个以十六罗汉信仰为主题的洞窟。窟顶藻井中央浮塑团龙,四披画棋格团花图案。正壁(西壁)为盝顶龛,龛内存清塑一铺五身,丑陋不堪,不屬于敦煌艺术的范围,龛内壁画则属于沙州回鹘风格。龛顶、龛东披绘团花图案,南披、北披各绘一散花飞天,龛西披画佛像的华盖,两侧各画一身童子飞天。
南侧童子飞天髡发,前额中央系一红色小布条(用途不明,似乎是儿童吉祥物品),右耳上方有一长长的头发向后飘扬,穿背带裤,双腿粗壮,裸露在外,右脚穿红色毡靴(左脚弯曲在身后,未画出毡靴),右手持小花盘,盘中仅一朵花,左手持一朵花待撒;北侧飞天髡发,前额中央系一红色小布条(用途不明),左耳上方有长长的头发向后飘扬,也是穿背带裤,双腿粗壮,裸露在外,右脚穿红色毡靴(左脚弯曲在身后,未画出毡靴),左手持小花盘,盘内仅有一朵花,右手持一朵花待散(图4-1、图4-2)。
第97窟两身童子飞天髡发,大腿粗壮,体型、发式、装束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的风格。辽代与敦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髡发发式看,可能存有辽代的风格,但目前学术界通过与回鹘人物的比较,推测此窟为沙州回鹘洞窟[7]。
四 莫高窟髡发人物画的意义
髡发是春秋战国以来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发式,有学者认为:“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自有渊源,不是来源于中原的髡发刑徒。而是游牧民族驰骋漠野,当苦沙尘,索性髡发以免梳洗之劳。契丹人的髡发,直接承继鲜卑人的社会习俗。”[8] 髡发原本是北方沙尘频发地区游牧民族的一种发式,便于打理,后来逐渐变为一种礼仪,是族属的象征。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纳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放弃了一些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形成了中国佛教。佛教艺术的传播也是这样,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原汁原味的犍陀罗与秣菟罗佛教艺术作品,而是适应本土文化的佛教艺术风格。以南朝风格为例,南朝士大夫所喜欢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审美情趣首先在南朝佛教艺术中得到体现,并很快传到北朝,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就是典型的南朝艺术风格。南壁释迦多宝说法图中的两身飞天既有南朝“秀骨清像”的风格,又有北方游牧民族髡发的特征。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髡发人物图有神灵(飞天)、有世俗人物(俗装射手),世俗色彩浓厚,对于佛教信仰者而言,更为亲切,大大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上述髡发人物图分属于西魏、五代、沙州回鹘三个不同时期,前后跨度有500年之久,说明佛教的世俗化是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
参考文献:
[1]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40.
[2]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21-222.
[3]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壁画全集·敦煌·9·五代宋[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42.
[4]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222.
[5]沙武田.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J].中国史研究.2006(3):68.
[6]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1.
[7]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C]//敦煌研究院.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23.
[8]侯妍文.小议辽代髡发:以辽墓壁画为线索[J].工业设计,2016(6):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