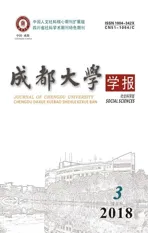热奈特叙事理论视角下的《远大前程》*
2018-03-19刘星
刘 星
(吕梁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吕梁 033000)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19世纪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对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远大前程》是狄更斯后期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在他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之后,对人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狄更斯把自己的道德观、伦理思想都融入到了这部作品之中。在小说的创作中,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小说的主线,但在一部饱满的小说作品中,空间形式的运用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主人公匹普少年时代的许多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的焦点人物匹普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因此匹普这个人物活动空间形式的转换正是串起这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通过细读,笔者对狄更斯特有的写作手法和叙事策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本文以法国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为基础,探析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通过巧妙的叙述手法控制审美距离,以实现小说的叙事美学效果。
一、热奈特叙事理论概述
热奈特是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结构主义认为:一切可以认识、理解的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永恒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是切入其中的思想路径与分析方法,可以直达事物的本质。热奈特的论著《叙事话语》和《新叙事话语》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经典之作。他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叙事时间理论,试图以此揭开文本内部的秘密。
热奈特在他的《叙事话语》中阐释了文学叙事中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他曾引用了梅茨的一段话来阐释叙事时间的双重性问题:“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即“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为另一种时间。”[1]12时间的“畸变”和“兑现”,是对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创造,即是把现实生活时间经验创造为文本的虚构时间经验。因此,对叙事作品中时间的考察,关涉到讲述时间和被讲述时间两个方面。讲述时间是线性的现实时间, 而被讲述的故事时间可以是被打乱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因此故事的时间可以是多维的。但在叙事中,叙述者不得不打破这些事件的‘自然’顺序,把它们有先有后地排列起来,因此,叙事的时间是线性的。故事与叙事在表现时间上的不同特点为改变时间顺序达到某种美学目的开创了多种可能。”[1]4
热奈特对叙事时间的讨论分为三个方面:时序(故事事件的时间顺序与它们在叙事文本中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时距(故事事件的时间长度与它们在叙事文本中的时间长度之间的关系)、时频(故事事件的重复程度与它们在叙事文本中的重复程度之间的关系)。热奈特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界定虚构文本的叙事时间。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视野中的时间是可知的、可被结构化的时间。叙事中出现的时间打乱现象,如插叙、倒叙、预叙等,对时间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改变历时性线状叙事的单一格局,开创了共时性立体化叙事的新方法,开拓了叙事表现的新局面。但不管怎样,这些只是时序性时间的不同结构方式而已,在阅读的过程中,叙事时间最终都能被还原成时序性时间。
二、叙事话语特征的突破
布斯指出:“任何阅读体验中都具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四者之间含蓄的对话。上述四者中,每一类人就其与其他三者中每一者的关系而言,都在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甚至是身体的轴心上,从同一到完全对立而变化不一……那些通常归诸于审美距离加以论述的因素当然会出现:时空的距离,社会阶级或言谈服饰习惯的差异——这些和许多别的因素用来控制我们涉及审美对象时的感觉……具有‘间离’作用……。”[2]87他指出“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2]89
在《远大前程》中,皮普的成长可以说是其良知超越不成熟的理想主义的过程。皮普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非常渴望完善自己,他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自己可以有“远大前程”。皮普想要实现自我完善的愿望掩盖了他原本善良的本性。小说中很多地方他的表现得差强人意,对真心关爱自己的乔、毕蒂和马格韦契表现得很势利,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读者的同情。读者总是站在皮普一边,盼望着他转变,希望他有好的结果。这一效果就是由于狄更斯恰当地控制了“距离”。
小说中有两个皮普:成年的叙述者皮普和小说人物年少时的皮普。少年的皮普是一个慷慨无私、善良宽厚的人。“他的心地与读者的一样;他注视着自己年青的自我似乎先是远离读者,后来又回到读者那里。”[3]103狄更斯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揭示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成年皮普叙述了自己年少时的人生经历。因此,在小说中,“儿童的目光与成人的反思随着时间的进程互相交融,构成了作品的‘双重视角’。”[4]28狄更斯巧妙地使成年的皮普与年少时的皮普共同承担了小说的叙述任务。成年皮普的声音中透着远见和成熟。在小说中,成年的皮普不时取笑年少时的自己:“一方面提高我们对小皮普道德堕落的感觉,另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他倒霉时保留我们的同情,并确信他还会崛起。”[5]43
幼时的皮普心地善良。他非常害怕在沼泽地遇上的逃犯,但还是很同情他,决定“非得做一次小偷不可”,偷拿食物和锉给“那个可怕的家伙”。当得知警察在追捕逃犯时,皮普还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感叹到“好可怜的两个苦命人啊!”并且“希望找不着那两个人才好呢”。在这一部分,尽管皮普表现出了自己的善良品质,可是他却一直在自责,强调自己的“罪过”:“一想到自己当夜就得去偷乔大嫂的东西,心里就有一种犯罪的感觉”[5]57。这时的皮普眼中,连沼泽地上的牛群都在责备自己,叫自己“小贼”,认为自己做的是件“卑劣的犯罪勾当——私通罪犯”[5]57。
这一部分,叙述者用儿童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孩童时的不成熟,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又符合主人公儿童的身份。读者要真正理解小说人物皮普,就不能仅限于皮普的自我描述,而要超越他,把目光放在他的具体行动上,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去衡量、去审视。所以读者眼中看到的小皮普不是“小偷”、“罪犯”,而是一个充满怜悯、同情心的人,这时读者和皮普的距离是拉近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小说中,皮普并没有被描绘成完美无缺的,得知自己将获得一大笔遗产后,皮普变得很势利,与读者的距离不断拉大。“解决纵有要命的缺点也要保持同情这一问题,主要是运用……主人公本人作为叙述者。”[4]85叙述过程中皮普不断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持续不断的内心活动表明其身上的缺点是可以弥补的。“能够为犯错误的皮普提供安全的避难所”。“一般来说,内心视角所提供的内心历程愈深刻,人们愈容易心甘情愿地信赖叙事者,愈会对他具有同情感。”[4]48
三、叙事话语的美学效果
在小说第18章中,贾格斯律师出现并告诉皮普,他将马上继承一笔财产时,皮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少年的自负使皮普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眼中看到的家里“一切都那么粗俗下贱”,“总觉得住的、吃的,愈看愈不像话”。于是,“那见不得人的内心里,便愈来愈觉得这个家丢尽了我的脸。”[6]61甚至觉得满天星星“都不过是些贫苦下贱的星星”,无非是“乡野景物”。因为“马上要身价百倍了”,觉得自己的小卧室也变得狭小简陋。但是,远大的前程就在眼前,皮普却“感到心慌意乱,彷徨不定——究竟是这间小屋子好呢,还是我即将去住的上等房好?……究竟是铁匠铺好呢,还是郝薇香小姐的庄屋好?毕蒂好呢,还是艾丝黛拉好?”[6]162有时候自己很清楚和乔在铁匠铺要过的这种平凡而清白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丢脸之处,相反倒是很值得自尊,引为幸福,但是“突然之间又痰迷心窍”,开始幻想郝薇香小姐会使自己“飞黄腾达”。
皮普要走,乔和毕蒂都很伤心。皮普却认为自己很优秀,应该离开这样的环境和上层人生活在一起。尽管如此,当天晚上看到乔和毕蒂在一起悄悄地谈论自己,皮普还是为即将离开他们而感到悲伤:“心里又是悲哀,又是诧异——怎么交好运的头一天晚上,就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寂寞凄凉呢!”[6]162甚至觉得自己的床“也变成了一张很不舒服的床,再也休想像往常那样躺在上面睡得又香又甜了。”[6]162然而第二天,皮普又表现得很势利。在裁缝铺做新衣服时,听任特拉白对自己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甚至接受潘波趣的邀请,任由潘波趣一个劲儿地巴结他。要离开家前往伦敦时,不愿意乔去送自己,因为觉得“我们两人在一起势必显得太不相称”[6]162。可过后他又对自己“卑鄙的意念”而后悔,为自己如此势利地对待最爱自己的人“哭了一阵”,眼泪洗涤了蒙蔽“心灵的凡尘俗垢”,从而增加了抱愧的心情,看清了自己的忘恩负义。
小说人物皮普的内心矛盾充分显示了年少时心智的不成熟,这时叙述者皮普和小说人物皮普之间在道德、理智、认知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通过成年的皮普对早年由于自己的幼稚无知所犯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阻止读者置身作品中人物的世界,使读者与皮普的距离时远时近,产生了“张力”。“规定了读者与事件的距离,并如此产生了小说的美学效果”[7]46。
到伦敦“受上等人的教育”之后,皮普变得更加傲慢自负。乔特意来伦敦看望他,可他却担心朱穆尔会因为乔而看不起自己,“尤其念念不忘的是彼此身份的悬殊”[6]242;回到镇上去看望郝薇香小姐和艾丝黛拉时,为了炫耀自己,“为自己编造种种理由和借口”去住饭店而不愿意住在乔的家里。这时狄更斯笔下的皮普可以说被描绘得势利到了极点,读者为他对乔的态度感到痛心,可以说两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了最大值,但读者并没有因此对皮普产生厌恶之感,仍然与他站在一起,同情他,期望着他的改变,这一效果是由于狄更斯插入两个片段又将两者的距离拉近了。
返回伦敦前,皮普走在镇子的大街上,察觉出自己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看到大家羡慕的眼光,感到很得意。可就在这时遭到了特拉白裁缝铺小厮的几次嘲弄。皮普写到“这使得我大为难堪”,“弄得我大为狼狈”。小厮不断想出新花样取笑皮普,一直跟在后面撵,“他把我撵过了桥才算罢休,我就这样丢尽了脸……被撵到旷野里来了。”[6]272
“同情的笑声从来都不易获得……对于缺点并非来自令人同情的美德的那些人物,同情他们的笑声尤为困难。”[5]92皮普表现出来的势利出于想成为一个“绅士”的愿望,并非来自“令人同情的美德”。因此,要使读者笑话主人公所犯的错误,同时又盼望着他的改变并因此有好的结果,加入这类情节是很必要的。
小说插入伍甫塞在舞台上的滑稽表演,用意也是嘲笑皮普从一个普通人一跃成为上等人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舞台上的笑话不断,轮到伍甫塞扮演的哈姆雷特出场时,“观众便只顾拿他开玩笑了”。观众总是“对伍甫塞先生抱以哄堂大笑”,笑声“始终围绕着他转……”[6]282。皮普在描述自己的缺点时,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读者知道皮普内心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的缺点是有希望改变的,因此虽然对皮普的表现不满意,但看到他被戏弄、被嘲笑时,仍然同情他。
随着情节的发展,皮普不断成长,善良的本性逐渐突显了出来:他为自己对乔和毕蒂的态度感到内疚,恳求他们的原谅;暗中帮助好友赫尔伯特;刚开始得知真正资助自己的人是没有文化的逃犯马格韦契时,皮普感到“对他厌恶得不能再厌恶了”,却为他的安全担心。到最后皮普写到:“我丝毫也没有厌恶他的心情了……我只觉得他待我恩重如山;这许多年来始终对我情深意厚,感恩不忘,宁愿倾囊相报。我觉得他待我,比我对待乔真要高尚千倍。”[6]503这表明良知最终超越了不成熟的理想主义,皮普完成了成长的过程,最终又回到了读者身边。
“距离在文学阅读过程中是动态而富于变化的,可以从大幅度的距离降至零,也可以从完全同一到截然对立。”[7]51小说中存在的价值观、道德和理智等方面的距离主要是指信念与规范而言的。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和读者之间“各自的信念与规范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而最佳的阅读效果是随着阅读的展开”,使其“达N——致”[8]121。小说主人公皮普的成长可以说是其良知超越不成熟的理想主义的过程。皮普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非常渴望完善自己,他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自己可以有“远大前程”。可以说皮普想要自我完善的愿望掩盖了他善良的本性,小说中很多地方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对真心关爱自己的乔、毕蒂和马格韦契表现得很势利,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读者的同情,读者总是站在皮普一边,盼望着他的转变,希望他有好的结果。这一效果就是由于狄更斯恰当地控制了“距离”。《远大前程》的叙事策略与美学效果就在于狄更斯巧妙地控制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使叙述者皮普视角的变化与其心理的成长相辅而行,时远时近,到最后与读者的“期待视域”相融合,从而充分显示了其小说的美学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王泰来.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3.
[4]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林骧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6]查尔斯·锹斯著.远大前程[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7]刘炳善.英国散文与兰姆随笔翻译琐谈[J].中国翻译,1989(1):46,51.
[8]张锡坤.新编美学辞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