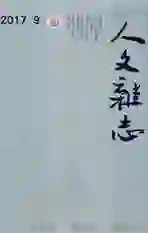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现代城市记忆的历史限度
2018-03-10温权
温权
内容提要 当下,资本生产通常以地理事件的形式凝结为拜物教化的城市景观。故而,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理论始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升格为阅读资本城市秩序的空间性叙事。它揭示出三重辩证关系:第一,资本空间生产的共时态结构同城市地缘风貌的历时态变迁彼此形塑,且在货币之于土地属性的修饰环节中,成为扰动城市地理想象的消极因素;第二,资本自身形态的间歇性让渡和城市规划蓝图的拜物教愿景相互裹挟,并于实体资本虚拟化的趋势内,成为瓦解城市空间座架的始作俑者;第三,资本运转无法规避的阶级冲突与城市人群形色各异的空间身份有机融合,进而借助碎片化的生产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成为动摇城市日常根基的否定性力量。应当说,嵌入城市空间结构但最终遭遇地理学瓶颈的资本辩证运动,可视之为消解城市文明记忆的异化过程。其实质,是解读城市发展轨迹的文化-政治性地理坐标,被资本逻辑预先设定的历史限度所遮蔽。换言之,在马克思经典论断的语境中,资本对城市景观的持续唤起无异于对现代城市精神的不断褫夺。
关键词 资本逻辑 城市记忆 地理景观 虚拟资本 阶级政治
〔中图分类号〕B0-0;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9-0025-11
由《资本论》及其手稿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植根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全景式逻辑学关照。据此,在资本生产、货币周转、商品循环等范畴的辩证框架中,马克思试图通过概念演绎的方式阅读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历史症候。无独有偶,对于资本的当代属性而言,其“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内在趋势,已然“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刻画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地理特征。”①作为反映资本社会结构的空间座架,后者集中投射于表征货币增殖和价值剥削的城市拜物教景观之内。于是,寓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能进一步拓展为解构现代资本城市样态的空间性叙事。它囊括了有关城市基本构成要素之于资本逻辑的三方面地理-历史性辩证关系:
首先,是在土地属性被资本化的过程中,资本空间性生产同城市历史性重构的博弈及其对城市直观印象的间歇性篡改。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②所以,作为城市地理始基的土地本
身才能褪去自然属性,并接受资本逻辑与货币法则的规训。于是,能否与变动不居的资本空间生产节奏保持一致,就成为取舍现存城市景观的惟一标准。当二者发生激烈冲突而资本的未来地理预设最终胜出时,关于现代城市的既有空间想象势必被不断颠覆。其次,是在实体资本被虚拟化的环节内,货币职能性让渡与城市投机性扩张的媾和及其对城市规划契约的阶段性否定。金融信贷业的崛起强化了货币资本对城市基础设施营建的干预力度。其无限增殖的投机特性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创造了可能。但“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职能性货币的虚拟化,无疑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加之投机行为带来的资本信用危机,已然被金融泡沫抽空财富基础的过度城市化空间,自然会周期性地破坏自身既定的利益承诺。再次,是在阶级矛盾被弥散化的趋势下,个体空间身份碎片化和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耦合及其对城市日常根基的总体性褫夺。实际上,“城市日常生活与资本空间生产是彼此近似的问题,其母体都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连贯过程。”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76,pp.7~8.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通常将城市塑造为“保证劳动力日常交换与更新的市场性琐碎区域。”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p.127~128.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本隶属于不同阶级的城市差异性人群,就再次被资本生产与消费的碎片化序列所细化。它在巩固资本空间秩序的同时,不可逆转地摧毁了个体之于城市认同的根基。
应当说,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运动在城市景观中所遭遇的地理学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城市文明能够在历史记忆维度自我传承的可能性。当资本空间生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把真实的市民社会改造成迎合货币权力秩序的抽象场域时,用于定位城市阶段性文明形态的文化-政治性地理坐标就被资本划定的虚假轴线遮蔽了。而被迫接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生活于假象当中的现代城市人群,则“不顾风险地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代能够将假象变得如此清晰明白、令人信服且‘无比真实的参与者。”N.Gabler, Life the Movie:How Entertainment Conquered Reality, New York:Knopt,1998,p.4.一旦城市精神的社会发展史成为资本逻辑的空间生产史,人们关于城市记忆的最大历史限度必然止步于资本地理性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对资本社会矛盾的指认,又可视为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历史前景的批判性隐喻。
一、资本化的土地属性与被颠覆的城市印象
现代城市景观的确立是资本空间生产对社会地理座架进行历史性重构的结果。其形态更替与结构调整的轨迹同资本逻辑的内在节奏彼此吻合。因此,作为表征货币增殖与价值积累的抽象场域,“城市通常被看作巩固资本某一特定生产方式,或根据市场需要产生全新交往规则的地缘性节点。”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then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p.203.在实证科学的语境下,它总是以“自身的物理线路以及作為‘代谢工具的网络体系的循环流转,表征出资本辩证运动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过程。”Eric Swyngedouw,“Metabolic Urbanization,” in N.C. Heynen, et al.,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006,p.21.而现代城市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的形成,则肇始于资本的货币权力对之前土地属性的规训。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讲道:endprint
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对旧形式发生了作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者。因为,现代土地所有权代表这样一个过程:地租-资本-雇佣劳动……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3~234页。
从中不难看出,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转变对城市结构的时代特征及其隶属文明形态的类别具有明确的标识作用。因此,土地属性的资本化既意味着抽象的资本逻辑获得了具体的地理表达方式,又暗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前现代城市想象的强制性终结。尽管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而言,“并非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在由过去的‘社会-空间形成过程和当前由长期的历史、社会构成的地理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环境中,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美]爱德华·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9页。但是,资本之于地缘环境的野蛮改造显然打断了人们对城市文明轴线的连续编织。从“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要求“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进而按照资本逻辑“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伊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城市的社会职能与空间印象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向。与前现代社会中土地仅仅是城市交往体系的静态容器这一状况大相径庭,为资本空间生产所裹挟的现代文化-政治图景,已然将土地资源的社会属性视作决定城市存在样态不可或缺的能动因子。它与劳资结构、雇佣关系抑或财富垄断等范畴凝定在一起,进而勾勒出资本城市压迫普罗大众,以及围绕土地利益而展开的阶层对峙的混乱场景。如此一来,当下每一幅城市地图就不能“仅仅看做法律、政治或地形特征的分界图,而是应该看做争夺土地利益的策略联盟和行动的马赛克图”,[美]哈维·莫勒奇:《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地点的政治经济学》,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后者扰乱了农业社会时期单一刻板但却极端稳定的城市地缘格局,并且凭借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为日后资本主义城市体系的持续动荡埋下了伏笔。
鉴于此,因土地社会属性转变而导致的现代城市景观同前资本主义城市形态的分裂,就只是资本逻辑颠覆城市地理想象的开端。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而后者无疑折射出资本与土地所有制关系间的倒错,即城市的“空间构造是由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决定的,并非主张地理形态是事先决定的。”[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0页。在这样的情形下,自身用途已然被资本化的土地资源,势必推动以之为物理始基的城市空间根据资本生产与循环的阶段性需要做出周期性的结构调整。于是,在积极的方面,“资本主义由此制造了一个与它自己在特定历史时刻上的积累动态相称的地理景观。”[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而在消极的方面,受资本剩余生产影响的城市地缘环境,其固有的人文地理结构必然发生间歇性的更迭。它促使“位于城市日常基础设施的反复破坏与篡改中心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力量,决定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循环与代谢。至于这种兼具流动性与循环性的否定力量,不啻为能够嵌入且改变城市景观的中介。”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 in N.C. Heynen, et al.,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6,p.234.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对当前城市格局的接纳还是颠覆,作为资本生产载体的现代城市空间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主导权。与之相反,它又再度退回到同前资本主义时期相类似的暗哑状态,并任由资本的异化权力对其进行随意的操控。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分别揭示了资本逻辑与土地属性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变迁中,各自所遭遇的地理学悖论。他指出,一方面,从资本生产之于土地产权的修饰作用来看,虽然“资本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存在看成只是资本对旧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暂时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上述关系解体的产物;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这种暂时的发展过程就不过是利润的限制,而不是生产所必需的东西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本必然“竭力取消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所有权,并力求把它转交给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从而将其视为应当被资本政治权力再度打磨的异己性对象。如此一来,资本生产就陷入了与土地环境持续地融合以及对峙的怪圈当中,且不得不根据价值积累的需要反复调整它同城市格局的辩证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就土地财产之于资本积累的限制作用而言,既然“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那么以固定资本或不动产形式呈现的土地资源,则“必然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487页。这就使附着于土地之上的靜态资本,同货币自身不断实现价值增殖的动态趋势相敌对。前者作为被资本异化的活劳动在空间层面创造的地理景观,“既是过去资本发展的至高荣耀,也是阻碍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牢笼。而这完全导源于该景观的营造本身与资本突破空间瓶颈的旨趣相矛盾的事实。”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p.247.为此,选择性地舍弃或重构不合时宜的城市“遗产”并适当改变其下辖土地的实际用途,就成为资本空间性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endprint
据此可知,以土地资本化为开端的现代城市发展史,既是同前资本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断代史,又是受资本逻辑裹挟而不断自我解构的异化史。在马克思看来,与资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④这一趋势并行不悖的状况,是变动不居的城市景观及其表征的社会文化记忆,随时可能被资本的空间辩证运动所消解。在历时态的层面,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在一个时点创造了一套适应其需要的景观,而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为了适应资本积累永恒的扩张的力量,又会破坏它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景观。”[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谢富胜、李连波等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后者又嵌入社会人文地理图景的横断面,并于共时态的维度揭示出,资本主义“城市内的空间和场所重构不过是其所处的更广泛关系重组的活跃部分”。它旨在“呼应——甚至希望影响——更广泛关系的重组。”[英]多琳·马西等编:《城市世界》,杨聪婷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在这样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记忆将会不可逆转地产生错乱:以“现在”的城市风貌为分界点,它的“过去”仅仅是资本之前创造但已然被自身废弃的“过时”景观,同早已碎片化的前现代痕迹共同组成的残缺不全的桥段;而它的“未来”则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异化生产中,沦为全新的城市规划与旧有的地缘格局彼此博弈的战场或牺牲品。二者同时说明,在资本逻辑的地理辩证法当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供提取且具有历史价值的城市记忆素材。
诚然,对于城市地理而言,它“首先应当获得一种重新阅读、重新估价和重新转译的途径。其风貌与全景不仅是当前的客观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过去的遗迹。因此,通过我们的见闻,将早已消失的景象进行重新描述和创造”无疑是合理的。G.Bruno, Streetwalking on a Ruined Map,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3.然而,资本逻辑的地理想象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当无从“怀旧”的现代城市随时面临空间形象的自我崩解时,居于其上的资本霸权必然会对人类文明进行一次次辛辣的讽刺。此时,所谓城市的文化记忆不过是资本空间运动轨迹的再现。它以与资本生产相契合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为社会结构(网络组织)的基础”,而一旦“这种交换不再存在,这种网络也就破裂了。”[英]史蒂夫·派尔等编:《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与失序》,张赫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脆弱性决定了现代城市印象的易逝性。后者无法脱离货币增殖机制之于土地社会属性的地理性修饰而独立存在,因此它在历史层面能够保存的内容及其限度,均以资本的市场法则为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本连贯的城市总体记忆就在构成其物理基础的土地被资本零分碎切的过程中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由资本异化生产与货币空间周转填充的抽象世界。
二、虚拟化的资本职能与被篡改的城市契约
如果说资本异化生产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性改造构成摧毁城市记忆物理性始基的开端,那么在之后形成的“货币-空间”结构中,资本形态间的彼此让渡对城市规划方案的影响和干预,则从根本上取消了现存城市景观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造成该状况的直接诱因,毋宁是决定城市发展轨迹的职能性资本自身属性的虚拟化。它与资本为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并试图拓展有限的城市地缘空间这一目的密切相关。对此,马克思曾反复强调,“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换言之,资本对城市记忆的褫夺,旨在最大限度地构建货币及其内含的社会关系得以自由运转的抽象场域。后者“作为一个充满虚幻的整体空间……不仅与‘亲身体验的经验世界相对抗,而且还具有令人生畏的抽象性消解性力量。……它涵盖了‘商品世界与‘资本逻辑的环球战略,以及货币之于国家政治的异化权力”。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pp.53~54.鉴于此,从履行特定职能的资本形式对设定城市格局的规划方案所具有的操控作用来看,其中涉及两方面互为因果的内容:
首先,是用于营建城市基础设施或整合社会财富秩序的职能性资本,在货币循环网络中的虚拟化。这集中体现为,以银行信贷业为主要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对资本输出路径的重新定位。在当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就是,伴随着资本空间生产对城市地缘景观的持续改造,原本相对聚合的社会财富已然分散于隶属不同空间单位且被私有产权分割的差异性个体手中。如此一来,在地缘结构上支离破碎的小型实体性资本,就无法承担城市改建所需的大规模长期性投资。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77,p.296.这显然与资本不断重构城市格局的历史趋势相抵牾。结合前文所述,既然现代城市的形成与资本的空间积累密不可分,并且它始终以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为发展前提。那么,城市景观的重构就以资本生产方式的调整为圭臬。另外,在资本弹性积累的过程中,凝定于某一空间单位的特定商品部类,其价值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它在整个资本空间结构中的灵活周转。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空间结构本身却作为阻止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被创造出来。”(参见[美]大卫·哈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后者既表现为一定时间段内对资本生产形成阻滞力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又表现为商品流通所必须逾越的城市外在空间壁垒。因此,为迎合不断加速的资本增殖,而对不合时宜的城市景观进行不间断的调整与改造,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绕不开的前提。实际上,“某些资产本身就带有的规模效应,且这些资产通常为中小投资者无法染指”[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68页。这一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它恰好为银行信贷业的出场提供了最有利的契机。毋庸置疑,在目前的情形中,只有以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以国家为后盾的政治组织,才能为此提供资金与制度上的保障。于是,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就不得不作为一个神经中枢,来管理和调节资本的逐级循环。”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 1985,p.7.從而,催生了以金融信贷体系为主要特征的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置换。至于金融信贷业的资金来源,刚好是被货币循环体系均质化的区域性实体资本。而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置换无疑表明,“当实体资本的规模、数量和耐用性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加时,由资本主义演化出的更加复杂的信用体系,必将成为处理实体资本流通的关键环节。”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p.265.它旨在消除因资本地理性分散而产生的空间摩擦,并将彼此孤立的资本运行结构,纳入统一的货币价值体系。对此,马克思不无疑虑地指出:endprint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过敏现象。⑦[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441~442页。
何谓“整个机体的过敏现象”?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无疑指涉虚拟化的货币资本试图通过已然被资本化的土地,使整个城市社会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不可否认,以银行信贷业为座架的金融货币流,的确为财富增长型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大限度地聚集起了可用资本。但它却以指向未来的虚拟社会财富对关乎当下的真实城市景观的褫夺为代价。既然实体资本得以集中的前提是金融机构对未来收益的许诺,那么预期能否自我实现,就构成整个信用链条的基石。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预期的未来价格自身又取决于市场对某种类型资产的热情”。并且“人们又普遍难以抵制市场对某类资产的热情所带来的影响。”[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这就把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权交付到充满风险的资本流通领域。加之“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然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当虚拟资本的供给额大于某一区位的城市空间承载力时,“指向财富垄断的权力中心化城市,必将在财富的重压下解体。”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sod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2009,p.92.后者既是金融體系可能出现的信用危机投射于盲目扩张的城市建设层面的消极后果,又是货币资本的恶性膨胀反映在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领域的逻辑必然。
其次,是既定城市空间发展轨迹或现存社会关系框架的地理性基础,对虚拟资本流的功能性依赖。应当说,由于现代城市景观是资本逻辑空间演绎的产物,故而它没有任何机会“去讲述不同的故事,去追随另条道路。它们被强制整合进入那些设计队列的人之后的行列中。”进而,在引发自身“空间体周期多样性随之而来的闭锁”之后,又“阻隔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发挥作用。”[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也就是说,已然被纳入资本运行体系的城市空间,只能按照货币周转法则指定的线路得以建设。如此一来,“城市化过程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直接。它不需要其他制度的控制形成作为中介,”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它使全部城市位置似乎都必须屈从于自由流动的金融规律。”[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3页。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途径对金融虚拟资本的过度依赖,又反过来加剧了货币权力对整个城市社会关系的统摄。而后者,是生息资本对全部城市印象的异化。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相关章节中旁敲侧击地提道:
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的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⑦
其中涉及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预言,即城市景观的真实性将被虚拟资本的神秘力量抽空。一方面,对于资本来说,金融信贷产业和货币生息体系的出现,为理论上具有无限增殖能力的资本自身,创造了现实化的途径。随着现代信用制度的完善,“货币变成了无须黄金证明的、没有实体的象征,而围绕着这个象征性存在或者说符号,人们展开了金钱游戏。”[日]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郑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4页。他们用指向未来的利益期许彼此建立契约,并在后者假设的生产场景中推动资本向既定积累目标前进。于是,在另一方面,借虚拟资本之手在特定地缘环境中已经建设完毕的城市景观,其作为固定财产的现实性就不得不从资本未来积累的时间段中获取。而这无疑是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无法克服的悖论:由于资本累进增殖的信用链条不能被人为终止,故而能够为此时城市建成环境提供资金保证的彼时货币总额,只能再度作为城市下一阶段发展的资金储备,且被金融机构重新虚拟化。这样一来,与资本无限积累的节奏相吻合的城市规划逻辑的确具有不断扩张的前景。但后者却以城市当下和未来的真实地理景观被货币信用体系完全虚拟化为代价。于是,伴随着“虚拟的他处与他时的产生,以及凝视的商品化。这种被货币规训的的时间与空间在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就被集中起来。”A.Freidberg, Window Shopp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179.它构成职能性资本凌驾于城市空间之上的跳板,但“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且将之想象为“超现实或神秘的实体”,进而对其顶礼膜拜。[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这实际上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依托金融信贷行业而不断完善的虚拟货币体系对城市空间记忆的消解,与它对城市规划契约的间歇性篡改密切相关。作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应的共识,资本在某一时间点对城市阶段性发展轨迹的设定或干预,通常以能为后者带来相应的利益为前提。因此,转换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资本对城市空间享有的自由规划权利,同它能否实现城市社会财富持续增殖的责任并行不悖。二者构成“资本-城市”契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虚拟资本的所有表现形式,“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换言之,虚拟资本体系的维系高度依赖信用链条的完整。倘若操纵整个货币市场的银行信贷部门出现信用危机,那么用于投资城市地缘建设的全部资金序列就会发生巨大的断裂。加之宏观调控与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当今日渐式微,无法兑现最初利益承诺的虚拟资本流必将单方面更改它对城市发展愿景的设定。这集中表现为,已投入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被迫停工、未及完全改造的局部城市风貌较之先前更加狼藉,以及无法妥善解决的城市改造负面影响等等。总而言之,“这种正在发生作用的虚拟性,这种已经实现的潜在性,构成了一种盲区”。[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7页。它标志着资本逻辑对城市景观的践踏,以及对作为城市记忆地理性档案的篡改。endprint
不得不说,虚拟资本“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但这依然无法掩盖资本主义城市规划陷入囹圄的尖锐事实。此时的城市景观早已成为资本信用危机的地理性载体,它对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遭遇的悖论始终抱以无意识的接纳。因此,城市社会的记忆史只能被视为资本增殖的混乱史。后者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城市秩序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进而消解掉能够反映城市阶段性历史-地理风貌的长时段空间档案。尽管“我们的确还处于在固定的地方想象中,但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和权力是在资本簇拥的流动空间中组织起来的,其逻辑的结构与支配性正在从源头改变地方的意义和活动。”Manua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p.459.因此,当资本因随时可能出现的信用危机而变更城市契约,且被迫终止的城市改建与满目疮痍的地缘格局彼此交汇时,经验性的社会记忆就与未完成的城市设想渐行渐远。这不啻为现代社会走向集体无意识的征兆,而始作俑者毋宁是随意修饰空间的资本自身。
三、弥散化的阶级冲突与被粉碎的城市根基
无论是资本空间生产对城市土地属性的直接改造,还是紧随其后的货币形态的让渡对城市地理秩序的间接干预,实则都是以更为精致且隐蔽的手段巩固现代城市景观内长期存在的阶级剥削关系。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既然作为资本具体呈现样态的各种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那么,寓于同一城市空间内但具有不同地理定位的差异性人群,势必遵循资本“物”的尺度,被迫分散于社会等级序列的各个区段当中。这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原本呈现为二元对立的劳资冲突或阶级矛盾,将在日趋碎片化的城市日常生活图景内,衍变为个体多元空间身份彼此间难以调和的张力。
鉴于此,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政治记忆的地理性载体,城市“既是充满私人的和阶级张力的奇特混合体,又能在社会基础设施的再生产中,将个体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以及政治过程都包含在等级化的组织形式之内。”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11.进而,以空间叙事的方式,把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弥散至纷繁复杂的当代日常生活之中。而造成上述状况的直接诱因,是自上世纪中末叶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为缓解因自身恶性增殖而不断加剧的政治-经济性危机,试图在其所操控的地缘环境中寻找突破口的被动尝试。作为一个重构城市地理想象的颠覆性历史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之后的人类社会文化图景。对此,在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的棱镜中,很容易于学理层面获知以下实证性的事实: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种深层次重构,其中最显著的部分是空间修复。为努力从20世纪60年代的多种危机中复苏,努力减少破坏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城市、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构成的地理布局已经被重塑。……其相对简单的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混杂化,同时,原有的一些边界变得模糊,制造出越来越多因城区扩大或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形成的地区性城市,共同组构的多中心或网状布局。[美]爱德华·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转向以及社会地理结构的日趋离散,却混淆了原本清晰的城市政治叙事,并将之前泾渭分明的阶级关系渗透至虽构成资本异化症候但不涉及主要病灶的其它社会因素当中。从而,以转移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弱化了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的理论解释力。“阶级政治”源自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解放政治规划。根据马克思对资本剥削与劳资矛盾的体认,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分别对长期处于资本压迫,并最终有能力进行彻底革命的人群,即无产阶级给予了不同维度的定位与高度的期望。而后者与资产阶级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是无产阶级自身利益诉求的达成,又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对此,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307页)然而,随着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左翼理论家便纷纷展开对“无产阶级”乃至“阶级”概念本身的质疑。例如,英国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就认为,当今世界已然不存在一个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那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参见[美]科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38页)与此同时,匈牙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瓦伊达也指出,“当工人阶级坚决地反对其他阶级时……个体利益和阶级利益总是相符的。然而,当这一过程的实现变得具体化时,协调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就变得不可能了。”此时,纯粹的物质需要与阶级的激进需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之前高度统一的阶级成员,也随之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工人官僚开始出现,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显出端倪。为无产阶级成员“所追随的不是关于普遍合理化的权威方案和规划,而是被卷入到利益集团的社团主义之中。”(参见[匈]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杜红艳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纷纷放弃了对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定位,并进一步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他们在“激进和多元民主的规划中”,通过把工人群众重新定义为“新工人阶级”,进而在身份政治、地方性运动以及社群主义的簇拥下,将“阶级”(class)阉割为“群体”(group),从而使激进性的“阶级政治”被置换和软化为妥协性的身体政治、性别政治或者生态政治等。(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Pluto Press,1982,p.77)这就在取消自身斗争属性的同时,投入西方资产阶级右翼改良主义的怀抱。而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在否认马克思有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这一论断之后,又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矛盾已经在无所不在的潮流中从政治表达了它们自己,而且它们的影响也已全面化了,或者说跨越了阶级。城市政治不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一种附带现象。……在城市政治领域,我们发现这些新的差异是以社会空间集体消费的不平衡为基础的。”⑥[美]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3、53页。也就是说,阶级政治的消隐标志着审视城市群际关系的对象,将发生从总体的政治冲突向局部的经济冲突蜕变。而伴随着批判视角的游移,旨在彻底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运动就被意欲维护资本异化生产的消费结构调整措施所取代。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endprint
第一,从资本逻辑对城市群际关系的一般定位来看,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就是,为资本逻辑的创造性破坏力量所推动的城市空间景观的持续变迁,势必把其下辖的居民“都卷入到大规模的力量角逐之中。围绕城市的意义、城市生活的节奏和尺度,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地点与密度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一旦具有不同空间身份的差异性群体希望控制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各自携带的竞争性需要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激烈冲突。”John R. and J.R. Short,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3,pp.152~153.加之以区位为节点的城市住宅市场的运作,这些冲突必然会弥散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人群内部,并滋生出瓦解后者达成文化-政治共识的消极诱因。与之相应,资本逻辑的空间策略还把原本单一的城市居民“划分为轮廓分明的亚群体,这些亚群体占据着城市极不相同的各部分,具有不同的住宅和设施标准。这种阶级内部的分层奠定了居民内部的差异和意义的新基础。”[美]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3页。如此一来,资本城市空间同普罗大众最为重要的关系,即以剥削为核心内容的劳资冲突,就被群众内部的利益分歧逐渐冲淡了。
对此,马克思曾做出过一种解释,即“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言下之意就是说,在纯粹的经济学层面,所谓的个性或群际区分不过是资本空间生产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与以资本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旨趣的劳动分工密切相关。而后者恰好在城市辖区内部,营造出“大量的、分散的、而且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延伸以及它们不平衡或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⑥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面,关乎城市居民最根本利益的政治诉求,被庸俗化为对具有不同空间身份的差异性群体全部消费旨趣的满足。藉此,资本生产及其连带的政治组织方式就以“物”的尺度,实现了城市人群的“全体利益”。但实际上,“所谓的‘全体利益通常不过就是工商企业利益在政治上能被人们接受的变形罢了。”归根结底,它仍然无法脱离资本对城市空间及其下辖居民生活样态的钳制。[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而另一方面,资本在迎合城市不同人群形色各异的消费取向的同时,又在社会公共领域强化了主体间政治理念的疏离。从而,使原本就支离破碎的现代城市空间彻底转变为纯粹“私人社会”的集合体。其中,“人们对公众的、非个人的生活漠然置之,冷眼旁观,并使意义和价值从私人生活的领域中撤离。”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Vintage, 1978,p.133.此时,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城市主体,尚且要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尽量争取一席之地,遑论他们能够有效地形成关于城市认同的共识,进而反对异化的资本城市政治制度加诸于己的残酷剥削。而资本逻辑凭借对城市多元文化-政治生态的刻意夸大,已然使狭隘的经济诉求瓦解了普罗大众投射于城市景观之上的美好想象。此时,个体完整的城市记忆将不复存在,只有片断性的物欲诉求肆意编码。
第二,从资本逻辑对城市区间关系的一般规划来说,既然城市空间作为一种隐喻,同资本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确立(货币与商品不断流通的‘自由贸易)以及主体性(流动单子的个人主义)息息相关”,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修饰下,它必然被“描写为可牵制、可操控的空间。”[美]本·哈默:《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这集中反映在,原本统一的城市辖区被资本循环序列依次拆分为具有不同职能的碎片化空间单位。而后者通常构成隶属社会各个阶层的城市人群展开日常生活并参与政治实践的地理学边界。它们在日趋多元且更加精细的资本部类生产中,使“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页。从而,形成彼此孤立并携带明显政治分歧的社区性聚居群落。因此,城市空间中星罗棋布的社区景观,毋宁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行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促使“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模式发生了被动性变革”的结果。[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值得一提的是,阶级关系向城市社区的泛化无疑加剧了“城市人口在关乎其日常生活能否得以维系的食物、能源,以及其它商品和服务性资源的多元网络体系中的冲突与争端。”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 in N.C. Heynen, et al.,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6,p.238.于是,当城市内各个阶层的人群希望最大限度占有社会资源,并防止他者染指其既得利益时,以共同居住的社区为地理坐标的阶级联盟就应运而生了。它们是个体资源相对匮乏与资本价值绝对积累的消极产物。反映在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层面,后者“具有这样一个双重特征: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薛毅编:《现代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页。换言之,资本主义城市中不同社区的存在样态及其相互关系,通常具有“地理隔离”的属性。而寓于其中并且呈原子状分布的“孤立的居民已然发现,他们的生活业已变为一种与稳定的重复性景观的义不容辞的消费密切结合的纯粹的重复性琐事。”[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言下之意,就是当社区间的空间壁垒成为资本权力向个体日常生活渗透的渠道时,“加速的空间隔离过程可能会降低我们共同生活的能力。”[美]曼纽尔·卡斯特尔:《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它既表明货币关系对主体间天然的社群关系予以取代,又意味着城市之于下辖居民的空间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行将崩解。endprint
毋庸置疑,阶级关系向城市日常生活的弥散与泛化,折射出构成个体空间身份的地理坐标和文化-政治背景的深度错乱。尽管资本逻辑从中捕捉到规训社会人群行为方式并促使自身摆脱困境的契机,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碎片性再生产而导致的城市总体空间印象的缺失,作为资本在当代实现价值累进增殖的重要载体,城市的日常根基已然开始坍塌了。这虽然是城市空间关系的“失序”,但它更是“‘自由市場经济的特殊秩序的产物。”[英]史蒂夫·派尔等编著:《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与失序》,张赫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页。应当说,由资本对城市景观的直接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失忆,在陷入混乱的城市日常生活中最终得以肉身化。它意味着,之前的资本对城市印象的不断否定,已经转化为城市中的差异性个体对自身隶属社会文化背景的自我否定。此时,构成现代城市发展史的记忆素材就丧失了保存的必要。因为,资本逻辑为个体认知周遭世界的范围划定了天然的历史界限。而后者是他们所处的地缘环境被资本再次修改的临界点。
结语
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适用范围由平面化的一般社会结构拓展至立体性的总体城市空间,标志着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辩证运动获得了地理学的关照。而在对《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梳理和阅读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的学术前提,即“仔细检视马克思的著作,就能发现他已认识到资本积累是发生在一定地理学背景下,并且会创造出某种特殊地理结构这一显著事实。”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p.237.这无疑指认了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在特定语境当中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变迁史。然而,作为城市物理座架的土地环境、决定城市发展轨迹的规划方案,抑或组建城市社会样态的日常生活,都在资本逻辑的历史-地理性辩证法之内被异化了。它们突显出已然资本化的城市空间及其辖下居民在关于自身文化-政治定位方面的无能。试想,当城市或城市人群在与过去彻底决裂之后又无法于当下完全重塑自身的历史意义,而资本的空间生产与循环又可随意编码与拼贴碎片化的城市社会景观,如此一来,能够确立城市总体形象的所有记忆性环节就都无一例外地丧失了。
换言之,资本剥削的真正残酷性绝不仅限于它对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榨取,而是有关人类历史记忆与文明保存能力的野蛮褫夺。后者肇始于资本空间生产在城市地理格局中遭遇的悖论。为使现存的城市地缘风貌迎合资本积累与结构调整的节奏,选择性的破坏或目的性的篡改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与当下文明记忆的城市痕迹,就成为资本缓解自身危机而被迫采取手段的联带效应。于是,城市景观就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产生之地,也是矛盾被发现和被解决的场所”。它的易逝性和混乱性决定了现代资本流通空间“堪为经济变化的熔炉,堪为社会冲突的舞台。”[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页。即资本从空间的源头遏制了普罗大众形成稳定社会记忆的可能。如此一来,伴随着城市形象在个体观念中的缺失,分别指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类文明轨迹就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被人为地过滤或稀释了。它成为一个记忆的空场,滋生出历史虚无主义或政治犬儒主义的心态。
鉴于此,从历史上变动不居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城市景观中,破译资本隐性政治症候并还原马克思激进革命指向的尝试,是还原当代人类文明记忆的必由之路。Bernard Magubane,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12, 1990,p.535; Gordon Clark, “Book Reviews: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73, no.3, 1983,pp.447~449.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横断面上,凭借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反思,再次确立了阶级斗争理论之于变革当前社会不合理状况的必要性。而打破资本空间辩证法对城市地理想象划定的历史限度,不啻为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创造性运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城市景观中的重要尝试。它旨在从构成现代文化-政治体系的城市节点出发,凭借对人类记忆史领域的介入,从唯物史观的大背景中再度确认资本主义必将瓦解的可能性。故而,对资本城市记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思,可视为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以及资本逻辑三者在地理维度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