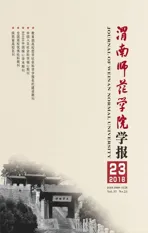归有光与王世贞关系探析
——兼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
2018-03-07张荣刚
张 荣 刚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阳 550018)
一、王世贞初论归有光及归、 王关系的发展过程
归有光出生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嘉靖四年始为苏州府生员,十九年举应天府乡试第二名,至四十四年中进士,卒于隆庆五年(1571)。王世贞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二十六年成进士,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考之归、王生平、交游以及著作等,两人关系的产生始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对归有光的评论。
据《艺苑卮言》序言以及徐朔方《王世贞年谱》可知,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评论的时间是嘉靖三十六年。而针对王世贞的评论,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注]明代陈文烛《孤屿山人项思尧墓表》(《二酉园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9册第165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中记载:“参政公卒于东粤矣……往北试,有及期,传大父封君公卒者……竟持服而归。时永嘉县令慕君才名,大加礼遇,忌者争毁,部使者购捕甚急。寓居京师,事渐白。至丁卯,病不能试也,束书东归。”参政公即项思尧父亲项乔,卒于嘉靖三十一年,而“传大父封君公卒者”则应为嘉靖三十五年春闱前之事,因此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五年礼部会试项氏均未参加。其后项思尧“寓居京师”,正与归有光所说“永嘉项思尧,与余遇京师”之事相合,《项思尧文集序》说“思尧怀奇未试”,则指嘉靖三十八年礼部试,故可知《项思尧文集序》作于嘉靖三十八年。中做出了“妄庸人”[1]21的回应。因此,嘉靖三十六年、三十八年为两人初始关系产生的时间,且此一关系也仅仅是间接的关系。
嘉靖三十八年之后,王世贞与归有光的关系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世贞有《送归熙甫之长兴令》二首,其一谓:“泪尽陵阳璞始开,一时声价动燕台。何人不羡成风手,此日真看制锦才。若下云迎仙舄去,霅中山拥讼庭来。莫言射策金门晩,十载平津已上台。”其二又谓:“墨绶专城可自舒,应胜待诏在公车。春山正好时推案,化日何妨且著书。到县斋宫留孺子,诘朝车骑请相如。客星能动郎官宿,白雪阳阿兴有余。”此二首作于嘉靖四十四年,王世贞自注道:“子与时在邑,与熙甫善,故云。”[2]478子与,即徐中行,故王世贞以诗赠归有光,应当与徐中行有一定的关系。第一首言及于归有光及第之事,慰其虽晚得一第,然其才能终有施展机会;第二首则又有勉励之意,归有光进士及第后,京师有入翰林为庶吉士的说法,而最后以年老授为长兴县令,故其失望之情或有流露,王世贞诗中“墨绶专城可自舒,应胜待诏在公车”之语,盖为勉励归氏之意,而“推案”“著书”言其仍可以有所作为,“留孺子”“请相如”则又期望归有光留意人才。
《震川先生集》有《与俞仲蔚》《与王子敬六首》篇,也记载二人关系进一步发展之事,其中《与俞仲蔚》中说道:“前奉别造次,不能达其辞。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凤洲行省矣。”[1]881此处所说则与王世贞赠诗事照应。《与王子敬六首》又道:“王元美自大名还,致彼抚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当作书院山长耳。方尔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复作行计。”[1]890归有光任职长兴,与当地大户有矛盾,遭其排挤,遂有隆庆二年明升暗降于顺德之事,归有光乞疏欲自去,然得诸相善者为劝,始赴任顺德,而王世贞即为劝说者之一,故文中有“得元美此言,始复作行计”之语。
此外,《震川先生集》中有《思质王公诔》篇,即为王世贞父王忬而作。嘉靖三十九年王忬因兵事下狱被杀,归有光此篇即作于第二年。近人林纾认为:“然震川与世贞不相能,至斥之为妄庸,何以允为吴中士大夫作,想此时世贞之名尚未大盛,而忬之名重于吴中,故有是作。”[3]129若按林氏之意,则归、王之间断不会有诗书往来之事;若认为“世贞之名尚未大盛”,则《项思尧文集序》中“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之语又当作何解释?是故,归、王间初始龃龉不合的矛盾,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也并没有使二人的关系止步不前。
由是而言,归、王关系之始末,始于嘉靖三十六年《艺苑卮言》、嘉靖三十八年《项思尧文集序》的创作;至嘉靖四十四年之后,归有光既成进士,两人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层次关系,即有着诗书相赠及往来。而两人间初始之龃龉不合,似乎已成陈年旧事而未尝再提起。必须指出的是,归、王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并非是归、王关系的全部,也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至少在归有光去世之前是如此。
二、王世贞再论归有光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的评论,除了引起归有光“妄庸人”的诋斥外,陆汝陈、陆明谟皆向王世贞写信以相责问。而正是这些责问,是王世贞再论归有光的原因之一。
陆汝陈是王世贞中表兄,其具体所责内容今不可知,然而从王世贞《答陆汝陈》中可略窥其梗概。王世贞说道:“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陆师粗及归生,非欲雌黄令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为仆见归文不多,辄便诬诋,使仆衔后生轻薄之愧。……归生笔力小,竟胜之,而规格旁离,操纵唯意,单辞甚工,边幅不足,每得其文,读之未竟辄解,随解辄竭,若欲含至法于辞中,吐余劲于言外,虽复累车,殆难其选。”[2]148由文中称归有光为“归生”可推知,此文作于嘉靖四十四年以前。就王世贞所论而言,“单辞甚工”“篇幅不足”,是归有光记家庭琐事、抒情言志之文的特征,也正是今天视为归氏代表作品的特征,而“规格旁离,操纵唯意”是此类作品的创作方法。是故,王世贞此处所论,亦并非苛刻“诬诋”之言,正如徐学谟所说:“其指摘吴中诸公与熙甫之短,亦似中窾。”[4]5168
陆明谟之事,王世贞在《书归熙甫文集后》中有言及于其事,并且在该文中王世贞对归有光有着更为深刻的论述,王世贞说道:
余成进士时,归熙甫则已大有公车间名,而积数年不第,每罢试,则主司相与咤恨,以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而同年朱检讨者,佻人也。数问余,得归生古文辞否?余谢无有。一日忽以一编掷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邪?”且谓何不令归生见我,当作李密视秦王时状。余戏答:“子遂能秦王邪?即李密,未易才也。”退取读之,果熙甫文,凡二十余章,多率略应酬语,盖朱所见者杜德机耳!而又数年,熙甫之客中表陆明谟忽贻书责,数余以不能推毂熙甫,不知其说所自。余方盛年骄气,漫尔应之。齿牙之锷,颇及吴下前辈中,谓陆浚明差强人意,熙甫小胜浚明,然亦未满语。又数年,而熙甫始第。又数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贻余者,卒未及展,为人持去,旋徙处昙靖,复得而读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论议书疏之类,滔滔横流不竭,而发源则泓淳朗著;志传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爱脱赚法,唯铭辞小不及耳。昌黎于碑志,极有力,是兼东西京而时出之。永叔虽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颇右永叔而左昌黎,故当不识也。他序记,熙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也,起伏须婉而劲,结构须味而裁,要必有千钧之力而后可;至于照应点缀,绝不可少,又贵琢之无痕,此毋但熙甫。当时极推重于鳞,于鳞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熙甫与朱生皆不可作矣,恨不使朱见之,复能作秦王态否?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辈为蜉蝣之撼不容口。当是于陆生所见报书,故无言不酬。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5]55-56
就文中内容而言,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自“余成进士”至“盖朱所见者杜德机耳”为一层含义,此时期应该是后七子唱和之时,而王世贞所见的归有光文章,“多率略应酬语”。其次,自“而又数年”至“又数年而卒”为一层含义,主要叙述了陆明谟贻书相责之事,所责内容针对的就是《艺苑卮言》中的评论。再次,自“客有梓其集贻余者”至“止毋但熙甫”,主要内容是对归有光的再论述,针对归有光不同文体作品,予以较为详尽的评述,扬其所长,摘其所短。今考之《震川先生集》,亦可以认为是中允之论,论议书疏之体与明代场屋中二三场所考诸体相近,而正是归有光所擅长的。韩愈志传碑表之割爱脱赚法,即明人所说的架空议论,而这又是明代经义时文中“凌驾”之习的渊源,归有光《詹仰之墓志铭》等即具有此种特征。最后,自“当时极推重于鳞”至末尾,似乎是对自己早年所作所为的遗憾,然而与归有光早年的龃龉不合,是自己“盛年骄气”所为,于今也没有了意义,故“吾又何憾哉”。
《归太仆像赞》[注]娄坚《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学古绪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1295册第11-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所载:“当是时,吴之以高文称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无异同,及归自留都,从其家求画像,摹为小幅,系以传赞,属予书之。”王世贞万历十六年任南京兵部侍郎,十七年六月转任南京刑部尚书,旋南归至家,其间到嘉定拜访了徐学谟,同时相聚之人有唐时升、娄坚诸人,八月赴南京任,《归太仆像赞》似乎即作于此一时期。作于王世贞晚年,也是再论归有光中重要的一篇文章。赞作为一种文体,明代徐师曾《文体辨明序说》谓:“其体有三,一曰杂赞,意专褒美,若诸集所载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是也。二曰哀赞,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者是也。三曰史赞,词兼褒贬,若《史记索隐》《东汉》《晋书》诸《赞》是也。”[6]2114王世贞所赞归有光等吴中往哲,自元末明初处士周寿谊、翰林编修高启始,凡一百一十二人,其旨意即在“意专褒美”。其序赞归有光时说:
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2]179
此文与《书归熙甫文集后》所述相比,显著的不同是只有赞美而无指摘,当然这是由文体特征所决定的。至于文中赞语,本即颂美之辞,然而却是后世争议的部分,俟后文复论。
王世贞再论归有光,与《艺苑卮言》中所论者相比,没有了早年的骄盛之气,尤其是归有光像赞序中所给归有光古文所学与成就的评价,其卓识远在晚明众人之上。归有光与王世贞为文同是以《史记》为法,然而所得不同,章太炎尝谓:“震川与凤洲争名,二人皆自谓学司马子长,然凤洲专取《史记》描摹之笔及浓重之处,震川则以为《史记》佳处在闲情冷韵。”[7]248章氏所说的“闲情冷韵”,大概指的是《史记》中的后妃、外戚传。而王世贞在赞语中的“余岂异趋”,或许是其“殊途同归”的感叹。
王世贞对归有光作品的再论述,既与其晚年对文章的认知有关,也与外部因素有关,如前文所述陆汝陈、陆明谟的责问,即是外部因素之一。事实上,在王世贞再论归有光的外部因素中,徐学谟所起到的作用是最为显著和直接的。徐学谟与归有光相友善,对归有光古文、经义时文皆有着欣赏和同情的态度。而徐学谟与王世贞为乡试同年,两人的关系为莫逆之交,徐氏尝自言,“余以怯于饮,复拙于修辞,遂不能追随公后”[8]617。
关于归、王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徐学谟在其文集中也有记载。徐学谟认为归有光古文辞“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而这一特点是“元美不尽知”的。徐学谟也对当时秦汉派的弊端提出了批判,并且对王世贞所推崇的李攀龙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徐学谟对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对王世贞的诋斥,认为归有光“未免过激”。总之,徐学谟认为归、王“皆吴中之俊,前此罕有其俪,然其言矛盾不相容如此”,因此“姑记以俟知者衡较之也”。[4]5169-5170或许是同与归、王相善的缘故,徐学谟并没有对归、王的是非对错予以评价。然而,或许正是由于同为归、王好友的缘故,徐学谟才反复向王世贞推扬归有光。王世贞尝致书徐学谟,道:“况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故当于熙甫不薄,第无由相闻耳!”[2]514以此而言,王世贞推崇韩、欧等唐宋之文,对推毂归有光是有作用的,至少在王世贞看来是如此,而从这封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徐学谟应该向王世贞推扬过归有光。
徐学谟《归有园稿》卷十九有《与王凤洲司寇九首》,徐氏在第二首中说道:“熙父文章,其用小处,尽识古人面孔,唯结构无法,间失之弱。所以吾丈前时阔略之,故特为拈出,令其一生辛苦,不至没没耳。非敢肆横议以自外于门墙也。乃今吾丈公听并观,不肯自怙其见匪直,能妆熙父,而弟亦不蒙鄙夷矣。真菩提之心哉!”[8]4此文作于万历十七年,文中熙父即归有光。观徐学谟信中所言,“前时阔略之”者,盖指王世贞所作《书归熙甫文集后》,而“乃今吾丈公听并观,不肯自怙其见匪直,能妆熙父”者,盖又指王世贞所作归有光画像赞序而言。事实上,《归太仆像赞》中王世贞所论归有光“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之语,与徐学谟所说“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又是相一致的。
归有光固为明代古文大家,然而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科举制度决定着士子的前程,左右着他们的命运”[9],归有光“八上春官”而不第的现实,使其声名在当时的文坛上远不如王世贞,徐学谟因欣赏而同情其辛苦与遭遇。是故,徐学谟不仅不遗余力地推扬归有光,而且还向王世贞推荐,以借其在文坛上的盛名显扬之,正如晚明黄淳耀论徐学谟时说道:“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龂龂不为之变,弇州晩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甫,则亦自公发其端云。”[10]738
三、钱谦益与王世贞晚年“自悔”说
王世贞晚年反复再论归有光、推毂归有光,与徐学谟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然而正是由于王世贞晚年推毂归有光,才使得钱谦益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说有了可能。
对于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中说:
当是时,王弇州踵二李之后,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径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支柱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识者谓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而弇州之迟暮自悔,为不可及也。”[11]559-560
及其论王世贞,则又说道:
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息,浮华解驳,于是乎淟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论文,则极推宋金华。而赞归太仆之画像,且曰“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矣。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未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之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如是。[11]436-437
上述类似观点,在钱谦益文集中其他篇章亦可以看到。钱氏将归、王初始龃龉不合的关系,叙述的生动形象,而王世贞晚年“自悔”说亦遂之而产生。文中所涉内容,主要来源于《项思尧文集序》《吴中往哲像赞》和《艺苑卮言》等。那么,钱谦益是如何“扬归抑王”,以及如何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的呢?
上文最为精彩生动的莫过于归、王二人关于“妄庸”的对话,这段精彩的对话源于娄坚,而娄氏原文说道:“先生尝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讥,或曰‘妄诚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闻者莫不心厌焉。”[12]11由文中可知,此处所对话之人显然不是王世贞。至于王世贞所论《艺苑卮言》的“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等语,四库馆臣认为见于《读书后·书李西涯古乐府后》,然笔者考之《读书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丛书集成续编”本以及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均未有上述王世贞所论之语。故以笔者愚见,四库馆臣大概因袭于钱谦益所说,而钱氏所言则不知其所本于何。同时,钱谦益所言“极推宋金华”之说,又源于王世贞所作《书宋景濓集后》,然而文中王世贞所极推崇的,指宋濂十二年中作文之多而已;至于宋濂作品,王世贞认为“以典实易宏丽,以详明易遒简,发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晓”[5]52,并未见其“极推”到何种程度。
然而上述内容却正是钱谦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的立论基础。通过归、王二人关于“妄庸”的精彩对话,钱谦益扩大了归、王初始间的龃龉不合,而像赞中“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则又为“弇州之迟暮自悔”做铺垫。同时,借《读书后》中王世贞自论之言,则又坐实了其晚年“自悔”。事实上,这是钱谦益笔下的归、王关系,也是钱谦益笔下的王世贞晚年“自悔”。
对于《归太仆像赞》中的“自伤”“始伤”的区别,钱钟书先生尝就此提出了较为深刻和详尽的论述,认为钱谦益以“刀笔伎俩”将原文中的“始伤”改为“自伤”,从而造成“词气迥异”的效果。[13]163-165而正是凭借“刀笔伎俩”,钱谦益构建了“扬归抑王”的归、王关系,并进而提出了王世贞晚年“自悔”说。事实上,钱谦益杜撰史事的“刀笔伎俩”,除了上文之外,也曾借助于汤显祖、徐渭等“诋毁”王世贞,如王世贞拜访汤显祖一事,汤氏尝自言:“无所相益,有以相损。因自隐避,不敢再谒尚书之门。”[14]1234对于此事清代的王宏论道:“予谓牧斋欲訾弇州而适著其美,其誉义仍也,君子以为犹诋也。”[15]409
那么,钱谦益为什么要构建“扬归抑王”的关系,以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呢?事实上,这与晚明文坛的流弊,以及钱谦益的文学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钱谦益在晚明文坛上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钱氏对于公安派、竟陵派与秦汉派皆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其中对竟陵派和秦汉派所批判则最为激烈。究其原因,正在于两派在当时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故而其流弊影响亦大。而钱谦益为文主张则是宗唐宋古文的,批判打击竟陵和秦汉派实际上与钱氏提倡唐宋古文是互为表里的。而王世贞不仅主盟文坛数十年,而且还是秦汉派的领袖,所以其“抑王”也是必然的了。而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尝力抗王世贞,因此“扬归抑王”就成了钱谦益的必然选择,正如黄霖先生所说的“借钟馗以打鬼”,黄先生说道:“钱谦益尽管连篇累牍地宣扬归有光的文章,但主要是出以‘恶乎稗贩剿贼、掇拾涂泽之流’,借钟馗以打鬼,扬归有光来批复古派,实际上他并没有对震川文章作过认真的分析。”[16]而借曾经的文坛领袖来推扬归有光,即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则是对复古派最彻底的批判。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对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有了客观而清晰的认识,归、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是由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的评价所引起的,并导致了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诋斥。然而,这种龃龉不合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也不是归、王关系的全部内容。在归有光成进士之后,归、王关系则有了诗文往来的深层次关系,可以说与初始龃龉不合的关系发生了转折。
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再论述,可以认为是归、王关系的深化,而这种深化主要又围绕着初始间的龃龉不合。王世贞再论归有光,对归氏作品有了较为深刻而详细的论述,并认知到了归有光作品的价值和地位,然而这种再论述和新的认知,则又与徐学谟等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这种再论述和新的认知,又为钱谦益“扬归抑王”提供了素材和土壤,并进而提出了王世贞晚年“自悔”说。需要指出的是,钱谦益借助杜撰或者“刀笔伎俩”,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文坛上复古的弊端,更是为了提出自身宗唐宋文学的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