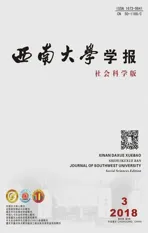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观念、实践及当代启示
2018-02-12陈洁
陈 洁
(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市 100084)
一、回归自然的设计风格
在古典时期,高雅艺术被当作奢侈品和身份的象征物,只为少数贵族所拥有,与平民百姓无缘。工业革命之后,艺术生产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成了商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潮流似有把普通大众也席卷进去的趋势。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催生了大量廉价、粗陋的艺术产品,与此同时,手工业时代的工匠被迫退出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家的灵性和艺术品的光韵在机械复制中被大大损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威廉·莫里斯的出现和他所倡导的艺术观念,在工艺美术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和态度,是人生经验的凝结和社会态度的表达,也包含了对理想生活和社会图景的构想。从威廉·莫里斯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的艺术观念的形成基础。威廉·莫里斯1834年3月24日出生于英国沃尔瑟姆斯托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家境富裕。莫里斯成长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这个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大英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走向了世界之巅。它的领土达到了3 60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全球70%,1870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62%。“整个英国站在机器生产的最前方,经济财富飞速地膨胀。科学功利主义无限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科学‘工具理性’的崇拜。”[1]但莫里斯的家族并没有在城市内居住,莫里斯6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一处坐落于乡间的大别墅:伍德福德府邸(Woodford Hall),邻近爱萍森林(Epping Forest)。他曾独自一人骑马穿越爱萍森林,并惊叹艾塞克斯河(Essex River)的美景。1851年莫里斯17岁时,随母亲一道前往于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水晶宫”国际工业博览会,当时的企业主只关心商业利润,而艺术家又对现实生活不屑一顾,因此展出的产品大都设计低劣、风格混乱、趣味低俗:“蒸汽机的机体被加上哥德式的纹饰,金属材料的产品外观被用油漆漆上木纹,纺织机器上加上了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部件”[2]。面对这一切,年轻的莫里斯表现出相当地反感。19岁时,莫里斯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为成为神职人员而学习神学。大学时期结识了正就任牧师的爱德华·伯恩·琼斯,二人结为终生挚友并于日后一同加入拉斐尔前派。牛津生涯使莫里斯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为爱好中世纪的一切艺术、设计和建筑。22岁时和伯恩·琼斯结伴在法国北部徒步旅行,遍访了哥特大教堂,也发出了类似“搭乘令人作呕的、充满硫磺味道的、噪声极大的火车是一件可憎的事情”[3]的感慨。返英后莫里斯和伯恩·琼斯一同参与了乔治·埃德蒙大街的哥特复兴建筑工程。期间结识菲利普·韦伯,三人交好并一起开创了工艺美术运动。
从莫里斯的成长经历中可见,莫里斯的家庭既不是在工业革命中得益的暴发户企业家,也不是受剥削压迫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使其在开创工艺美术运动时,得以理性地分析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弊;而在英国城市化的浪潮中举家搬迁到乡间,使得莫里斯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大自然的环绕中成长,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莫里斯强调简洁和回归自然的设计风格,以及他对机器抵触情绪的来源。
莫里斯把强调简洁和回归自然的设计风格付诸了实践,最值得称道的案例就是红屋的设计。红屋是莫里斯的婚房,莫里斯希望红屋成为一个理想的生活家园。他认为当时市面上的家具与装饰都过于矫揉造作,因此自己制作了所有的室内物品,所有的家具器物和陈设都按照中世纪风格逐一设计制造,蚀刻玻璃花窗、壁画、挂毯都取法古代教堂。红屋的建筑装饰效仿13世纪的传统,强调简洁、自然之美,制作精致温厚,强调艺术统筹指导下的调和的设计与手工艺之美[4]。红屋把高蹈的艺术引入到了日常起居的设计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成为工艺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
尽管红屋的设计主要取法古典传统,但以自然、简洁风格抵制工业时代艺术的庸俗粗陋,无疑具有先锋的意味。莫里斯以自己工业美术设计观念回应时代、社会,他所采取的回应方式属于“反省性的反映”,类似于中国的山水画。中国的山水画“想超越社会,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5]。莫里斯的设计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艺术趣味,也包含对社会状况的反思和干预,表达了他的人文设计理念。
二、“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
人性的自适、健全,是许多艺术家所追求的,并力图融入他们的艺术表现中。莫里斯的人性和社会观念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等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的普遍使用不仅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生产条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6]。“当时的劳动条件比欧洲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凄惨。每天工时长达12至14小时,工厂的门窗都经常上锁。五、六岁以上的儿童被雇来当童工;他们的工时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在1802年仅仅缩短到每天12小时。在1833年有6.1万名男人、6.5万名妇女和8.4万名18岁以下的儿童在纺织厂劳动。1814年以前在矿井发生的事故都无人过问。”大步向前的经济发展把人文情怀抛在脑后,并影响到艺术设计,市面上的产品大都“设计上或是软弱无力,或是粗糙拙劣;实际上所有的工业艺术都是装饰过度,庸俗不堪”[7]。资本主义的拜金精神与利益崇拜,为莫里斯所不屑,他意识到工人的生存境遇与工业艺术的现状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把目光投向了饱受压迫的工业无产阶级,提出了“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
莫里斯所提出的“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其内容为:“人人都应该有工作做,这是正确而必要的:第一,做值得做的工作;第二,做高兴做的工作;第三,做条件保证下的,既不致过分疲劳、也不过分紧张的工作。”关于人人做“值得做的工作”,莫里斯认为劳动者被压迫从事苦役般的劳动、贫困、失业、环境恶化等都导因于“竞争的商业在用无限的工作制造无用的东西”,倘若社会不去做那些不值得做的东西,一切矛盾便可消解;关于人人做“高兴做的工作”,莫里斯认为存在一种不变的“人的天性”,人们“劳动的天然安慰”就是这种天性,人的一切艺术活动都出于这种天性[8]。莫里斯认为:“对于工人来说,从前工作没有分工,心灵手巧的工匠熟知生产的每道工序,作品从设计到完成都是工匠思维的结晶,充满了很多人性的东西:希望、快乐、恐惧……”[9]因此,他希望每个工人都成为艺术家,工人在创作每个作品时,作品中都包含了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每个作品都与众不同,而不是工业化的简单加工复制。莫里斯提出的“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着眼于把工人从资本和机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的艺术化来保障人性的舒张和艺术的品位。
莫里斯对艺术所持的人性立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充满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怀,试图以之解决工业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他提出的“艺术与劳动混合”的主张,把大众纳入工艺美术运动的思考中心,以大众为艺术实践和艺术享用的主体,形成了自己的大众艺术观。在同代艺术家以厌恶的心情远离陷入贫穷境地的人们,把自己视为上等人和美的传播者时,莫里斯却提出艺术必须是“为人民所创造,又为人民服务的”“要不是人人都能享受艺术,那艺术跟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不仅提倡艺术为大众所享受,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1861年借红屋完工之际,莫里斯在母亲的资助下,与福德·马多克斯·布朗、伯恩·琼斯、罗塞蒂、韦伯一同成立了“莫里斯、马歇尔与福克纳商社”(MMF)。MMF商社的成立宣言的概略中提到:“所有的制作活动以商业操作付费。但,商会目的是经营优良的装饰,所以商会的制品的美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价位——价位远比想象的便宜”。莫里斯受拉斯金的“艺术经济”的影响颇大,认为质量上乘和能够持久使用的原创作品,只要拥有一件便可持续性地使用,不需更换,因此即使最初的价格并不低廉,但最终仍会使它们变得“便宜”[10]。莫里斯对于产品的材料要求货真价实,对于产品的工艺要求精益求精。并且,莫里斯也非常认同拉斯金的关于制造商在纯粹的商业责任之外还有责任的观点,把塑造公众的趣味作为最终的目标指向。他在1880年的演讲《生活的美》中提到:“教育大众……以至于我们可以以适当的价格愉悦地购买商品装饰生活;愉快地卖掉商品,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价格和工艺的合理引以为豪;心情愉悦地工作,从容地制作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商品。”[11]在莫里斯的大众艺术观中,创作、享用、教育三位一体。他认为,艺术不是一群孤芳自赏的艺术家在小圈子内的小打小闹,而是属于社会大众的,是可以在社会上为大众起到教育与引导作用的。艺术不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在通过劳动的过程当中,便可以感受到艺术的愉悦。当人性不再受到任何的压迫时,人性便能获得释放,人性中蕴藏的智慧与真善美便能得到展现。这种相信大众的本性,并把艺术归还于大众的思想,既是对资本、机器主宰工人、艺术的一种反驳,也开拓了工艺美术的新路向。佩夫斯纳曾提到:“我们应该把下列成就归功于他,即一个普通人的住宅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一把椅子或一个花瓶再度成为艺术家驰骋想象力的用武之地。”[7]工艺美术进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就赋予了大众创作、享用艺术的权力和机会,并赋予了艺术以人民性。
三、莫里斯的困境与当代启示
莫里斯的艺术观念,着眼于回归自然、尊重人性和服务大众。针对莫里斯的艺术观念,后人给予了很多名称,包括情感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甚至空想社会主义。显然,莫里斯的艺术观念和实践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莫里斯出身于中产家庭,曾在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学习,所交的朋友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户人家子弟,这些成长条件使得他的艺术观念既带有启蒙色彩,又多少有些理想化——尽管他的目光是向下的,为工业时代的大众生存状况而忧心忡忡。他提出的“艺术与劳动混合”主张,期望每个工人都成为艺术家,在现实中难以真正实现。因为莫里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工业时代的工人数量,远远大于中世纪的工匠数量。而这些工人们,如果没有了机器的诞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不会成为工匠。成为工匠需要的是技艺,一个毫无基础的门外汉,需要时间与精力,甚至金钱的投入,经过学习后,才能成为一名工匠。但工业时期选择成为工人的大多数人,受到金钱或能力上的限制,并无法享受这般“奢侈”,他们需要的是立即拿到工资换取粮食,他们需要的是迅速地投入工作维持生活。工业革命也许迫使他们在没有窗户的工厂中重复着毫无生趣的工作,却也给予了他们一个低门槛的谋生方式。
莫里斯的一些观念并非没有可商榷的余地。他在艺术上无比推崇人性的高度,但人性本身是否绝对崇高?又或者说,人性都是普遍一致的吗?人与人的差异性是否也会相应反应在人性之上?“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思想与“人人生而有罪”的基督教思想的矛盾,正体现了人类对于人性的把握上意见相左。盲目地相信人性解放的力量,也许仅仅是上层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随着释放人性所产生的无法预计的连动后果,也不一定是精英分子所乐见的。
莫里斯走向大众的艺术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有时甚至需要妥协。1870年,莫里斯公司为了进军家居装饰市场,暂时放弃了教育大众的目标,采用了市场流行的几种元素,加以参考学习;1876年10月,因为靛蓝色的提取存在问题,莫里斯最终放弃了长时间的自然染色系列实验,而选择了暂时使用现代的化学染料[12]。莫里斯的言行不一受到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质疑,他们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伪善的表现。罗塞蒂就曾嘲笑莫里斯从来都不施舍乞丐[13]。这是事实,莫里斯从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更想去消除造成行乞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帮助乞丐维持其行乞生涯。但梦想越宏大,面临的苦难也越艰险。莫里斯晚年写作的《乌有乡消息》中,勾画了一个与工业革命初期完全不同的21世纪的英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和谐相处,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一切社会的丑恶与压榨都消失殆尽,一切都建立在人的反思与全面发展的自觉之上[14]。莫里斯在现实中未圆的梦想,似乎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实现。莫里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中推行时困难重重,虽无法彻底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工作状况,但仍然有一些追随者,因为“其妥协方案下的产品符合了低一层次的中产阶级,其理想产品则符合了具有一定文化层次和某些附庸风雅的人群”[12]66。
莫里斯对于现代设计和社会主义理想所做出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他的艺术理念和立场,对于当今社会亦有借鉴的意义。孕育莫里斯思想的维多利亚时代,与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尽管相隔久远,但人人分享艺术的问题同样存在。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后进国家抓紧机遇,以“金砖五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加大发展的力度,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加重信息化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建设比例,力图在大数据时代抓住机遇,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众对于信息产业普遍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产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扁平化,逐步实现阶级的平等。但与此同时,艺术文化却再次匍匐在迅速发展的技术脚下,人云亦云的扁平化平面设计,不伦不类的新古典简欧风格家具,哗众取宠又肤浅低俗的都市建筑,都表明了人的审美趣味又一次被技术的更新迭代所戏弄。人类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而创造出信息技术,却在不知不觉中越发地受制于信息技术。现代人“奴隶般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所做的一切全是无用的。人创造了征服自然的方法,但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本身。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机器的奴隶”[15]。艺术的个性、光韵在信息技术时代被进一步磨损。
莫里斯相信大众的本性,并把艺术归还于大众的思想,在当今的互联网扁平化社会中正在兑现。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许多曾经坚实的屏障堡垒:知识众包的维基百科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难度,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个人都获得了发声的机会,3D打印技术的实现颠覆了制造业的思维方式,人民专车和民宿出租的横空而降把共享经济的概念推到了发展浪潮的最前端。曾经被职业、身份和年龄所明确划分归类的社会族群,而今被重新打乱,并以一种无序的随机配对方式进行重新组合与互相碰撞。新技术与新概念的层出不穷和速度之快,使得法律与行规的制定远远滞后,也令我们得以目击种种社会乱象与奇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也许正是人性得到部分解放后的真实状况。但是,互联网时代没有让所有人获得均等的享用机会。先于众人掌握了互联网技术与思想的人们,利用信息技术迅速地聚集财富;而没有占得先机的中产阶级,也因为拥有快速习得互联网技术的能力(会利用网络)与资金(买得起电脑或手机),紧紧跟随互联网大鳄们的动态,时刻更新工作的概念与生活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扁平化社会的设想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他们切切实实体验到了,也享受到了众包知识和分享经济的甜头。但需要警惕的是,科技的进步,是否在同一时间内,垫高了底层人民进入市场竞争时的门槛?莫里斯所提倡的审美追求,被众多史学家评论为奢侈消费的审美。而信息时代的所谓公平和平等,实质上也是建立在拥有网络的前提上。那无法获得网络使用权的人呢?他们的平等与公平要如何申诉?作为一个盈利的商业机构,莫里斯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使用了资本主义的盈利方式,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则应该时刻把欠发达地区群众不忘于心,通过政府的力量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来。只有到那个时候,所谓的“扁平化社会”才能名副其实,对于扁平化社会的讨论才有实质意义。
今天的信息时代,许多看似快捷方便的高科技概念,仍然需要许多劳动人民的支持才得以运转。就以快递为例,如果没有了开着三轮电动车穿梭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快递员,在大数据调度下的科学物流分配仍然无法解决送货上门的问题。但作为物流链中关键一环的快递员,能够彻底理解整个物流分配的逻辑与规律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为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分析其所带来的价值意义时,如果过于关注工作者是否理解其工作的原理和逻辑,则似乎有些狭隘和吹毛求疵了。至于劳动的过程是否带来愉悦,劳动如何获得艺术愉悦感的问题,我们如果把“艺术”的范畴稍加扩大,而不仅仅局限于“美”的表现,那么,大部分的工作熟能生巧后所形成的一套外行人无法掌握的“行业秘诀”,而行家们高效熟练地完成工作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
莫里斯说“如果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艺术,那艺术跟我们有何相干?”,这句话换到今天来说,可以转换为“如果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互联网,那扁平化社会跟我们有何相干?”机器和技术的更新迭代对于人性的侵蚀实际上并不需要过多担心,因为人类的审美趣味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反,它有着自我更新的能力。更值得提防的应该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抛弃一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只在中产和上层社会发生的扁平化社会,充其量也只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如果说莫里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因为其精英身份和公司的商业性质而无法得到彻底实现,那么在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扁平化信息时代,这一切并不遥远。
参考文献:
[1] 于文杰,杨玪.按照传统的方式重新设计世界——论威廉·莫里斯情感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念[J].学术研究,2006(1):102-108.
[2] HENDERSON P. 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M]. Great britain: Jerrold and Sons L.t.d.,Norwich,1967.
[3] MORTON A L.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Morr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3:8.
[4] 高茜.威廉·莫里斯的红房子活动研究[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1):77-80.
[5]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
[6] 朱永春.从现代艺术运动中的四个课题看威廉·莫里斯美学思想[M].美术观察,1999(3):74-77.
[7] N·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M].北京: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1987:1-7,25.
[8] 威廉·莫里斯.艺术与社会主义.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90-98.
[9] MAORNS W. On Art And Socialism[M]. essays and lectures, art wealth and riches, London:John Lehmann Ltd.1947
[10] 小野二郎.ウィリアム·モリスーラディカル·デザインの思想[M].东京:中公文库,2011改版(1992初版).
[11] MORRIS W. The Lesser Arts[C]//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 XXII,1910(5):22-23.
[12] 麦静虹.莫里斯的商业理念——从《威廉·莫里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设计和企业》谈起[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1,9(2):61-66.
[13] 威廉·冈特.拉斐尔前派的梦[M].肖津,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62-3.
[14] 高振平.威廉·莫里斯的启示[J].现代装饰,2015(2):133-134.
[15]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