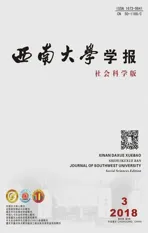骗取贷款罪:反思与限定
2018-02-12欧阳文星
郝 川,欧阳文星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市 400715)
一、立法背景及司法争议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金融业务所渉领域不断扩大,随之金融欺诈行为也日渐增加,严重危及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 123亿元,而刑法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对此却无能为力。原因如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证明;二是由于刑法规定的空白,对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即使造成贷款的重大损失,也不能以犯罪予以处罚。以银行为首的金融部门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相关会议上就大力提倡增加和扩宽关于金融犯罪的条文和条件,认为“有必要将刑法对于金融风险的‘防御战线’前移,对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金融欺诈行为予以犯罪化,以构建‘截堵的构成要件’,严密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1]。基于此,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以骗取贷款行为具有危及金融机构贷款利益的社会危害性将其入罪无可非议,然而法的另一边即是自由,刑罚较之其他制裁措施更为严厉,不可轻易发动。刑法对于骗取贷款罪的规定看似简单明确,然而,司法实践理解不一。例如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用途作虚假陈述,但未造成贷款风险或者损失的,司法实践对此判决并不一致,既有有罪判决,也有无罪的裁判。因此如何理解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以及欺骗手段,仍须考验法适用者的智慧。另外对于该罪的“造成重大损失”等的认定也存在诸多分歧,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二、欺骗和多次行为的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犯罪。可是对于何为重大损失以及情节严重,理论和实践对此理解不一。鉴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此进一步细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因而司法实践对于采取欺骗手段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达到立案标准的,应予以追诉;然而,对于采取欺骗手段取得贷款100万元以上的,在何种情形下成立犯罪以及多次骗取贷款的理解却有不同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申请贷款时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没有形成贷款风险,则行为人不应构成本罪”[2]。也有学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的认定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应站在刑法的高度来看。……本罪中的‘欺骗手段’应达到足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程度”[3]。
学界争议不断,同样,司法实践对案件也处理不一。(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判决在一审认定被告人邓宏构成骗取贷款罪后,虽然行为人实施了骗取银行贷款行为,但事后由担保公司全额偿还,并未造成任何损失,依法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对被告人作出了无罪判决。(2014)川刑终字第617号判决,对于类似行为却做出了有罪认定,认为担保公司汇通公司代其向农发行旺苍支行偿还贷款本息,挽回了银行的损失的情节仅为量刑情节,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不影响骗取贷款罪的成立。
罗克辛教授明确指出:“在刑法中不存在没有行为不法的结果不法。”[4]仅以贷款损失或者贷款危险是否发生为骗取贷款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将导致不合理结论的出现。行为人稍有瑕疵的欺骗行为,都可能被错误地评价为骗取贷款罪,这明显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并非所有欺骗行为都成立骗取贷款罪,欺骗行为是一规范的要素,需要根据某个特定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违法性意味着行为通过规范违反造成法益侵害。这样的违法性概念,不是要否定法益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刑法只有在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达到了违反行为规范的程度时才能实施惩罚”[4]。保护法益是刑法规范的元点,“行为有无价值,取决于其所追求的事实、状态、结局有无价值”[5],至少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具有行为无价值,即有法益侵害或者危险的行为才能进入刑法立法者的视野。
将什么行为作为禁止对象,是由刑法的目的决定的。换句话说,某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取决于是从什么目的上来说。刑法规范服务于保护法益的目的。利益是目的指向的对象和内容,无论是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者还是结果无价值论者都承认,刑法是保护利益的,而认清犯罪保护法益是正确理解犯罪性质的前提。对骗取贷款罪本质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其保护法益的洞察,唯此才能合理界定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保护法益是“金融机构对贷款资金的所有权”
由于骗取贷款罪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些学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认为,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金融管理秩序不是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和司法都将对贷款资金所有权无任何风险的欺骗手段获取贷款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说明此法条为裁判规范而非行为规范,这恰好回应了否认金融秩序为骗取贷款罪的保护目的之判断立场。
如果认为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那么凡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均应定罪。但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并不认同。在立法过程中,“银监会建议将该罪由‘结果犯’模式改为‘行为犯’模式,以是否实施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不是以结果作为构成要件。即以‘数额巨大的’和‘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骗用贷款罪’成立的要件”[6]。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并未采纳该建议。同样,司法也认为仅有骗取贷款行为不成立犯罪。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对于确实设定足额担保等确保贷款资金安全的骗取银行贷款行为的,也并未按犯罪处理。
我国刑法并不处罚所有的以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的行为,因为“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7],不能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我们可以将“具体犯罪的定义上规定更加严厉的行为规范,而在裁判规范上并不一定将这些行为都入罪”[8]。对于骗取贷款,虽然立法者规定了骗取贷款罪的行为方式为欺骗手段,但对应否将所有欺骗贷款的行为纳入刑法之中仍心存犹豫,以至于骗取贷款罪的刑法规定并未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指引,这里两者存在着分离。
第二,个体骗取贷款行为本身不具有侵害金融秩序的危险。
犯罪构成要件是刑法目的的体现。作为法律的刑法也不例外,目的也是刑法的创造者。刑法中每一个条文,其产生都源于一个具体目的,也就说立法者规定具体的犯罪都是基于保护特定法益的目的。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是为了实现刑法的目的,可以说具体犯罪的法益保护目的是正确适用构成要件的指南。
骗取贷款行为会对金融安全的危害是认定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为金融秩序的逻辑起点。金融管理秩序并不会受个体骗取贷款行为的影响而造成混乱。换言之,个人骗取贷款的行为并不会使得整个金融管理秩序遭受损失或者侵害,因而,金融管理秩序不是骗取贷款罪的立法目的。
第三,金融秩序不属于刑法上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
关于集体法益和个人法益之间关系的认识,刑法学界主要存在着一元的法益学说和二元的法益学说的争论。一元论认为,个人利益是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集体法益不过是个人法益的衍生,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二元论认为,集体利益与个人的法益一样,在刑法中具有独立的地位。“集体法益的重要性、集体法益的独特性和提前保护的有效性,决定了刑法对集体法益予以单独保护具有必要性。……如果完全否认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会导致刑法无力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如果无限制地承认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会使得刑法演变为防范未来风险的工具,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被忽略,法的安定性被消解。……实际上,刑法上一直存在着无法直接还原成个人法益,但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需要刑法加以保护的共同利益,对于社会生活来说,这些共同法益本来就具有重要性。”[9]也就是说,不可分割性及其根源上的特殊性是需要刑法保护的集体法益的一个重要特征,如环境犯罪、生态犯罪等。事实上,当前我国金融秩序的价值选择并非是全体人的生活利益,而是重视金融机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的保护,轻金融关系相对人权益的维护,目前的金融秩序是为了金融机构的个人法益而存在的。因此,可以说我国的金融秩序具有可分割性,且能还原为个人法益,不具有刑法上集体法益的特征。另外,金融经济发展靠竞争,将金融秩序设置为刑法上保护的法益也会影响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的行为仅给特定的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不致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更谈不上侵害到金融管理秩序。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机构贷款对贷款资金的所有权”,因此将骗取贷款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明显不妥,侵犯财产罪那一章才是其应然之归宿。
(二)欺骗行为的性质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成立骗取贷款罪,表明了进一步扩大入罪处罚范围的刑事政策动机。然而犯罪本质是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因此,是只要行为人实施骗取100万元以上贷款即行为一律入罪,还是必须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才能认定为犯罪,学界观点不一,司法实务也一直饱受困扰。孙国祥教授认为,“将欺骗贷款罪的最低入罪标准限定为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化”规制模式决定的”[2]。
笔者赞同孙国祥教授的观点,但认为其理由欠妥。因为虽然在我国法律对犯罪规定是定性加定量“二元化”规制模式,但不乏仅行为即可成立犯罪的行为犯和抽象危险犯之规定。
第一,从可罚的违法性角度看,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本身侵害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所有权的危险性较低,未达到值得刑法处罚的违法程度。
犯罪是违法行为,但并非所有的违法行为皆是犯罪,违法行为成立犯罪须其违法性达到一定量的程度,也就是说,达到以刑罚为必要的可罚的违法性。总之,“各种犯罪,均已预定着一定的严重违法性,行为即使该当于犯罪类型(构成要件),但如果其违法性极其轻微(琐细的违法行为),从而未能达到法所预定的程度时,犯罪不能成立”[10]。
不要求具体危险结果的单纯骗取贷款的行为,未达到成立犯罪所要求的违法程度。从立法角度而言,单纯行为成立犯罪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本身具有较高的危险性被刑法禁止。例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二是保护法益较为重要,一般为超个人法益的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自身的法益侵害危险性低,且保护法益是个人法益,不具备上述的特征,因此成立犯罪须借助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使行为人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
第二,虽然司法解释未有足以危及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所有权的规定,但并不能否认其为具体的危险。因为法律上规定的“足以……”不是认定具体危险犯的唯一标准,即使刑法无“足以……”的表述,也不能否认法条对应的罪名为具体危险犯。例如,放火罪虽未有“足以……”的规定,但司法实践认定放火罪,具体危险为构成要件。
骗取贷款罪法条表述的后半段规定“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为入罪标准。从对骗取贷款罪的规定来看,即便有欺骗行为,但在不出现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刑法上也能容忍该行为。立法者规定了行为之外的足以影响不法的条件,也就是欺骗行为的对象为100万元以上贷款法益侵害具体危险形成时,行为才在刑法意义上应受处罚。
综上,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利益,作为骗取贷款罪处罚根据的危险,应该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也就是欺骗行为所导致的潜在危险现实化,达到了可罚的违法性程度,对引发侵害法益的行为才能进行处罚。这里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和资金运行并不会造成任何风险的多次之外的欺骗贷款的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骗取贷款罪的行为。犯罪的本质为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任何一种行为如果没有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就不构成犯罪,这就形成一种硬约束。
第二,离开了行为的时空环境,仅根据欺骗行为本身往往无法得出是否具有侵害法或危险的结论。虽然行为人都使用欺骗手段从银行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贷款诈骗成立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具有利用意思和排除意思,而骗贷行为人仅具有利用意思。因此,贷款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行为实施的同时,侵害法益或者危险也随之出现;而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因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并不会随之相伴而生。
仅根据客观的欺骗手段来确认是否构成犯罪,可能会出错。例如,行为人虽然采用了导致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的欺骗行为,但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担保,这时贷款资金并无风险。骗取贷款罪的目的是保护贷款资金的所有权,那么,行为人即便实施了的较强欺骗程度的行为获得了贷款,因不具有贷款资金,无任何风险,不构成犯罪。
(三)多次欺骗行为的认定
司法解释规定,以欺骗手段多次取得贷款作为骗取贷款罪成立犯罪条件之一。对于多次违法行为入罪的根据为何,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多次违法行为反映出明显的危险性格,刑法明确以客观行为的次数为基础设定刑罚而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11]。也有论者认为,由于违法行为多次反复,导致了违法的数量积累变化成为犯罪的质,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反映了违法的量的积累到犯罪的质的变化过程”[12]。对于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问题,也有论者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解释,“尽管每次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但是多次累计相加就有可能触及犯罪的红线,此时,刑法是将多次违法行为作为整体,综合评价其社会危害性程度的”[13]。
笔者认为,事实并非上述如此。首先,人身危险性不能成为定罪的依据。多次欺骗行为作为骗取贷款罪的入罪条件,当然不能把其所体现的人身危险性纳入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下进行考察。其次,从量变到质变的学说无法解释量变到质变的根据,缺乏一个肯定的对特征的描述,无法确立一种独立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一标准过于模糊,故不具有实际的效用。笔者认为,犯罪是违反规范,进而侵害法益或者危险的行为,多次欺骗的违法性主要由行为的多次予以体现,也就是说此时法益侵害性是通过欺骗行为的次数来说明,而不是行为本身,行为的多次使违法性升高到可罚的程度。作为违法性提供实质根据的多次,当然属于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的要素,需要行为人对欺骗行为多次有认识。
立法将欺骗行为的多次纳入构成要件,恰恰是一种以警示人们远离该类不法行为类型,之所以刑法以构成要件的形式将其类型化,是因为这种被禁止和否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代表着是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换句话说,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多次”实施的行为达到了刑事可罚的程度。因此,以多次骗取贷款行为为成立犯罪要件的,要求各个骗取贷款的行为不应是犯罪行为,而只能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各个骗取贷款的行为均未造成20万元以上直接损失或者未骗取100万元以上贷款且达到具体法益侵害的危险状态。
骗取贷款罪的多次犯没有未完成形态存在的空间。相比其他类型的骗取贷款罪而言,多次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没有贷款数额和直接损失的要求。如果在认定多次欺骗行为时将未完成形态的欺骗行为也视为一次骗取贷款,则多次骗取贷款的入罪条件会变得更为宽松,刑法打击面有扩大之虞,也无实际必要。
三、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的认定
如果说《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在当时并没有把握好刑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应该有的尺度而刻意放宽入罪条件,那么经过十年的司法实务和社会发展,我们更加应该理性分析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的性质。
(一)“重大损失”属于归责于行为人的客观处罚条件
由于刑法明文骗取贷款行为在“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才能成立犯罪,对于这种“重大损失”在具体犯罪构成当中,属于何种要件,处于什么地位,难免有争议。笔者认为,这里“重大损失”属于归责于行为人的客观处罚条件。
客观处罚条件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不明确,不同的学者在使用时所指内涵并不相同。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属性和体系性地位,刑法教义学上有三种主要观点:(1)与违法、有责无关的独立的处罚条件说;(2)独立于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之外的犯罪成立条件说;(3)属于违法要素说。
柏浪涛教授认为,客观处罚条件是一种与违法、责任无关的单纯处罚条件。因为,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处罚条件之一的结果表现为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危险,但客观处罚条件并非违法要素,因为其非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化的结果[14]。笔者同意其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是与违法、责任要素无关的独立处罚条件。
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属于归责于行为人的客观处罚条件。理由如下:
第一,骗取贷款罪中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骗取贷款中的欺骗行为并不能自然地、直接地导致重大损失的结果。从类型性角度看,骗取贷款罪中欺骗行为并不蕴含造成贷款资金重大损害的危险,重大损失的出现往往在行为人意料之外,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也就是说,重大损失不是骗取贷款罪构成要件欺骗行为类型性的危险的实现,是一种偶然结果,在行为人认识之外,不是构成要件要素,属于一种客观处罚条件。
第二,重大损失应是行为人引起的结果,与行为人无关的结果不能归责于行为人。
重大损失的结果与骗取贷款中的欺骗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将贷款资金的重大损失结果归责于欺骗行为是有疑问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行为人欺骗行为之后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以欺骗手段获得贷款违反刑法规范,刑法要惩罚的毕竟是在法律上与某一结果相联系的人,这样行为人将重大损失和欺骗行为共同决定的违法归责于行为人才合乎情理,否则,归责结论不仅缺乏公正的基础,也达不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既然成立犯罪条件之一重大损失始终受归责的制约,将重大损失视为单纯的事实的探寻并不妥当。因此,由被害人自身造成的重大损失不能归责于行为人,也就是其并非骗取贷款成立犯罪条件的“重大损失”。司法实践中,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怠于行使诉权,以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导致贷款资金损失的,因和行为人无关,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被害人的作用和犯罪成立与否有关,被害人的“自我负责原则已然被提升为法哲学的基本原则”[15]。被害人应该对结果的不发生负责,乃是决定刑事归责的重要标准。
金融机构有采取措施自我负责的义务。“由于受害人的自我答责已经切断了将引发结果的举止客观地归属于他人的链条,因此,他人到底是故意地还是过失地做这些事情,都是根本不重要的。”[16]因此,即使他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金融机构并未穷尽方法保护自己利益的不作为所导致的结果不应归责于他人。
(二)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计算的时间结点
重大损失是骗取贷款罪的追诉标准之一,对于认定犯罪至关重要。然而,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形成的时间较为模糊,以至于认定重大损失的时间难度较大。另外,由于贷款损失数额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裁判时应以何时为依据来确定最终损失数额存在不同见解。
笔者认为,逾期还款的数额不是骗取贷款行为造成的损失,金融机构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产生的未能偿还的贷款本息,才是骗取贷款行为造成的损失。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相关规定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时间明确为金融机构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6〕23号)文,未将逾期还款情形认定为损失。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发〔2001〕416号)对贷款“损失”明确定义为:“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由此可见,该《指导原则》很明显是要求金融机构首先履行民事追索义务的,在通过民事追索手段不能实现债权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贷款损失。逾期未还款情形下,“直接经济损失”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其次,如果被害人没有尽到自身保护法益的义务,法律就没有必要对其法益予以保护。这是因为:第一,刑法作为预防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本身就不应该被任意采用。被害人如果有能力在动用刑法手段保护其法益之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或确实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此时刑法的介入才具有意义。第二,金融机构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履行相应的职责,不仅可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也为司法机关对行为人骗取贷款行为进行刑事追责提供了证明。
重大损失数额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未给以明确答案。当前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借款人与金融机构协议的还款日期为限计算造成损失数额;第二种观点,以公安机关立案时点计算造成损失数额;第三种观点,损失数额的起算以公诉时点为宜;第四种观点,以法院一审宣判前借款人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数额。”[17]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法院裁判时对于重大损失的认定应以立案为时间结点。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关于立案须以犯罪事实存的要求。从立法目的看,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为金融机构对贷款资金的所有权,必须以行为人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作为犯罪的依据。因为重大损失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是限制刑罚发动的。因此立案前,已归还贷款,没有造成2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以借款人与金融机构协议的还款日期为限计算造成损失数额明显不妥,以立案时为计算点,才能构成犯罪并固定法益侵害的结果,进而区分骗取贷款罪的罪与非罪。
其次,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把公诉前法益恢复的事实看作成立犯罪后的从宽量刑情节,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比如,《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后,以法院一审宣判前借款人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最终损失数额,可能会导致“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和诉讼过程中最后将作为不构成犯罪处理,办案人员可能承担错案的不利后果,如此束缚办案人员手脚将影响对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有悖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18]。
参考文献:
[1] 陈洪兵.骗取贷款罪的准确适用探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38-143.
[2] 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中的三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12(5):38-44.
[3] 靳丹青,郭路明,李娜,等.浅谈骗取贷款罪及立案追诉标准[N].山西经济日报,2011-07-31(7).
[4] 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法益观[J].中外法学,2011(5):944-957.
[5] 周光权.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J].中国法学,2012(1):175-191.
[6] 孙铭.“行为犯”模式核定骗贷罪[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6-23(13).
[7] 周韶龙.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2):111-120.
[8] 王永茜.论刑法上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分离[J].清华法学,2015(5):145-160.
[9] 王永茜.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J].环球法律评论,2013(4):67-80.
[10] 木村亀二.刑法の基本問題[M].東京:有斐閣,1979:197.
[11] 刘德法,孔德琴.论多次犯[J].法治研究,2011(9):83-93.
[12] 李恩民.多次违法构成犯罪初探[J].人民检察,1999(2):11-13.
[13] 叶萍,张志勋.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1-76.
[14] 柏浪涛.构成要件符合性与客观处罚条件的判断[J].法学研究,2012(6):131-146.
[15] 冯军.刑法中的自我答责[J].中国法学,2006(3):93-103.
[16] 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 [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2.
[17] 刘环宇.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6:20.
[18] 王杨.论渎职犯罪“损失”之判定[J].时代法学,2011(6):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