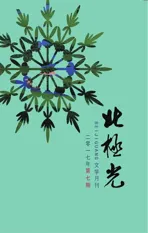那个年代
2017-09-15李广生
⊙李广生
那个年代
⊙李广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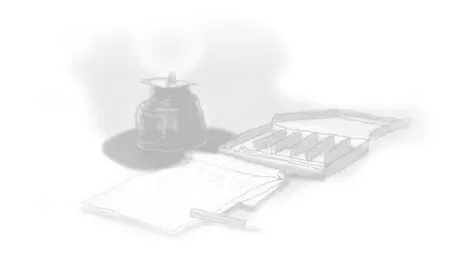
那面镜子
那面镜子,无疑是当时家中最为光鲜的一个物件了。
镜子一直高高雄居在老宅里屋的西墙上,从外屋一脚跨进来,迎面是一个敦敦实实的柜子,里面堆满了衣服鞋帽、针头线脑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柜子之上便是那面冷峻高悬、光芒四射的镜子了。
镜子长一米左右,宽七十多公分,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长方形。镜框原来是鲜艳的红色,后来时间久了,风吹日晒,颜色就一点点淡了下来。那个时候的镜子大同小异,多多少少都生动活泼地画着几朵花、几只鸟,或者几个人;有的还会识时务地写上几句铿锵有力的标语口号,后面尾随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我家的镜子也不例外,左上角空间巨大,右下角旗帜鲜明地伫立着两个英雄人物:一男一女,一兵一民。男的一身戎装,手握铁拳,目光坚毅;女的衣衫褴褛,苦大仇深,长发如雪。不用猜,一看便知道,那是《白毛女》里的大春和白毛女,再看衣着打扮和白毛女直立的脚掌,典型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芭蕾舞造型。就在昂首挺胸、奋勇向前的大春和白毛女的身后,工工整整地书写着一行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红色大字: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再将镜子翻转过来,可以看见镜子后面糊着的几张旧报纸,那是用来保护镜子娇贵的漆面的,防止被什么愣头愣脑的硬物磕了、碰了、划了。尽管报纸已经被氤氲的岁月熏染得又黑又黄,但外形还是很完整的,从上面残存的一些内容看,应该是1968年4月1日的报纸,《人民日报》或者《黑龙江日报》。那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当然这是后来的说法。当时全国人民正轰轰烈烈地投身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呢,哪有闲得屁滋滋响的人想起来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洋节呢。而那时候我还在娘的肚子里转筋呢,直至三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我才呱呱坠地,风风火火地来到这个喧嚣的尘世。也就是说,那张报纸比我的年龄还要大,而那面镜子,我应该称之为“镜哥哥”才对。
那面镜子尽管近在咫尺,但是父亲以及我们兄弟四人很少光顾,绝大多数时间都被母亲占据着。而忙碌的母亲也只是在早起、晚睡洗脸的时候照几下而已,其余的时间镜子几乎始终处于一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孤寂之中,日复一日地辉映着日月星火寡淡的光芒。
偶尔,我们也会偷偷摸摸登爬到柜子上,小猫小狗似的在镜子面前探头探脑,小鼻子小眼儿地照来照去。有时一不小心,碰翻了柜子上的瓶瓶罐罐,免不了大人们的一顿训斥,于是再很少去招惹那个危机四伏的镜子了。
几年后,里屋的北炕扒了,柜子顺势挪了过去,镜子也脚前脚后地移到了北墙之上。因为屋子举架低矮,阳光羸弱,即便人站在镜子前面,里面也是黑乎乎的一片,因此从那以后镜子便成了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摆设了。
镜子始终如一地老守着自己的田园,犹如一个时间的见证者,亲眼目睹和默默记录了一个家庭四十年的沧桑变迁。直至2008年的夏天,父亲扒拆了老宅,翻建了新房,那面已经老朽得面目全非的镜子才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着那栋拔地而起、宽敞整洁的新房,心绪复杂的我在倍感欣喜的同时,不觉从心底滋生起一缕淡淡的忧伤来。因为在老家,我突然感觉找不到根了,我的根似乎就在那间千疮百孔的老宅里,就在那面灰头土脸的镜子上……
于是我开始努力寻找那面镜子。在将仓房翻了个底朝天后,终于见到了那面久未谋面的镜子。那一刻,我欣喜万分,俨然邂逅了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许多往事也在那一刹那间一一浮现,我仿佛看到了多病的母亲、早逝的小弟,看到了那个贫苦而幸福的六口之家的蹉跎往昔……
后来,镜子被我带回了大庆,一直放置在家中。可是那面镜子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者健忘症,因为即便我们像过去那样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但它已经认不出我来了,目光呆滞、表情木讷,甚至还有一丝冷漠。
我想,或许只有让它重新沐浴在老家明媚的阳光下,回归到那间风雨飘摇的老宅里,才能一点点忆起那段早已逝去的时光和那些远离它的人吧……
那只木箱
木箱的底部有几行字:药名、数量,然后是落款——上海的一家制药厂。当我从三站药店搬回那只木箱的时候,还清晰地嗅到了一股浓烈的中草药味儿,当归、陈皮、龟甲,裹在一缕起起伏伏的风里。
小时候,我对中草药就情有独钟,有事没事跑到三站药店,木头一样柱在柜台前,眼珠一错不错地看那个胡子拉茬的老中医望闻问切地给别人号脉,然后探出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探囊取物地从一个个小木盒里抓出一把把形容枯槁、颜色暗深的中草药来,那味道浩荡、亲切、逼真,让我想起许多遥远的、素未谋面的植物和动物来。而那只木箱,确切说那只药箱,便是老中医送给我的,他的女儿和我同班,而且同桌。
其实细看那只木箱,制作很粗糙,原材料清一色是二尺多长、一寸多宽的木板,被一枚枚钢钉固定在十二根一寸见方的木方子上,如果用力掰扯的话,不消三五分钟就能摧毁成一小捆烧材。但即便这样,木箱搬回家以后,还是被父亲据为己有了,而且落了锁。
尽管对此我嘟哝了好几天,父亲的脸仍是不红不白的,说一个男孩子家家的,也没啥东西,要箱子能装个屁呀。我当然不想装屁,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能装一些自己东西的箱子而已,至于装什么东西,那可就多了,什么小人书了、弹弓了、溜溜了、啪几了、夹子了,等等,恐怕得装满满一箱子的。
后来,不知父亲又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又大又好的木箱来,于是喜笑颜开地将原来的那只木箱还给了我。父亲肯定不会知道原来那只木箱背后的故事,因为自从老中医送给我木箱之后,课上课下老中医的女儿总是粘着我,让我帮她写作业、抄情书、打群架,被她指使得跟木偶似的。
木箱物归原主后,我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便有了归宿,分门别类地盛装在了那只木箱里。尤其是一些好吃的,比如五月节家里分的鸡蛋、八月节分的月饼,待弟弟们甜嘴巴舌地吃光了,我的还锁在木箱里呢,拿出来,骄傲地展示,然后一小块儿一小块地掰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不时发出那种类似父亲喝烧酒时吧嗒嘴发出的自给自足的、幸福的声响来。尤其秋天的时候,下了第一场霜,一一将菜园里的一些尚未成熟的青柿子采摘下来,用棉衣密密实实地裹上,锁在箱子里,十天半月后,一个个便莫名地金黄灿烂起来。在北方乡下寒冷的初冬里,能够品尝到柿子凉爽、酸甜的美味,真是幸福极了。
十五岁那年,我读高中,那只木箱又风尘仆仆地跟着我来到了县城。随之木箱的命运,以及我的命运便发生了变化。因为情窦初开的我自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写日记了,喜欢谁了、讨厌谁了,有什么高兴的事了、烦恼的事了,都一一记录下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那把小小的锁头防君子却防不了小人,木箱一次次被撬开,日记一次次被偷看,个别精彩的片断甚至还被班里的同学当众声情并茂地朗诵,弄得我讨厌的那个老师停了我三节课,并且面红耳赤地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了检讨;而那个我心仪已久的女生呢,则羞得面如桃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脸地骂我是小流氓。
自此,那只连我仅有一点儿小秘密都保护不了的木箱,彻底在我的心里失了宠,以前那些泄了密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我开始变得自私、多疑,甚至是偏执,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眼里更多了几分敌意。
而那个老中医的女儿呢,初中还没毕业便辍学了,随即到南方打工去了。期间还给我写过几封信,尽管信里错字连篇,我还是读出了老中医女儿竭力要表达的一点儿暧昧来。但是我仅仅回过一封信,在信里,有一行字描了又描,我明确告诉她:那只小木箱已经被我拆了,拆成了一小捆烧材,正好煮了一顿饭……
那四棵柳树
那些日子,父亲时不时就拎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子,嚷嚷着要把那四棵树砍了,说那四棵树长得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占茅坑不拉屎,成不了材。母亲一边咳嗽,一边大声地表示坚决反对,说树风里来雨里去的,都长一房子高了,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吧。父亲终究拗不过母亲,树于是就“斧”口脱险了。
父亲打心眼儿里腻烦的那四棵树,都是柳树,长在园子的一隅,粗细基本一致,打小就歪歪斜斜的,怕冷似的簇拥在一起,就像数九寒天围着火盆取暖的我们兄弟四人。由此,我们猜测,那树肯定不是哪个人精心种植的,一定是野生的,没人管,没人问,因此一路下来,长得支棱八翘,很是随意。后来听人说,我家老宅的位置原来是生产队的牛圈了,我因而进一步设想,那柳树的种子极有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牛儿们带回来的呢。
园子东面毗邻生产队场院的地势有些低洼,那四棵树便生长在低洼之处,尽管貌不惊人,但春夏时节,还是翠翠绿绿地凌驾于周边的玉米、葵花等农作物之上,蔽日遮荫,俨然一个天然的华盖。初春时节,随手折下一些较细的柳枝,拧成叫叫,含在嘴里,呜里哇啦地一吹,春天的气息便生机勃勃地浓了。盛夏的中午,我和弟弟们则争相从父亲的责骂和熏天的酒气中逃离出来,栖卧在斑驳的树荫下,眯眼侧耳,一会儿看看蓝天白云,一会儿听听虫吟鸟鸣,间或有丝丝缕缕的风儿吹来,身子骨便酥酥软软起来了。
那个时候,家里还养着一只猫儿,三四岁的样子。那猫儿也和我们一样淘气,屋里屋外玩耍够了,就几个箭步蹿到树上,眼睛瞪得溜圆,仿佛有根线儿牵着似的,随着枝杈间那些雀跃的小鸟儿飘忽不定。猫儿有时玩得乏味了,就从树上轻轻地跳下来,先是用脑袋蹭我们的胳膊大腿,示好,然后顺势躺下来,伸几个懒腰,亲热地和我们拥挤在一起。于是我们的世界就定格在了那四棵羸弱的树下,没有了学校的约束,没有了大人的呵斥,地当床天当被,旁边还有一只善解人意的猫儿,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呀。
但是有一年,树突然生了虫子,尽管我们心急如焚,可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把钱撒在那几棵在他眼里一文不值的破树身上,因此虫儿们便有恃无恐地疯狂繁衍起来。虽然我和辍学的小弟一天从早到晚手忙脚乱,但是怎么捉也捉不净,索性就不管它了。树招了虫灾,有的地方出现了破损,渗出许多汁水,脏兮兮的,像人流的脓,有时会滴落在我们身上,令人厌烦。渐渐地,我们也远离了那几棵树,尽管这样做,从内心来讲是多么的不情愿。
好在树们终于逃过了那场虫灾,受伤的地方结了厚厚的痂,麻麻癞癞的,彻头彻尾破了相,而父亲看它们的眼神更是多了几分敌意。
又过了一年,四棵树当中的一棵突然枝枯叶黄,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打不起一点儿精神。父亲终于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兴冲冲地持着那把明晃晃的斧子,一下下奋力地将那棵树砍掉了。转过年来,余下的三棵树,也重蹈了第一棵树的命运,成了父亲斧下的牺牲品,并被细致地劈成了烧柴。那一年的冬天,也是记忆中我家的老宅烧得最热的一年,可我的心头却始终环绕着一丝凄冷。
如今,老宅已经倒掉了,多病的母亲和苦命的小弟也相继离开了这个鲜活的世界。原来园子的低洼之处亦被新土一点点铺垫起来,和周围的地势基本持平。每当我们兄弟三人回到老家,和父亲团坐在新房子里推杯换盏的时候,我的目光总是不经意地投向园子的一隅。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那四棵树,仍然活着,仍然坚守在原来的位置,那里还有一片斑驳的绿荫,绿荫里还有四个唧唧咯咯的男孩儿和一只蛰伏的猫儿,他们的头顶还有一群天真活泼的鸟儿,在忘我地歌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