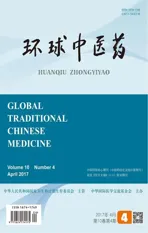古医家论治牙痛理论源流及思路初探
2017-06-21朱鹏举陈士玉谷峰
朱鹏举 陈士玉 谷峰
古医家论治牙痛理论源流及思路初探
朱鹏举 陈士玉 谷峰
通过对古医家论治牙痛理论源流的简要回顾与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自殷商至明清时期,古医家不断思考牙痛的病因,探求牙痛的治疗,逐渐形成了较为明晰的论治思路,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内经》相关论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古医家论治牙痛思路值得今日中医药工作者借鉴者有:明辨龋齿之有无;脏腑辨证重肾胃,经脉辨证重阳明;六淫邪气重风、热,内生邪气重痰、瘀,而寒痛亦不可忽视。
牙痛; 论治; 理论源流; 思路
牙痛,又称牙疼、齿痛、牙齿痛、牙齿疼痛,相关病名尚有肾虚齿风痛、齿风肿痛。而龋齿则因多见牙齿疼痛之症,亦经常被古医家归于齿痛的范畴,故欲探讨古医家论治牙痛的思路,当以古典医籍中关于牙痛、牙疼、齿痛、牙齿痛、牙齿疼痛、肾虚齿风痛、齿风肿痛、龋齿等相关记述为基础。以下试在对古医家论治牙痛理论源流的简要考察中对牙痛的论治思路加以分析。
1 古医家论治牙痛理论源流概要
1.1 殷商时期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关于齿病的记载。如“贞,疾齿,御于父乙”(《殷虚书契》)、“贞,疾齿,眚于丁”(《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前者是说武丁患有齿病,而治疗的方式是祭祀父乙,后者是说齿病给武丁带来了严重的痛苦,可见商王武丁生前曾深受牙痛的折磨。
不但如此,甲骨文中已有“龋”字,其形作虫蚀齿牙之象,或许是龋洞的形成、严重疼痛的出现促使古人想到了牙齿受到了虫蚀。由商人发端的虫蚀之说,历经数千年,至清代仍为众多中医学者所采信,时至今日还深深影响着国人。
1.2 秦汉时期
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史记》“仓公传”,记载了淳于意以灸左手阳明脉与苦参汤漱口的方法成功治疗龋齿的一则病例,并论及此病“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漱)”,较前人虫蚀之说有了极大的进步。
《内经》中关于齿痛与龋齿的记述颇多,其中有与仓公之说相合者,如《灵枢·经脉》所言“大肠手阳明之脉,……是动则病齿痛”“手阳明之别,……实则龋”与《素问·缪刺论》所谓“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皆是其例。不但如此,《内经》中还论及通过局部触摸诊察龋齿痛的方法,即《灵枢·论疾诊尺》所谓“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而其关于牙痛、龋齿的治疗更反映出此时的医家已具有辨证论治的思想。如《灵枢·杂病》云“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以是否恶寒饮为辨,而《灵枢·寒热病》说“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足太阳有入頄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頄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泻之,虚则补之”,更是利用经脉学说断龋齿的病位,并在此基础上辨别证候的虚实。此外,《内经》中“肾主身之骨髓”(《素问·痿论》)、“齿者,骨之所终也”(《灵枢·五味论》)等认识亦为后世论治牙痛、龋齿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口齿论》虽已失传,但其出现足以说明口齿科在这一时期已有长足发展,甚至出现了独立的趋势。《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存留的张仲景用雄黄、葶苈子、猪脂治疗小儿疳虫蚀齿的宝贵经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赏用。
1.3 晋唐时期
据《晋书》“温峤传”记载,“峤先有齿疾”,后因拔牙,“中风而卒”,可见晋代已有医家能够成功运用拔牙的方法治疗牙疾,不然温峤是不会轻易尝试的,或许这可以说明拔牙在此时已用于治疗牙痛、龋齿之类的疾患。
隋唐时代皇家的医疗机构太医署分为五科,耳目口齿为其一,可见此时口齿科已独立于内、外科之外。
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九专论“牙齿病诸候”,对“牙齿痛候”“牙痛候”“齿痛候”“牙虫候”“齿虫候”“齿龋注候”等做了详细论述。其文曰:“牙痛候 牙齿皆是骨之所终,髓气所养,而手阳明支脉入于齿。脉虚髓气不足,风冷伤之,故疼痛也。又虫食于齿,则根有孔,虫于其间,又传受余齿,亦痛掣难忍。若虫痛,非针灸可瘥,敷药虫死,乃痛止。”“齿痛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齿是骨所终,髓之所养。若风冷客于经络,伤髓冷气入齿根,则齿痛。若虫食齿而痛者,齿根有孔,虫在其间,此则针灸不瘥,敷药虫死,痛乃止。”“牙虫候 牙虫是虫食于牙,牙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牙疼痛。食一牙尽,又度食余牙。”“齿虫候 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食一齿尽,又度食余齿。”“齿龋注候 手阳明之支脉入于齿,足阳明脉有入于颊,遍于齿者。其经虚,风气客之,结搏齿间,与血气相乘,则龈肿。热气加之,脓汁出而臭,侵食齿龈,谓之龋齿,亦曰风龋。《养生方》云:朝夕琢齿,齿不龋。又云:食毕,常漱口数过。不尔,使人病龋齿。”
考其所论,主要理论基础本于《内经》手阳明经脉的循行路径。唐代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两部大型方书,皆有关于牙痛的记述。其中,《千金要方》中有“七窍病”之设,而“齿病”即在其中,《千金翼方·小儿》中“齿病”一项,两书虽未对牙痛、龋齿的病机做具体论述,但所列齿病诸候与《诸病源候论》颇同,或其理论认识与巢元方大致无别。另一位唐代医家王焘在所著《外台秘要方》中亦收载有大量治疗牙痛、龋齿的方药,理论论述则直引巢元方之说。
1.4 宋代
宋代原设太医署,后改为太医局,设九科,而口齿兼咽喉为一科。北宋时期,在徽宗赵佶领衔主编的《圣济总录》中,关于牙痛机理与治疗的记述集中见于“牙齿疼痛”“肾虚齿风痛”“齿风肿痛”“齿龋”“牙齿动摇”诸候。观其所论,认识较隋代的《诸病源候论》又有较大进步,而理论根据则仍在《内经》。以下引述书中与牙痛机理相关的论述并略加分析。
其论“牙齿疼痛”曰:“牙齿疼痛有二:手阳明脉虚,风冷乘之而痛者,谓之风痛;虫居齿根,侵蚀不已,传受余齿而痛者,谓之虫痛。二者不同,古方有涂敷漱渫之药,治风去虫,用之各有法也。”(卷一百二十)主张论治牙痛当首辨病因是风是虫,如此方能做出正确治疗。
论“肾虚齿风痛”曰:“肾生骨髓,齿者、骨之余,而髓之所养也,足少阴经虚,气血不能荣养骨髓,故因呼吸风冷,或漱寒水,则令齿痛而不已。”(卷一百二十)在《内经》肾藏精生髓充骨、齿为骨之所终的理论基础上,明确强调肾虚则易受风冷侵袭而发牙齿疼痛,提示治疗牙痛当重视补肾以扶正。
论“齿风肿痛”曰:“齿风肿痛者,齿根虚浮,牙齿疼痛,或遇呼吸风冷,其痛愈甚,则龈槽肿赤,乃至动摇,此盖手阳明经虚,风客其脉,流注齿间,故为齿风肿痛之患也。”(卷一百二十)重视龈槽肿赤与手阳明的关系,提示治疗牙痛当重视补手阳明之虚,祛手阳明之风。
论“齿龋”曰:“齿龋之病,由风热邪气,客于手足阳明二经,其状龈肿,或脓出而臭,久则侵蚀,齿龈宣露,一名风龋。”(卷一百二十)其重视手足阳明,似是在《内经》“阳明主肌”之说上得出的新认识。
论“牙齿动摇”曰:“手阳明支脉,入于齿,足阳明之脉,又遍于齿,为骨之所终,髓之所养,若经脉虚,风邪乘之,血气损少,不能荣润,故令动摇也。”(卷一百二十一)重视手足阳明经脉与肾,可以说是将《内经》经脉循行、阳明主肌、肾藏精生髓养骨、齿为骨之所终等诸多理论运用于牙齿类疾患的辨证之中。
可以说,《圣济总录》的相关认识既是对前人认识的继承与创新,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理论水平,并为明清诸家论治牙痛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宋时期,张杲在《医说》一书中对牙痛的辨治思路做了简明概括,云:“牙疼有四:一曰热,二曰冷,三曰风,四曰蚛。热者怕冷水,冷者怕热汤,不怕冷热即是风,牙有蚛窍者即是蚛牙。用药之法,热用牙硝、郁金、雄黄、荆芥之类,冷用干姜、荜茇、细辛之类,风用猪牙皂角、僵蚕、蜂房、川草乌之类,蚛用雄黄、石灰、砂糖之类。热牙宜于牙龈上出血,肿牙痛用药毕皆以温汤嗽之。”(卷四)虽所言不多,但对于牙痛的辨证要点、治疗方法均有清晰交待,以便临床取法。
1.5 明清时期

《杂病源流犀烛》是清代中期沈金鳌的代表著作,该书将牙痛分为风热痛、风冷痛、热痛、寒痛、痰毒痛、瘀血痛、虫蚀痛七类,显系在《普济方》五种牙痛基础之上又加细化而成。据此可以认为,牙痛的论治思路在明清时期已经成熟。
2 关于牙痛论治思路的思考
2.1 古医家论治牙痛思路的理论分析
结合以上牙痛论治源流的简要浏览,可以看出古医家论治牙痛的思路已经明晰。综观诸家论述,今日论治牙痛,似当重视以下几点:第一,辨龋齿之有无。牙痛可以是单独出现的症状,也可以是龋齿的临床表现。古医家似乎并未将牙痛与龋齿完全分开,其关于虫蚀痛的论述提示遇到牙痛当辨龋齿之有无。有龋齿者,当于龋齿的治疗方法中求之;无龋齿者,再做进一步辨证。第二,脏腑辨证重肾胃,经脉辨证重阳明。从脏腑而论,因肾主骨而齿为骨之所终,故论治牙痛当重肾胃二脏;从经脉而论,手足阳明入于龈,牙痛多兼见牙龈肿痛或萎缩主症,故当重视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经。第三,六淫之中重风、热,内生邪气重痰、瘀。六淫之中,热性炎上,而“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论治牙痛当重风、热之邪。据《普济方》所论,“热则生痰,毒气上攻”,而“热搏于血”,可“令血有瘀滞”,故牙痛多有与痰毒、瘀血相关者。今人更有久病多痰多瘀之说,而牙痛每多迁延日久,自当重视痰毒瘀血。此外,牙痛中尚有寒痛,亦不可忽视。
2.2 论治思路的常用药物印证
据今人高建荣等[1]的研究,在古今105种中医药文献224首方剂中,治疗牙痛时,使用30方次以上的最常用药有细辛(67)、石膏(50)、甘草(41)、白芷(40)、升麻(40)、麝香(34)、青盐(33)、川芎(31)、玄明粉(30)、荆芥(33)等10种,使用20方次以上的一般常用药有薄荷、防风、黄连、冰片、大黄、当归、生地黄、硼砂、连翘、花椒等20味,而使用10方次以上的次常用药则有乳香、黄芩、荜茇、草乌、雄黄、栀子、黄柏、蟾酥、川乌、没药、羌活、高良姜、朱砂、巴豆、赤芍、僵蚕、桔梗、牡丹皮、青黛等39味。若对这些药物加以分析,不难发现:从归经来说,入少阴、阳明二经者居多,这体现了古医家重视肾胃、阳明的思路;就药物性能而论,又是热性药居多,具有疏风清热功效者居多,这无疑又说明古医家论治牙痛重视祛风清热,而细辛、麝香、花椒、雄黄等具有杀虫效能的药物的使用,则说明杀虫止痛这一治法的重要性;细辛、花椒、草乌、川乌等温里药的使用,又说明寒邪亦是治疗牙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通过对古今医家常用药物的统计分析,可以证明古医家在论治牙痛时是按照其对牙痛病因病机的思考用药的,而这些方药能够沿用至今,则可以证明古医家论治牙痛思路在临床中的有效性。
[1] 高建荣,吴承艳.治疗牙痛方药中医文献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3,24(10):47-48.
(本文编辑: 董历华)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4)
110032 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内经教研室
朱鹏举(1980-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黄帝内经》及中医学术史研究。E-mail:chixinmu0378@126.com
R22
A
10.3969/j.issn.1674-1749.2017.04.025
2016-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