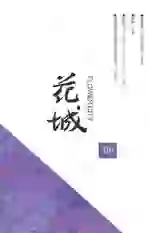鬼神到底有没有
2017-06-09刘庆邦
刘庆邦
“从前哪”,这是故事开头的习惯用语。这样开头,是从时间上给故事一个定位,确定一下故事的时间含量,表明故事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否则就算不上故事。讲故事的人愿意拿“从前哪”开场,多少有点儿摆谱的意思,显得自己见多识广,是有些资历的,不然的话,就蒙不住人家。本故事和讲故事的人未能免俗,也得从“从前”讲起。
从前的故事当然很多,地里长了多少庄稼,人们肚子里就装了多少故事。只是从前的故事普遍有些老,发芽概率不是很高,再生能力有些萎缩。而眼下才是故事的疯狂生长时期,每个人都仿佛是故事的发生器,层出不穷的新故事如刚出炉的面包一样,让人目不暇接。既然是新故事,还冠以“从前”干什么呢?这不仅是叙事策略的需要,从根本上讲,任何目前所发生的新故事,都不是孤立的,都不是凭空而来,与从前还是有些联系的。
拿这地方来说,从前鬼总是很多。如果说白天是人的世界,到了夜晚,就换成了鬼的世界。整个白天也不全是人的世界,据说在晌午头的坟地里和寂静的旷野里,鬼们也会出来活动,也很活跃。也就是说,鬼们喜欢黑暗、寂静的时间和地方,哪里有黑暗和寂静,必定伴随着鬼的出没。按这样的说法,鬼其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想啊,就算是大白天,黑暗的地方还是有的,床底下,灶洞子里,红薯窖里,黑得都很密实,都应该有鬼的存在。寂静的时候更多。一阵旋风刮过来,人们会说,那是鬼在驾车。杨树叶子哗哗啦啦一阵响,人们惊了一下,说是鬼在拍手呢!鬼是隐身的,鬼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鬼。人走路慌慌张张,有时会一头撞上鬼。若撞上比较宽厚的鬼,鬼笑笑就拉倒了,顶多说上一句,人哪,就是一团欲望,有欲望催着,就会瞎跑瞎撞。若撞上调皮的鬼呢,鬼魂腾地一跳,会附在人体上,搞出多种多样的名堂。有老太婆突然作女儿状,把自己的丈夫叫爹,例数爹对娘如何如何不好,要求爹今后要对娘好起来。别人一看便知,这是掉进水塘淹死的女儿的魂附在娘的身上了。也有平时循规蹈矩的女儿家,突然手舞足蹈,做的是疯癫状,唱的是以前不敢唱的曲儿,说的是以前不敢说的话。村里人一看,一对比,很快得出判断,这是村里前不久去世的一个疯老太太的鬼魂附在这闺女身上了。
如同鬼魂可以随时附在人体上,这里鬼和神也没有明显的区别,似乎鬼就是神,神就是鬼。比如每家都死过人,他们不肯把亲人说成鬼,也不敢把死人说成神,采取的是模糊的说法,把死人说成魂。谁家闹鬼了,说是谁谁的魂回来了。清明节到坟前烧纸呢,也说是给先辈的魂烧纸。一个魂字,把鬼神都代表了。
斗转星移,时代到了现在,鬼神的境遇怎么样呢?人们对鬼神的看法如何呢?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哪里有什么鬼神,从外面开来一台推土机,已经把鬼神推跑了。又从外面开来一台轧路机,已经把鬼神轧得粉碎,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鬼神的影子了。之所以没了鬼神,人们找到了三个原因。一是人烟太稠了,房子盖得太多了,挤占了鬼神的空间。鬼神被挤兑得无处待,无处躲,只好退出历史舞台。二是鬼神最喜欢寂静,最害怕喧嚣和热闹,连早上的鸡叫声都不敢听。而现在一天到晚空气里都是歌声、笑声、机器轰鸣声、电喇叭声等,无处不在的强大噪音早就把鬼神吓坏了。三是习惯了在黑暗中活动的鬼神见不得光亮,光亮一来,他们就得赶紧退避。农村通电以后,电光像一把把利剑,无处不劈到,鬼神哪里还有存在的余地呢!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以前钟馗很吃开,过年时钟馗的画像卖得很快。因为钟馗是妖魔鬼怪的克星,请一张钟馗的画像贴在屋里墙上,大鬼小鬼就不敢进来。时下既然没有了鬼,钟馗这尊专事斩鬼的凶神就用不着了,歌星影星笑星的照片大行其道,钟馗仗剑的画像备受冷落。
然而,事情也有例外,在秋后的一夜秋风秋雨之后,高堂村的高子民家就闹起鬼来。
高子民家院子门前是一条南北长的村街,村街两边住着十多户人家。村街本来就很狭窄,加上街两边的墙根堆着一些玉米秆和一些准备翻盖房子用的建筑材料,显得更窄。这样的村街,开进一辆小轿车还凑合,要是开进一辆卡车,肯定得被卡住。和高子民家住对门的妇女叫张又凡。张又凡的丈夫长年在外地打工,只有张又凡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里留守。张又凡除了种好自家的地,也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现在的农村几乎家家都要盖新房,村村都有建筑队,到处都是工地。只要你想打工,又有打工的能力,在家门口照样可以把工打得满地跑。这天吃过午饭,张又凡走出院子门口,返身锁上院门,刚要去村南的一家建房工地干活,听见有人叫着她的名字喊她:你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口吃的吧,这两个狠心贼要活活饿死我呀!
张又凡听得一惊,不由地站住了。她听出来了,喊她跟她说话的是高子民的娘。因张又凡的丈夫也姓高,跟高子民是平辈,按辈數,张又凡应该把高子民的娘叫大娘。张又凡对大娘家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大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当教师,二儿子在镇上做生意,就数三儿子高子民没本事,只能外出打工,或在家种地。自从大伯下世后,大娘就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吃住,一个儿子家住两个月,半年轮一遍,一年轮两遍。年过七十的大娘如今生病瘫痪在床,头发不能自己梳,脸不能自己洗,水不能自己喝,饭不能自己吃,什么都不能自理。大娘该轮到在三儿子高子民家吃住了,高子民用一辆架子车把大娘从他二哥家拉了回来。把大娘拉回家后,高子民没让大娘进他们家的堂屋,用塑料布在院子的南墙根搭了一个棚子,让大娘住在四面漏风、八面透气的棚子里了。高子民两口子在棚子里连小床都不放,直接把装有大娘的架子车往棚子里一推就完了。他们既不给大娘吃,也不给大娘喝,用意很明显,把大娘饿死冻死算拉倒。面对这种情况,张又凡怎么办呢?她很想到高子民家的院子里去看看大娘,给大娘送点吃的和喝的。可是,不敢哪!她倒不是多么怕高子民,而是怕高子民的老婆。高子民原来的老婆和高子民生气,喝农药死了。这个新老婆是高子民在南边打工的地方带回来的,据说这个老婆是在城里做电灯泡的下岗工人。这个城里女人厉害得很,她的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说话自称老子,把大娘骂成老不死。不用说,不让大娘进屋,要把大娘冻死饿死,一定是这个狠心娘们儿的主意。她张又凡要是敢给大娘去送吃的,高子民的老婆不把她骂出来才怪。她家和高子民家是对门邻居,进门不见出门见,她要是和高子民的老婆闹翻了脸,以后怎么来往呢!张又凡犹豫了一会儿,没敢进高子民家的院子,还是轻手轻脚地走了,只管干活儿去了。
傍晚下工回家,张又凡再次听见大娘喊她:又凡,又凡,你可怜可怜我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呀!
大娘这次喊得比午后还要迫切,还要绝望,张又凡听见大娘喊她,不由得又站住了。她的眉头皱了皱,心里像是在打仗,又像是在给自己鼓勇气。就在这时,张又凡隔着院墙听见高子民的老婆在严厉叱责大娘:瞎喊什么,你个老不死的老东西,再喊我把你的喉咙系子掐断!
子民呢,他躲到哪里去了?你让他出来,我问问他,我还是不是他娘!
张又凡听不下去,赶紧回到自家院子里去了。
天阴了,下起了小雨。张又凡还是烧柴锅做饭,她烧着锅,由大娘想起了自己的娘。想着想着,她鼻子一酸,眼角就湿了。去年冬天,娘搭乘一辆农用三轮车去亲戚家参加亲戚儿子的婚礼,因结冰路滑,三轮车一头栽进路边的河里,把娘给淹死了。可怜的娘,还不到六十岁,还没享到什么福,她还没有来得及在娘跟前尽一点孝心,娘就一去不回。等她得到消息赶到娘家,不管她哭得怎样昏天黑地,娘都双眼紧闭,不再跟她说一句话。自己没有了娘,她看到别人的娘都像自己的娘,不能看到别人的娘受苦。大娘目前的处境,让她实在难以忍受。人一代接一代往下传,人都是孩子,也都是父母,孩子对自己的娘怎么能这样呢!别说大娘还有一口气,还是一个活人,就算大娘是一只小猫小狗,也不能让“小猫小狗”活活饿死呀!
做好了饭,张又凡让女儿吃吧,她却吃不下。女儿问:妈,我看你怎么有些不高兴呢,你是不是又想我姥姥了?
张又凡勾起手指把眼角沾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谁都有娘,谁也不是从树杈子上掉下来的。
我也有娘,我也不是从树杈子上掉下来的。女儿的问题是:你们都是喊娘,我们现在怎么都是喊妈呢?
这都是跟外面的人学的,好像谁家的孩子不喊妈,谁家就是老土。吃妈不说吃妈了,说成吃奶,也是跟外边的人学的。我看坏就坏在啥都跟外边的人学上。
妈,我不跟外边的人学。
那,等我老了,干不动活儿了,你会管我吗?
女儿的回答是:妈妈不会老。
麦要熟,蚕要老,谁都会老,妈妈怎么不会老呢!妈妈不但会老,还会死呢!等妈死的时候,你会哭吗?
女儿丢下饭碗,一下子扑进妈妈怀里,当时就哭起来:媽妈妈妈,我不让你死,我就不让你死!
张又凡把女儿抱住:妈妈跟你说着玩呢,妈妈现在不死,妈妈离死还远着呢!妈妈的闺女还没长大,妈妈怎么舍得离开我闺女呢!
就在当天夜里,风一阵,雨一阵,高子民家里闹起了鬼。
鬼是后半夜闹起来的,高子民家院子的大门发出了砰砰的响声。村里很多人家翻盖了房子,院子的门由木门换成了铁门。而高子民家的房子还没有翻盖,院子的门还是桐木做成的木门。桐木门如鼓,在人脚已定的深夜,响起来是骇人的。这样的响声显然不是秋风造成的,秋风只有推门,不会擂门,风推门的声响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响声也不是秋雨打在木门上造成的,雨点打在门上,只会发出麻麻达达细碎的声音,而木门骤然发出的声响是集中的,像是报警的意思,又像是挑战的意思,显然是外力所为。木门既响,不知睡在堂屋的高子民两口子听到没有,反正村里不少听角灵敏的狗们都听到了,它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回应。它们的回应不能说不积极,但都没有赶到事发现场来。这是因为,现在农村狗的地位和待遇也发生了变化,纷纷从家奴性质变为宠物性质,主人或把它们关在屋里,或拴在院子里,不许它们再在村街上乱跑。加之乡下偷狗卖狗肉的盗贼也很猖獗,不让狗出门,也是出于对狗身安全的考虑。听到门响的还有高子民的娘,高娘的胳膊和腿虽说坏了,她的耳朵还没有坏,加之她饿得睡不着觉,门响第一声她就听见了。一听到门响,高娘就哭了起来,猜想一定是自己的丈夫回来搭救她来了,她哭诉说:他爹,他爹,你总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只能到阴间去跟你见面了。他爹呀,你不知道我受的是啥罪啊,他们把我扔到门外边,不给我吃,不给我喝,是要活活饿死我呀!天灵灵,地灵灵,风灵灵,雨灵灵,你赶快救救我吧,给我一口吃的吧!
第二天吃早饭时,高子民家闹鬼的事就在村里传开了,说是高子民的爹昨天夜里回来了,给高子民的娘送吃的来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高爹不错,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忍饥挨饿,趁雨天月黑,潜回家救妻子来了。现在的孩子指望不上,真正心疼高娘的只有在阴间的高爹了。不过大家也有不能释怀的地方。据说鬼和人分处在阴阳两界,日常所吃的食品是不一样的。鬼们所说的馍,是一些砖头头子;鬼们所说的油条,是一些破鞋壳子;鬼们所说的烙饼,不过是一些枯树叶子;烙饼里面卷的小鱼儿呢,说来更让人恶心,原来是一些拖着长尾巴的蛆虫。就算高爹给高娘送了吃的,可哪一样能入口呢,能挡饥呢!高爹夜里打门,说明他没能进院子,没能把食物交给高娘。他既然把吃的东西拿来了,就不会再拿走,有可能会留在大门外头。于是就有人端着稀饭碗,或拿着夹了咸鸭蛋的馍,到高子民家院子门口去看究竟。雨停了,地上有些湿。斑鸠在村街上走,给人的感觉,斑鸠的样子有些鬼头鬼脑。麻雀在门楼子上叫,人们听来,麻雀的叫声也有些鬼里鬼气。高子民家的院子门还没有打开,表明他们两口子还没有起床,还在被窝里睡觉。自打从南边带来一个跟本地说话口音不一样的女人,高子民的精力几乎都用在这个女人身上了。在高子民家院子门口的地上,好奇的人们没有看到馍、油条、鸡蛋、小鱼儿什么的,只看到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烙饼。当然了,所谓烙饼,只是一些被风吹落的树叶子而已,那些树叶子有小张的,也有大张的,小张的是杨树叶子,大张的是桐树叶子。这样的“烙饼”,羊能吃,兔子能吃,人怎么能吃呢!但有人把一片绿中带黄、厚墩墩的杨树叶子捡起来了,递向另一个人说:来,给你一张烙饼吃。另一个摆着手说:我不爱吃烙饼,留着你自己吃吧。你吃的时候,最好卷上一些小鱼儿,那就更好吃了。
高子民的娘听见门外有人说话,问:谁呀?谁呀?
门外的人好久没见到高子民瘫痪的娘了,以为她死了,已经变成了鬼。猛不丁听见高娘说话,他们像听见鬼说话一样,不由地惊了一下,逃也似的离开了。
随后全村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没人牵头组织,是自发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也没人出题目,是参与讨论者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讨论的题目一开始比较具体,高爹到底回来没有?半夜打门的动静是不是高爹弄出来的?讨论进行下去,题目变得抽象起来,现在到底还有没有鬼神?有争论才有讨论,争论双方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老山为代表的老年人,另一派是有过在城里打工经历的年轻人。老山今年虚岁都超过了九十,一口牙都掉光了,可他还活着。回顾高堂村人老八辈的历史,老山是活得年岁最大的一个,刷新了该村的人寿纪录。他不但活得耳不聋,眼不花,舌头还很灵活,什么话到他嘴里还能变成笑话。可奇的是,老山活着,他的老伴儿跟她一块儿活着,老伴儿还天天给他做饭吃。这样一来,老山家就成了村里老年人聚会的场所,每天都有不少老头老太太,自己拎着小板凳,到老山家里集合,说话,交流信息。关于高子民的爹半夜回家打门的消息,他们都深信不疑,神情上都有些兴奋。鬼们好久没有回过村了,好久不管村里的事了,谢天谢地,高子民的爹,那个大好人,那个喂了一辈子牲口的人,他总算回来了。他回来是对的,眼看他的老伴儿就要饿死了,他不管谁管呢!他们对高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觉得他弄出的动静还不够大,他起码应该惩治一下高子民的老婆,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尝尝鬼神的厉害。而年轻的一派,压根儿不相信高爹半夜打门这一说,他们说,哪里有什么鬼神,鬼神都是人制造出来的,造鬼有鬼,造神有神,不造鬼,不造神,啥鬼神都没有。他们判断,高子民家半夜门响,一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村里没安装摄像头,要是像城里一样,到处都安有监控摄像头,鬼神就会彻底消失。
高子民路过老山的家门口,老山把他喊住了。老山也姓高,跟高子民的爹是同辈,高子民应该把老山喊大爷。老山把高子民叫你小子,说你小子干得不善哪,听说把你爹都惊动了,你爹半夜回来给你娘送吃的,可有这事?老山这样问话时,坐在门口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都看着高子民,死人显灵,干预家里的事,他们都想看看高子民害怕不害怕。
不料高子民毫无惧色,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可笑,我爹都死了十好几年了,腿骨脚骨都该沤烂了,他怎么可能回来!
那可不一定,你爹虽说死了,他的魂还在,你对你娘怎样,他都看着呢。你要是对你娘不好,小心你爹捏得你脑袋疼。
那些老頭老太太一致附和老山的话,说就是就是,人不厉害魂厉害,谁都得对魂害怕着点儿。
我没见过魂长什么样,谁想怕谁怕,反正我不信,我也不怕。
老山说:连魂都不怕,我看你这孩子完了。人都有老的时候,都有爬不动的时候,我来问你,等你老得爬不动了,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不给你吃,不给你喝,你有啥想法儿?
人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我啥想法儿都没有。
我再来问你,人都有死的时候,等你死了,你愿意不愿意自己有魂?
这个问题高子民大概没有想过,他皱了一下眉,像是往遥远的地方想了一下,又像是感觉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魂,才说:我到街上去办点儿事,没工夫在这里跟你们说闲话。你们说的都是落后话,已经赶不上当前的形势了。高子民说罢,像是急着要到街上去赶形势,走掉了。
不管高子民信不信有鬼有魂,他家闹鬼的事情仍在继续。鬼的动静有所改变,鬼不打门了,变成往高子民家的院子里扔砖头。高子民准备翻盖房子,买了不少红砖头,都垛在他家的院墙外头。为了防止别人偷他家的砖头,他在砖头垛子上洒了白石灰水子,做了记号。往高子民家院子扔的,就是那些带有记号的砖头。这不算偷高子民家的砖头,只是把砖头换个地方,还是物投原主。整块的砖头一共投了三块,落在高子民家院子的地上,一砸一个坑。大概砖头扔得抛物线比较高,碰到了卧在院子里一棵矮棵上的一对公鸡和母鸡,鸡两口子夸张地啊啊叫着,从树上落了下来。
高娘再次很快做出了回应,她说:他爹,他爹,你进来吧!你不是会变吗,你变成一只雪老鸹飞进来吧。我只要看见有雪老鸹飞进来,就知道是你进来了。你赶紧把我带走吧,别让我在这儿受罪了。
村里的狗叫声你传我,我传你,再度叫成一片。不知谁家还传出了小孩子的哭闹声。
高娘这次还喊了高子民:民儿,民儿呀,是你爹回来了,起来去给你爹开门。你开了门,赶快闪身躲开,别让你爹的魂撞客着你,附在你身上。要是你爹的魂附在你身上,你就不是你了。
高子民开门从堂屋出来了,他手持一支打开电门的手电筒,把电筒又粗又长的光棒在墙头和院子里挥舞了几下,张口就骂人。他骂的不是他爹,像是另有所指:他妈的,谁干的?谁干的?有种站出来,背后扔砖头算什么本事!
白天在工地上,那些民工动手又动嘴,也在讨论高子民家闹鬼的事。只动手不动嘴的是张又凡,她在埋头砌砖,没有参与讨论。张又凡从和泥、搬砖、提泥巴兜子等打下手的笨重简单劳动做起,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步一步变成了可以站在脚手架上掂刀砌砖的技术工人。也就是说,张又凡原来只是一个小工,由于她干活不惜力,又用心学习技术,就变成了建筑队里的大工。一个女人家能当独当一面的大工,在乡下盖房工地上是很少见的,不光她在脚手架上站得高,工地上的人确实都对她高看一眼。下面的人看见了,砖头在张又凡手里显得十分轻巧,她拿起砖来,比都不用比,瞄都不用瞄,一块接一块就砌在墙上了,砌得又快又齐。眼看着,一面墙被她越砌越高,长起来的墙都快要把她遮住了。有人知道张又凡家和高子民家是对门邻居,问张又凡:高子民家闹鬼闹得那么厉害,你不害怕吗?
张又凡说,她和孩子一进家就关门,天一黑就睡觉,外边发生的事她一概不关心。不管啥事,关心才害怕,不关心就不害怕。
噢,害怕来自关心。问话的人想了想,觉得张又凡的话似乎有些道理。那么,问话的人又问:你认为人世上到底有没有鬼魂呢?
这两天,工地上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七言八语,没有形成定论。而张又凡作为一个大工,既然在摆弄砖头方面技高一筹,在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独到的见解呢?工地上的男男女女都望着张又凡,想听听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又凡觉出别人都在看她,她脸上不由得红了一下,她说她也说不好。张又凡手中的瓦刀在砖头上画了一下,又说:我听俺娘说,人最怕亏心,谁做了亏心事,鬼就去找他;不做亏心事,鬼就不找他。
听张又凡这么一说,大家拿高子民和他老婆一对照,觉得这就对了,因为高子民和他老婆对老人不孝,所以鬼才去找他们。
不过,也有人有疑问,怎么就断定夜半到高子民家打门和扔砖头的是高爹的魂呢?
这时有人说出了一个判断的方法,说其实很简单,要知道是不是高爹往院子扔东西,只看东西上沾的有没有牛毛就可以了,因为高爹喂了一辈子牛,他身上和手上沾的都有牛毛,不管他拿什么东西,都难免会沾上牛毛。
这样的话也许被高爹听到了,这天夜间,扔进高子民家院子里的三块砖头上不但沾了泥巴,泥巴上都沾有牛毛。牛毛里有黄牛毛,也有白牛毛,表明高爹喂过的牛是很多的。
高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闹鬼,高子民的老婆有些坐不住了,她要求高子民赶快收拾出一个纸筐,并带上猪肉、馒头、水果等供品,到公爹的坟前去烧纸,希望老头子不要再闹腾了。她没有改变对婆婆的态度,没有让婆婆到堂屋去住,也没有给婆婆送吃的和喝的,只是想通过化纸送钱的办法,阻止一下老头子的闹鬼行为。她每天都蒸大米饭,还炒回锅肉,煎鱼,弄得家里香气腾腾。她弄出的香气肯定会扑到婆婆的鼻子里去,可她就是不给婆婆吃,馋死那个老不死的老东西。
高子民不想收拾纸筐去烧纸,他说,一去坟地里烧纸,就等于承认他家确实在闹鬼。
高子民的老婆把灯泡眼一瞪:老子叫你去,你就得去,你敢不听老子的话,老子罚死你!
不知她对高子民的处罚有哪些项目,反正高子民对老婆的处罚像是很害怕,老婆一提处罚,他马上表示投降,说好好好,一切都听你的,行了吧!
高子民收拾好了纸筐,正要出门去烧纸,村主任登门到他家来了。高子民想把纸筐藏起来,已经来不及了。村主任问他干啥去,他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干啥。
高娘听见村主任来了,开始呻吟。她的呻吟长一声,短一声,颤抖得厉害,像是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又像是告诉村主任,她快要死了。
村主任把躺在塑料棚子里架子車上的高娘看了一眼,问高子民怎么回事?
高子民说没什么,婆媳之间闹点矛盾,属于正常现象。
不太正常吧。这几天村里群众议论纷纷,说你家接二连三闹鬼。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认识的?
没什么认识,你不要听一些人胡说八道。
话恐怕不能这么说。群众是什么,群众就是神,群众的意见,代表的就是神的意见,我看你们两口子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不然的话,你们家就很难保持稳定。
高子民的眉头皱了皱,这才把手中的纸筐往上提了一下说:我这不是要去地里给我爹烧纸嘛!
你去烧纸是对的,说明你心里还透气,并不是顽固到底,不可救药。但是,你不能只照顾死人的情绪,当务之急是把活人照顾好,不能眼睁睁地把活人变成死人。我给你大哥、二哥都打过电话了,让他们都到这里来,你们开个会商量一下,看看下一步如何赡养和孝敬你们的母亲。
说话之间,高子民的大哥来了,大哥黑着脸,好像是生气的样子。大哥没跟村主任和高子民说话,也没等老二过来开会,直奔塑料棚子下面喊娘。高子民的老婆没有从堂屋里出来,她把开着的屋门关上了。跟随大哥走进塑料棚子的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公鸡和母鸡的头都举得像鸡冠花一样,“花朵”随着好奇和探究的心一下一下颤动。从大门外面进来的还有一只别人家的小牛犊,小牛犊大概觉出院子里无利可图,气氛也不对劲,折转身走掉了。不知从哪里传出一阵笑声,像是夜猫子发出来的。大哥喊娘,娘没有答应,大哥说:娘,娘啊,我拉你去医院。遂拉起架子车,把娘拉走了。
2017年5月16日(北京和平里)
至6月2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十月作家居住地)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