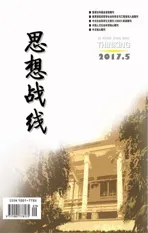论造型艺术中“看不见”的部分
2017-04-11
论造型艺术中“看不见”的部分
王新
造型艺术自然是视看的艺术,但其精义往往结穴在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自形式而言,造型艺术中有触觉感的线条,画“转过去”的体量,计白当黑的负空间,画面中的隐含结构与“势”“力”,从最微小的笔触、到中观的结构、再到宏观的风格“相反而能相成”的融合“分寸”,都是“看不见”的部分。从内容而言,作品背后往往隐含着“时代精神”和艺术家“潜意识”;“时代精神”,尤其是时代意识形态,会深入积淀到艺术家的“潜意识”,对其进行内在规束与说服,形成艺术作品中本应该说出来、却没有说出来的一些“裂隙”与“空白”,自然就成了“看不见”的部分;落实而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圈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凝结在作品中的某些“社会关系”,也成为“看不见”的部分。由此可知,艺术学迄今有一条尚未言明的重要原理:中外造型艺术经典中“看不见”的部分,往往决定了“看得见”的部分。在今天这个机械图像横行的“视觉中心主义时代”,我们重新思考和品味经典艺术中“看不见”的部分,对艺术学界之专业探究,以及整个社会视觉教养之提升,皆有饶深意义。
触觉感;潜结构;分寸;时代精神;潜意识;圈子
海明威的“冰山原理”道明:文学作品宛若冰山,看得见部分只“八分之一”,而水下看不见部分有“八分之七”,且看得见部分往往由看不见部分决定,所以作家要删繁就简,苦心经营那“看不见部分”。这一点,对造型艺术来说,同样重要。造型艺术固然是不离视看的,但造型艺术,尤其是古典造型艺术,其精义往往结穴在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其实所谓“看不见”,也不是真正看不到,而是指:若没有正大高明的教育点化与培养、不经过艰苦琢磨、苦心体味的学习与觉悟,从而绝难登堂入室,一窥“造型”的堂奥,最终对造型艺术中最气韵生动的部分,视而不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不中不西的艺术教育,导致诸多专业人士对中西造型艺术中“看不见”部分视而不见。所以本文力图建基于中西方一流艺术大家杂花生树的艺术作品及艺术笔记,探隐索微,从形式层面的线条、体量、空间、结构、风格与内容层面的“时代精神”“潜意识”“裂隙”与“空白”诸要素,较为完备地爬梳、深描与揭明出一系列造型艺术中“看不见”的精义,以正当下艺术的流弊,更图抛砖引玉,望方家教我。
有触觉感的线条
中西艺术分殊不啻霄壤,然有一共识,即一条有质量的线条,一定是“写”而绝非“描”出来的,故而这种线条,“极易唤起视觉上的触摸感,其质感、量感、速度、力度、节奏,皆活泼泼地牵引着观者之眼,对它进行触摸感知,从而在想象中,追溯完成艺术家画线时的所有身体姿势、动作与过程,这样的线条散发着艺术家创作时的原初身体气息,是一个‘视觉与动作纠缠在一起的身体’参与其中的结果”。*王 新:《素以为绚:“德国学派”素描四大特征》,《美术报》“域外版”2017年2月18日。
西方古典艺术史上,曾有漫长时光,画家同时是雕塑家,因此绘画自然会带有雕塑感,有学者指出西方造型艺术纯正形感培养:
一方面是在素描或雕塑造型时,想象每一笔,每一刀都是手在缓缓地,丝毫不遗地抚摸对象表面,而绝不是概念化的所谓边线,同时感觉内部的骨骼肌肉自里向外突起生长的压力,不放过任何一道皱纹,静脉和凹凸。*王天兵:《西方现代艺术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显然,这样的线条,极富触觉感。
维也纳学派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较早就洞悉了这一秘密,他认为,古埃及艺术就体现了富有触摸能力的视觉,顺流而下则是古罗马晚期艺术、哥特艺术和巴洛克艺术;而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在分析弗兰西斯·培根的“感觉逻辑”时,径直指明,培根牛油一般流淌的怪诞造型,正是继承了古埃及而来的视觉触摸传统。*[法]吉尔·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 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这点与著名油画鉴定大师贝伦森的“触觉理论”不谋而合。
证之以艺术史:达·芬奇线条雍容,拉斐尔线条纤弱,伦勃朗线条挥洒,梵高线条重拙,珂勒惠支线条犷野,贾科梅蒂线条怯弱,科科希卡线条严苛,莫迪里阿尼线条弹“性”蠢蠢,席勒线条痉挛而色情*孙建平,康 弘编著:《大师的手稿》,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直到当代的油画大家戴维·霍克尼还如是说:“在伦勃朗、毕加索和梵高那里,这一切都动人心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但却激动人心:发现如何将自己看到的东西简化成单纯的线条——包含着体积的线条。”*[英]马丁·盖福特:《更大的信息——戴维·霍克尼谈艺录》,王燕飞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可见,这些个性鲜亮的线条,都各个渗透着艺术家的性格、气质与身体气味,从而富有触觉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富有一流触觉感的线条,也彰显与成就了一流艺术家;从这些线条,也可以敏锐而细腻地触摸他们的身体、气质与命运。
中国艺术史上,与这样富有触觉感的线条差可比拟的就是“笔墨”(为了对应线条,这里略去“墨”,只谈“笔”)。中国画老到的用笔,写出的点、线,极富触觉感,细腻微妙,如书论言“以拔山举鼎之力,为美女插花”,乍看矛盾,实质即言线条触摸感,似轻实重,举重若轻,恰可对应倪瓒的用笔:轻松写去或拖去,而劲力内涵,力透纸背,圆位、厚味十足;恰如同油画家伦勃朗的线条,轻松挥洒中浸润着苍辣情味。这点,正是中西艺术在最深源处的会通与共识。
中国画用“笔”之触觉性,体现在技术形态、身体情态、文化品态三个层面,约略申述为:
技术形态层面,有触觉感的好的用“笔”,往往富有圆味、金石味、厚味与拙味。圆味,既指线条透入纸背的立体感,又指行笔运动中,“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刘熙载《艺概》),重心在行与止、奇与正的多维张力中,始终能葆有均衡,而创造出来弹力饱满的线条。著名书画收藏家、书法鉴定大师王季迁先生指明,好的笔墨是,“当重心在笔墨的中心时,就会产生好笔墨的效果,就像在舞蹈中,舞者不跌出重心之外。在笔墨中,不管是一条线,或是染的一大笔,不论笔墨是宽是窄、重或轻、湿或干,只要重心妥当地安置在笔的活动中心之内,就达到了我所说的好笔墨的主要条件”。*[美]徐小虎:《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王美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76页。金石味,为中国文人所创造,即将远古民间金石苍老朴实的质地,引入线条,以祛除文人用笔轻滑流利之弊,故这样的线条,涩,重,老。厚味,既指迹厚,又指味厚,用笔能“圆”,能“重”。*童中焘:《中画画什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10页。有余味,有格调,自然有厚味;八大,王原祁便是用笔能厚的典范。拙味,中国艺术用笔,在一切精熟圆通后,最终要化身朴拙,通达聪明深处的笨;因此拙味也是中国线条中最深的厚味。
身体情态层面,有触觉感的好的用“笔”,散发着艺术家创作时的原初体味与气息。由于中国毛笔、水墨和绢纸的灵敏活泼,中国笔墨与中国艺术家的身体情态往往贴合无间、血脉牵连。有这样一个事例:史载,明清之际,大书家傅山落笔满纸烟云,如惊蛇入草,却骨力雄健。其长子亦擅长书法,模仿其父字体,达到了以假乱真地步。一次,其长子故意将自己所书之字放到父亲桌上,看看傅山能否辨别。傅山见后,误以为自己所书,黯然神伤,叹曰:此字中气已绝,我将不久于人世矣!长子遂一旁窃笑,一月之后,其子暴死。傅山再视其字,恍然大悟。显然,无论这个笔记中的故事真实与否,都深刻折射着中国艺术家对自己笔墨的敏感:笔下的线条,全息着创造者的全副身心。中国文雅传统中,“拙规矩于方圆”,相对中规中矩的“界画”线条,一条散发着身体感的线条,品级要高很多。
文化品态层面,有触觉感的好的用“笔”,讲究文化与教养对线条的濡养、提炼和升华,这与西方偏重身体感、技术感的线条迥然相异。换句话说,中国艺术的线条中,尤其是文人线条中,流淌着鲜明的文化品类与品格的血液,比如董其昌轻松、随意、甚至略带幼稚味的雅洁线条,与八大蕴藉、清洁、掺以苍茫味的线条,都是以佛禅格调入画,经佛禅文化提炼而成的;又如黄公望清疏绵长的线条,颜真卿中正雄厚的线条,都分别体现着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精、气、神。中国线条的妙处,还在于即使同一品类的线条,还可现出品格高下,如倪瓒、沈周、文征明,皆为文人趣味,皆求雅,但倪瓒的线条,柔中涵刚,沈周的线条刚中带柔,文征明的线条则一味刚木,明显倪瓒最雅,沈周次之,文征明斯下。当然,这既关乎文化格调,更关乎天赋才情。可见,中国艺术看似简单地用“笔”,背后其实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生态的全面滋润与节节濡养。
画“转过去”的体量
体量是西方造型艺术的精髓所在,获得一个结实、厚重而又浑整的体量,令所有古典造型传统谱系中的艺术家,终生孜孜以求。罗丹强调,“没有线,只有体积”,梵高说,他画葡萄就要画出其浓汁即将从内向外炸裂溢出,施坦伯格分析毕加索大量女性裸体画时指出,毕加索终生都在追求如何全方位再现人体,他的素描“被赋予了视觉的拥抱”。凡此可窥这些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努力:在焦点透视的单一视角与有限空间中,在画布上,如何画“转过去”的体量。他们的努力,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绘画大师们的努力。
那么,究竟如何画“转过去“呢?西方古典造型传统中积累了丰厚经验,归纳而言,有三个方面:
其一,“转着看”。把“体积看成一整块(A lump)仿佛是从一个中心逐渐增长变大,可以把一个环绕着它的圆筒顶起、顶破的有生命的团块,完整、饱满而又实在。这实际是保持对物体背面的知觉,是转着看,英文叫Modeling”;*王天兵:《西方现代艺术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同样,施坦伯格研究毕加索立体主义风格形成的原始动力时,也指出,他全方位再现人体,人体各侧面融合在一起,“是对阿尔戈斯这位偷窥王的狂想,据传这位独眼巨人能从一百个角度观察事物”。*[美]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当然,毕加索是通过对焦点透视系统的拆解,来实现体量的追求,可以说既作出了探索,却也降低了难度,然而“转着看”的眼光是一致的。这里要强调,“转着看”,意味把对象看成一个具有“触觉感”的浑整实体,这个实体,由一个中心,自内而外地膨胀着生命张力,如同罗丹说,其人体雕塑细腻鲜活的外表,正是生命劲力自一个中心由内而外层层涌发所致。
其二,在边廓线上着力。中国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在诸多场合谈到,中国画家画不出西方画家那样浑厚的体量感,主要症结在边线与边线以后的那一半体积上,大多人皆只能画到边线为止,也就是只能画出对象可见的一半,画布背后的另一半,完全无从着手;他自己也很长时间为此困惑,直到在欧洲研究了大量绘画原作,“从国外回来,我就专门研究解决边线的问题,不是用虚实的办法,而是用比较清楚明确的手法,处理边线也非常深入,使它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个面,让它转过去”。*殷双喜:《我学素描的体会——靳尚谊先生访谈录》,《美术研究》1999年第4期。罗杰·弗莱精细入微地研究塞尚的边廓线时,异曲同工地指出:
他实际上是用画笔,一般以蓝灰色勾勒轮廓线,这一线条的曲率自然与其平行的影线,形成鲜明对比,并且引人注目,然后,他不断以重复的影线回到它上面,渐渐使轮廓圆浑起来,直到变得非常厚实,这条轮廓线不断失而复得。他想要解决轮廓的坚定与看上去后缩之间的矛盾,那种顽固和急切,实在令人动容,这自然导致了某种厚重,甚至笨拙感,但是它却以赋予诸形体一种我们业已注意到的那种令人难忘的坚实性与庄严感而告终。*[英]罗杰·弗莱:《塞尚的静物画》,选自沈语冰主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就是这样,塞尚用柔嫩敏感的细笔触,一点一点,堆垛边廓线,同时一层一层迟疑而抖擞地反复加强边廓,其静物浑厚的体量感,跃然而来。
其三,以浑整的圆曲体,概括所有表现对象。从体积,而非线、面出发,把握实体,这其实是原始先民富有的一种先天能力,文明人孩提时也富有这种能力,但由于重重教化,后来逐步丧失了。塞尚的体量感,另一重要的来源,就是他擅长用圆锥体、圆柱体,来概括一切对象,罗杰·弗莱指出,他其实是受到非洲土著艺术唤醒,土著人一开始就用梨、香蕉这样的圆曲体,来把握一切,他们拥有完整的空间直觉。事实上,西方古典造型传统中,一直隐含着以圆曲体表现体量的努力,就笔者对丢勒、珂勒惠支、全显光、舒传曦等“德国学派”艺术家研究来看,“德国传统”造型训练中,就是以圆曲体概括与表现一切,从而获得极好的体量,迥异于苏式素描的“调子”造型。
为什么圆曲体概括比影调使用,更能塑造出体量感呢?秘密在于圆曲体能画“转过去”,对象被艺术化处理为层层叠叠相互交接的圆圈,这些不同的圆圈,在显现部分是具体实在的形体,不显现的部分,是圆曲形结构的潜在形体结构;因此每条线都应延长去看,这延长的线又转了回来,这是圆曲体结构的特点;看得见的是外结构,看不见的是潜结构,结构内外有别,潜结构对外结构有微妙的影响,深蕴着艺术真义。*全显光:《素描求索》,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3页。详见王 新《素以为绚:“德国学派”素描四大特征》,《美术报》“域外版”2017年2月18日。雕塑家钱绍武对此真义亦明了于心,他说其“形体学第一原理”是:
凡是有生命力的东西,都要在平均的大气压力层中挤出一个能够容纳它生命的空间,那么这样的形体,在外形和形式上都必然是圆形或椭圆形,因为大气压力是平均的,鸡蛋从外观上看是椭圆形,但在鸡腹中本身是圆形的。自然的生命体要在自然空间形成,那么平均的压力下必然形成圆形,并且每一个空间都是饱和的圆形,它的圆形的大小、就是能量的大小、生命力的大小、张力的大小。*钱绍武:《雕塑形式语言之我见》,《雕塑》2004年第1期。
在这里,钱先生令人信服地为圆曲体表现找到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计白当黑的负空间
跟体量感紧密关联的是空间,形体嵌入空间的张力大小,就决定了体量感的浑厚与否。空间中实体形体以外的部分,即是负空间,略似于阿恩海姆指出的“图—底”关系中的“底”;艺术家在造型时,创造了一个雕塑或绘画的“正型”,同时便创造了一个负空间;优秀的体量浑厚的艺术,一定是“正型”与负空间两相摩荡、张力雄强、达乎完美的作品。然而,负空间容易为人忽略,故申论之。
“德国学派”艺术大家全显光在其影响卓著的《素描求索》开篇阐明,“实实在在的形体占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叫它实体,或叫正形体,实体以外的空间,我们叫它虚体,或叫负形体……绘画不仅要对正形研究,也要同时研究负形,正负形之间的关系。有时在正形中有序合理,而在负形中却杂乱无章,因而不能产生美感”,*全显光:《素描求索》,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8页。所以深受伦勃朗影响的全显光,是创造正形与负空间的高手,其代表作“钟馗”,虽则厚重结实、精力弥满,但对负空间没有扩张性侵入,而是在两者的交互对话中,葆有一种庄重的纪念碑式的自持,宛若伦勃朗浩瀚黑暗中庄严铁铸的老人。
油画巨擘伦勃朗同样认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要有能够画出一个篮子周围空气与一个鸟笼周围空气之不同的技艺,实质就是说,要能把握物体体量与周围空间的交互关系,把空间看成一种负的体积;这在终生深潜中西、融会中西、卓然独创的艺术大家赵无极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他说,当他见到塞尚“圣维克多火山”油画风景时,顿时意识到那种山与天空色块交接浑融难分的情况,与中国范宽、米芾的画法接近,山到了天里面,天到了山里面,没有明显的边缘。他还指出,自己油画中的“空”,“是一种生活的空间,要生活在里头,要在里面经历。实与空要相连,空实是同一生活空间的不同层面”。*叶维廉:《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中国画的生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赵先生苍茫无际五音繁会的油画意境,显然渊源有自。当然,赵先生的风景整体意境十分东方,但从负空间的角度看,张力结实,侵入无际,毋庸置疑,非常西方,绝非自在散漫的东方。
一般来说,西方艺术史上,正型与负空间交接摩荡的张力较大,如贾科梅蒂雕塑负空间强势挤压正形、亨利·摩尔雕塑则负空间直接侵入正形,布代尔雕塑则正形激荡、凌驾负空间。较之西方,中国艺术中正形与负空间的张力明显要小,且绘画与书法分途:元代后,绘画正形与负空间的张力渐小,书法则反之,到明代臻于顶峰。中国书学中早就有“计白当黑”的理论,说的就是要注意书法作品中除了实有笔划外的负空间,“密不透风”,“疏可走马”,书法学学者邱振中先生曾用剪纸镂空的方法,对书法史上的多幅名作之负空间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好的作品,一定同时在负空间上秩序优美,节奏响亮,且越好的作品,正、负张力越强,线条越圆厚。
隐含结构与“势”“力”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拥有一“结构骨架”,这个骨架就是此事物的独有格式塔,近似于中国艺术中所指的“神骨”,因此艺术无论写实与写意,都在于艺术家对其“结构骨架”的捕捉与表现。而“结构骨架”一进入画面,则往往就成为了画面中的隐含结构。隐含结构,也由此成为艺术家风格的独特标示,如拉斐尔的圆形结构,丢勒的正三角形结构,王蒙的S型结构,颜真卿的正方形结构,八大山人的倒三角形结构,这些隐藏结构与艺术作品的外在形态相得益彰,或者可以说,正是这些隐含结构由内而外地生长出了外形的千般风姿。阿恩海姆甚至指出,文艺复兴艺术向巴洛克艺术风格之递嬗,从隐含结构而言,实质是由圆形与正方形,向椭圆形与长方形之转变。而且,看不见的“隐含结构”往往又是造型艺术中的微言大义所在,以阿恩海姆对乔托的名作《哀悼基督》分析为例,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画面中隐含着一个先斜线后垂直线的结构,即从左下角耶稣基督后仰的头部开始,一道山脉,顺延右上,逐渐攀升,到尽头处,顿时转化为一棵笔直的秋树,随之上升,通过枝叶,发散到四面八方的空中。这一结构,实质暗示了耶稣死而复活的精神主题。*[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有意思的是,西方艺术史有这样一个形式规律,越往古典时代,艺术大师们的画面中,越乐于隐含一些结构,如达·芬奇画面中的三角形、拉斐尔画面中的圆形,提香画面中的十字形;越往现当代,这些隐含结构越来越少。也许,这与古典时代的世界观有关,大师们更乐于相信世界本质上有着优雅而恒定的秩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自然神论中。更有趣的是,对比中西方艺术史,可以发现,中国绘画中的隐含结构以不规则的有机形为主,而西方则以规整的几何形为主,中西艺术的分殊,于此可见一斑。
更深一层,组成“隐含结构”的要素之间,自然会“结构”出“势”与“力”,“势”是结构的动态趋势呈现,“力”是结构的立体空间凝结。“势”“力”亦是艺术中难以言传、看不见,但可以心会的东西。如强悍、朴厚、大刀阔斧,蔑视一切修饰的“势”“力”,就是“德国学派”的艺术风格特质,从伦勃朗,到表现主义的珂勒惠支、诺尔德,到今天新莱锡画派的图霍尔斯基、亚诺·莫尔,乃至中国的全显光,莫不如是。全显光工作室素描教学,迅速画出“看不见”的“势”和“力”,是“德国学派”素描入门的标尺。又如,同为狂草,张旭是料峭峻健的“势”“力”,怀素则是潇洒奔泻的“势”“力”,气格殊异,其中微妙,能不深辨乎?
相反相成的“分寸”
伟大的艺术,其涵摄诸端、吞吐辽阔的能力,往往超乎寻常。根据艺术史的审美经验,我们往往可以见到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即伟大作品:从内涵上看,往往拥有一种两端相持、“正、反”对峙的两难困境,困境越大,腾跃的层次越高;自形式而言,从最微小的笔触,到中观的结构,再到宏观的风格,皆能收拢与融“合”“正”与“反”两种完全相悖的质素,而达到浑然自成的境地,当然这种“相反而能相成”的形式中,“正”“反”融“合”的“分寸”,三七开,还是五五开,往往是“看不见”的,只能凭高明的创造手腕拿捏。
从笔触而言,两种相反审美质素融合,上文略有论及,现申论之:中国书法,讲究“棉裹铁”,说的就是笔线中能刚劲内含,柔中带刚,至于“柔”几分,“刚”几分,其分寸感,很难具体计量,欧阳询用笔,劲健中透着俊秀,褚遂良用笔,劲健中跳跃着柔嫩和敏感;如果对应到西方,伦勃朗用笔,苍率中有细腻,塞尚用笔,细嫩中有老健,说的是同样的道理。齐白石80岁时对胡橐总结毕生用笔经验“半如儿女半风云”,“工者如儿女之有情致,粗者如风云之变幻,不可捉摸。用笔前要和小儿女一样细心,要考虑是中锋还是偏锋,还要注意疾、徐、顿、挫来描绘对象,下笔时要和风云一样大胆挥毫”。*山西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编著:《田园 匠心 诗趣:齐白石书画精品展》之“齐白石题画诗与画语录撷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这里,齐白石既言说了创作状态的“小儿女”和“大风云”,也点出了自身用笔正反两赋的妙处。
从结构而论,两种相反审美质素融合,在古典艺术之后较常见,以中国的八大山人与西方的塞尚为例,前者构图喜险峻中取平正,八大山水中经常用倒立的三角形山石,为画之主体,山石上或山石下,皆是岌岌可危的鸟、鱼等,形势险峻,但其一定会在对应的位置,取重量足够的物象、题款或印章等平衡之,这样整体就通达了平正;塞尚则反其道而用之,他的静物乍看铜雕铁铸,整体十分平正,但细细推敲,则平正中暗含险峻,他常用的桌子、果篮、桌布、水果,往往有着“拗”“救”之妙,显得动势暗含、丰富异常。
自宏观风格而论,如董其昌书画艺术有“熟中生”的格调,就是一种笔墨、构图在纯熟后的自然与自由,这种自由有时还显出一种似乎功力不到的随意,这就是生味,是中国文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犹如黄宾虹绘画,看似黑、乱、麻、密,但细细看来,“乱而不乱”,其中自有历历分明的笔墨秩序,也就是他说的“融洽中的分明”,*黄宾虹:《黄宾虹谈艺录》,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5页。黄宾虹把“融洽”和“分明”两种审美质素融合得很好。实际上,中西艺术会通的最高境界处,亦能常常见此现象:如浑厚,是中西艺术皆追求的大境界,然浑厚者,很多难以华滋,如中国的范宽、西方的米开朗琪罗;如果能够合“浑厚”与“华滋”为一体,则审美层级顿然跃升,通达了艺术极境,中西艺术史上,王蒙、伦勃朗皆是浑厚而能华滋的大师。
如果放宽眼界,这样相反相成的“分寸”,除造型艺术外,在其他艺术类型中亦屡见不鲜,诗词艺术,王国维赏欧阳修“豪放中有沉着之致”,顾随说李白雄伟而能俊秀,叶嘉莹言辛弃疾豪放而婉约即是。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把“度”作为其实践哲学的“第一范畴”,并且认为“美是人对‘度’的自由运用”,*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之“为什么度是第一范畴”,北京:中华书局,2014。这正好从哲学的层次,揭明了艺术与美的“分寸感”本质。
图像学的“潜意识”与“时代精神”
以上诸论,皆是阐析形式上“看不见”的部分;实质图像内容上,也存在“看不见”的部分。一般而言,大多造型艺术所见即所知,但也有部分艺术,尤其是古典艺术,所见非所知,即画面内容中存在“看不见”的部分。这种“看不见”的内容,往往就成为了图像学大展拳脚的地方。
西方艺术史上的图像学方法,由瓦尔堡开创,到潘诺夫斯基集大成,形成了一个严谨完整的图像内容释读方法系统。要而言之,分为三个循序渐进的层次:*陈怀恩:《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
其一,前图像学描述,针对事实和表现性主题,依据风格史验证(认知不同历史条件下,使用何种形式表现事实和情感)。
其二,图像志分析,针对约定俗成的构成形象、故事和寓意的世界,依据类型史验证(依据文献知识,识别图像背后的特定文本与习俗主题)。
其三,图像学分析,针对构成象征价值的世界,依据文化象征史验证(依靠综合直觉,洞见特定主题所表现的人类心灵基本倾向)。
概而言之,图像学有三个层次:一是形式和事实描述,二是“用典”识别,三是图像背后隐含的“时代精神”和艺术家“潜意识”揭明。一般情况下,生活在自己图像传统中的专业人士,对图像第一、二层次内容会熟知,所见即所知,故可不论。唯有第三层次的内容,往往成为真正“看不见”的东西。举例而言,潘诺夫斯基曾如有神助地解释过丢勒《忧郁1》、提香《神圣与世俗的维纳斯》。他认为,《神圣与世俗的维纳斯》中裸体维纳斯代表纯粹理念美,着装维纳斯代表尘世的、肉欲的力量,丘比特以柔和注视,把两者和谐联系在一起,他进而证明这幅画象征了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念,终而揭明文艺复兴时代对人的确证要通过爱和美来实现。以一幅形质鲜美的作品,去蕴藏宏大的“时代精神”,这自然未必是画家自己本人最初寓意所在,但读者未必不可作如是解释,而且从艺术批评来说,对“看不见”部分的澄明,应是题中之义,更体现出批评的品位与见识。
另外一种画中“看不见”、甚至连画家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东西,即艺术家的潜意识流露。比如梵高的《农鞋》,海德格尔曾诗意而不着边际地描述了“农鞋”如何声声召唤着不在场的“农妇”,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在丰饶与匮乏中,蹒跚出场;但艺术史大家迈约尔·夏皮罗有意较劲,引用充足证据,证明这双《农鞋》并非“农妇”的,而就是梵高本人的。其实,无论这双实有“农鞋”是谁的,但作为艺术作品的《农鞋》,它就是梵高的。从敞开的醒目的磨破鞋洞来看,显然是寓意匮乏,联系梵高悲惨的感情生涯,可以看成其“性欲”的隐喻。用图像学理论概而言之,“农鞋”不只是一双农鞋,它再现了一双“农鞋”,象征了匮乏,表现的是性幻想。
更深层次而言,“时代精神”,尤其是时代的意识形态,会深入、积淀到艺术家的“潜意识”,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内在规束与说服,这就形成了艺术作品中本应该说出来、却没有说出来的一些“裂隙”与“空白”,此两者,自然也就成了看不见的部分。以孙慈溪油画《天安门前合个影》为例,在一个大家庭的合影照当中,最正中、最显赫的位置,原本理应是老祖父端坐,代表东方式的家长权威;但孙慈溪油画中这个位置上,“老祖父”恰恰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幅毛主席画像,联系这幅画创作于1963年,“时代精神”的说服效果,不言而喻。
艺术家“圈子”之痕迹
艺术作品内容中看不见的艺术家“潜意识”与“时代精神”,往往可以落实为艺术家的社会文化交往“圈子”之影响。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凝结在作品中的某些“社会关系”,也成为“不可见”的部分,比如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常常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艺术史家巴克森德尔对一份1445年的合同进行研究,发现佛朗西斯卡的绘画中,就明显留下了一个赞助人的痕迹,赞助人假艺术家之手,创作了构图、造型、色彩等:
前述的卢卡师傅必须承诺如此作画:一、所有人物都要在前述的拱顶上完成,二并且尤其应注重每个人的脸部及中部以上的所有部位,三卢卡不在场时,不能作画,四我们商定所有的混色应该由卢卡师傅亲手完成……*转自[美]霍华德·S.贝克尔《艺术界》,卢文超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同样,中国宋代精工富丽的诸多宫廷绘画中,有“宋徽宗”的痕迹;明代浙派绘画粗豪雄壮的风格中,有明代贵族的品味,扬州八怪的绘画中,有普通市井小民的气息。艺术家的“圈子”广泛而灵活,一般来说,越成功的艺术家,交往圈子越广泛,作品自然不可能全面映射此诸多关系;以与作品创作关联紧密程度而言,应该是赞助人(直接要求)、师长(风格影响)、帮手(代笔或合作)、同行(竞争比较)、朋友(品味感染)等的影响,渐次递减。显然,这些 “圈子” 关系,在作品中或显或隐的痕迹,如果没有专业研究与相关知识,自然也是看不见的。
总之,通过对一个造型艺术作品诸要素中“看不见”部分的详尽阐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经典作品生命的复杂性、曲折性与微妙性。造型艺术也不仅仅是用来“看”的,还可以是用来“摸”的、“听”的、“读”的和“想”的,这也正是经典艺术之魅力所在。 在今天这个机械图像横行的“视觉中心主义时代”,视觉压倒其他一切感官,视看也变成一过性的快餐消费,我们重新思考和品味经典艺术中“看不见”的部分,对艺术学界之专业探究,以及整个社会视觉教养之提升,皆有饶深意义。
(责任编辑 廖国强)
The “Invisible” Parts in Plastic Arts
WANG Xin
Plastic arts are certainly visual arts, but their essence often lies in those “invisible” parts. In terms of form, plastic arts contain tactile lines, modeling of depicted volume, the negative space created by “considering white or blank as black”, the hidden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movement and strength in the depicted images. The propriety of the complementary opposites in the micro strokes, the meso structure and the macro style all belongs to the “invisible” part. In terms of content, artistic works often carry zeitgeist and the subconscious of the artists. Zeitgeist, especially the ideology of the time, will be so accumulated in the subconscious of the artists that it will constrain and convince them intangibly. It will form some “cracks” and “blanks” in the works that should have been filled in. Those “cracks” and “blanks” naturally become part of the invisible. In a sense, artistic works are the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artistic circles. Som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represented in the works are invisible, too. Thus, there has been an unspoken principle in the study of arts: the invisible in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plastic art classics always determines the visible. In an age of “optical centralism” dominated by mechanical graphics, we need to review the invisible in classic art works, which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fessional artistic probes and to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s taste for art works.
sense of touch,latent structure,propriety,zeitgeist, subconscious, artistic circles
王 新,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J06
:A
:1001-778X(2017)05-01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