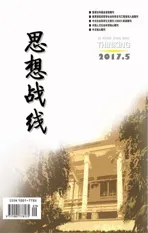理性选择、历史范畴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建构
2017-04-11,
,
理性选择、历史范畴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建构
黄淳,易定红
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理论问题,更需要把这一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理论问题。为此,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把历史范畴而不是把理性选择作为首要的理论对象,建构能够分析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系、思想体系、文化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辩证方法。这就要求我们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识别不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文明理性内涵的不同认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对人自然属性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人社会属性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分析中国民众对主客体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能够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
历史范畴;理性选择;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学的方法论
目前人们认识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西方主流经济学、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思想,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途径。*参见顾海良,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张 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学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属性。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例如李斯特的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也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同样也强调中国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历史属性。*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和思想都强调,历史不仅应该是经济学的现实对象,“历史”作为一个范畴,也应该是经济学的理论对象。但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了经济学的理论问题,理性选择作为一个概念则成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参见[英]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 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以理性选择为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了分析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实证方法,使其更类似于自然科学,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易于被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鉴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广泛的影响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历史范畴而不是理性选择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首要的理论对象?在历史范畴的基础上,又将如何综合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就此,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首先,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经济学理论共同的现实对象。但是,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活动性质的抽象认识不同,建构的理论问题、对象与方法也不同。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理论问题,把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对象,建立了分析制度与政策效果的经验实证方法,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把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理论问题,把历史范畴作为理论对象,建立能够综合认识现代历史进程演进逻辑的辩证方法。
其次,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本身就是推动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问题。20世纪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分析方法:对人自然属性的经验实证分析方法;对人社会属性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对人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只是这些分析方法的理论成果之一,侧重于对人自然属性的经验实证分析。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则建构了综合认识现代化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理论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建构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综合理论体系的最高峰。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身的历史条件、认识与实践主体。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运用辩证方法,综合认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为此,中国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建自身的哲学思想,综合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理论与思想,在中国民众所思、所言与所行的基础上,建构能够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演进逻辑的理论体系。
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象与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活动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内容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其首先通过个体理性选择描述经济活动配置稀缺性资源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经由供求理论,将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为社会的理性选择,建立了分析市场经济配置稀缺性资源的机制与效果的经验实证方法。20世纪后,在理性选择范式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继续发展。例如,计量经济学完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制度和政策效果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完善了对市场失灵的条件以及政府作用的分析,凯恩斯扩展了对货币非中性的分析,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扩展了对策略理性分析,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扩展了对人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特征的分析等。然而,就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的经济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性而言,理性选择的分析始终难以就此做出有效的回应。而作为人类历史上重大转变的现代化,经济学需要就这种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做出回应。
(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与对象:现代化的性质与历史范畴
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具有历史性。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中国也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为此,经济学还需要回答,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换言之,我们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现代化的性质。
一切社会现象、社会存在或者社会生活都是人们的行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更为具体地,是人们所思、所言、所行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历史学家通过描述人们的思、言、行描述历史,可以说,历史也是社会现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社会现象就是历史范畴的外延。
首先,人们的实际行动呈现为所创造种种具体的文明事物,例如,人口、消费品、劳动工具、家庭、乡村、城市、法律、制度、政府、国家等等。这些具体事物构成了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文明体系。而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性质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转变不仅伴随着社会商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这些发展还推动着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的变化,推动着现代企业、现代政府、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说,现代化是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伴随文明体系的剧烈变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西方现代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此时,人们面临的一个具体思想任务是认识怎样的文明体系是好的(善的),例如怎样的法律制度是好的。而判定一个文明体系是好的(善)的基本标准之一,则是这个文明体系是否能够真实地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社会的思想体系具有真、善、美的内容,使得人们对文明体系善恶性质的判定,不仅能够体现人们对自身主观目的美与丑的认识,也能够体现人们对自身行动客观结果真与假的认识。现代化也是人们思想体系的现代化,而理性(reason)则是现代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最后,现代化还是人们言语方式的现代化。人们通过言语活动交流思想,言语活动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符号的使用,使得社会具有文化属性。人们不仅通过言语活动表达和交流思想,还通过实际行动使得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具有了思想内涵。我们可以将社会现象看成是人们通过言语活动把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历史是人类文化体系的变化发展,表现为人们的言语方式,以及文明体系与思想体系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现代化的一个文化特征是,货币成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使用的最一般的形式符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德]西梅尔:《货币哲学》,于沛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现代经济学正是研究人类文化这一形式特征背后原因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作为了理论的逻辑起点,准确地把握了人际交往的商品化作为现代文化的基本性质。
因此,我们不能够脱离个体行动的选择,抽象地叙述“历史”,这样叙述的历史是没有任何具体社会生活内容的历史,或者是没有任何外延的历史范畴。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脱离社会存在文明、思想与文化的具体历史内涵,形式化地分析所谓个体的“理性选择”,因为任何个体行动的意义总是由历史范畴的具体内涵规定。为此,当我们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时,历史范畴就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
(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现代化价值与原因的理性内涵
把现代化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现代化的价值与原因?这涉及对现代化历史范畴理性内涵的哲学认识。
现代自然科学发源于西方社会,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源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一个是源于文艺复兴以来对可观测现象因果关系的实验。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仅是获得经验知识的方法,还是一种人文精神,使得人们相信人是可以通过发现正确的思维方式创造新的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由此实现人自身的目的,创造人存在的价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认识到,人自身而非上帝是他所生活的世界的创造者,人的理性(reason)是这种创造力的原因。
笛卡尔对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及其对两者关系的分析,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理性精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出发点。*参见[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从主客体关系出发,力图完整地认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理性内涵。但是,西方现代哲学对理性内涵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例如,休谟对因果关系经验知识客观性的质疑,边沁对因果关系经验知识功利性质的认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真善美思想体系理性内涵的逻辑分析,以及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现代化历史范畴的理性内涵概括如下:
第一,人们思言行的社会现象是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在实践上表现为文明体系,在认识上表现为思想体系。人们通过言语活动将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联系起来,并赋予文明体系思想的意义,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文化体系。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是历史范畴的哲学抽象,即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是历史范畴。
第二,人在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中同时具有主体性与客体性,并体现着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人在对主客体关系不同属性的认识与实践中展现着人不同的价值追求:福利、公正与自由。
第三,人在福利、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追求中展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的思维方式表现为范畴体系形成概念并运用概念的逻辑过程。历史也是范畴和概念变化发展的逻辑过程。
总之,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在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中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理性地(rational)配置稀缺性资源,更应该是如何创造性地认识与实践主客体关系。此时,理性(reason)是人们探索人自身创造性原因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即具有客体性内涵,体现人行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具有主体性内涵,体现人行动的主观能动性。而政治经济学所要发现的规律,不仅仅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规律,更应该是人类创造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的辩证逻辑。
(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与综合
当我们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而不仅仅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时,就需要把历史范畴而不是理性选择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当我们考察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之间的关系,或者考察现代文明体系、思想体系、文化体系的理性内涵时,可以进一步提出三个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如何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认识工业化、商业化与金融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第二,现代文明与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人的福利、公正、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三,货币表现的价格现象(包括工资、地租、利润)与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人的福利、公正、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显然,比较于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具有历史性,政治经济学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把握历史进程的辩证逻辑。
接下来,将通过对20世纪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考察说明,经济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对人在主客体关系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进行有所侧重的研究,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另一种趋势是:辩证综合地认识人在主客体关系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是第一种趋势中的多种理论成果之一,侧重研究了人的自然属性,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是第二种趋势的一个理论成果。对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或者对现代化的性质与理性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
二、20世纪前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分析方法与综合体系
如何科学地认识西方社会工业化、商业化和金融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20世纪后,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成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并使得经济学更像一门自然科学。但是,考察20世纪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将有利于我们从历史、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角度,理解西方经济学家对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之认识,从而,客观评价西方不同经济学理论的价值。
(一)亚当·斯密的综合体系*参见[英]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亚当·斯密创建的综合体系奠定了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后续发展的基础。亚当·斯密看到了人类社会由狩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不仅是人们生存技巧的变化,同时也是法律制度的变化,以及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亚当·斯密的学术抱负是以语言为线索,探究人类的思维能力如何使得人能够从最初简单的努力开始,逐步形成了复杂的现代文明体系。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前者以人的社会属性为出发点,分析公法形成的思想原因,后者则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出发点,分析私法形成的思想原因。在对现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分析中,亚当·斯密展示了一种将逻辑演绎、经验归纳与历史描述综合起来的辩证的研究方法。
其中,《国富论》有四个部分:经济理论(卷1,卷2)、经济史(卷3)、经济思想史(卷4)和经济政策(卷5)。理论部分提出了经济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增长与分工、价格(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息)与价值、财货周转与货币。国富论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史,亚当·斯密通过对经济史的描述表达了他看不见手的历史观念,例如,在历史的变革中,封建贵族为了经济利益如何放弃了政治权力等等。最后,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亚当·斯密把现代社会的文明体系与思想体系,以及思想体系与思维方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把历史范畴,作为了研究对象。
(二)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三种方法的发展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在方法上有三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李嘉图的分析方法是逻辑演绎。*参见[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有矛盾。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同的处理,试图化解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矛盾。但李嘉图并没有把增长与分工的关系作为理论的内生问题,李嘉图的核心问题是分配,并认为决定分配的法则具有社会属性。李嘉图以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这一社会法则为逻辑出发点,在周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资本品,实际上也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的一种耐用的财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交换的本质,是长时段的劳动与短时段劳动的交换。为此,利润与工资的决定都服从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的法则,由此试图建立一种逻辑一致的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李嘉图通过不同区域土地农作物生产量的不同,解释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总之,李嘉图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分析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法则。
不同于李嘉图,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方向侧重于研究生产—消费中的自然规律,其研究方法不是以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这一社会法则为前提的逻辑演绎,而是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这个方向的研究把人的消费动机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在此基础上对生产、消费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并由此解释价格现象(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息),例如萨伊。*参见[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赵康英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这种研究方法把发现具有自然属性的一般经验规律作为经济学的理论任务,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增长矛盾关系的发现。*参见[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 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这一方向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成为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萨伊和马尔萨斯的贡献,代表着一些经济学家力图把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确立为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以使得经济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
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以李斯特为先驱的描述性的历史方法。*参见[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无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萨伊,都试图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寻找理论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通常都具有规律性或一般性,不论其是先验逻辑的还是经验实证的。有别于此,李斯特展现了一种历史学家对理论方法的警惕和质疑,李斯特直接在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据,此时,理论不过是分析历史与政策关系的一个中间环节。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李斯特发现,解释不同国家兴衰的关键,是一国经济政策是否把国家竞争能力作为首要目标,以及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恰当政策。而一国之民族精神则是影响国家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李斯特强调了国家在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世界关系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国家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内涵。*杨虎涛:《李斯特谱系:一再被强调的国家和逐步被重视的社会》,《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在李斯特之后,以罗雪尔和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美国制度学派发展了经济学的历史方法。
(三)约翰·穆勒与马克思的综合体系
在这些方法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在一个理论体系中综合分析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成为了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19世纪形成了约翰·穆勒与马克思的两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穆勒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者,对认识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较为充分,故此处侧重于对穆勒的分析。
穆勒功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源于边沁,边沁的功利主义使得法学成为了一门经验科学。良好的法律体系需要通过经验知识来支撑,而经验知识需要通过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科学认识来获得,并且这些知识是可以不断增进的,由此不断推动法律体系的发展。*参见[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穆勒发展了功利主义:首先,穆勒以个体为出发点,认为人行动的目的(效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容。其次,穆勒认为,人们不仅会将功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个人生活中,还会将功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此时,禁止人们在运用功利主义原则时的相互伤害是人的社会意识。由此,维护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原则将转变为人们正义的社会意识,正义的社会意识又成为法律的公正原则。*参见[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而在阐明功利主义个体层面的福利与社会层面公正的含义后,法律面临着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穆勒又阐述了功利主义的辩证内涵,把功利主义发展成了自由主义,即好的法律还应该把个体不加限制地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作为目标加以追求。*参见[英]约翰·密尔《自由主义》,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穆勒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了功利主义的福利、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观,建构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意识形态。穆勒由此也成为西方社会现代意识形态重要的奠基者。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依次分析生产与消费问题,分配问题,以及交换与价格问题。*参见[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金 镝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首先,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部分,穆勒明确指出,社会的生产—消费活动服从自然规律。人类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二部分,穆勒分析了分配问题。和李嘉图一样,穆勒认为,分配有着自身的社会法则,区别于生产—消费的自然法则。但不同于李嘉图把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作为分析分配问题的逻辑前提,穆勒指出,社会如何分配产品本质上是政治问题,社会对产品的分配具有任意性,政治力量可以任意决定分配的比例。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未必能够归属劳动者,只不过统治者可以将通过暴力建立的分配比例,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确认而已。穆勒明确指出了政治的经济功能,以及法律制度的政治属性。但是,社会民主化的进步必然使得法律制度面临着价值评判。面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穆勒认为,人们不能够以生产效率来判定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好坏。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会存在着生产效率问题,也都存在着激励问题。如果社会只是面临效率与激励问题,无论在哪种制度下,人类的智慧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穆勒将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效率的价值追求,作为了评判不同经济制度好坏独立的政治理念,由此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总之,穆勒的分配法则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社会与精神的法则。最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三部分,穆勒又用因果关系的经验方法分析价格的决定问题。穆勒把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润作为可观测的交易现象,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解释决定这些现象的其他因素是什么。显然这些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供给方,一个来自于需求方,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价格。由此,穆勒也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分析方法的基础。
虽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综合性,但穆勒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四个重大的区别:首先,不同于穆勒从生产—消费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描述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性质,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劳动、土地的社会属性。其次,穆勒虽然坚持了分配的社会与政治属性,但实际上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再次,不同于穆勒将生产、消费的自然法则与分配的政治法则割裂开来的做法,马克思强调了物质财富生产技术的变迁对所有制形式变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秩序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参见孟 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最后,两者对经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福利、公正、自由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穆勒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力求建立一个涵盖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382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周转理论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把这种周转理论发展成为了一种历史理论。马克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生产”的周转过程,社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还生产人和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思想体系。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把这个历史过程描述为逻辑演进的过程。进一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将劳动价值理论发展成为了剩余价值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资本积累,由此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综合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之间的矛盾,并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分析,预见共产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演进趋势。
(四)理性选择与新古典经济学
边际效用革命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也放弃了亚当·斯密的历史分析方法,李嘉图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及穆勒对生产—消费的自然法则与分配的政治法则之间的区分,试图在生产—消费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确立经济学所谓纯粹的理论对象。*参见姚开建《经济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首先,边际效用理论把消费中的自然规律作为了解释价格的出发点,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从消费的角度解释效用和价格的关系。边际效用理论也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概念的逻辑基础。其次,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把边际效用理论的分析方法扩展到了生产的时间过程中,其时差利息理论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资本的基础。再次,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将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扩展到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决定上,把劳动、资本和土地都作为生产要素看待,并把社会的分配法则归属为生产—消费中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法则,由此排除了分配的社会与政治属性。最后,马歇尔在供求理论的框架下对新古典经济的理论内容进行了综合。马歇尔通过所谓的连续性假设,将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动机都归结为性质相同的动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并把这种同一的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力图把收益—成本的分析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的一般方法。进一步,马歇尔把货币看成是人类所发明的大规模度量人经济动机的工具,使得货币脱离了其应有的政治属性,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实体经济与名义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
总之,亚当·斯密之后,在萨伊、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消费的自然属性出发点,通过对个体选择的数学抽象,建立了一种形式化的理性选择概念——约束条件下的目标优化,把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对象,将经济学的问题描述为了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理性选择也成为了经济学家通过分析人的行动扩展因果关系经验知识的逻辑基础。这种研究方法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更像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比较而言,马克思把历史范畴作为理论对象,马克思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综合不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让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与学科体系建构
虽然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发端于西方社会,西方的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身的历史条件、认识与实践主体。中国现代史是中国民众在其所思、所言、所行中呈现出的文明体系、思想体系、文化体系转变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认识中国现代史的性质、价值与原因,用理论认识的逻辑把握中国民众的历史实践逻辑。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中,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法,在中国自身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基础,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综合性地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参见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中国现代史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形成新文明、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历史,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需要在综合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重建,创造新理性。*参见高得步《中国价值的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应当说,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有对中国现代化性质与理性关系的独立自主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来源于西方的经济思想相对于中国政治经经济学建构的理论价值。
首先,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实证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不同层面的经济管理与相互协调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家庭、企业与政府经济决策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效果与机制成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经济决策总要有会计核算的内容,并需要与他人交流一定的经验知识。所以,社会需要一种建立在会计核算基础上的,解释人们经济决策与市场运行关系的共同的知识体系。显然,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属于这种共同的知识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助于人们总结与沟通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参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易定红《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其次,我们应该确认,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国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有着自身独立自主的历史创造性。当我们通过分析中国民众对主客体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认识中国现代历史的逻辑时,就需要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国现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认识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但是,对中国现代史演进逻辑的完整把握,不是通过一种理论或一门学科能够单独实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应该是对管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学相互关系的建构,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不同理论与学科的作用。此时,哲学是将不同学科联系起来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成为综合性地建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哲学基础。
最后,我们还应该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实践为出发点,广泛地认识其他西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扩展我们对历史范畴辩证内涵的认识。例如,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西方非主流经济思想中国意义的认识;*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学者关于福利、公正、自由理性内涵多样性认识的比较研究等等。
四、结 语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仅是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的社会生产—消费方式的变化,同时也是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一历史过程有着自身的文明体系、思想体系与文化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性质,具有自然、社会与精神的属性,展现着中国民众对主客体关系的历史创造性。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完整地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为此,我们需要把历史范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首要的理论对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建构能够综合经济思想和理论多元来源的理论体系。
致谢: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极有价值的修改和完善意见,作者作了相应修改,但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甘霆浩)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Category and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HUANG Chun, YI Dinghong
As China is in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a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doe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ed to treat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scarce resources as a theoretical issue but it needs to examine the nature, value and causes of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as a theoretical issue. Therefore,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hould take historical category rather than rational choice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theoretical stud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method that helps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modern China’s civilization, ideology and culture. It requires us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al schools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of rationality in modern civilization differently. We shou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alyze Chinese people’s creativity i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by drawing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ies their empirical methods for analyzing man’s natural attributes, their deduction methods for analyzing people’s social attributes and their historical methods for analyzing man’s spiritual attributes. Suc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ay enable the logic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al theories to better capture the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category, China’s modernization, methodology of economy
黄 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易定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F01
:A
:1001-778X(2017)05-01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