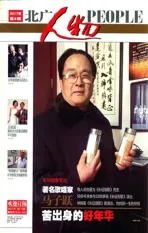辛德勇:考古无法为海昏侯翻案
2017-03-27张琳
辛德勇:考古无法为海昏侯翻案
进入未央宫的刘贺并不甘于做傀儡皇帝,他手下的人也开始图谋倾覆霍光的权势。短短27天后,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称刘贺“行昏乱、危社稷”,将其废黜。

随着海昏侯墓被打开,集“帝”、“王”、“侯”于一身的刘贺进入大众视野。大墓能让刘贺死后一瞬的哀荣呈现于人们眼前,却无法体现历史之多变及刘贺命运之浮沉。史料典籍中的刘贺究竟是何面目?他的命运又是哪些人在操纵?《海昏侯刘贺》是第一部有关刘贺的历史传记。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使用最常见的史料《汉书》、《史记》等,进行交叉分析,通过汉武帝、霍光与汉宣帝的活动,勾勒出刘贺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命运怎样在出生之前便已预伏,并最终被宫廷权力争斗吞没。
昏乱的“海昏侯”
相比于一些皇帝与权臣,史料典籍中对废帝刘贺的记载确实稀少。这恰恰构成了辛德勇的书写冲动:“如果直接记载很多,一清二楚,我也根本不会写这样一本书。”通过史料交叉分析勾勒出刘贺的形象,是希望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一个背景性的材料。“没有了背景,实物没办法说明问题。即使出土文物比史料更详细地反映了一些情况,那也是在历史大背景下分析的。”
《海昏侯刘贺》共七章,其中对刘贺的专门讨论仅有两章。全书始于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晚年的感情生活与政治作为,终止于刘贺去世。“如果把从汉武帝晚年到汉宣帝执政时期的历史看作一场宫廷政治大戏,刘贺仅仅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小插曲,是一条主线之外微不足道的人物”。“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走不便。”这段少见的关于汉代帝王外表的描述,来自宣帝派到昌邑监视刘贺的山阳太守张敞。随之一同到达宣帝手中的,还有那句“清狂不惠”的评断。在辛德勇看来,正是这次奏报让宣帝放下心来:这位废帝实在不足忌惮。此后一年,宣帝便封庶民刘贺为海昏侯,令其移居豫章。
自此,刘贺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四年后,他以一位列侯的身份死去,葬入如今位于南昌观西村的这座大墓之中。而在成为海昏侯之前,他曾是大汉帝国的皇帝,虽然只做了27天。
刘贺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转折便是他称帝又遭废黜的过程。受汉武帝托孤的权臣霍光,在汉昭帝死后急需寻找下一个傀儡皇帝,当时的昌邑王刘贺“有幸”入围,于公元前74年登基。
“清狂不惠”的评价的确不算冤枉。刘贺是带着主持先帝丧仪的任务进入未央宫的。有官员提醒他:按照礼法,刘贺望见都城就应大哭。可刘贺却当着霍光和文武百官的面,回答:“喉咙痛,不能哭。”
进入未央宫的刘贺并不甘于做傀儡皇帝,他手下的人也开始图谋倾覆霍光的权势。短短27天后,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称刘贺“行昏乱、危社稷”,将其废黜。刘贺从故地带去的200名臣属也被诛杀。辛德勇通过《汉书》中的零星记载分析,刘贺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憨傻”、“不精明”。“比如,宫廷政变应该是非常机密的,但他下令把长乐宫的禁卫换了,那是守着太后的人。这样一来,就是逼着霍光动手了,霍光本身就非常精明,不到这一步他也不会动手。大臣废皇帝,怎么粉饰,都是没道理的。”
刘贺之后,霍光又找来与刘贺年纪相仿的刘去病充当皇帝,这便是后来的汉宣帝。同是傀儡,宣帝成为开创西汉中兴局面的明君,刘贺却被霍光扣上“行昏乱”的恶名,黯然离去。在辛德勇看来,“刘贺是更有优势当上皇帝的,不仅长一辈,他还带了200个自己人一同进入未央宫,宣帝基本是孤身一人”。
宣帝的沉稳老辣,正反照出刘贺之“昏”。在霍光专权之下隐忍多年,直至其死后,宣帝才逐渐掌握权柄。可是,“汉宣帝从未否定霍光,因为他知道,如果霍光是非法的,那么他的皇位也是不合法的了”。辛德勇感叹:“霍光大奸大恶却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清史,便是当时宣帝以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海昏侯墓出土了作为祭祀先祖之用的大量金饼,上有铭文“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等字样。然而,刘贺早已被宣帝规定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辛德勇认为,这显示了他依然抱有重返宗庙之祭的幻想,制造这些金饼的做法无疑犯了忌讳,也是他脑子“不太清楚”的表征。海昏侯墓出土的钱币及金器为汉代考古发掘之最。辛德勇认为,这又与史料记载汉武帝晚年的政治作为与后宫斗争紧密勾连。汉武帝之所以将昌邑这片富庶之地分封给刘贺之父刘,是因为宠爱其母李夫人。刘贺被废后,霍光让他继承了作为昌邑王的所有财产。据辛德勇推测,墓中财富的来源就是两代昌邑王在封地的积累。
信史书,还是信文物
如同刘贺在整个西汉政局中的微不足道,辛德勇早年读《汉书》时,这个人物也从来是个被匆匆略过的人物。直至十多年前,宣帝改元的问题引起了辛德勇的兴趣,刘贺的命运才为他所关注。这里头还有一桩公案,牵涉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王国维曾在一枚斯坦因发现的敦煌汉简中,看到关于本始六年三月的记录。然而,根据《汉书》记载,宣帝的本始年号仅用了4年,接下来一个年号应是“地节”,所谓“本始六年”应该是“地节二年”。王国维未曾破解这个疑团,只留下“其中必有因”的评断就溘然长逝。辛德勇出版于2013年的学术文集《建元与改元》收录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西汉的几位皇帝根据阴阳数术变换自己的年号。而霍光操纵汉昭帝和汉宣帝的年号,让本该使用4年的年号沿用至第六年。恰好在“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汉宣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元。他不仅将公元前68年改为“地节二年”,还溯及既往,将之前的年号全部纠正过来。但已经入土的文献却无法修改,于是便有了那枚“本始六年”的汉简。
改元仅仅是汉宣帝与霍光家族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的一次小战役,却让辛德勇对一度与宣帝处境相似的刘贺有了更深的认识。如今大墓打开,相关文物近在眼前,辛德勇反倒颇为平淡。“没有特别的东西带来很大的触动和意外,也没有让我感觉文物中体现出来的刘贺与《汉书》中的刘贺有什么不同。”这位被认为是“少数具有深厚文献功底”的“文献派”,总对“颠覆史料记载”这样的话语保持高度警惕。
围绕着海昏侯墓,种种想要一语惊人的推测经由媒体传播,越发夺人眼球。辛德勇担忧这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在北京做展览,以及积极的宣传,这项工作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的解释要慎重、严谨一点。”比如孔子的出生时间、制作蒸馏酒的年代、刘贺的真实人格等,都曾被热议。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镜,背后铭文记录的孔子生年与《公羊传》、《梁传》等不同,有人便称考古实物改写了孔子生年。但在辛德勇看来,从时代上看,《公羊传》梁传》这样的传世文献,成书时间远比刘贺下葬的年代早。同时,从典籍的权威性看,《公羊传》、《梁传》等也都比这面铜镜背后的铭文要权威。
去年3月,考古工作者公布了墓中乐器、两周青铜器以及一些儒家经典简牍等发现。部分专家由此猜测:刘贺实则为情趣高雅的正人君子,《汉书》等典籍中的“动作亡节”、“清狂不惠”之说,仅为霍光等人的诬陷。辛德勇觉得,这样阐释文物,同样是脱离了史书提供的历史背景。儒家经典本就是皇室子弟的基本必修科目,在墓中发现这些典籍,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对史料的轻率否定,其实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学术界也同样有着追逐、迷信新出土文物的风气。近年来,“新材料、新发现、新方法”成了很多学术会议的标题。辛德勇感叹,新出土文献大家抢,因为总能出成果。其实真正的疑难,过一万年也总有文章可做。有人看不出来,只是因为没花功夫。大量的戏说历史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更通俗化的东西会更受到关注。对这些戏说,历史学家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它,而是给予讥讽和打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这样层次的内容。
张琳据第一财经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