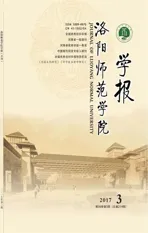关于“技术本身”及其价值再创造
2017-03-12吴致远
吴致远
(广西民族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6)
关于“技术本身”及其价值再创造
吴致远
(广西民族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6)
考虑到技术的动态性、过程性和应用性, 学界一度否认“技术本身”的存在。 从技术存在的多种形态出发, 笔者认为“技术本身”在有限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 “技术本身”概念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技术哲学必须对“人工自然”中各种人造物的结构、功能、范型及其演变进行分析, 从中提炼、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方法与原理, 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接地气”的基础性工作, 而非静止的、脱离语境的形而上学立场。 从“技术本身”概念出发可以对“技术中性论”问题、“技术异化”问题、技术控制问题、技术创新管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有新的思路和解答。 关键词: 技术本身; 价值再创造; 技术哲学; 技术相对中性论; 技术异化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它可以使存在者现身, 也可以使存在者隐退。 这一点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明显。 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可以揭示出一个新对象, 开启一个新领域, 引申出一套新理论; 同样, 它也可能掩盖一些事实、现象, 模糊有关认识, 过滤掉一些本该关注的东西。 所以, 在学术研究中“说明”一个概念可能比“定义”一个概念更重要。 在当前技术哲学研究中, “技术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详加辨析、说明的概念。
“技术本身”是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 意指与技术应用相区别的技术本体及其现象。 技术哲学与STS研究必须关注“技术本身”, 对技术人造物以及各类技术实践活动进行实证分析, 从中提炼、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方法与原理, 为学科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经验转向”的本质要义。 然而很长一个时期以来, 技术哲学与STS研究的这种合理转向却不时地为“技术本身”概念所困扰。 有学者指出, “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难以截然分开, 技术总是要应用的, 离开了应用技术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技术, 甚至是“死技术”。[1]240,[2]57还有学者指出: “‘技术本身’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 常常是在与‘技术应用’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实质上就是把技术看作是脱离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非历史的、现成的静态存在。”[3]国外学界也有类似看法, “技术是一种行为过程而并非一种静止的‘物’, 没有被称为‘技术’的简单的物”, “技术尽管是由事物构成的, 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下定义的事物”[4]xiii。以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人自居的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甚至宣称: “根本没有所谓的技术‘本身’, 因为技术只存在于某种应用的情境中。”[5]53这些认识使面向技术本身的相关研究受到挑战, 其正当性受到质疑。
以上情况使“技术本身”概念的澄清变得十分迫切, 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个概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而且对于当代的技术实践、技术管理活动关系重大。
一般来说, 人们说“某物本身”“某事本身”“某人本身”都是指存在一个客观实体, 其或者是一个在物质、能量、信息等形式上具有实在性的物理客体, 或者是一个具有明确界定的精神客体, 我们的意识仅就其直观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把握它, 而不涉及其关联项, 比如它与他物的关系、它的派生物以及对它的看法评价等等。 总之, “×本身”不是一个
捉摸不定的东西, 不是一个不能把握的东西, 否则这个表达就是无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本身”, 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确实有其局限性, 因为技术恰恰是最难于界定和把握的东西, 它的存在领域广阔浩瀚, 形态千变万化, 指称难以穷尽。 技术哲学产生至今, 学者们为给技术下一个较为周全的定义可谓殚精竭虑, 给出了不下上百种的表述方式, 这些定义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 但又都有自己的片面性, 不能穷尽技术的内涵, 难以赢得广泛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研究“技术本身”, 确实有盲人摸象之嫌。 “技术本身”概念的另一个困难——“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难于分开——其实也来源于对技术的理解。 陈昌曙、远德玉两位技术哲学家以及国外的J.皮特等人把技术主要理解为有关制作的实践行为和过程, 而不是静态的技术人工物和相应的知识, 他们认为, 作为机器、工具、设备等存在的技术物只是技术的要素, 而不是“技术本身”。[2]57如此理解的技术自然会把应用看作技术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把技术的应用先在地包含于技术本体之中了。 所以, 对于技术本质理解上的分歧是“技术本身”概念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每门学科在发展中都会出现对于学科核心概念定义、理解上的分歧(尤其是一些新兴学科), 这些分歧和争论是学科发展的动力, 客观上孕育着学科演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可以生发新的学科分支。 技术哲学在新世纪之初对于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与争论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技术哲学在获得了对学科对象——技术——的充分认识后, 开始沿着技术价值论、技术认识论、技术存在论、技术创新论等不同的方向快速推进, 出现了大量成果。 但是在这种良好态势下, 我们还应当警惕学术分歧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混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学术研究的推进, 致使学术研究遗漏掉一些重大主题, 甚至迷失方向。 所以, 我们需要经常回归到学科的核心概念上去, 反思已有认识的不足, 补充新的发现和认识, 审视研究对象中可能蕴含的重大课题, 及时进行学科综合。 本来, 概念、范畴只是理论工作展开的脚手架, 是深化认识、导致发现的手段, 而不是一劳永逸、固步自封的工具。 当一个概念无助于解释新现象、容纳新事实时, 要及时对其进行补充、修正, 以适应学术发展的新需要。 与此类似, 一些原来不太合用的概念, 在进行适当限定说明以后, 通过赋予新的内涵也可以获得新生。 正如《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一样, 马克思在对以前的“价值论”进行批判后赋予了“价值”一词新的含义, 由此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由此, 我们反观“技术本身”这个概念, 笔者认为其被重新界定说明之后仍是可以有效使用的, 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理论建构功能与实践指导意义。 对其重新定义须从对技术现象的分析入手。
鉴于从正面定义技术的难度, 吴国盛教授曾提出了一种反向思维:我们不能在肯定意义上穷尽技术是什么, 但可以在否定意义上说明技术是什么: “技术不是什么呢?技术不是自然。”[6]183如此理解的技术就具有了最广阔的领域, 技术与人的存在就具有了同构性, 技术与人的本质就具有了最深刻、最内在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的话, 可以发现技术存在有多种样式, 发明、制作、器物、制度、规则、知识、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程序软件等均是广义的技术物, 虽然其形态千差万别, 甚至没有任何共同性, 但是却都具有非自然的人工属性。 考虑到这一点, 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把技术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作为物质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意志的技术。 作为物质客体的技术包括器具、设备、仪器等, 作为过程的技术包括发明、制作、应用等人类行为, 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理论、规则、经验等, 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需要、意愿、意向等。[7]212-340可以看出来, 在四种类型的技术中第一、第三种都可以独立存在, 而第二、四种并不能独立存在, 必须与其他类型的技术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这样看来, 米切姆所说的第一、第三种技术都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技术本身”, 因为这些对象均有一个相对静态的存在, 即在其投入应用之前都是可以进行相对确切的把握和静观的分析的, 就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而言, 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本身”。 “技术本身”一方面表明技术有一种原初状态, 有一种“现成状态”, 它可以被确切地把握; 另一方面表明它面向未来而有着“待确定”的可能, 在未来的使用中它可能“异化”自身而成为他物, 我们称技术的这种面向未来而重新定义自己的情形为“价值再创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以技术人造物为对象进行静态分析并不意味着持有一种“静态的技术观”, 对“技术本身”进行静态分析, 分析各种人工物的结构、功能、范型及其演变是技术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接地气”的基础性工作, 并不是“非历史的”“与社会环境相脱离的”形而上学立场。 卡尔·米切姆很早就指出: “有关技术的哲学讨论提供了大量明显不相容的及片面的定义……不同意见的适当的解决办法是对技术的结构的和/或者现象进行分析, 描绘其不同的类型及其关系。 只有这样一种分析才能为每一种单独的技术描述的相对真实与重要性提供一种基础。”[8]232所以, 我们提出“技术本身”概念旨在使技术哲学研究奠基于经验事实与实证材料之上, 扬弃传统技术哲学极少关注技术实践, 缺乏对技术本体的内在了解和详尽考察, 而仅从先验的人文原则出发对技术进行价值评判的做法。
笔者认为, 一旦我们确立了“技术本身”概念并具有了技术价值再创造的认识后, 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一、技术中性论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 哲学界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传统的“技术中性论”进行了系统批判, 确立了“技术负荷特定价值”的基本认识。 但是, 与此同时, 学界却出现了两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一种是, 当人们面对一件具体的人工物可以用于甲目的也可以用于乙目的时, 人们便会对其价值的无偏向性(中立性)无从说明, 因而或者再度回到“技术中性论”的老路上去*如姜振寰教授在《技术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 “技术是中性的, 其本身不存在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 吴国盛教授在《技术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认为, 技术中性论是不正确的, 同时又认为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参见姜振寰:《技术哲学概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69页;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99页。, 或者把“技术本身”与“应用”合二为一, 认为只有在应用中的技术才是技术, 否则就是“死技术”。 另一种使人困惑的现象是,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负荷价值的技术“皆有政治性”、“技术是一种规划好的统治”、“技术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 甚至成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力量”(这种认识一度为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温纳等人所主张, 并有众多的追随者); 另一方面多数人却在无条件地、乐观地发展科学技术, 希望技术上的进步使人类最终摆脱压迫、束缚, 争得自由和解放。 笔者认为, 以上困境的出现是由于没有面对“技术本身”, 缺乏对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价值及其类型学的研究。
当我们面对“技术本身”时可以发现, 每一个技术人造物都是一个“有限的价值实体”, 其“有限性”表现在, 其自然属性和结构以及其所负荷的人的意向为其用途划定了一个有限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外, 这个技术物要么是无法使用的, 要么是不合用的。 这时候, 我们可以说该技术物具有价值上的“非中立性”。 如一款女装不能用于饮食、不能用于交通, 如果一位男士穿上也会颇感别扭, 在这些情况下女装不能成为选择的对象。 但是, 在技术物的自然属性、结构与意向表达所容许的范围内, 所有的应用都是可能的, 可以为任何特殊的目的服务。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该技术物具有价值上的“中立性”。 比如, 这款女装可以为不同的女士所拥有, A、B、C三位女士尽管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着装的目的不同, 但是穿上该款衣服后都是很合适的。 这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款女装对A、B、C三位女士来说具有价值上的中立性, 或者更确切地说, 具有“相对的”价值中立性。 因为, 这款衣服客观上对应着一个消费群体, 该群体尽管在身份、地位、经济收入、教育、信仰等方面有市场学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但是该群体内部被视为“均质化”的、无差别的。 从该款衣服的功能看, 在其获得的社会规定性范围内并没有明确的排他性和价值指向性。 由此, 笔者提出“技术价值相对中性论”, 该理论认为, 技术是人的创造, 负荷人类价值, 但是相对于各种具体的应用目的而言, “技术本身”可能会呈现价值中立性, 具有多种用途上的可选择性。 基于这个认识,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论断:技术负荷价值是绝对的, 技术呈现中性是相对的, 不适当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在《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一文中笔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不过由于没有确立“技术本身”概念, 这一观点没能充分展开。 请参见《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6期, 第116—121页。从这个思路出发, 我们也就认识到, 各种具体的人工物尽管具有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价值中立性, 但是其“本身”一开始就是包含目的、意向和价值的, 而不是在后来的应用中才获得了目的性和价值性。 也就是说, “技术本身”具有不依赖于应用过程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 其价值的相对独立性为未来的各种可能的应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是其价值再创造的基础。
在获得了“技术相对中性论”认识后, 对于上述第二种困惑就会具有较为清楚、合理的解答。 “技术本身”既然是一个有限的价值客体, 那么相对于人类无限多样性的需求, 其只能承担部分特定的价值功用, 而不是万能的。 也就是说, 现实的技术都是“小写的、复数的、具体的”技术, 是负荷特定价值的技术, 而不是马尔库塞等人所谈论的“大写的、单一的、抽象的”技术, 不是一个集各种功能于一身的“巨机器”。 不同领域的技术所负荷的价值有明显的差异, 具有多元性、异质性, 不能通约为“政治性”或“善恶性”。 所以, 用某一类型的技术所负荷的某一方面的价值属性(如政治性)作为“技术全体”皆具有的属性, 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现实中人们之所以无条件地去发展科学技术, 一个方面是由于部分技术的政治属性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容易被人忽视; 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技术人造物和技术活动确实不具有政治属性, 更确切地说不具有以阶级(或集团)对抗为特征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性”。 在笔者看来, “政治性”不仅是一个质的概念, 还是一个量的概念, 即政治性不仅可以用“有、无”来判定, 还可以用“强、弱”“大、小”来衡量, 具体情况与技术活动的主观意图、行业领域、范围大小和社会组织方式有关。 一般来说, 如果从事技术活动的主体没有特殊的政治考虑, 没有把特殊的政治意图物化在技术人工物中, 那么“技术本身”就是无政治性的。 如在广大的民生领域和非垄断的自由竞争行业, 技术活动多由分散的社会个体承担, 他们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并不是为了构建、维持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 所以无论其技术活动还是其相关产品都不具有政治属性。*一种观点认为, 之所以说技术皆有“政治性”, 还在于技术人造物总会造成某种政治性效应。 但是肖峰教授指出, 从后果、影响、关联性等去界定技术的政治性是无意义的, 因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能具有这种“政治性”, 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一切事物都具有政治性。 参见肖峰:《关于技术的政治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1期, 第3—5页。与此相反, 那些有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诉求, 并在技术物中表达了这种诉求, 从而形成了维护特定人群利益的技术设计才可谓具有“政治性”。 如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战略格局的大型工程技术活动, 以及规模化经营的垄断组织为了形成“独占权”而从事的技术活动, 其技术产品由于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差别性”而具有政治倾向性。 当然, 在政治宣传领域、军事技术领域、艺术审美领域、生产技术领域、医疗保健领域等, 技术的政治属性有明显的强、弱之别, 而且随着技术活动影响范围从宏观到微观的递减, 技术的政治性也呈现出由大到小的递减趋势。 这样, 在广大的政治因素没有参与的领域和政治倾向不明显的领域, 人们强调的主要是技术的生产、生活功能, 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内涵, 人们无所顾忌地、非反思地从事这类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技术异化问题
技术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备受思想界关注的话题。 人类为了争得财富、自由、幸福而创造的技术不断地转化为贫困、剥削和悲剧的根源, 技术上的每一次成功总是伴随着社会与自然方面的代价付出, 技术上的不断强大似乎映衬的是人类的弱小、无助和失落, 一句话, 技术日益成为一个背离人性的、反身相挟的“他者”。 对此, 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进行过痛心的揭示, 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变成贫困的根源。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 毋庸争辩的事实。”[9]78-79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触目惊心的“技术异化”,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技术异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技术异化”概念, 但是注意到了技术异化现象, 并在“异化劳动”主题下深刻阐发了技术异化思想。 笔者认为, “劳动”与“技术”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 “劳动”的着眼点是人自身, 技术的着眼点是“人工自然”。 如果把二者视作是对人类创制行为不同角度概括的话, 那么劳动表征的就是人类创制行为的体能耗费及其社会价值, 它通常要以技术为条件, 借助技术来实现, 并且表现为技术活动和技术产品。 马克思所反思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就是在机器技术背景下展开的, 正是机器工业技术使“异化劳动”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 同时也使对“技术本身”的思考成为主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写道:“我们知道,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 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认识论——引者); 迄今人们从来没有联系着人的本质, 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 来理解这部心理学……通常的、物质的工业(……)是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 以异化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 那种还没有揭开这本书, 亦即还未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从感觉上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心理学, 不能成为真正内容丰富的和现实的科学。”(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年, 第80—81页)尽管马克思没有写出以“技术哲学”为标题的专著, 但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却是奠基在对机器技术体系科学认识之上的, 如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社会再生产理论等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结构的分析。后来的研究大多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 着重从制度、文化和观念的角度探讨人的解放, 把“技术本身”作为无辜的、免受质疑的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对此, 笔者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提出另一种思路, 可谓是对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的一个补充和发展。
在英文中, 表达“异化”含义的词是alienation, 这个词来源于更早的拉丁文alienatio, 具有疏远、生疏、分离、让渡、转让等含义(德文中的Entfremdung是对alienation的翻译)。 词源考察表明, 从alienatio到alienation, 异化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先后获得了神学、社会学和哲学上的专有含义。 现今, 作为一般性哲学范畴, “异化”的基本含义是“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 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10]35。从“异化”的这个最“一般性”含义出发, 可以获得关于“技术异化”的广义理解。
与纯粹的自然物不同, 技术人造物的显著特征是其包含着人的主观意向性, 内含了人类意识的技术物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体、价值与事实的结合体、应然与实然的结合体, 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物质实在性与精神超越性的统一。 “技术本身”的这些二重性特征决定了技术异化是社会发展中的“常态”, 而不是长期以来理论界所认为的只是某些特定的社会阶段才产生的“病态”。 原因在于技术物中被“固化”的价值观念总是会随着该技术物的流转而遭遇到“异己”的其他价值观念, 从而产生冲突、碰撞、调适等互动关系, 这些关系因其具有直接的物质实在性效果而影响到人们的实际生活, 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事情。 随着其作用的方式、范围、程度、规模、时间和立场的不同“技术异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技术本身”的角度出发, 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形式的技术异化:其一,技术应用的异化。 是指对“技术本身”的应用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人类价值规范, 或者违背了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共同价值, 这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技术异化”, 也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技术异化”。 尤其是当这些不合理的应用成为一个社会中持续发生的宏观现象时, 此类“技术异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 其二, 技术本身的异化。 这种形式的“技术异化”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指技术物中包含着技术发明人或技术占有者的特殊意图、特殊利益, 相应的技术结构功能方面的设计能够使技术发明者(或技术占有者)持续地获得灰色利益, 从而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侵害, 形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 此类“技术异化”由于具有合法性形式, 常常能堂而皇之地长期存在下去, 凭借其隐形的利益剥夺机制, 使受害方“有苦难言”。 如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垄断技术组织, 它们制订的各种霸王条款就是基于其特殊的技术设计来实现的。 另一类是指技术人造物本身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伦理规范, 甚至是违背法律制度的, 如各种赌具、盗具、酷刑具、毒品等。 这类“发明”由于天生具有“恶”的性质, 而不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发明创造”, 但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类“技术”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阶段。 “技术本身的异化”的前一种形式长期以来处于十分隐蔽的状态中, 以至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没能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 游离在思想家们的视线之外, 这种情况直到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相关著作问世后才有所改观。 “技术本身的异化”的后一种形式虽然也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但由于人类对其早有“定论”而不在“技术异化”问题讨论之列。 第三形式的“技术异化”笔者命名为“技术价值再创造的异化”, 是指技术物在后续的革新改造中获得了新的应用功能, 甚至偏离了发明者的初衷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进化”之路。 相对于其最初“意向性”而言, 我们说技术本身发生了异化, 获得了新的价值意向。 这样理解的“技术异化”不再具有贬义的成分, 而是对“技术进化”现象客观化的表述, 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异化”概念。 广义的“技术异化”是社会发展中的常态, 只是在特定情形下才会出现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技术异化”。 从创制过程来看, “技术本身”一旦产生, 就有一个移用、改造、再发明的过程, 这时候“技术本身”往往会偏离最初的路线, 沿着不同的应用目的和构思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 “轨道既包含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也包含了社会的需求和限定、博弈和妥协。 类似于生物进化, 先前‘基因’的遗传、变异与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及众多‘行动者’及其网络的‘冲撞’等)的选择, 使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沿特定方向演进”[11]。技术轨道虽然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但是其一旦形成就会对技术选择的其他可能性形成排斥, 从而形成“惯性”“自主性”与“排他性”。 如果这种“惯性”“自主性”积累了足够多的负面效应从而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构成挑战, 那么技术就进入到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技术异化”状态了, 当这些负面效应变得积重难返时, 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由此, 在进行“技术异化”批判时, 我们便可以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 从技术本身的二重性本质出发, 在具体的、现实的、动态的联系中去把握人与技术的关系, 避免单一视角的狭隘性。
以上分析表明,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技术异化”还是创新论意义上的、 广义的“技术异化”, 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 只是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不同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这就打破了以往把“技术异化”只同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连, 认为“技术异化”只发生于特定社会形态中的认识。 与此同时, 笔者还认为消除“技术异化”不仅要对制度、观念进行变革, 还要对“技术本身”进行改造, 即对技术形成过程进行民主化、人性化干预和控制, 这样才能使技术彰显正义、维护公平、守护人性、创造神性。 回顾“异化”理论发展史, 逻辑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笔者的上述思想: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再到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和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理论思考走了一个曲折迂回的路线, 最终回到面对“技术本身”的起点。 这可以说是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原则的回归, 是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迈进的又一条途径, 即在改造世界的技术实践活动中来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 这是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化, 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延伸。 我们的根据是, 思想成熟期的马克思已经显示出从“工业本身”的历史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了, 其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奠基于“物质生产本身”之上, 并且认识到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 就是说, 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 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12]255。现在, 重新研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已经包含了“技术异化”的思想, 只是这朵含苞的花朵未及充分绽放而已。
三、技术控制问题
由于没有看到“技术本身”价值的相对中立性, 许多研究者每当看到同一项技术人工物既可用于行善也可用于作恶时, 便茫然不解, 从而把“技术本身”同“技术应用”捆绑到一起, 认为技术与应用不可分, 甚至把“技术本身”归结为具体的应用行为, 最终以应用决定“技术本身”的价值。[13]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一个著名观点, “词语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 这句话与“技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何其相似。 笔者认为, 这种高度相似性就在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人造物, 技术哲学的一般结论应该适用于语言学研究, 这一点也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方式中看出来。 每当他阐述有关观点时总是以技术物品来佐证, 这说明作为人造物的语言也具有技术之本质。 尽管有维氏的观点作支持, 笔者依然认为“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分别是技术存在的不同方式或者不同环节,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依然是可分的。 在现实世界中, 存在大量的尚未投入使用但准备投入作用的技术物品, 有大量处于闲置状态的技术设备, 有大量技术专利、技术设计、技术人才作为战略储备支持着我们的“硬实力”, 它们以“不在场”的方式而“在场”, 我们显然不能说它们是“死技术”, 是没有意义的技术。 事实上, 维特根斯坦之后的语言哲学家如赖尔、斯特劳森等人, 已经明确提出应该把“语词的意义与语词的指称分开”, 甚至提出“语句与语句的使用区分开来”。[14]222
承认“技术本身”的存在并且在适当条件下把其与“技术应用”分开, 在技术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之一就是技术的管理控制问题。 如果我们把“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看作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在从事技术管理时只能是“事后管理”, 即只有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技术行为发生后我们才能对其管理, 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或惩治。 因为此前这种行为还没有发生, 我们不能对未发生的行为进行管理, 充其量只能进行宣传告诫。 但是, 如果我们视“技术本身”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与“技术应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对“技术本身”进行“事前管理”, 对于那些有潜在应用危害的技术物品进行严格控制, 以防不合理、不正当使用, 更要防范这些物品用于违法、犯罪行为。 现实社会中, 对于技术物品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进行“事前管理”的, 针对枪支、炸药、麻醉品、成瘾药物等技术人工物国家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可以看到, 凡是对这些物品进行严格管理的国家, 相应的犯罪率就很低, 而疏于对这些物品进行管理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都有很高的犯罪率。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 在枪支犯罪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一些人依然抱着“是人在犯罪, 不是枪在犯罪”的错误认识。 殊不知技术人造物中所表达的人的意向性对接触该物品的人具有引导、指示作用, 它作为无声的语言对接触者形成“劝导”和“诱使”, 使那些心理防范能力较弱的人能够轻易步入误区。
四、 对技术创新管理的启示
技术创新是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技术创新自然应该是STS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技术创新, 而没有对技术创新的风险给予足够多的重视。 这种风险一方面来自“技术本身”, 另一方面来自于“技术应用”。 就“技术本身”而言, 任何创新都有自然与社会双重效应, 一方面是对自然的一种改变, 这种改变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完全预测的后果; 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价值体系格局的一种改变, 这种改变在社会系统中也会引起连锁反应, 因而具有不可完全预期性。 就“技术应用”而言, “技术本身”的应用、转移、改造与再发明也是一个社会价值的再创造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的过程, 是行善与作恶并存的过程, 如何使技术在社会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框架下健康发展是一个要不断面对的课题。 所以, 技术创新需要确立风险意识, 我们不能使创新的代价大于收益。
有鉴于此, 笔者认同“技术本身”概念的实践有效性和学理正当性, 作为“技术人工物本身”简称而理解的“技术本身”, 不但可以有效指称人类社会中林林总总的技术现象及其类别、形态, 也可以把多种形式的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统一起来, 把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家所主张的小写的、复数的技术同经典技术哲学家所谈论的大写的、单数的技术整合起来, 从而有效沟通不同层面的技术理解, 有效沟通理论与实践, 把技术批判从“价值”延伸到“事实”、从“人”延伸到“物”。 在此情形下, 技术哲学家可以直面(无所顾忌地面对)各种形式的技术人造物和技术事实, 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这样我们就可以部分理解, 为什么屡遭诟病的“技术本身”一词不断为技术哲学家们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无论国内的技术哲学家还是国外的技术哲学家均是如此), 甚至连明显反对该概念的技术哲学家本人也在不经意中反复使用。
[1]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240.
[2] 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57.
[3] 李宏伟.技术的价值观[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5).13.
[4] PITT J C,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Xⅲ.
[5] 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3.
[6]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83.
[7] 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朱春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212-340.
[8] MITCHAM C. Types of Technology[M]∥MITCHAM C.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An Annual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Volume 1). Greenwich: JAI Press Company,1978:232.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78-79.
[10]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35.
[11] 吕乃基.技术“遮蔽”了什么?[J].哲学研究,2010(7):9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55.
[13] 芦文龙.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8):45-49.
[14]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219-222.
[责任编辑 尚东涛]
On “Technology-In-Itself” and Recreation of Technology’s Value
WU Zhi-yuan
(CenterofScienceandSocialDevelopment,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Nanning630006 ,China)
Considering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researchers used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technology-in-itself”. In view of technology’s diverse modalities I argue that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in-itself” is tenable in some sense.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in-itself” discloses a wide research field to u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hould face “man-made nature” and analyze the structure, function, type and evolution of artifacts so as to abstract universal concept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his work is necessary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is basic to research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cknowledg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in-itself” isn’t the static and de-context viewpoint of metaphysics. If we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in-itself” several traditional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technology neutralism, technology alienation, technology control,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etc. could acquire new thought ways and be solved appropriately.
technology-in-itself; re-creation of valu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relative neutralism; technology alienation
2016-09-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问题研究”(15XMZ068); 2010年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技术追问的后现代路径”; 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资助; 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广西与东南亚民族人才小高地资助
吴致远(1967—), 男, 河南安阳人,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史与STS问题。
N031
A
1009-4970(2017)03-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