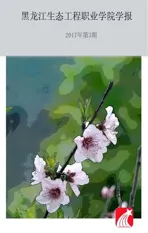论我国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
2017-03-10李前龙左甜
李前龙 左甜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论我国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
李前龙 左甜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英美对抗制诉讼模式下产生了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品格证据因可能侵犯被告人公平审判权而被法庭排除。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但却无系统化的规则予以约束。品格证据的运用使被告人面临道德审判,侵犯了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刑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立法使我国有构建品格证据规则的可能。
刑事审判;品格证据;公平审判权;证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品格证据规则也称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缘起于英美法系证据法。其核心观点是,被告人的品格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存在相关犯罪事实的依据。我国并未构建起具体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但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则很普遍,典型的如被告人过去的社区表现、犯罪行为等。然而,品格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品格证据是否会影响审判者对事实的认定?一个人能否因其品格而被定罪?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套证据规则而加以厘清。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a)条规定了品格证据的一般规则:品格证据的禁止①。(该条规则存在诸多例外情形,非为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不予列举)根据这一规则,法官不能依据被告人曾经在相似境遇实施过盗窃而认定被告人存在盗窃行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被排除,并非因其不具有相关性。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1]。品格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上的人格—行为理论,即一个人的行为倾向与其人格有相关性。在实践中,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多被验证。因此,说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而被排除理由不够充分。美国杰克逊大法官在著名的“Michelson v.United States案”的判决中解释了排除品格证据的理由,即并非因为被告人的相关品格特征与待证事实间没有相关性,而是担心陪审团可能会太过看重品格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依据被告人大致的不良记录而使自己未审先判,使被告人丧失了就该特定起诉进行公平辩护的机会②。可见,英美法系证据法对品格证据的排除,主要是出于其有可能侵犯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使被告人陷于道德审判的境遇,从而受到法律不公正待遇的考虑。
英美法系品格证据的排除主要是在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阶段。独特的英美证据规则之所以存在最久远并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理由是,它可以弥补那些担当临时法官角色的业余人士所具有的智力和情感弱点[2]。然而我们的法官能否在事实认定阶段保有理性与情感的独立而不受品格证据的影响呢?深受传统的道德文化的影响,基层法官恐怕并不能完全摆脱道德审判的拉扯,从而可能会在事实认定阶段受到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影响而未审先判,从而侵害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人能否因其品格被定罪?如果品格证据会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那么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严格的品格证据规则。
2 构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措施
2.1 我国传统文化中难以摆脱的道德评价
我国有重实体的诉讼文化传统,自古注重个人的品行。道德评价成为这个社会最一般、最主流的社会评价。总体来说,我国传统法治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道德意味,通常某个人的伦理品性、道德品质和社会评价是其人格的整体最重要的部分。在我国古代传统刑事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的品格也是裁判者看重的因素,对法官心证会形成较大影响,裁判者甚至直接依据品格证据而做出判决。这种文化背景下,法官很难完全从道德评价体系直接转入法律评价体系,社会公众在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对刑事被告人进行纯粹的法律评价而忽视其个人道德品行。因此,品格证据规则的推行可能会面临较大的舆论压力。这是与英美法系国家民众倾向于法律评价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必照搬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规则,而应当结合实践中人们对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接受程度,以规则构建的轻缓化和本土化来构建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
2.2 实体正义价值追求下对品格证据的漠视
英美法系国家更加注重诉讼的程序价值,程序正义往往比实体正义更加重要。这也是英美证据法形成的诉讼文化基础。而我国则偏重实体正义,有时甚至不惜违背程序而追求实体正义。在不断查明的一些冤假错案中,被错判的被告人往往因其品格不佳、行为不端而被认定为嫌疑人,可见基于品行的道德评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我国典型的重实体正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必然难以接受带有程序正义价值追求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
两种价值追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对证据法态度的不同。然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很难获得平衡。品格证据规则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与被告人公平审判权的保护,正是我国犯罪控制模式的刑事诉讼所需要作出改进的地方。在构建品格证据规则时我们需要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基本的程序构造,逐步推进品格证据规则的建立。
2.3 品格证据规则与一元化审判组织形式的契合困境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一元化审判组织形式不适合源自二元化审判组织形式的品格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品格证据规则虽诞生于英美法系二元化审判组织形式中,但并非脱离了二元审判组织形式就无法立足。品格证据规则所蕴含的对被告人公平审判权保障的价值选择,以及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无论如何在刑事审判中都是可以而且应当兼顾的。我们需对英美品格证据规则进行一定的本土化修改,以适应我国一元化审判组织形式。因此,审判组织形式的差异并不能否定我国应当构建品格证据规则。
3 构建我国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3.1 刑事审判法官排除品格证据的干扰以作出客观评价
有学者认为,美国品格证据规则依托审判组织形式的“二元制”,即陪审团负责认定事实,法官裁定法律问题[3]。因而我国一元制审判组织形式不能提供品格证据规则的土壤。然而,如前所述,品格证据规则基于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可能受品格证据的影响而做出情绪化的审判的考量,是对陪审团“道德审判”的制约。我国虽无审判组织的二元制,但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官由于专业素养的差异以及受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过早接触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则难以避免受其影响而做出道德性的判定。比如法官看到某被告人社区表现不佳,或者有过犯罪行为,则会倾向于作出有罪认定。因此,在刑事案件审理的事实认定阶段,我们应当控制法官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接触,使其不能知晓被告人犯罪前科的相关记录,以保证法官不受被告人品格证据影响而作出客观判断。
3.2 实现控辩平衡的价值选择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仍然是偏向于犯罪控制模式的,这一模式下控方作为刑事程序的主导者,在证据收集和庭审控诉中都占据明显优势,造成控辩双方的势力差异。在这种模式下,控方可以任意使用被告人品格证据以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控诉。而被告人本来就处于对抗公权力的弱势地位,再被法官以品格证据进行道德审判,将会加重控辩双方地位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不引起法官对被告人可能产生的偏见,建议不将被告人以前受过刑事处罚的记录或者不良品行记录作为起诉中的内容[4]。即检方起诉的内容排除品格证据,从而回应保障被告人公平审判权的要求。
3.3 量刑个别化的现实需要
现代刑罚社会复归理论认为,“处罚”被定罪的犯罪人,给其适当的“处遇”,目的是为了使其再社会化并且重返社会。刑罚处罚的对象是犯罪人而非仅仅行为本身。在量刑阶段充分考量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实现刑罚的针对性,更有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报应并非刑罚的唯一目的,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报应作为刑罚的目的已经逐渐淡化,代之以教育和转化目的,以帮助被告人重新回归社会。因此,在量刑阶段充分考量被告人的品格,有助于实现刑罚的教育和转化目的。但应以被告人良好品格的适用为主,限制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运用,以体现刑法的人文关怀。
3.4 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刑事案件中对被害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并未有明确的限制,而被害人的品格往往涉及到被害人的隐私权,典型的如强奸案件。我国强奸案中没有针对被害人人性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这种滞后导致了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是否采用以及如何采用性品格证据具有极大的裁量权[5]。同时,刑事案件中的辩方在辩护中也会尝试向法院说明被害人不佳的品格,从而将案件的发生原因归责于被害人,或者作其他证明目的。司法实践中的“重打击,轻保护”理念导致对被害人保护的不足。如果不加限制,被害人的这些隐私将会受到极大的侵犯,使被害人无法正常回归社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因此,有必要权衡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规范控辩双方对被害人品格证据的适用。
此外,构建我国的刑事案件品格证据规则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据法体系。平衡“重实体轻程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实现程序和实体双重价值的并重,这也是司法实践的需求。品格证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也有现实基础。
4 构建我国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可行性
4.1 立法及司法解释存在相关规范
我国虽无一般的品格证据规则,也无品格证据一词的使用,但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存在着关于品格证据的运用,比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九十条③及2013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三百九十三条④都提到了被告人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显然,被告人曾受过刑事处分这一事实便属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虽然立法并未明确品格证据,亦未有品格证据排除的理念,但至少具体的品格证据在法律中得到了反映。因此,在构建我国的品格规则时完全可以延续这样的路线,以形成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比如,限制起诉书中关于被告人前科的记录。
4.2 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
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对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较为普遍。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会充分考量嫌疑人的日常行为习惯等品行,以确定是否暂缓起诉。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时也会调查被告人的社区评价、行为习惯等,以实现量刑的个别化,以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尽快回归社会。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被告人的前科,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都会查询嫌疑人是否存在犯罪前科。这些实践可以为我们构建一般的品格证据规则提供借鉴,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发现我国品格证据的实践存在哪方面问题,从而为建立品格证据规则提供方向。
4.3 一元化审判形式亦可构建品格证据规则
品格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基于陪审团的二元化审判组织形式。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一元化审判组织形式不具有构建品格证据规则的条件。即使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排除”了具有偏见性影响的证据,该证据对法官的自由心证已经产生了影响,缺少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而引入品格证据规则,难以达到相应的效果[6]。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虽然我们不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但是证据可采性规则在法官审判中仍然有其市场[7]。陪审团并非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基础,我们可以限制检察院在起诉时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比如禁止列举被告人的前科事项,而只在量刑阶段向法官开示被告人的前科事项,以辅助法官的个性化量刑。
5 品格证据规则的具体构建
5.1 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
第一,定罪阶段中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规则。应从一般的排除规则开始,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及出庭支持公诉阶段不得首先提出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证据。比如,不得在起诉书中列举被告人前科,而只能在被告人提出自己良好品格证据的前提下提出针对性的品格证据予以反驳。即,提出品格证据的主动权在被告人一方。其次,法官应当明确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与待证的犯罪事实之间欠缺足够的相关性,并会给审判者带来偏见,应不予采纳。检方使用品格证据的例外情形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比如,盗窃罪中多次盗窃的情形,属于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检方可以使用。
第二,量刑阶段中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现代司法在量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这就包含了犯罪人的日常行为习惯、人身危险性等品格特征,以实现个别化的量刑,避免犯罪人对社会公众的侵害,也帮助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我国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通过社会调查获取的关于未成年人的个人成长经历、行为习惯等品格证据是量刑阶段品格证据运用的良好实践,可予以扩大适用。
5.2 被害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
被害人的品格往往由辩方提出,以试图说服法官,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存在过错。典型的如强奸案中,对被害人性品格证据的使用牵涉到被害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如果不加规制,被害人的隐私权将受到侵害。笔者认为,应根据案件类型构建具体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性犯罪案件,应当对任何一方提出被害人性品格证据进行严格限制,包括禁止提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前的性关系证据以证明是经过同意的;并且应当禁止提出被害人生活作风不佳,或者曾从事性服务工作等品格证据,以免给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对于故意伤害类案件,如果被告人首先提出被害人生性好斗的品行,以此证明自己属正当防卫,则控方也有权提出被告人相关的品格证据以反驳之。
5.3 证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
证人的概念在西方两大法系有所区别。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包括当事人、专家证人及知晓案情向司法机关陈述的第三人,范围广泛;在大陆法系国家,证人专指知道案件情况而向司法机关陈述的第三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8]。所以我们在构建证人品格证据规则时,可以扩展适用于专家证人和当事人。证人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是为了查明证人的可信度,如果一方当事人对证人的可信度持有异议,可以提出证人的品格证据,但仅限于证明证人的可信度,并且这种允许还要考虑证人的隐私权保护。
5.4 配套制度的完善
品格证据规则并非独立运行,仍需其他配套规则予以辅助才能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实现品格证据规则的价值。
第一,完善品格调查制度。品格调查已经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基础,但仍需进行细化规范。首先,调查主体的规范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⑤。《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也作出类似规定。然而具体的调查主体并未明确规定,因此需要确立专门的调查机构,提升社会调查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同时也能很好地保护被调查人的隐私权。其次,规范调查内容。对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调查应当限于对被告人量刑有主要作用的品格证据上,比如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等,要防止对被告人隐私权的侵犯。最后,规范调查的方式。具体的调查方式应予以明确规定,比如可以采取会见、走访、档案查阅等。特殊案情可以采取特殊方式,比如阅卷调查、人格测量等。
第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品格证据规则同样拘束证人,如果证人不出庭,则该规则便失去了规范意义。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证人多出于担心被告人的打击报复,以及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费用等而不愿出庭作证。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构建专门的证人保护制度。当前法律赋予了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可借鉴用于证人保护。此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应予以具体化,证人出庭费用的负担应明确承担主体。最后,可以构建拒绝出庭作证的制裁规则,对拒不出庭作证者予以司法制裁。
第三,完善违反品格证据规则的制裁程序。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则如同缺少车轮的车子,是无法运行的。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和落实需要法律后果为保障。比如,对于检察院向法院提交的载有被告人前科信息的起诉书,法院可予以退回。在庭审中对违规使用品格证据的一方可采取训斥、罚款等处罚措施。
6 结语
品格证据在刑事审判中并未直接改变事实的认定,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中立法官对被告人的认知,从而可能导致法官对被告人形成潜在的偏见,影响法官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我国刑事司法普遍存在对品格证据的运用,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未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排除庭审中不适当的品格证据,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即“为证明某人在具体场合按其品格行事而提出有关此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②宋洨沙.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品格证据之比较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2(5).
③该条规定:“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二)是否受过法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时间。”
④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的,应当制作起诉书。 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否受过刑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和时间,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等。”
⑤具体规定如下:“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
[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7.
[3]崔起凡,姜剑涛.美国品格证据规则的解读与借鉴——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1(8).
[4]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48.
[5]王禄生.美国性品格证据适用规则之借鉴[J].法学,2014(4).
[6]崔起凡,姜剑涛.美国品格证据规则的解读与借鉴——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1(8).
[7]易延友.最佳证据规则[J].比较法研究,2011(6).
[8]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61.
责任编辑:卢宏业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in China
LI Qian-long, ZUO Tia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Exclusionary rule of character evidence arises from Anglo American adversarial litigation model.Because of possible infringement of the defendant′s fair jurisdiction, character evidence was ruled out by the court. The existence of the character evidenc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practice in China is out of the constraint by the systematic rules. The defendant will face moral judgment with the use of character evidence,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fair trial will be violate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criminal character evidence in China. Application of character evidence of juvenile defendant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to construct the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in China.
Criminal trial;Character evidence; Right to a fair trial; Probative value
10.3969/j.issn.1674-6341.2017.03.025
2016-12-13
李前龙(1990—),男,河南周口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D925.2
A
1674-6341(2017)03-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