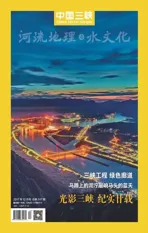河流与青草
2017-02-05安歌编辑任红
◎ 文 | 安歌 编辑 | 任红

哈萨克族牧民逐水草而居。 摄影/视觉中国
那乐园下临诸河,
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
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
——《古兰经》
从新疆伊犁州昭苏县城到夏塔乡约80公里,从夏塔乡到布拉特草原是15公里。小李是我路遇的北京来的自由摄影人,因为同路,所以搭上了伴儿。本来我们俩是想步行到布拉特草原的,顺便感受一路的草原风光。但这想法遭到了哈萨克司机布尔兰拜的取笑。没有路,他说。然后他补充说,你们根本不认识那些路,草原上的路都是这样这样的。他用手七拐八拐地比画着。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而且,他说,要过两条小河,都有这么深。他用手在身上比画着,开始手比画在膝盖上面,然后就从膝盖比到肚脐那儿。我看得笑了,水在你身上怎么涨得那么快。
布尔兰拜也笑,哎,是这样的嘛,他说,有时候它这么深。他的手比到膝上。如果它一高兴,就这么深。他的手比在肚脐上,然后手停在那儿,他用眼睛里的笑意看着我,这么深的时候,它在谈恋爱。
说得我们都笑了。那它现在谈恋爱吗?
布尔兰拜说,我也不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它想谈就谈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哈萨克语里,布尔兰拜的意思是风。哈萨克族人喜欢用河流、山川、风雨和大地上的生命,为自己命名。
我们上了布尔兰拜的那辆白色北京吉普,去看看那条和人不一样的河水有没有谈恋爱。
草原上的路正如布尔兰拜所说,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而且方向也正如他七拐八拐的手势,布尔兰拜正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他的身体随着方向盘在拧动着,好像他开的不是车,而是一条在波峰浪尖上跳动的船;马达也好像不在横冲直撞的车上,而是在布尔兰拜拧动的身体里,也许不是马达,布尔兰拜身体里就像藏着一匹马。我们的头不时与车顶进行着亲密接触,开始的时候我还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喊,我的腰没有了。布尔兰拜在前面幸灾乐祸地笑:骑马,骑马……他喊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像骑马那样,身体不能紧紧地赖在马背上,而是随着马的颠簸让身体不时离开马背,才可以免除颠簸之苦,好的骑手都是深谙此道的。后来只要前面有大的沟或者坡,布尔兰拜都会提前喊,要飞了,要飞了……这时候他开的好像又不是船了,而是一架飞机。我们随着他的喊声,让身体离开座位。
在布拉特草原上,除了车轧出的道路,确实没有看到一块裸露的地皮。当我们的车驶过那些车辙的时候,飞扬的尘土一路在绿草如茵的草原漫起。有时因为前面的路被石头和水挡住了,司机布尔兰拜就会一下把车拐进草地上去,我心疼那些草,忍不住喊,不要轧那些草!布尔兰拜说,不轧怎么走。然后又安慰我,不要紧,它们会长出来的。
布尔兰拜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只有水手和渔民才敢说爱大海……牧民对草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有真正的牧民,才能说爱草原。因为这一切,触及到他们生命的基础。而我们对草原的爱,哪怕是归家意义上的,其实也就停留在对美的爱与自己的思念上,仿佛对家人和旧照片的爱。
哈萨克人认为春天新长出的青草、树枝、树叶是生命的延续,所以不能随便揪草、折树枝,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报复。在哈萨克人的习俗中,放火烧地、向河水撒尿都是重罪。而揪一把青草,向着苍天诅咒是最恶毒的。如他们的谚语所言:“地上的万物,都是青天的恩赐。”

夏塔古道北入口,它翻越天山主脊上海拔3600米的哈塔木孜达坂,沟通天山南北,是伊犁通南疆的捷径。 摄影/东方IC
对哈萨克人来说,那些“白白得来的”恩赐的草是他们的命之所系,他们对草的珍惜,其实也就是对神灵的恩赐、对自家牲畜、对自己生命的感恩与珍惜。
无论在日常生活或搬迁、转场的过程中,哈萨克牧民对水源和草地都十分爱护,不仅大小便远离水源,连洗衣服做饭也与水源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取水时宁可自己费时费力,也不对水源做任何改动,一切保持原始自然;他们居住过的宿营地,从未见过裸露的地表,也没有任何垃圾。虽然生活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但他们也不随便埋葬他们的死者,他们在春夏秋冬牧场分别有着专门的墓地。从来没有人强行规定他们这样做,但每一个哈萨克人都自觉遵守着这些——这是哈萨克人和草原之间的一种契约,是和草原祖祖辈辈一起共存而产生的一种骨肉亲情。
哈萨克人崇拜独树,生长在荒野上的独树是尊贵的,不能毁坏和砍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传说中独树支起了哈萨克人的天空和大地,抑或是哈萨克人逐水草而居的不断迁徙的生活本身就是孤独的,对独树的崇拜,或许也是哈萨克人对孤独的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理解。
车开到了河边,水面不宽,也就四五米的样子,水色是白的,水流非常急。对面有一对骑摩托车的青年,从他们卷起的裤腿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下水测过水的深度,显然摩托车是无法通过的。布尔兰拜用哈萨克语和他们讨论着水势。

昭苏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海拔在2000米左右,是一块群山环抱的高位山间盆地,冬长无夏,春秋相连,是新疆境内唯一一个没有荒漠的县,以出产“腾昆仑,历西极”的天马著称,也是新疆乌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摄影/视觉中国
我问布尔兰拜,咱们的车能过吗?
现在不行,布尔兰拜说,它们正恋爱得厉害呢。
那它们什么时候不谈恋爱了呢?我问布尔兰拜。
谈着谈着就不谈了,水和人一样嘛,布尔兰拜说,人也要做饭,放羊,不能光谈恋爱,水也不会光谈恋爱的。
不时有人骑马渡过河水,我指着摄影师小李问带我们来的乡村司机布尔兰拜:“你能不能问他们借一下马,我和他,让我们先过去?”
“你们?”布尔兰拜笑了,“你们不行,你们骑,马就不走了。”
这让我想到诗人周涛讲过的一件往事。
周涛是会骑马的。年轻的时候,他因有急事骑马到另一个村去,傍晚遇到一条涨水的河。马死活也不愿意渡河。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哈萨克帐篷,就打马过去,寻找帮助。打开帐篷发现里面只有一位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大概有八十多岁了。周涛喝着她倒的茶,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心想今晚过河可能是无望了。没想到哈萨克老妇人听了他说的情况后,立马站起身来,带他到河边。哈萨克老妇人拉着自己的马,侧身跨上周涛的马,周涛那匹先前面对河水胆怯不前的马突然全身一闪,仿佛通了电,平稳地踏入了河水。马从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双腿夹紧的动作里,得到了指令,知道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骑手——哪怕她已经八十多岁,哪怕她非常瘦小,但马不管这些,它只认真正的骑手,需要从真正的骑手那儿找寻勇气的。
在哈萨克族的人生礼仪里,对一个男孩而言,他所要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礼仪就是他的出生礼“齐勒达哈纳”,第二个重要的人生礼仪就是骑马仪式。哈萨克小孩五岁就开始练骑马了。马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也不仅仅一个陪伴,马和他们声息相通,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们荣誉的一部分。
说着马,河水对面的一个中年哈萨克人对着河水唱起了那首有名的哈萨克民歌《黑走马》:
骑上这种马的时候想到哪儿都可以去
哪里有风哪里就有我黑走马的身影
只要我有梦想
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
站在这片哈萨克草原,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明白,我看到的,是遥远:遥远的河水,遥远的草原,遥远的黑走马,遥远的梦想……重温这味道,可能是我这次回到草原的目的,可能也是所有回归者的目的,在我们无法理解的生活中,理解可能的自己和自己的可能性。人一动起来,那种可能性就开始开放了,逐河流与青草而居的哈萨克人也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