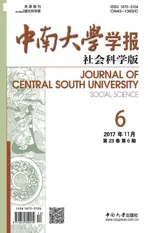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
——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
2017-02-03潘泽泉杨金月
潘泽泉,杨金月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性差异与“强弱关系”不平衡性效应分析——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
潘泽泉,杨金月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一直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强度结构往往被忽略。文章运用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基于资源提供的农民工的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网络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缘关系不再是农民工维持社会网络边界的依据,友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重要依赖资本;农民工整体上与城市居民处于隔离状态,存在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其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不同影响。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内部构成;强关系;弱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1],关注的是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它构成了人与人连接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社会援助体系。借助于社会网络,个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获取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指导、建议和信息,从而对个体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2]。尤其是在当前正式制度支持缺位或不足的语境中,人际关系网络是流动农民工获取资源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依赖资本和路径。“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3],跨地域、职业和阶层的流动极大拓展了农民工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业缘、友缘、趣缘等连接纽带被纳入生活实践,“农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社会联系愈多,他们整合于和融入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高”[3]。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网络的重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涵,融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进行专门的学术性研究、提出专业性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走出农村、脱离乡土生活场域的流动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强关系存在于农民工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他们的信息来源、找工作的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4],使农民工社会网络整体上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 低”[5]的特点;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基本事实对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持续影响,生活场域和职业场所的高流动性使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不断的裂变和重构状态,具有高异质性的弱关系逐渐进入生产和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入的有效路径。那么处于裂变之中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结构怎样?在“强关系——弱关系”视域下又会呈现何种特征?除了受现代化、城市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外,还存在哪些影响因素?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二) 相关文献回顾
1. 关系强度——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范式
“网络分析在社会关系层次上将微观个体和宏观结构联系起来。”[6]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关系的力量》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文献,通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研究,他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四个指标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7−8]。强关系产生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不同类型的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因为弱关系的分布范围更广,通过弱关系更能跨越群体去获取信息和资源,实现信息在不同群体间的流动,相较而言,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而且他认为,人们是出于理性的需要才去发展和使用弱关系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这是他“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核心依据。
林南在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中发展和修正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他认为在分层社会结构中,通过弱关系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跨阶层流动,如果弱关系对象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它将比强关系带给行动者更多的资源,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成员间关系的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9]。边燕杰将关系力量研究引进了国内学术领域,他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的运用,认为通过求职者个人社会网络流动的是工作分配决策人的影响力而不是就业信息,在工作分配中,人情关系的强弱将引起分配结果的明显差异,工作更多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10]。
2. 裂变与重构: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社会网络研究在国内的起步较晚,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研究是其中一个热点议题。李培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工具性地运用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亲缘关系网络”存在于他们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制度安排的惯性造成了农民工生活地域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 离[4]。天然性、同质性和乡土性是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11],传统“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农民工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成本,但却难以提供城市资源,重构社会网络成为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然[12]。渠敬东采用农民工生活轨迹的“生存——发展”分析框架,考察了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认为在生存阶段,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提供了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社会资本;在发展阶段,除了“强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外,农民工还必须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13]。李汉林认为“农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社会联系愈多,他们整合于和融入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高”[3],因此,积极拓展“弱关系”网络,形成“强关系——弱关系”结构合理的新的“差序格局”,对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已有文献中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具有突出的数量化特征,相关学者将社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或影响变量,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5−6]、生育性别偏好[14]、社会排斥感[15]、城市适应[16]、生活满意度[17]、城市认同[18]、社会融合[19]等做出了良好的解释。
目前关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探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重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特征分析,缺少内部结构研究。本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入手,探讨在以发展弱关系为目标的分析框架内,农民工人际关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强度结构,并对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思考。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2年6月至9月进行的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融入社区、融入企业、融入学校)状况调查,该调查的抽样总体为湖南省地级市所有流动农民工,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仍持农村户籍,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为确保抽样的准确性和样本代表性,此次调查从湖南省的14个地级行政区中抽取了7个地级市(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娄底、衡阳和湘西州),并以PPS抽样随机抽取了10 000个样本。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 987份,删除含有本研究所用变量为缺失值的个案,最终得到9 179个样本用于统计分析。此次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个人基本信息、就业、子女教育、社区融入等多方面信息,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从样本的基本分布来看,此次调查对象以地域内流动为主(60.18%),非本地市户籍的占39.82%;性别结构中男性占多数(60.18%);未婚或同居的占30.79%,大多数已有婚姻经历(68%);有务农经历的有6 669人(72.7%),“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民工占多数,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元结构中的流动劳动力有很强代表性。
(二) 变量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交往性 网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关系强度,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正式福利制度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支持,按照农民工从中获取的具体支持内容对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类型划分,具有充分的理论传统和现实价值。范德普尔将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取的支持分为情感支持(与配偶有矛盾时舒解、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实际支持(家务劳动、患病时帮助、借钱、借生活日常用品、帮助填表)和交往支持(一同外出、拜访)三大类型[2];张宏文、阮丹青从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20];王毅杰、童星把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交往支持三种,并操作化为7个问题进行了测量和分 析[5]。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情况,本文以农民工从关系网络中获取的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于问卷中“当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来谈?”“当经济上有困难时,您一般向谁借钱?”和“在城市,您经常交往的对象是?”三个问题,要求被访者从“亲戚”“老乡”“同事”“朋友”“城市当地居民”和“其他”六种关系类型中选择一个来回答。
关系强度命题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议题,格兰诺维特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产生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边燕杰根据再分配体制下的人际关系特征,将求职者的社会关系分为相识、朋友和亲属三类,并把前者定义为弱关系,后两者界定为强关系;王毅杰、童星则仅将亲属关系称为强关系,而把朋友关系作为中间型关系;也有学者在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时将亲缘和地缘关系作为强关系,把友缘和其他关系归为弱关系。[14, 19, 21-23]为深入观察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力量差异,本研究将问卷设计的六种答案进行连续化处理,分别赋值为1=亲戚;2=老乡;3=朋友或其他;4=同事;5=城市当地居民,分值从低到高代表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渐进变化,得分越高代表农民工“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的关系类属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越大。
2. 自变量: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经济地位特征
结合以往研究经验,文章将从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经历、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得五个指标;流动特征用流动距离、流动时间、职业稳定性和居住稳定性四个指标来描述,其中流动距离用“是否持本地市户籍”来测量,流动时间是指进城务工时间,职业稳定性和居住稳定性分别操作化为在务工地“是否换过单位”和“是否换过住处”的二分变量; 经济地位特征包括平均月收入(取对数)、工作岗位两个指标,其中工作岗位赋值为1=管理人员;2=技术工人;3=普通员工。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三) 分析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和关系强度,为此文章先描述分析农民工三种社会网络的关系类型分布,然后再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农民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因素。具体模型为:

其中是因变量,代表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是截距,是模型无法解释的随机误差,回归系数分别表示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作用,即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目标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弱关系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描述性分析
表2给出了农民工三种社会网络的关系属性分布。总体上来看,城市当地居民在农民工的三种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比例都很小,整体上处于一种群体隔离状态,朋友关系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要依赖资本,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主要由朋友关系构成,通常向亲戚或朋友寻求工具性支持,朋友和同事是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交往对象。具体而言:(1) 当心情不好时,有54.5%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向朋友倾诉,而选择向亲戚和老乡倾诉的均不到12%,说明亲缘和地缘等先赋性关系不是农民工获取情感支持的主要渠道,这与张宏文、阮丹青[20]在1999年对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研究结论相似,即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到家族关系之外寻求精神支持,与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从亲属获取精神支持的特征相反。同时,被调查对象选择向同事倾诉的也只有15.6%,流动后的业缘关系并不能向农民工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2) 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分别约有43%和34%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向亲戚和朋友借钱,亲缘关系仍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要经济资本,与李树茁等[21, 22, 24]的经验发现一致,同时朋友在农民工的实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选择向老乡和同事借钱的分别只有8%和约11%,地缘和业缘关系不是农民工获取工具支持的主要渠道。(3) 农民工交往性网络的关系属性分布相对较为平均,约32%和37%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朋友和同事作为在城市的主要交往对象,选择亲戚和老乡的分别有10.3%和12.2%。相较而言,农民工在城市交往对象的关系强度差异不大,突破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界限,选择跟同事、城市当地居民(6.2%)交往的比例较大,在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中,同事关系分别占15.6%和11.2%,“城市当地居民”均只有0.36%,说明农民工的跨地域、职业和阶层流动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事实,极大拓展了其社会交往范围,社会联系的广泛性显著提高,但“身体”进城并不代表对城市生活的完全适应和融入,在情感、经济等维度上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仍处于隔离状态,弱关系的资源提供仍显薄弱和不足。

表1 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n=9179)

表2 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属性分布(%)(N=9 179)
(二)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回归分析
农民工从传统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也是他们拓展和维护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逐渐被削弱、弱关系的逐渐生长和扩张。以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基础,结合以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从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三个方面,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影响因素,具体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1. 个体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影响
(1)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结构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分别比女性农民工低11.7%和9%,但男性农民工的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却比女性高12%。(2) 年龄对农民工的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普遍影响,年龄越大,由强关系构成的可能性越大。15~24岁、25~34岁两个年龄组对三个因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0.01水平上显著,都为正且15~24岁组的回归系数更大,说明控制其他因素后,15~24岁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25~34岁年龄组,35岁以上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来自弱关系可能性最小。(3) 婚姻经历对农民工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的强度结构影响显著,而对其交往性网络的作用不显著。婚姻经历对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控制其他变量后,与没有婚姻经历的农民工相比,有婚姻经历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由强关系构成的可能性更大。(4) 正式学校教育和证书获得对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构成具有普遍正向影响,但正式学校教育对工具性网络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数字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后,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越大;与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相比,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从弱关系获取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支持的可能性分别高出4.3%、9.1%和8%。

表3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注:***<0.01, **<0.05, *<0.1。
2. 流动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影响
(1) 流动距离对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可能性的抑制作用显著,对与弱关系对象经常交往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与本地市的农民工相比,非本地市农民工从弱关系获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的可能性分别低9.1%和0.6%,流动距离是影响农民工情感性网络(0.01)和工具性网络(0.05)的显著变量,但对其交往性网络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2) 流动时间对农民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不同,对“情感性网络”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的作用分别在0.05和0.01水平上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从具体统计结果来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的务工时间每增加一年,他们的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分别下降1%和提高2.4%。(3) 职业稳定性对农民工的情感性和交往性网络的关系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对其工具性网络强度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具体而言,控制其他因素后,在务工地换过工作单位的农民工的情感性和交往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比没有换过工作单位的农民工分别低5.3%和高4.9%。(4) 居住稳定性仅对农民工的交往性网络有显著影响,对其他两种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没有换过住处的农民工相比,换过住处的农民工选择与弱关系对象经常交往的可能性 更低。
3. 经济地位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影响
(1) 月收入水平对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结构均有显著作用,但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同。具体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月收入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从弱关系摄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的可能性分别增加4.3%和15.4%,但获取交往性支持的可能性会降低9.4%。(2) 农民工情感性和交往性网络的强度结构有显著的工作岗位差异,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从管理人员到技术工人再到普通员工,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岗位每下降一个等级,其情感性和交往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将分别降低2.6%和3.7%。但工作岗位对农民工的工具性网络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资源提供和保障性功能入手,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三种类型,并把其放进“强关系——弱关系”的分析框架内,在进城农民工以培育和发展“弱关系”为理性目标的话语背景下,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探讨了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及影响其强度结构的可能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如下。
一是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类型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与以往研究关于农民工“生活地域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4]和强关系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要依赖资本[5, 11, 12, 15, 22]的结论不同,文章发现农民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模式不同。亲缘、地缘等传统性关系不是农民工情感性和交往性支持的主要来源,但“亲戚”依然是农民工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求助对象;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社会资本的业缘关系仅是农民工交往性网络中的首要关系,其在另外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仍占有很小比例。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和市民化的多层级、分阶段的渐进性特征相似,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并非具有天然的整体性特征,而是在实践的动态发展中存在较大的构成性差异,在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中,先赋性与后致性关系、强关系与弱关系会呈现不同的分布形态,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因此也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是地缘关系不再是农民工维持社会网络边界的依据,友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重要依赖资本。在农民工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朋友均占有较大比例(30%以上),与张一凡、冯长春[23]对北京市农民工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与之相反,老乡所占比例均较小(最高只有12.2%),地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弱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朋友”“老乡”概念在日常生活使用中的模糊性所致。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社会有一种攀亲戚、讲交情的人际关系现象,“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社会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方式普遍盛行,关系密切、来往频繁非亲属关系的可以称为朋友,一面之缘、有利可图的也可以是朋友;老乡也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概念,出了门不但同属一个不同级别行政辖区的可以称为老乡,甚至同一个语言系统、遵循同一套做事标准的也可以是老乡,所以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结果,宏观结构性变迁带来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基本事实,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相应具有了流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内容、结构、规模、异质性、网络资源含量等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先赋性、强关系的弱化,后致性、弱关系的发展是这一变化的本质内容。
三是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关系网络,存在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走出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生活场域的农民工整体上与城市居民处于隔离状态,数据显示,仅有6.17%的被调查农民工选择城市当地居民作为经常交往对象,甚至在他们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中城市当地居民所占比例均只有0.36%。如果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视为一个从强到弱的连续统的话,除了交往性网络的强度结构稍显均衡外,强关系在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仍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仍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资源能力弱,存在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这将进一步强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的“内敛性”和“趋同性”,使其囿于内群交往和阶层内流动而引起群体偏见、歧视、拒斥性认同和社会地位固化,加剧农民工社会融入和市民化的难度和复杂性,甚至助长贫困、失范行为等社会问题的内卷化。
四是除了年龄、教育、工作岗位和劳动时间存在普遍影响外,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有不同影响。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含有弱关系的可能性整体上高于男性的结论不同[22],男性农民工的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这可能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具有普遍的性别差异有关;教育,特别是职业资格证书获得对农民工从弱关系摄取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印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25];年龄越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越低,说明老年农民工在社会关系网络重构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对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转型是个重大挑战;婚姻经历抑制了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说明姻亲关系的加入而使亲缘关系范围扩大,限制了农民工从弱关系获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的可能性;事实上,流动时间的增加、单位转换和住处转换经历并不总是会带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反而会对农民工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客观经济收入对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与弱关系对象经常交往的可能性,印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26]。
农民工是当前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弱势群体,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依赖资本,甚至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过程本身就是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入过程,融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是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为此,本研究建议:(1) 政府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重构的主导力量,应该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在教育、就业、住房、卫生、医疗等多方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从“生 存——经济”到“身份——政治”的社会政策转向 ,从制度上根除城乡差异,消减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改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和市场能力。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多是自发和自组织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通过正式就业渠道的少,因此,应该完善制度安排、孵化专业社会组织,为流动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和职业培训,消除和疏导流动中的社会问题,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2) 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是农民工在城市的落脚点,必须关注到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性、职业的不稳定性和分割性,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场域中的“空间实践”,即他们在城市的人际关系状况。在社区建设中,构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机制和交往平台,调动农民工积极性,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提高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实现农民工在城市“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双重转变。 (3) 作为社会网络重构实践主体的农民工个人,也应积极参加如职业大学、夜校等社会成人教育,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并获得证书,提高个人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增加资本存量。关注务工地的城市建设和社区建设,积极参加公共活动,发展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突破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界限,弱化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关系的作用,实现“强关系——弱关系”结构合理的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转型。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之处:农民工社会关系强度结构的操作化是本研究的基础,但出于量化研究的要求,只能将原本极具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概念操作化为几个具体的、相对简单的测量指标。这样的操作化过程及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由于受研究者学识水平和实际条件的限制,只是多种可能性研究路径中的一种。另外,此次调查所观测到的影响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因素是否具有普遍解释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最后,本文旨在用有限的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和强度结构,而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重构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复杂过程,对其实践图式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大样本的追踪研究。
[1] Mitchell J. CReay.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C]// Mitchell J. CReay.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69: 1−50.
[2] Mart G M. van der Poe1.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J]. Social Networks, 1993, 15(1): 49−70.
[3] 李汉林. 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C]//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 1996(4): 42−52.
[5] 王毅杰, 童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2): 42−48.
[6] 李树茁, 任义科. 中国农民工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3): 19−29.
[7]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73, 78(2): 1360−1380.
[8] Mark 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Second Edi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5, 81(1): 264.
[9] Lin Na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 Connections, 1999, 22(1): 28−51.
[10] Bian Yanjie.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385.
[11] 司睿.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J]. 社科纵横, 2005, 20(5): 133−134.
[12]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 社会学研究, 2003(3): 99−110.
[13] 渠敬东. 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4] 李树茁, 伍海霞.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基于深圳调查的研究[J]. 人口研究,2006(6): 5−14.
[15] 陈黎. 外来工社会排斥感探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 社会, 2010(4): 163−178.
[16] 陶菁. 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7): 201−204.
[17] 马丹.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J]. 社会, 2015(3): 168−192.
[18] 蔡禾, 曹志刚.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48−158.
[19] 悦中山, 李树茁.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J]. 社会, 2011(6): 130−152.
[20] 张文宏, 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 社会学研究, 1999(3): 14−19.
[21] 李树茁, 任义科.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8(2): 1−8.
[22] 李树茁, 杨绪松.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67−76.
[23] 张一凡, 冯长春. 进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建筑工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12): 111−120.
[24] 李树茁, 杨绪松.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1): 25−33.
[25] 赵延东, 王奋宇.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4): 10−17.
[26] 潘泽泉, 林婷婷. 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3): 108−115.
Analysis of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d imbalance effect on “strong-weak tie:” Based on a surve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ree Inclusions” in Hunan province
PAN Zequan, YANG Jinyu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have received clos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s a fundamental issue. But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and the strength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s have been ignored. Based on a surve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ree Inclusions” in Hunan province, the present essay establishes a serie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ntimental, instrumental, and contact networks in terms of resources supply, that geographical relation no longer maintains the boundary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that friendship relation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dependable resources, that migrant workers are isolated from city residents, where exist widespread imbalance effects between “strong-weak tie,” and that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in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networks.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ternal structure; strong tie; weak tie
[编辑: 胡兴华]
2017−04−20;
2017−06−25
201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4JZD015)
潘泽泉(1970−),男,湖南武冈人,博士,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社会心理与行为;杨金月(1986−),女,河南新乡人,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分层与流动
C91
A
1672-3104(2017)06−0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