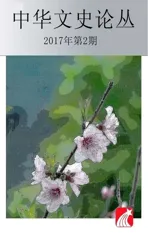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2017-01-28劉大立
劉大立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劉大立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 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關鍵詞: 劉錫鴻 海防籌議 英軺私記 臉譜化 心理矛盾
一 臉譜化的劉錫鴻與真實的劉錫鴻
雖説在晚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比起那些左右時局的人物來説,劉錫鴻正如《走向世界叢書》主編鍾叔河先生所言“其人無足稱述”。*鍾叔河《“用夏變夷”的一次失敗》,劉錫鴻《英軺私記》,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12。但是在他身上卻彙聚着“守舊”與“改革”兩股潮流的激烈衝撞,他的一生行止和所留不多的著述是我們進入歷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晚清歷史温度和深度的最好途徑。劉錫鴻(約1822或1823—約1883或1884),廣東番禺人,原名錫仁,字雲生。出身貧寒,但“魁岸負氣,有不可一世之概”,考取舉人後便入幕府,對内平亂緝匪,對外抵禦英國軍隊,“克復廣州東炮臺”,因戰功而“獎刑部員外郎”。光緒二年(1876),出任駐英國副使。因與正使郭嵩燾不合,調駐德國正使。四年,回京,任光禄大夫。後參劾李鴻章,以“妄議”革職。著有《英軺私記》,奏摺、書信等編入《劉光禄遺稿》二卷,刊刻行世。*《劉錫鴻傳》,《碑傳集三編》卷一七,《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頁1721上—1722中;《清史稿》卷二一二《交聘年表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785—8788。
劉錫鴻任職京都時,與洋務派主要人物李鴻章、郭嵩燾、丁日昌等討論内政外交及洋務等問題,寫下了《復李伯相書》、《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録辛未雜著二十二則寄答丁雨生中丞見詢》等書信,闡述了自己的政見。*見《劉光禄遺稿》卷二,《清代詩文集彙編》(68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768下,773下,779下,796上。劉錫鴻一生事業中最輝煌的階段是出任了首任駐英公使的副使,寫下了《英軺私記》,這是他一生中影響最大的著述。回國後,劉錫鴻在官場中頗感寂寞,他不斷寫成各種奏摺上陳朝廷,希望引起注意,其中直接影響了清政府決策的就是《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摺》。*《劉光禄遺稿》卷一,頁759上。但是上奏並未改變他的境遇,他在一腔怨憤中不自量力地上書彈劾李鴻章,遭慈禧太后下諭革職,徹底斷送了自己的仕途,以與洋務派對立的形象終其一生。
大約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劉錫鴻漸漸引起了學界的興趣,不僅在討論晚清歷史的各種論著(包括中國臺灣學者和日本學者的論著)中不斷被提起,專門研究他的論文也日漸增多,甚至出現了以劉錫鴻爲研究對象的專著。但是通觀這些論著,我們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都習慣於這樣一種研究模式,那就是首先確立“洋務派”和“守舊派”這對立的兩極,然後將所研究的對象歸爲其中的一極,對劉錫鴻而言那當然是守舊派甚至是頑固的守舊派一極。接着就從守舊派應有的屬性出發去觀察描述分析劉錫鴻的行止言論,力圖使他與守舊的形象保持一致,“劉錫鴻的守舊思想”也就成了這些論著的出發點和歸宿處。可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於,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劉錫鴻的身上有越來越多的與守舊派角色不一致的地方。然而在這種研究模式中,學者們還是堅持從守舊定位出發的立場去解釋這些不一致的地方,認爲劉錫鴻是“變而不化”,*葛志華《論“劉錫鴻現象”》,《南通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只不過是“保守中的趨新”,*任雲蘭、熊亞平《保守中的趨新——劉錫鴻反對修建鐵路思想之再分析》,《學術研究》2009年第9期。或者是“一個保守者的思想轉變與堅守”、“保守思想的嬗變”,*李娟《一個保守者的思想轉變與堅守——〈英軺私記〉中劉錫鴻的科學觀》,《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斷定他雖然“置身於不同國度,浸潤在不同的文明中”,“受到的刺激更直接、更猛烈”,“他的思想變化”也“更具代表性”,卻仍然無法跨越“崇古尚禮的藩籬”。*王雅娟《内外回應的展現——劉錫鴻保守思想嬗變研究》,《前沿》2013年第11期;王雅娟《無法跨越的藩籬——劉錫鴻政治思想研究》,《社科縱横》2013年第11期。由於已經貼好的“保守派”標籤,再怎樣變化也不過是保守的微調而已。更有甚者,即使是明顯背離保守思想的舉措,例如劉錫鴻宣導開礦而且是主張民采以“利民利國”,與李鴻章爲開源籌餉而“開煤鐵各礦”的計畫不謀而合,也因爲已經加給劉錫鴻的“保守派”標籤而被扭曲,説“他開礦的動機不是爲了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生産,而是從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秩序出發”,所以,“儘管他的開礦思想不自覺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但仍舊屬於保守主義的範圍”。*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85。難道開礦時招標承包鼓勵民營(詳見下一節)不是刺激資本主義因素嗎?顯然這是戴着有色眼鏡看問題,視改革進步爲保守落後。
另外一種見解則是在研究對象上進行所謂的“一分爲二”,但是所分出的“二”彼此並無關聯。例如認爲劉錫鴻身上與守舊思想不一致的地方是“洋務思想與反洋務思想的交相雜糅”,*宫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或者是“變與不變的交替”、“開明與保守的混合”。*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第六章第二節,頁288,290。“雜糅”、“交替”、“混合”這些詞的使用似乎進了一步,增加了劉錫鴻身上與守舊不一致的思想成分的比重,卻不能解釋它們何以能與守舊思想同處於一個大腦之中。
如此看來,這樣的研究模式向我們呈現的只是一個個臉譜化的人物類型,無法深入到這個人物的内心去探求真實。在分析一個歷史時期的風雲變幻、大勢走向時確實有必要將臺上人物概括成簡單的類型來探求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對局勢的左右,但是當研究的目光定格在一個具體人物身上時,我們期待還原出的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生活過來的活生生的“人”,他有血有肉有豐富的以至矛盾着的内心世界,他有可能大聲疾呼着保守派或者洋務派的口號,心中卻有另一種聲音在糾葛不清,也有可能出於個人利益而在“保守派”和“洋務派”這兩極之間趨利避害難以作非此即彼的抉擇,從而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話語場景中發出不同的聲音。
就劉錫鴻而言,他一生行事並不複雜,但他的内心世界卻由於特定的人生經歷和特殊的性格特徵而充滿着糾結。本文通過史料的爬梳解讀,發現決定他一生言論行止的其實是兩重始終難以克服卻又在不同環境中此消彼長的矛盾,導致他經常顯現出保守派的形象,某一階段又會站在洋務派改革的立場上,而在呈現出改革傾向時卻又不忘喋喋不休一番守舊的話語。這雙重矛盾一是政治理念上的: 劉錫鴻其實是一個有眼光有才幹的官員,他雖然意識到了洋務、改良纔是出路,卻又執念於大清“政令統於一尊,財賦歸諸一人”的體統,*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91上。這兩種思想始終此起彼伏並存於他的内心;另一則是個人性格上的: 劉錫鴻是一個缺少政治操守、品行有虧的人,儘管有了清醒的認識,但是左右他的是不同情勢下怎樣的立場纔能有利於宦海仕途的通達。抓住這兩對矛盾纔能深入其内心世界,解釋他的一生。
二 政治理念上的矛盾: 早期劉錫鴻的另一種解讀
(一) 劉錫鴻與洋務思想的一致
除了王闓運《湘綺樓日記》、《郭嵩燾日記》之類零散雜記之外,劉錫鴻在出使前關於洋務的言論,主要體現在他參與由恭親王奕訢發起的關於“海防籌議”大討論而寫下的《復李伯相書》、《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等書信,尤其是《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中有更爲集中的表達。不少學者僅憑其中的部分表述就將劉錫鴻定性爲守舊派。的確,這些書信中確有不少相當保守的意見,例如重農抑商,例如反對製造或購買船炮,例如倡節流反開源而反對造耕織機器辦招商輪船等等。但是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到,其中亦有不少完全可以定性爲對洋務派認同的意見,試歸納如下:
首先,是關於對外開放的總體大勢的認識。他説:
互市之局已成,此時萬難閉關。且以造化之理推之,中土生齒太繁,勢須拓地外洋,資以生聚。今輪船所過水泥激而成淤,漸變高岸,洋面日狹,來往日繁,百數十年後不難合海外爲一家矣。*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93上。
如果不將“洋面日狹”看作是一種寫實而是關於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關係必將日漸緊密的隱喻的話,我們不禁贊嘆劉錫鴻爲中國和世界的將來描畫了一幅遼闊的前景圖畫。對比只想閉關中土妄自尊大的保守派,可以用“開放”來形容劉氏的胸懷。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也説“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治之。今互市之局千古創見,所以銜勒諸夷者必惟中堂是賴”,*劉錫鴻《復李伯相書》,《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71上。即敏鋭地看到了時代已是“千古創見”的“互市之局”,此語與李鴻章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屬異曲同工。而“非常之人治之”是指李鴻章變法革新的“非常”之舉,雖不免有奉承之嫌,但畢竟表明了劉氏的立場。當然出於他的歷史局限,儘管有了“互市之局已成”這幅圖畫,還是在“聖朝撫馭遐荒,臣僕遠人不分疆域彼被”的視野中勾畫出來的。*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93上。
其次,搞洋務,就必須與洋人打好交道。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守舊派盲目仇外排外將洋人視爲“蠻夷”,又怯於與洋人打交道,“以其爲洋人也而異視之、驚畏之”的心理,他認爲“夫洋人固猶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能視之如中國尋常人,平心定氣以與相接,則無堅不破矣”,洋人“若有挾而求逞兇相向者,則以我固怯退,彼益敢於奮前耳”。*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3下。從中不難窺見劉錫鴻的開朗坦蕩心態。
再者,洋務派痛恨不負責任的“輕言戰爭”的清議,劉錫鴻則以“西洋之事當以和爲主,以守輔和,而戒與輕戰”與之呼應。指出“和戎”是爲了“免民於兵燹”,也是爲了能“以暇日修舉政令,自固本根”,因爲“方今司庫告竭,民力且殫,若復罄厥脂膏示强海外,竊恐外患未至内釁已興”。而“修舉政令,自固本根”之後,“比其有意挑釁萬難俯就,則即以政令之嚴明者督飭將士,用我所長實力守禦,自無不足以卻敵”。*劉錫鴻《復李伯相書》,《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72下,773上。從這些言論來看,他與洋務派有一致的禦外觀。
再次,劉錫鴻明確提出了派遣對外使節的設想,這在當時幾乎是驚世駭俗的。他認爲遣使是“今日要務”,對出使的人“須訪求慎擇,必其人慣辦洋務,或久於吏事,胸有經緯,舌辨(辯)且長者,方可保奏以備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觀念以與洋人交往爲恥,越是守舊越是如此。劉錫鴻則大膽地挑戰這種陋見,認爲符合出使條件的人即便“遠使非其所欲,亦當責以大義,優以曠典而遣之”。*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93下—794上。正是這種見識和勇氣,使他數年以後自己也走上了出使西洋的途程。
最後,劉錫鴻還在開礦的主張上顯示了他與洋務派完全一致的一面。開礦在當時洋務派與保守派的激烈鬥爭中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前者將其視爲“開源”,希望通過開礦來獲得發展洋務、抵禦外侮的資金,同時也是提振工商的一條途徑;後者則竭力反對,認爲“非不獲利於一時”,反而因此聚集了“無業之輩”,在礦源枯竭之後這批人失去了衣食之源而“勢必釀成事端”。*丁寶楨《籌議海防應辦事宜摺》,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頁99。在如此敏感的話題上,劉錫鴻鮮明地贊同洋務派主張開礦,着實令人吃驚和不解。因爲他本身是極力反對“開源”而要求“節流”的,在他日後所寫的《英軺私記》中也不乏反對開礦的言論。但是他確實明明白白地説,開采“各省金銀銅鐵礦及煤礦”有兩利,“蓋無業之民得以開礦,代耕衣食之源有自,利一”,“地獻其寶,物産豐富,其值自不能昂天下,咸嘉賴之,利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認爲不能由官府來開采,而要民營:“仿牙帖之例,募人承領開采,則利民利國,弊亦泯焉”,而且提出了“集衆所願納之數而較多寡,視其最多者許以承充”,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通過招標來承包,結果是“利歸於民,猶儲於國耳”。*劉錫鴻《録辛未雜著二十二則寄答丁雨生中丞見詢》,《劉光禄遺稿》卷二,頁801下—802上。見解之大膽超前,措施之切實可行,這樣的礦業推廣開來,無疑就是在發展工商業,在實現洋務的大目標。
(二) 劉錫鴻的核心思想: 先内治後洋務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即使在造船製器、購買船炮上,劉錫鴻的反對也不能與保守派的主張同日而語。
整體而言,他並非反對造船製器、購買船炮本身,“洋人槍炮精巧足備戰陣之用,非不宜於置辦”就表明了他的態度。*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4下。對主持中樞的改革派首腦恭親王奕訢提出籌議海防六條涉及的問題,他也並不反對,説“籌海方略固所宜講”。劉錫鴻的原則是“處事固有緩急輕重”,“内治未修而徒勤遠略則萬萬不可”,*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4下,793上。“先宜整飭法度,使之必行,然後可及船炮”。*《馬格理論中國無法治》,劉錫鴻《英軺私記》,頁65。可見在他的心目中,“近憂”和“遠略”是分得很清楚的,洋務派所關心的一些問題是遠略,而作爲近憂的“内治未修”如不解決,遠略就是空的。大清帝國已經到了風雨飄摇的地步,單是“堅船利炮”的洋務能挽救它的頽勢嗎?作爲下層官員的劉錫鴻,長期浸潤在政令不行、府庫空虚、吏治腐敗、民風衰頽的社會現實中而對此深有體會,他多次總結説:“海氛之惡由内治無實致之”,*劉錫鴻《復李伯相書》,《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68下。“中國空虚不在無船無炮而在無人無財”,*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5下。“人之慮在外寇,鴻之慮獨在内患也”,*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6上。感嘆二者之間“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85上。
劉錫鴻的遠近觀不無道理。多次戰敗,内治腐敗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後來有了“堅船利炮”,甲午海戰不也是一敗塗地?問題在於如何先解決“内治未修”的問題。一般的觀點都認爲劉錫鴻主張的是“恢復傳統儒家思想統治下的社會秩序,實現内政清明”,*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46。就劉錫鴻連篇累牘的論述來看確實如此,這也是論者將劉錫鴻歸爲保守的重要理由。但是我們發現劉錫鴻對内政的治理或許是另有深意的,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就隱隱透露了一點資訊。他説:“近年日本亦買輪船數具以備販運。然其國之强爲西洋所共畏,不自有輪船始也。”*劉錫鴻《録辛未雜著二十二則寄答丁雨生中丞見詢》,《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73下。生活在京都官場,劉錫鴻不可能不知道鄰國日本在同治七年(1868,日本明治元年)前後發生的“明治維新”運動,而“明治維新”走的正是先解決内治再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不自有輪船始”,就是在有西方利器之前就“其國之强爲西洋所共畏”。寥寥數語之中,劉錫鴻是不是有所暗示呢?
(三) 劉錫鴻思想的結構性矛盾
可見簡單地將劉錫鴻包括他的早期思想歸爲保守並不妥當。上面討論的數篇劉錫鴻所著中,《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是因爲郭嵩燾應奕訢要求寫《條議海防事宜》後“示”劉錫鴻“命評騭其得失”;《復李伯相書》是李鴻章對劉錫鴻“令就時事敷陳所見”,而寫給丁日昌的則是爲了“答丁雨生中丞見詢”。*見《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79下,768下,796上。可見在這些洋務派中堅看來,劉錫鴻遠非頑固不化的守舊派人物,所以纔會向他徵詢意見。早期郭嵩燾曾將劉錫鴻引爲知己,並稱他雖“於世事多未諳悉”,但“於洋務頗有見地”,*《郭嵩燾日記》(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1。也説明了這一點。
如此看來,我們只能説劉錫鴻是一個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的言行確實經常表現出强烈的保守傾向,在這點上我們並不想回避學界大多數研究所描述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應該客觀地看待他與洋務派的一致,而不應淡化、曲解之,或是視爲一種臨時偶發的現象。關鍵的問題在於找到制約這種矛盾的根本原因以解釋劉錫鴻的内心世界。
我們注意到他致郭嵩燾的信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議論,一下子就超越了洋務派當時多所關注的“利器長技”的層面,把注意力落在了“體制”的層面:
洋人之商賈與聞政,官商相保衛,資商力以養兵,非其法較中國爲善也,情形迥不侔也。
核心的一句話是中國與西洋的國情體制“情形迥不侔也”,西洋是:
洋人所謂國主,無異鄉里中之首事(注: 無上下等威之辨);所謂官,無異鄉里中之富室大家(注: 來中國商販多是此等人)。國主由公衆舉(注: 公舉公廢,本族無堪舉者,則求諸他族;本國無堪舉者,則求諸他國,均集衆議明辦理),畀以一定分禄(注: 國主不能全有其國土地,人各墾之而各有之),承辦一國之事而不能專斷其事,遇事則集富室大家及一國之衆而公議之(注: 議事院即鄉約公所之類,國主亦親就其地以聽衆議)。議既成,按貧富各出財力同爲辦理。此則其國主官商之體制,亦即其商賈聞政、合力養兵之由。
而中國則是:
中國天下爲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賦歸諸一人,尊卑貴賤禮制殊嚴,士農工商品流各别。涣汗頒而八方罔不承聽,矧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是;鈇鉞賜而諸侯始得專征,矧其在市儈之賤何得擅蓄甲兵。
兩相對比之後得出的結論是:
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國也!*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禄遺稿》卷二,頁790下,791上,791下。
今天看來劉錫鴻對西方政體的認識還非常幼稚,但是顯然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即西洋不同於中國者,簡言之,即國主非國家土地之主,人民“各有之”;承辦國事者不能“專斷其事”,遇事則“公議”;政令、財賦不歸一人,尊卑等級不嚴格,商人也能“參國是”。簡言之,他已經意識到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的迥異,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没有也不可能對二者利弊作出評論,但是能點明西方民主政體的特徵並將它與中國的專制政體對舉比較,僅此已是非常超前而難能可貴了。
對這段話細加分析,可以推斷劉錫鴻已經清楚地看到,洋務運動所宣導的一切其實都是與西方的政體聯繫在一起的,表面看來只是引進一些西方的器物,無非“堅船利炮”以及進而鋪設鐵路、開設礦山等等,但是器物層面的背後是制度層面,這些器物只有依托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纔能存在,因而它們一旦進入中國並且如洋務派所設想的要發展“製器之器”並擴展開來,勢必引起制度層面的變化,威脅到國家的政體安全。洋務運動初起之時恐怕還没有多少人能這樣看待問題。李鴻章雖然提出要“變通舊章”,但他仍然認爲“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並没有意識到爲了火器而“變通舊章”將會引起的制度性的變化。*《致總理衙門》,《李鴻章全集》(2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313。要不要維護中國“政令統於一尊,財賦歸諸一人”、“天下一家”的體制?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中不可能有人作出否定性的回答,劉錫鴻也不例外,所以他的結論是“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國也”。但是耐人尋味的有兩點,一是他並没有否定西方的體制,相反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試圖儘量借助中國社會中的鄉約公所、商人會館將這種體制解釋清楚;二是隱約之間對産生了“堅船利炮”的西方體制給予了優於中國的評價,“非其法較中國爲善也”的言外之意豈不是已經承認了西方之法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强大而“較中國爲善”嗎?儘管他馬上就用“情形迥不侔”作了消解。
劉錫鴻這段議論之後潛在的邏輯就是——洋務一旦開辦就不會僅是器物層面的引入,發展下去必將引發體制層面的變革而威脅到大清帝國;反之若要保持中國“數千載”以來“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的體制,就必須拒斥洋務。這是一對不能兼得的“魚”和“熊掌”,選擇前者就造就了洋務派,選擇後者就是守舊派。而劉錫鴻的内心就在於在矛盾的兩方面難以割捨,作爲忠心不二的大清臣子又清楚意識到洋務將會帶來的嚴重後果,他當然選擇了後者,在守舊派的立場上堅定地説出“夷狄之道未可施中國”;但是儘管他大聲疾呼通過治理“内政無實”來挽救清王朝,卻又對内政的無可救藥有清醒的認識,所以他並不完全拒斥洋務,相反對洋務的極致也就是西人之“體”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在他後來出使英德時對西方民主的法制法度的考察體認也可以看出來。
由此看來,劉錫鴻身上並非發生着“一個保守者的思想轉變與堅守”,也不是“保守中的趨新”,而是一開始内心就被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控制着。當他執念於清帝國的“夷夏之防”時,保守的一面就膨脹起來;而當他清醒地面對現實時,變革的一面又活躍起來。所以對他的整個思想來説這是一對結構性的矛盾,使他的言論行止中經常出現看似互相矛盾的現象。當然由於他根本的政治立場和官場的處境,更多的時候矛盾中保守的一面占了上風。
三 從《英軺私記》看劉錫鴻内心矛盾的欹側
劉錫鴻出使英德之後,由於直接面對西方的社會現實以及劉錫鴻本人的善於觀察領會、分析體認,他的思想震動可以説是巨大的,導致他内心結構性矛盾中變革的一面迅速得到提升。這在他的《英軺私記》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有要洋務就必須西體中用的傾向。
(一) 對西方世界的由衷贊美,與儒家理想中的世界聯繫起來
在赴倫敦途中所經過由英人經營的地方如中國香港、南洋、埃及,各種新的景象已經讓劉錫鴻暗暗稱道,而到了倫敦之後,西方世界的恢弘繁華更讓他激動萬分,發出由衷贊美之辭:
辭出後,乘便周遊街市。衢路之寬潔,第宅之崇閎,店肆之繁麗,真覺生平得未曾見也。……入夜,各街燈燭攢光,火山星海,殆無以過。*《初至倫敦》,劉錫鴻《英軺私記》,頁70。
衝擊力過後,在這樣一種心態中再去觀察英國的社會風貌,更是覺得完美:
兩月來,拜客赴會,出門時多,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囂,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地方整齊肅穆,人民鼓舞歡欣,不徒以富强爲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總論英國政俗》,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10。
可見即使在劉錫鴻這樣對西方尚有一定了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原先也不免以匈奴、回紇如此的夷類爲原型去想像歐洲諸國。
認識一步步深入,劉錫鴻眼光擴大到英國的政俗:
到倫敦兩月,細察其政俗,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别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虚文相應之事。*《總論英國政俗》,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09。
接着就對這些現象逐一作了考察:“無閑官”是看到宰相而下,各署官員人數都很少,但是“咸勤其職”,無論上下工作時都是“五官並運”,有“應接不暇之狀”;“無遊民”是“士農工商各出心計,以殫力於所業。貧而無業者驅之以就苦工”,所以“通國無賭館、煙寮,暇則賽船、賽馬、賭拳、賭跳,以寓練兵之意”;“無上下隔閡之情”是各鄉鎮都“舉議院紳一、二人”,“隨時以民情達諸官”,“民之所欲,官或不以爲便,則據事理相詰駁,必至衆情胥洽,然後見諸施行”;“無殘暴不仁之政”是指犯罪者固然監禁,但“仍優養之”,無殊死刑,也没有鞭刑,甚至對牛馬牲畜也不能“箠楚”;此外又有養濟院收養貧民難民,還有醫院爲他們“調攝”……“無虚文相應之事”則事關民風民俗,“有職役則終其事而不惰,有約令則守其法而不渝。欺誑失信,等諸大辱”,“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務盡委折,辯論務期明晰,不肯稍有含糊”,“不僞爲殷勤,不姑作謙讓”,已經到了“男女盡人皆然”而成爲風俗了。*《總論英國政俗》,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09,110。
劉錫鴻爲讀者,特别是爲那些仇洋恐洋視之如洪水猛獸的守舊派們描畫了這樣一幅美好的圖景,這在當時是難得的,而這一幅圖景正是儒家理想中的社會。這從一個角度調和了西方的“體”與中國國情之間水火難容的對立。
(二) 越過“用”的層面開始考察“體”的層面
劉錫鴻的可貴之處,是他對西方的認識跨越了表面的“用”,已經在思考“體”的深層次問題了。上文已經談到,他出國前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意識,來到英國後更是將目光投射到了英國的民主政體上,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倫敦方幾天,他便記録下了新獲得的對英國民主政體的認知:
英國之政,君主之,實民主之。每舉一事,百姓議其失,則君若臣改弦而更張。*《初至倫敦》,劉錫鴻《英軺私記》,頁70。
“君主”還是“民主”,問題本身對一個長期生活在清朝官場的官員來説已經是驚世駭俗的了,劉錫鴻卻還敢於與中國進行比較,明確指出“英人無事不與中國相反,論國政則由民及君”,“英本民政之國,不必其君治事”以及“君主不尊律例爲尊”等等在中國不可思議的現象。由此出發,劉錫鴻對這種政體層面上的種種制度作了深入的考察。例如民主政體的一項重要環節就是“開會堂”(議會例行會議),劉錫鴻親臨會堂審察並作了詳細記録,極力贊美道:
凡開會堂,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辯論之久,常自晝達夜,自夜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官政乖錯,則捨之以從紳民,故其處事恒力據上游,不稍假人以踐踏。而舉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蓋合衆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衆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開會堂情形》,劉錫鴻《英軺私記》,頁83。
他還考察了上下議院的機制,指出其運轉的本質是“紳主之,官成之,國主肩其虚名而已”。這樣的民主政治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簡直是匪夷所思,連“英國宰相之進退”都要“視乎百姓之否臧”,“持其失者多,則當國謝去,公舉賢能”。他還介紹了英國的上下議政院和爲官後不得“復事商賈”的規定,以杜絶腐敗。*《上下議政院》、《開會堂情形》,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02,84。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法律對專利的尊重——“人有一得之技,尊如朝廷”。他特别介紹了一位“妥瑪士者”的案例,因爲自己的“利炮新法”被“官中”盜用而“控刑司”,結果是“刑司”判令國王賠償“金錢六千”,可見法是“不能以勢相抑遏”的。*《英人之獎製造》,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05。對這種法律高於一切的體制,他感慨地總結道:
刑司之權,足以訊治其國主王公大臣。故英倫有君主不尊律例爲尊之語。*《英倫訊案規模》,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36。
民主政體需要言論自由,劉錫鴻在日記中就有很多篇幅介紹了“新聞紙”在政治運作中的作用,*《倫敦新聞紙》,劉錫鴻《英軺私記》,頁73。也由此盛贊“英人尚舌辯,專以能言爲才”,*《阿爾蘭之遊》,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99。因爲“其俗究以理之是非爲事之行止,非專恃强力者”,而是要“我理既足,衆心相喻,則左袒者必多”。*《安友會》,劉錫鴻《英軺私記》,頁206,207。
這時的劉錫鴻津津樂道於西方的民主政體,與在國内力主的“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是”的劉錫鴻似乎已經是判若兩人了。
(三) 對西方教育的重新認識
洋務之爭,核心問題之一是要不要引進西方的教育。對此劉錫鴻原先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出國時途經上海,參觀了格致書院(今格致中學)之後,曾經對其實行的西式教育痛斥一番。他的主要觀點是: 教育之言格致,“所以爲道也,非所以爲器也”,目的是要使人致力於“身心家國天下”。而“所謂西學,蓋工匠技藝之事也”,“非謂用功於身心,反先推求夫一器一技之巧也”,這樣的學校讓學生“入學而先事此”,就會“役亂其心,淆雜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最後導致“以百工商賈之行,而爲臨民治世之事”,所以他要將“格致書院”易名爲“藝林堂”,輕蔑地將其稱爲是一個“聚工匠巧者而督課之”的地方。*《觀格致書院後》,劉錫鴻《英軺私記》,頁50,51。
然而經過對英國教育的考察,他的西學觀被顛覆了。他帶着贊美的口吻寫道,在英國“人家生育子女,咸報鄉官。鄉官歲核户籍,省知已届五齡,即驅率入塾”。然先有小學階段: 先是教誦耶穌經,既長學書算勾股開方之法等;然後資稟特優者則進入大學階段: 習天文、機器、畫工、醫術、光學、化學、電學、氣學、力學諸技藝。*《英人講求教養》,劉錫鴻《英軺私記》,頁207,208。僅僅數月之後“所謂西學,蓋工匠技藝之事也”的見解已經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西學雖“不離乎工商之事”,然“其教術則工商,其教規則禮樂也”——“道”與“器”的關係已經被他闡釋得非常簡明而清晰。學校不再是過去想像的“猶百工居肆然者”,而是“每入其塾,規矩森肅”,“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遨遊,不得逾越尺寸”。*《英人講求教養》,劉錫鴻《英軺私記》,頁208。正是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男女子自幼咸入學讀書,天文、輿圖、算法、雜學無不畢講。十二歲以上,即皆能殫竭智力,以就一藝”。*《觀戴晤士報館》,劉錫鴻《英軺私記》,頁99—100。
更令人驚訝的是,劉錫鴻對原先以爲不過是“一器一技之巧”的西學如電學、力學、光學等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詳細記載了觀看光學實驗中微妙的變化過程,而電學實驗,他“廿八至三十,連日觀藝師演此”並作了詳細的描述。不久他又觀看了化學實驗,並由自己的身體不適了解了氧氣對健康的重要性,由此進一步領悟到“深房邃閣,鍵閉之久,乍入之而死者,中國以爲逢祟”,其實“非毒也”,而是“皆炭氣所爲也”。*《化學演試》,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38。
不僅如此,他對西方教育中通過各種手段廣開民智、普及文化的做法也非常贊賞。例如對博物院,“到此後急欲一往觀之”,觀後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爲博物院“非徒誇其富有也”,而是“放門縱令百姓男女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連御花園也“羅致五大洲千百國本料花草於其地,各有標記,著其名目功用及所自出”,然後“縱令百姓往觀,以資博物而擴其匠材醫藥之識”,禁不住感嘆道:“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一次參觀不够,還要“相期異日再觀”。*《播犁地士母席庵》、《御花園》,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11,113,131。
(四) 對商貿和製造業的重點考察
辦洋務,在軍需軍工之外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商業貿易的發展和製造業的興辦,這些當然都爲頑固派所竭力抵制,然而劉錫鴻在英德期間卻不遺餘力對它們進行了周詳而細緻的考察。
據《英軺私記》的記載,在軍事製造工業方面,劉錫鴻系統考察了各製造局各種魚雷火炮的演示和製造,並以一個内行的身份驚嘆七萬六千斤之炮的製造,説“從古未聞鑄熟鐵器能至此之大者”,而對火炮製法之精則贊美道:“英人之於火器,其精心審驗如此!”*《烏里治製造局》,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33。劉錫鴻的考察往往是有明確目的的,例如對“精於輪船槍炮”的阿木士湯和他的炮廠,便是“余欲見其人,並觀其局所製造”,而“遍觀其製成之炮”、“陸路炮車”以及軍工之外“用思之巧如此”的“活鐵橋”。*《阿木士湯炮廠》,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72,173。他尤有興趣於棉花火藥,以至於“商人曰阿遲博爾,知余考究此藥”而“請往”“觀其製造”。*《棉花火藥》,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90—191。
軍工之外,他考察了倫敦之東“以大池爲釀器,以深屋爲酒缸”,年出産“六十萬桶以上”的啤酒釀房,*《咇酒釀房》,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84。也考察了機器印書,並從因爲二十六字母“拼湊而成,故能若是速耳”,考慮到“若以中國字類之富,字畫之多,雖有機器,豈易全造其字戳而編排之哉”。*《看印書》,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79。又聞規模甚巨的“餑餑作房”而“當一往觀”,發現“其和麵、印餅、烤餅,皆司以機器”,而詢其“所以銷流之多”,“則曰自有火輪車船,貨物通於各國”。*《倫敦貿易之大》,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85。作爲來自農耕社會的劉錫鴻對機器耕作也表現出異常濃厚的興趣,詳細描述了機器用於農活的程式和效果。*《機器耕作》,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59—160。
在廣泛考察的基礎上,面對英國製造貿易業規模之大,劉錫鴻不由得感嘆道:
外洋貿易之大,當無有能過倫敦者。其製造槍炮、車船、機器、賣煤、鑄鐵、織絨毯布帛等處,固無論矣;乃至一屠宰之肆,一糖果之店,一餅餌之室,亦皆雇役數千人,羣然操作而無暇旁顧。*《倫敦貿易之大》,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84—185。
劉錫鴻甚至還看到了中國若也走上製造業商貿業之路必然要解決的一些問題,例如電報電信業的發展,例如工商業發展後的貨幣流通,例如對發明專利的獎勵,例如置辦船炮當知之事等。他甚至大膽作出了中國將走上“開金銀礦,置辦機器”的假設,在這種情形下就必須采用英國鑄錢局的方法來消除錢幣流通中的隱患:
今使中國開金銀礦,置辦機器,效爲英倫,錢幣私銷私鑄之患,誠可免矣。*《觀倫敦鑄錢局有感》,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18。
他贊同選送“一、二百人分赴各國船廠學習”、“自製槍炮亦然”的建議。劉錫鴻還與英國的商人們有了面對面的交流: 他站在商會的高臺上,對着“仰視而鼓掌”的商人們大聲説道:“諸君勤貿易,多積金帛以行善事,天將畀爾厚福也。”*《利文浦》,劉錫鴻《英軺私記》,頁204—205。劉錫鴻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英國商人之前,巨大的反差令人驚訝,這與他長期以來竭力主張重農抑商、重義賤利,判若兩人。
他的結論是,正因爲英國全體國民“莫不奮發以事工商”,“國之致富,亦由於此”:
英之衆庶,强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如人何哉?*《英人講求教養》,劉錫鴻《英軺私記》,頁208—209。
劉錫鴻原先反對洋務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機器製造發達之後會造成大量人口“失衣食之資”,所以他在參觀報館“刷印固不用人力”的機器之後,説“以余遲鈍之見”,若使用人力而不用機器,報館這點活就可讓“二萬數千人”之生機“托於此矣”,“何爲必用機器,以奪此數萬人之口食哉”?對此疑問,他接受了西方人士的意見並詳加記録,是“心愈用愈巧,貨愈出愈多,商賈之攬巨資者乃愈衆。豪富既衆,則百貨自易銷售,貧民自易爲生,國課自然充裕”,“此英之所以富也”。*《觀戴晤士報館》,劉錫鴻《英軺私記》,頁98,99。《英軺私記》中還大量記録了與西方人士以及學習西方深有心得的日本人士的交流,也反映了劉錫鴻在不斷地探求洋務之道。
平心而論,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所表現出的從西方之“體”到教育、到貿易製造的認識,以及他對西方世界的贊美和認同,在當時,尤其是這本日記還將呈送朝廷,不免保守官僚傳閲而遭詬病痛詆的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其考察之精細紮實,見解之深刻全面,若以洋務派郭嵩燾《使西紀程》中相關内容相比,可以説見識不在郭嵩燾之下,同時代中似乎難以發現超越於他者。
四 個人性格上的矛盾: 理性認知與利害關係之間
如果孤立地看以上劉錫鴻到英國後認識轉變的四個方面,他儼然已經是一個激進的洋務派了,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按説當時他身心都浸潤在西方文化之中並受到鼓舞,内心矛盾中保守的一面應該漸趨淡化,可是我們卻發現《英軺私記》中的奇怪現象,往往在記載了一個讓他興奮的新事例,描述了一個他獲得的新認識之後,馬上就又有大段迂腐的陳詞濫調接踵而至,而且在守舊的頑固程度上超過了他在國内的言論。例如纔對電學實驗有所心得並期待着觀看化學、力學實驗,接着卻是這些“英人所謂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製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觀電學有感》,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27,128。而要“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觀電學有感》,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30。剛對機器耕田作了充滿新鮮感的詳細描述,又對英人引導他去參觀“鐵廠、木廠,閲工截鐵、鋸木”表示厭倦,説“無非機器,皆非余所心屬”。*《機器耕作》,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61。甚至明明已經無理可言了,還要無中生有地胡攪蠻纏一番,例如洋人問及中國婦女爲何不能像男人一樣外出,竟搬出“頭則露”而腹部需覆蓋的陰陽歪理來使洋人“無以答”。*《論婦女》,劉錫鴻《英軺私記》,頁171。這樣互相扞格又彼此牽扯的記述和觀點在《英軺私記》中比比皆是。縱觀此書,可以説是一個歧見疊出、充滿矛盾衝突的混合體。
影響一個歷史人物政治立場的因素,主要是他的思想理念,但不可忽視的是,趨利避害、趨炎附勢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像劉錫鴻這樣一個缺少政治品格、一心謀求官運亨通的人而言。所以除了分析他政治理念上的結構性矛盾之外,也要分析他性格素養、道德理念上的矛盾。
劉錫鴻是一個自視甚高、極有抱負的人,這可以從同時代與他接觸的人的評價中看出來,王闓運就指出他“欲爲一代名人”。*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一),長沙,嶽麓書社,1997年,頁238。前引《碑傳集三編·劉錫鴻傳》也説他“魁岸負氣,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其志並不在著書立説,這種抱負得以實現的惟一途徑就是官場得志了,所以他對宦海仕途極爲看重。而劉錫鴻的個人品行,王闓運對他的評價是“不近人情,而以爲率真,故所至受詬病矣”。*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一),頁238。郭嵩燾曾經與他共過事,覺得他“於世故人情全不一加體察”,當然郭嵩燾從一個側面説這是“亢直無私”,*《郭嵩燾日記》(二),頁150。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其生平好剛而不達事理”,“賦性怪異”、“狂悖矜張”了。*《郭嵩燾日記》(三),頁280。從劉錫鴻的行事來看,他的性格豈止是不近人情,簡直是有點錙銖必較、心地促狹,導致他作出一些難以理喻的事情來。例如僅僅是没有處理好“副使”的職銜問題,他就與正使郭嵩燾反目成仇,向朝廷打小報告,蓄意“構陷”;也正是在與郭嵩燾的矛盾中李鴻章没有支持自己,向李鴻章示好又没有得到回應,便利令智昏地上奏參劾李鴻章而遭革職,徹底斷絶了自己的仕途。此舉連李鴻章都覺得不可思議,説“雲生數十年交舊,妄肆攻擊,爲可詫耳”。*轉引自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51。
但劉錫鴻又是一個觀察分析、行爲處事能力都很强的人。這可以從他早期任幕僚期間與太平軍、捻軍作戰以及辦團練捕盜治匪而聲譽卓著看出來,他在京期間受命對天津教案的審訊也證明了他的能力。他在英國、德國期間深入考察炮臺後回國寫成的《訪求築造炮臺模式摺》以及所上的《築造炮臺未盡事宜書》、《籌辦海防畫一章程十條摺片》等都顯示他的眼光及思考的深謀遠慮。*見《劉光禄遺稿》卷一,頁742上,746上,751上。
從這種道德性格上的矛盾觀察劉錫鴻,就會發現他一直周旋在保守派與洋務派之間,其中的利害得失決定着他政治理念中矛盾的消長。就劉錫鴻早期經歷來看,能影響他仕途的主要有兩人——毛昶熙和郭嵩燾,他們都是對他在平定内亂中表現出來的才能大加贊賞而關係日益走近的。但毛昶熙是保守派,郭嵩燾是洋務派,劉錫鴻必須在二人之間保持平衡,這也是影響到他早期言論中出現許多相互矛盾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海防籌議”之爭的階段,顯然郭嵩燾更占上風,而且通過郭嵩燾可以接近李鴻章、丁日昌等對他仕途更有利的人物,他的數封信件中傾向性的言論恐怕都與此不無關係。例如劉錫鴻大談治理内政、整頓吏治,其實在郭嵩燾讓他“評騭其得失”的《條陳海防事宜》中,就有相當的篇幅談“修内事”、“整飭吏治”等,*見《郭嵩燾奏稿》,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頁337—347。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劉錫鴻在《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中對郭嵩燾的迎合。
始終在保守派與洋務派之間周旋以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是《英軺私記》中大量矛盾敍説雜陳的原因之一。到了英、德之後,劉錫鴻正視現實,傾向於變革的一面强化了,但是他的《私記》是準備日後公開的,不能不考慮到保守派的反感,在《私記》中增添濃重的保護色是他的一種策略。劉錫鴻在《私記》中對西方的贊美認同其實不亞於郭嵩燾的《使西紀程》,但郭氏書後來“横遭非議”以至於被毁版,而《英軺私記》卻安然無恙,其中大量的保守言論不能不説起了很大的保護作用。
特别是劉錫鴻僅僅因爲“副使”的名義與郭嵩燾鬧翻之後,他意識到此時必須向保守派靠近,纔能保住自己的前程。對此我們認同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一文中的見解:“在事件中,李鴻藻、沈桂芬、毛昶熙、景廉等總署大臣皆輕賤郭嵩燾,嗅覺靈敏的劉錫鴻又一次捕捉到了政治風向,迅速脱去熱衷與精通洋務的外衣,以衛道士的面目出現,夾雜私怨,無中生有,以此企圖擺脱與郭嵩燾多年的干係,另尋靠山”。經王維江考察,《使西紀程》遭毁版後“劉錫鴻的確經常給李鴻藻、毛昶熙打小報告”以誣陷郭嵩燾。*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1995年第4期。這一切都促使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盡量渲染他的保守派的色彩,以至於給人以頑固不化的强烈印象。
劉錫鴻回國之後之所以更趨保守,《英軺私記》中對西方文明的新認識都被拋諸腦後不再提起,這與李鴻章並不看好他,在洋務派這裏已經無法謀得發展,只有保守派李鴻藻、毛昶熙等人纔有可能提攜他有關。事實上回國後他幾次提升的機會都是在李鴻藻官復原職後得到的,儘管最終並没有如願。*參見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頁247。
縱觀劉錫鴻的一生,其實有兩重矛盾在左右着他。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卑劣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主導了他的言行,從而造成了讓人眼花繚亂的表現。研究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簡單地貼上“保守派”的標籤,而應該還原他真實的心理世界。
(本文作者係辭海編纂處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