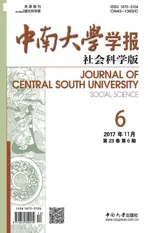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身份焦虑
2017-01-11王飞
王飞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身份焦虑
王飞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03)
身份问题是移民小说难以逃避的母题,而作为身份问题负面表征的身份焦虑,更是广泛存在于移民小说之中。不像其他移民作家,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其创作中,虽然也持续关注小说人物的身份问题,但很少直接处理移民经历。以移民为主人公的《远山淡影》则是特例。文章以《远山淡影》为研究文本,重点讨论移民身上表现出的身份焦虑,着重探究产生此种焦虑的原因,以及此种焦虑对人物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小说人物的身份焦虑要么造成他们的身份危机,要么为他们后来的身份建构打下伏笔,从侧面体现了作为移民作家的石黑一雄本人对身份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身份焦虑;身份危机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种族、修辞与后殖民》中说,移民是当今时代一个独特的潮流,是“20世纪晚期一个奇妙的大规模发生的现象”[1](211−212)。与移民现象相伴相随,移民文学也在当代世界文坛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正是一位典型的移民作家。在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石黑一雄通过对小说人物不同模式的“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探讨,突破了理论界“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二元身份认同,表现出一种流散、多元、包容的身份认同观。同时,作为身份问题负面表征的“身份焦虑”(identity anxiety)在其小说中也普遍存在。通过考察石黑一雄小说中身份焦虑的表现及原因,我们也可以对移民文学中广泛存在的身份困境窥斑见豹。身份焦虑在石黑一雄迄今为止的7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然而,石黑一雄直接处理移民经历以及移民身份焦虑的小说非常少。他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远山淡影》()就是这样一部移民小说。小说以移居英国的日本女子悦子为主人公,凸显了移民人物在母国与移入国文化之间徘徊的生活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焦虑。空间位移将悦子及其女儿景子带入另一个文化世界,打破了她们的原初身份,直接造成了她们的身份焦虑。与悦子的混血女儿、二代移民妮基不同,悦子和大女儿景子都属于一代移民,对移民经历及其带来的身份焦虑有着非常直接的体验。对于母亲悦子来说,身份焦虑一方面体现在她以及她的“影子人物”(double)佐知子孤独、空虚的移民生活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她与英、日两任丈夫之间文化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中。悦子与英国丈夫的矛盾体现了其与移入国英国的文化不能认同,而她与日本丈夫的冲突则体现了其与世异时移的当代日本的难以认同,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困境与其在英国的孤独生活一起反映出她自身深重的身份焦虑。空间位移带来的身份焦虑,在女儿景子身上达到极致,逐渐导致她的身份危机,从而最终选择自杀 身亡。
一、身份焦虑: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
身份问题(identity)涉及众多学科,同时也被众多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但对这一概念的专门研究始于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埃里克森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关注“身份” (identity) 和“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很自然地植根于向外移民、对内移民以及美国化的经验中”[2](93)。他注意到身份与移民以及移民经历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及身份危机之间的天然关联。身份问题是个体的社会归属问题,空间位移及其带来的文化相遇必然会导致移民的身份焦虑甚至 危机。
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也就是说,当身份认同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身份焦虑。身份认同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归属关系,所以在界定身份焦虑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身份认同的内涵。根据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观点,身份认同有“‘我’的认同”和“‘我们’的认同”之分。“我”对应着个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而“我们”则对应着集体的身份认同。我们在讨论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小说人物“‘我’的认同”。同时,阿斯曼对“‘我’的认同”又分了两个次范畴,即“个体的(individuell)认同”和“个人的(personal)认同”。由于“个体的认同”指的是一个人的“不可或缺性、自身与他者的不可混同性及不可替代性”;而“个人的认同”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结构会分配给每个人一些角色、性格和能力”[3](135),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小说人物个人的认同,也就是人物个体与社会存在的认同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归属感。
身份认同是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归属问题,处于个人(the personal)与社会的(the social)交汇处[4](8)。个人与所处的社会能够取得认同时,则可以建构身份;若个人与所处的社会不能认同,则相应地产生身份焦虑。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同时也是身份问题的最初体认,更是建构和重构身份的基础或者开端。从心理学上来讲,“焦虑”是“一种被‘困住’、被‘淹没’的感觉”,它让“我们的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或不明确”。焦虑的表现形式各异:或是“一种内在的‘痛楚’”、或是“心脏的收缩”,甚或是“泛化的困惑”[5](23)。同时,焦虑可以呈现出极端的强度和形式,因为它是“当人类视为与其生存同等重要的某种价值观遭遇危险时所作出的基本反应。恐惧是一种对自我某一方面的威胁……焦虑打击的是我们自我的‘核心’:这是当我们作为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东 西”[5](24)。由此观之,焦虑就与我们的自我、身份密切关联了起来。焦虑最为严重的影响便是“摧毁我们对自身的意识”,“使人迷失方向,暂时性地使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做什么的,并因此模糊了他关于周围现实的见解”[5](27)。我们可以认为,程度最高也是最为根本的焦虑形式,便是身份焦虑。
自我的价值观与身份,总倾向于依附特定的社会框架,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主导价值观是被人喜欢、被人接受以及被人赞同”。所以,作为一个心理问题,身份焦虑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来源于这种不被喜欢、被隔绝、孤独或被抛弃的威胁”[5](25)。促成我们身份焦虑的原因,并非单一地源自个体心理,更多的则是源自我们与周遭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他人,产生的摩擦冲突或者某种不和谐。简言之,“焦虑代表了一种冲突”[5](2)。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角色,应该相信什么样的行为原则。我们个人的焦虑有点像我们民族的焦虑,它是一种基本的关于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混乱和困惑”[5](21)。换言之,身份焦虑就是自我在社会的时空坐标上迷失了方向。极端的身份焦虑,必然导致身份危机。
罗伯·波顿(Rob Burton)借用石黑一雄小说《浮世画家》标题中的词语,将其小说主人公迷失方向的这种生活状态称作“浮世”(floating world):“浮世”指的是“身处两个(或者是道德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甚或是地理的)世界之间的叙述者用记忆和顿悟(epiphanies)编织出的精妙网络”[6](42)。空间位移致使石黑一雄的移民主人公身处两个不同的道德、意识形态及地理的世界之中,造成他们严重的身份焦虑。正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所说,人们“被困在两种生活模式之间,其结果是失去了理解自身的所有力量,他们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感,没有简明的认 可”[5](22)。在这里,“认可”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认同。身处“两种生活模式”之间,失去明确的身份认同,这也正是石黑一雄移民小说《远山淡影》中的一代移民悦子和景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身份困境。
二、孤独、空虚的移民生活:悦子身份焦虑的症状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也是他第一部直接处理移民经历的长篇小说。小说让石黑一雄闻名英国文坛的同时,也为他日后在创作中对身份问题的关注定了基调。小说主人公是移居英国的一代移民、日本女子悦子。在某种程度上讲,较之于逐渐融入移入国文化的二、三代移民,一代移民具有更为严重的身份焦虑。台湾学者李有成认为,《远山淡影》的叙述既是“回顾性的”,也是“分析性的”:说其具有“回顾性”是因为小说讲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回溯自己在战后长崎的生活故事,说其具有“分析性”是因为小说主人公通过一种自省的方式努力理解她的现在,她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一种“互动”[7](20)。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性的自省”“过去与现在的互动”,移居他国的小说主人公悦子得以思考自身以及女儿的身份问题。
小说开篇便点明小说叙述者悦子对身份以及身份焦虑的关注。小说以悦子与其英国丈夫关于小女儿取名问题的争论开篇:“我们最终给小女儿取名叫妮基。这不是缩写,这是我和她父亲达成的妥协。”[8](3)这段叙述,表面似乎是一段随口提起的普通家庭记忆,事实上却是叙述者精心设计的故事开端。开端不仅为整部小说关于身份认同、文化相遇、移民交融等主题定下了基调,同时也将悦子对身份的思考及其自身存在的身份焦虑凸显了出来。与此相似,同样是在小说开篇第一页,悦子讲起了“纯血统的日本人”大女儿景子的自杀[8](4)。强调女儿景子的纯日本血统,其实就是在强调她的身份。同时,景子的自杀,作为小说的根本氛围,笼罩于整部小说的情节之上。景子从小跟随母亲悦子移民英国,因为不能进行积极的身份建构而最终自杀。自杀源自身份危机,是身份焦虑所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也正是大女儿景子的自杀,加重了悦子自身的身份焦虑。
心理学研究认为,“空虚感和孤独感”相互交织,“是焦虑这种基本体验的两个阶段”;同时,“焦虑代表了一种冲突”[5](12−3, 22)。具体到移民小说,由于文化隔膜与冲突,空间位移的移民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一种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的两个主要症状——空虚感和孤独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空虚感源自孤独感,而孤独感在心理学中被描述为“‘置身在外的’、被隔离的,或者被疏远的感 觉”[5](12−3)。空虚感和孤独感这两种主要感受,在悦子身上有极为直观的体现。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女人,人到老年,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独自寡居英国乡村,悦子正是过着这样一种“置身在外”“被隔离”和“被疏远”的生活。小说中反复使用的“安静”一词对此种感受做了精确概括,正体现了悦子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小说开篇便写道,“我住的乡下房子和房子里的安静让她[妮基]不安,没多久,我就看出来她急着想回伦敦自己的生活中去。她不耐烦地听着我的古典唱片,……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不让我听到她的谈话。五天后她离开。”[8](3)由此从侧面反映出,悦子母女间隔绝的亲情以及悦子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这种“安静”的生活,不仅仅是回来只待五天的妮基的体验,更是叙述者悦子自身的日常体验。在小说结尾处,当女儿妮基问悦子一个人住在这里是否无聊时,悦子虽然嘴上回答“我喜欢安静”,却又不经意间道出了心声:房子太大,想要换个小点的房子[8](238)。这正好证明,悦子是在说谎,在强颜欢笑。正如辛西娅·黄(Cynthia Wong)的评论,“每当悦子提到一个幸福的场景,读者就会了解到她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悲伤和空虚。”[9](35)悦子极力掩饰焦虑的同时,却又不经意间凸显了自己的焦虑。
悦子掩饰自己身份焦虑的另一个主要方式,便是在回忆中创设了佐知子这一“影子人物”[11](21)。李有成认为,“过去一直在那里,而悦子有意识地避免回忆某些事件,事实上使她难以建构一幅更加清晰、准确的生活图景。”[7](22)通过讲述他人,从而反映讲述者自己的内心,这是石黑一雄最为擅长的一个叙述手 段[10](123)。讲述他人的故事,一方面可以映照悦子自己的过去和身份焦虑,另一方面通过回避过去的某些事件,加重了自身的身份焦虑。根据石黑一雄在访谈中的说法,“就她(悦子)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目的而言,佐知子代表了她(悦子)”[10](99),那么我们通过分析佐知子的生活状态也可以侧面观照悦子的身份焦虑。辛西娅·黄评论说,虽然小说中“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框架比较清晰,但是随着叙述者深入各自的记忆,这两个框架变得复杂化,而且偶尔还会为情绪所扭 曲”[9](18)。也就是说,在悦子的叙述过程中,佐知子逐渐与悦子重叠。佐知子的故事不仅反映了悦子的过去,同时也反映了悦子的现在。与叙述者悦子一样,在移民国外之前,佐知子就已经有过“国内移民”的经历:佐知子从东京搬到长崎,而悦子从中川嫁到长崎。佐知子之所以选择跟女儿万里子生活在河边“独自伫立”的小木屋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之所以想要跟随美国男友弗兰克离开日本到美国去,而不愿回到伯父和表姐的大房子里去住,主要原因便是那所房子“安静得让人想到坟墓”[8](208)。她的生活与悦子有着一样的“安静”和空虚,她的孤独感和空虚感也正是悦子身份焦虑的侧面反映。
三、与英、日两任丈夫的文化冲突:悦子身份焦虑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焦虑代表了一种冲突”[5](22)。个人与其所在的集体产生某种认同上的“冲突”,也便产生了个人的身份焦虑。由于空间位移,移民一方面割不断与母国的原初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生活的移入国又需要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对两个国家、两种文化都若即若离,造成他们尤为严重的身份焦虑。悦子的这种身份困境,在小说中象征性地表现为她与英、日两任丈夫都存在的文化冲突。她与英国丈夫的冲突,说明悦子对英国文化的不认同;她与日本丈夫的争论,又反映了悦子对战后时移世易的日本难以认同。难以认同却又必须建构认同,正是移民生活带来的这种认同困境造成了悦子严重的身份焦虑。
悦子的身份焦虑首先体现在她与英国丈夫的争论上。他俩的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日常生活层面,而是逐渐扩展至文化认同层面上,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他们的日常争论体现了一种“深重的文化冲突”[12](165)。事实上,悦子与英国丈夫的争论,也不止出现在小说开篇有关女儿妮基的取名问题,而是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叙述当中。例如,在一段关于悦子日本丈夫二郎的回忆中,悦子写道:“英国丈夫不理解二郎这样的人。我并非在深情地怀念二郎,可是他绝不是我丈夫想的那种呆呆笨笨的人。二郎努力为家庭尽到他的本分,他也希望我尽到我的本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称职的丈夫。而确实,在他当女儿父亲的那七年,他是个好父亲。”[8](114)悦子与英国丈夫的争论,不仅仅停留在现在,还回溯到了过去。她说二郎的好话,其实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就是在为日本文化做辩护。因为,这段描述中的二郎不仅是二郎个人,更是日本丈夫、日本父亲的典型形象。如此,悦子又一次将论述从个人的家庭层面扩展至国族的文化层面。在这段回忆之前,悦子强调,“事实上,虽然我的英国丈夫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日本的文化”[8](114)。如此看来,悦子同英国丈夫的个人争论,逐渐演变成英、日两种文化的争论,逐渐导致居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悦子产生了身份 焦虑。
另外,与英国丈夫的争论,还从小说开篇关于小女儿妮基取名最终扩展至大女儿景子身上。在回忆中,通过自说自话的方式,与英国丈夫争论两个女儿之间的异同点,悦子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身份问题的思考,“我的两个女儿有很多共同点,比我丈夫承认的要多得多。在他看来,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我丈夫并不知道小时候的景子是什么样子的;他要是知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个女孩在小时候有多么 像”[8](119−20)。英国丈夫由于没有见过“小时候的景子”,只见过随悦子移民英国后变得封闭、内向、孤僻的景子,所以只能看见景子与妮基之间的“完全不同”。作为知情人的悦子,却知道两个女儿存在“很多共同点”。但是,两个女儿最终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原因何在呢?这正是悦子的内心困惑所在。英国丈夫“把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景子的天性或二郎”[8](119−20)。在这里,天性和二郎其实是一对同义词:作为“纯血统的日本人”景子的天性来自二郎,而二郎的天性则来自日本文化。悦子的英国丈夫,作为一个并不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外人”,总倾向于对其进行模式化解读(stereotyping)。然而,悦子自己却“并不像我英国丈夫那样”[8](119),极力反对英国丈夫的这种“天性论”。在悦子的眼中,两个女儿拥有相似的“天性”,却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个问题让她开始深入思考身份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两个女儿正为悦子自己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身份认同之路,站在身份十字路口的悦子处在重重的焦虑之中。
悦子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状态以及她的身份焦虑,在小说中象征性地表现为她被夹在英、日两任丈夫之间。在批判英国丈夫的同时,她对日本丈夫二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也并非一味偏袒[9](35)。她一方面与英国丈夫争论,为日本丈夫辩护;另一方面,却也在通过批判,与日本丈夫进行辩驳。实际上,悦子与二郎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绪方的不同态度上。二郎与父亲绪方,对于政治、教育、美国文化、家庭责任,甚至下棋的棋术,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关于战后美国文化与政治对日本的入侵,绪方认为,“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从来没有,他们的做法或许很适合美国人,可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很不一样”。而二郎却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全是坏的。”[8](79)此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绪方关于美国人不懂日本“处世之道”的论调,与悦子对英国人和英国丈夫不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批判[8](114),几乎一模一样。就这样,通过观点的回响,悦子站在了绪方的一方,通过绪方之口与日本丈夫进行争论。与佐知子一样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与绪方一样不能认同自身所处的社会,悦子感受到深重的身份焦虑。当然,小说中也反映了身份焦虑的极端形式——身份危机。通过讲述与母亲悦子同为一代移民的大女儿景子的自杀,小说也观照了身份焦虑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四、身份焦虑的极端形式:景子的身份危机
个人与所处的集体不能取得认同时,便会产生身份焦虑。不过,由于强烈程度不同,身份焦虑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悦子身上表现出的孤独、空虚以及与周围其他人的冲突,只是身份焦虑的一般形式。身份焦虑也有其极端形式,即身份危机。当身份焦虑“打击我们自我的‘核心’”时,“我们作为自我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5](24),从而导致个体精神上的崩溃,甚至肉体上的毁灭。个体精神上的崩溃,体现在石黑一雄另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孤儿》中班克斯的母亲戴安娜的疯狂上;而肉体上的毁灭,则是本节主要探讨的悦子的大女儿景子的自杀。
景子的自杀,让悦子回想起多年前在日本长崎的一段关于佐知子及其女儿万里子的故事。在这段故事中,万里子是景子的“影子人物”,“可以被视作童年的景子,而景子则是到了国外之后的万里子”[13](56)。景子的身份危机源自她童年时的影子人物万里子的身份焦虑。正是童年时期的身份焦虑一步步导致景子最终的身份危机。事实上,在移民国外之前,万里子跟随母亲佐知子从东京移居到长崎,已经成了一种“国内移民”。正是这种移民生活,形成了万里子(以及景子)后来的孤僻性格以及有些怪异的行为模式。在小说中,万里子以与两个男孩子打架的情节出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动辄就跟人吵架的成年景子。移民生活,让万里子跟后来的景子一样,没有朋友,只有小猫作伴。而万里子当着悦子的面捉蜘蛛、吃蜘蛛的场景,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移民生活让万里子孤寂到极点而选择与宠物小猫认同了。关于万里子与小猫的认同,我们还可以考察另一个场景。在与悦子、佐知子出行之后,万里子抽奖抽中了一个大木盒,她希望用盒子做小猫的家,那样小猫就不会被母亲佐知子丢弃 了[8](158)。万里子担心小猫无家可归,正反映了她自己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状况以及流浪生活带来的身份困境。
悦子对万里子到了美国后将会不适应的担心,将万里子的故事与景子的故事紧密地联系起来。悦子对佐知子说:“搬到另一个国家,语言、习惯都不 同。”[8](49)这正是离开日本前,悦子对于女儿景子的担心。同时也是随同悦子一起抵达英国之后,景子的现实生活状态。关于移民生活给景子造成的身份焦虑,我们还可以从悦子的“影子人物”佐知子的话中看出,“想象一下我女儿会多么的不习惯,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都是老外的地方,一个都是老美的地方。突然有一个老美做爸爸,想象一下她会多么不知所措”[8](109)。这也正是景子跟随悦子移民英国后的真实写照。而多年以后,悦子和佐知子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景子正是由于不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移民生活,无法形成积极的身份认同,才最终导致身份危机,从而酿成了自杀的悲剧。
景子的身份焦虑以及最终的身份危机,主要体现在她在英国的移民生活中。正是因为她难以认同英国文化,将自己与家人、朋友隔绝,最终促成了她的身份危机与自杀。不过,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促成其自杀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移民生活所带来的文化隔阂。因为在其周围不存在可资利用的认同资源,由此产生了身份危机。景子的问题就在于“她不能适应移民生活。在英格兰,她没有在家的感觉”[14](166)。与母亲悦子一样,景子在英国没有朋友,更为糟糕的是,景子和自己的家人也没有融洽的关系。下面一段描写,让我们能够对景子的日常生活了解一二。
在她最终离开我们的前两三年,景子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她很少出来,虽然有时我们都上床睡觉后我听到她在房子里走动。她没有朋友,也不许我们其他人进她的房间。吃饭时,我把她的盘子留在厨房里,她会下来拿,然后又把自己锁起来。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妮基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8](63−4)
移民生活,让景子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与家人充满了争吵,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正如后来她在曼彻斯特的孤独生活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段关于景子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其实便是她在异国文化中移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她的房间构成了一个封闭空间,同样也照应了她没有着落的身份认同。
正是景子这种没有朋友、拒绝家人的状态,导致她的身份危机和最终的自杀。在景子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孤独、冲突到身份焦虑再到身份危机和自我毁灭的整条发展轨迹。与母亲悦子一样,景子没能够为自己建构一种妹妹妮基那样的文化杂糅的“流散身份”(diasporic identity)。正如石黑一雄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父母的评价:“我认为我的父母并未获得一种移民思维(mentality of immigrants),而常常就像游客一样,保持着自己的‘日本性’(Japanese-ness)。”[10](92)“移民思维”要求移民对母国和移入国文化都拥有包容的心态,这正是本文所说的流散者所拥有的心态。悦子和景子没能够为自己建构流散身份,主要是因为她们像石黑一雄的父母一样,有着一种“游客”思维。正是这种对移入国采取置身事外的游客思维,让她们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身处异国,却保持着自己的“日本性”,同时又不能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英国性”,景子比母亲悦子的身份焦虑更为严重,最终走上了自杀的身份毁灭之路。
五、结语
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在移民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山淡影》以移民英国的日本女子悦子为主人公,讲述了移民人物体验到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主要表现为孤独感和空虚感,以及个体与周围环境产生的冲突。此种身份焦虑,在悦子身上表现为孤独、空虚的移民生活,以及她与英、日两任丈夫在文化层面上的争论和矛盾。另外,身份焦虑还有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身份危机。在小说中,身份危机反映在与悦子同为一代移民的大女儿景子身上。景子最终以自杀为表征的身份危机源自其童年以及成长期郁积的身份焦虑。在景子身上,我们看到身份焦虑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作为身份问题负面表征的身份焦虑,也可能成为小说人物重建身份认同的基础。只有个体面临身份焦虑,才能够对身份问题深入思考,进而重建身份认同。以《远山淡影》为开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其创作中考察了不同人物源自不同原因的身份焦虑,以及最终为各自建构的不同模式的身份认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作为移民作家的石黑一雄本人对身份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1] Stuart Hall. Interview with Julie Drew: Stuart Hall on Ethnicity and the Discursive Turn[C]//Race, Rhetoric, and the Postcolonial. Eds. Gary A. Olson and Lynn Worsha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205−240.
[2]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 认同伦理学[M]. 张容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3]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M]. 金寿福, 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 Kath Woodward. Questioning Identity: Gender, Class, Ethnic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5] 罗洛·梅. 人的自我寻求[M]. 郭本禹, 方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 Rob Burton. Artists of the Floating World: Contemporary Writers Between Culture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7] Yu-Cheng Lee. Reinventing the Past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J].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April 1:1): 19−32.
[8]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9] Cynthia F. Wong. Kazuo Ishiguro[M]. Horndon: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 2000.
[10] Brian W. Shaffer, Cynthia F. Wong.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11] Brian W. Shaffer.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12] Taryn L. Okuma. Literary Non-combatants: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and The New War Nov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hD Dissertation, 2008.
[13] 周颖. 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14.
[14] 郭德艳. 英国当代多元文化小说研究:石黑一雄、菲利普斯、奥克里[D]. 天津: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2013.
Identity inxiety in Kazuo Ishiguro’s
WANG Fe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Identity is an inevitable motif in migrant novels, while identity anxiety, as a negative embodiment of identity, can be found in many migrant novels. Unlike other migrant writers, although the Japanese-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pays a continual attention to identity issues of the characters in his writings, he rarely deals with migrant experience directly., with migrants as its protagonist, is an exception. The present essay, focusing on, mainly discusses identity anxiety of the migrant subjects in the novel, involving the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s of this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anxiety either leads to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crisis, or foreshadows their later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mirroring sideways Kazuo Ishiguro’s concerns about and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as a migrant writer himself.
Kazuo Ishiguro;;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crisis
[编辑: 胡兴华]
2017−06−28;
2017−10−13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建构与身份认同:战后英国流散文学研究”(14YBA272);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学视域下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身份认同研究”(17YBQ004)
王飞(1983−),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剑桥大学英语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英语系交流博士研究生,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事学
I106.4
A
1672-3104(2017)06−01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