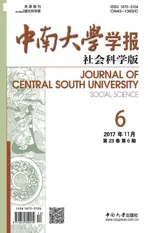“性与天道”的呈现与遮蔽
——论冯友兰“负的方法”
2017-01-11代玉民
代玉民
“性与天道”的呈现与遮蔽——论冯友兰“负的方法”
代玉民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在冯友兰创立新理学以“接著”宋明之理学“讲”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性与天道亦被承续其中。为呈现此智慧,冯先生创立了负的方法,此法是一种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形式、以呈现形而上学之神秘对象的形而上学方法。在呈现性与天道的过程中,负的方法借鉴了道家与禅宗的方法,试图以否定性命题呈现性与天道的“边界”,进而以此边界使人对性与天道有所知。实际上,逻辑性的负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直觉、体验并不契合,因而不能完全呈现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不过,从现代哲学角度看,冯先生却通过负的方法将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带入了现代形而上学领域,并使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
冯友兰;负的方法;性与天道;道家;禅宗
一、引言
冯契先生曾言“中国传统哲学中蕴藏着的最深邃的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1](170)。然而,20世纪以来,以性与天道为特质的中国哲学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变。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新理学”亦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中国传统哲学性与天道的智慧,以直觉、体验为方法,而新理学则更加注重理性精神与逻辑分析。虽然在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与新理学“格格不入”,但冯先生在新理学体系中并未放弃对性与天道的探寻与追求。
冯先生宣称新理学“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2](4)。西方逻辑分析法的引入,使得新理学并非“照著讲”,而对性与天道智慧的承续与呈现,正是冯先生“接著讲”的根本所在。那么,冯先生如何以逻辑分析呈现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为此,他特别借鉴了道家与禅宗的方法,创立“负的方法”。冯先生坦言,“圣学始于格物致知,终于穷理尽性。格物致知是知天,穷理尽性是事天”[2](183),而“负的方法”正是新理学中通达此性与天道智慧的途径。既如此,有待探讨的是,负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它如何呈现性与天道的智慧?这种呈现又是否成功呢?
二、什么是“负的方法”?
冯先生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3](183)。以此看来,负的方法与正的方法具有同等地位,但在新理学中,正的方法得到详尽阐明,而负的方法并未得到直接、明确的揭示。那么,什么是“负的方法”呢?
第一,从隶属的哲学形态看,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旨在建构形而上学体系。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3](274)
从形上学不能讲讲起,就是以负底方法讲形上学。形上学的正底方法,从讲形上学讲起,到结尾亦需承认,形上学可以说是不能讲。负底方法,从讲形上学不能讲讲起,到结尾也讲了一些形上学。[4](202)
可见,在说明“负的方法”时,冯先生潜在地将“形而上学”设定为其哲学背景。在冯先生看来,形而上学具有“能讲”与“不能讲”两个部分,正的方法只适用于形而上学“能讲”的部分,并不适用于“不能讲”的部分。为揭示形而上学中“不能讲”的部分,冯先生创立了负的方法。也就是说,负的方法是揭示形而上学中“不能讲”的有效方法。这样,形而上学便成为负的方法的适用范围,从所隶属的哲学形态来看,负的方法是一种以建构、完善形而上学体系为目标的形而上学方法。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负的方法隶属的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并非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建构新理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等哲学家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形而上学,常常被冯先生作为建构新理学的理论背景。冯先生在创立负的方法时,虽借鉴了先秦道家、唐代禅宗的思想方法,但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言,按照新理学的原则,它“必须排除实际内容,包括价值义涵和本体源头,不能对经验作积极的肯定或释义,而只能作抽象的逻辑的释义”[5](333),而“‘贞元六书’中所说的玄虚、空灵,尚不是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所说的玄虚、空灵的智慧”[5](336)。因此,从哲学形态角度看,新理学是西方哲学意义上,而非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进而,负的方法可视为一种具有西方哲学色彩上的形而上学方法。
第二,从方法的表现形式看,负的方法是一种逻辑分析法,旨在以逻辑命题对经验进行分析释义。
钟会及伊川的答案,以前人却觉其颇有意思,这就是说都觉其有哲学底兴趣。为甚么如此?其原因约有三点:(一)这些答案几乎都是重复叙述命题。(二)就一方面说,这些答案可以说是对于实际都没有说甚么,至少是所说很少。(三)但就又一方面说,这些答案又都是包括甚广。形上学中底命题,就是有这种性质底命题。[6](151)
“形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 义。”[6](153)
从隶属的哲学形态看,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那么,若就负的方法本身而言,从表现形式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对此问题的解答,需要考察形而上学命题的特点。在以上引文中,冯先生认为,重复叙述命题、对实际肯定甚少与外延甚广,是形而上学中的命题应具备的三个特点,而这样的形而上学命题,必然是一个主项、谓词等内容均具备的逻辑分析命题。因而,以这种逻辑分析命题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虽然在内容上较为空泛,但仍不失为一个以逻辑分析为特色的体系。冯先生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功用在于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的主张,与此正相契合。
这样,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一个以逻辑分析为特色的形而上学体系。冯契先生的“‘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1](164)论断,陈荣捷先生“冯氏最大的革新当然是他将理学的观念转变为逻辑的观念”[7]的主张与陈来先生认为冯先生“始终强调理智和理性的分析综合是基本的哲学方法”的说法,皆可以说明此点[8](326)。实际上,作为新理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负的方法必然与新理学的逻辑分析的基本形式相兼容。这样,从表现形式角度看,负的方法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必然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形式,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对经验进行分析、释义。对此,李景林先生将“负的方法”定位为一种形式主义方法,认为“突出了其哲学之‘形式主义’的特 性”[9](69),涂又光先生则直接指出“冯氏的负的方法是经过逻辑分析的负的方法”[10](179),二位教授殊途同归,均印证了负的方法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
第三,从所呈现对象的实质看,负的方法是一种神秘主义方法,旨在呈现不可被逻辑分析的神秘对象。
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力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主义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 “非多”、 “非非一”、 “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3](288)
冯先生认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终极是超越理智的一种境界或状态,即“承认有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者;在此境界中,个人与‘全’合而为一;所谓主观、客观、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11]。柏拉图、斯宾诺莎的“善理念”和“上帝”与人的同一状态,都属于这种不可思议言说的形而上学部分,此部分不可以被逻辑分析方法直接、正面地说明,因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据陈来先生总结,冯先生将神秘主义区分为三种层次,即“‘体验’的神秘主义、‘境界’的神秘主义、‘方法’的神秘主义”[8](325)。以此来看,形而上学体系中这种终极的神秘主义,属于“境界”的神秘主义。在新理学中,正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这一部分,为了对其进行揭示,冯先生创立了“负的方法”。
对此,涂又光先生认为,“讲知性,固然要用知性的方法;讲意志,讲情感,讲直觉,讲神秘主义,只要是‘讲’,仍然要用知性的或经过知性的方法,否则你讲的别人不懂。所用的方法虽是知性的方法,所讲的并不限于知性的内容。”[10](180)就负的方法而言,虽然对象是神秘的,但它仍是一种知性的方法。不过负的方法并不直接揭示、呈现形而上学中不可思议言说的神秘部分,而是以“非多”、“非一”、“非非一”等间接的、知性的方式来表显之。在冯先生看来,“用负底方法讲形上学所能予人底无知之知”[6](228)。对此,陈来先生表示“‘负的方法’就是作为方法的神秘主义,‘不知之知’就是指作为境界的神秘主义。哲学就是要通过负的方法,来达到那作为终点的‘不知之知’”[8](323-324)。由此可见,从所呈现对象的实质角度看,负的方法因揭示形而上学中“境界”的神秘主义,而成为一种“方法”的神秘主义,亦即神秘主义方法。
三、“负的方法”如何呈现“性与天道”?
负的方法虽是现代形而上学中的哲学方法,但它的出现却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渊源。在某种程度上,负的方法正是冯先生试图在现代哲学形态中承续与呈现中国传统哲学性与天道智慧的方法途径。那么,负的方法是如何在新理学中呈现性与天道的呢?
中国传统哲学以儒释道为主流,三家虽主张各异,但儒家之圣人境界、佛教之开悟光景、道家与玄学之真人风度,均是中国哲学最高境界之表显,即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人生境界,透悟性与天道的智慧。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先生对此有深刻的领悟,他表示:
中国哲学所求底最高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它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两句诗的前一句,是表示它是世间底。后一句是表示它是出世间底。这两句就表示即世间而出世间。即世间而出世间,就是所谓超世间。因其是世间底,所以说是“道中庸”;因其又是出世间底,所以说是“极高明”。即世间而出世间,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有这种境界底人的生活,是最理想主义底,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底。[4](6)
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即世间又出世间的智慧,冯先生把握得很准确。在他看来,这种智慧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世间的境界, 实际上,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性与天道的智慧境界。这表明,在新理学中,冯先生并未忽视或抛弃这一传统哲学的境界,恰恰相反,他在新理学中承续并呈现了这一境界。那么,冯先生如何在逻辑化新理学体系中呈现此性与天道的智慧呢?在很大程度上,负的方法正是冯先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而它又如何能够呈现这种性与天道的传统哲学智慧呢?其实,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有赖于负的方法对道家与禅宗方法的吸收与借鉴。
实际上,道家与禅宗也面对着与冯先生相似的问题,即如何借助语言分析表达不可被思议言说的“第一义”。为回应这一问题,道家和禅宗创立了各自的“负的方法”。
就道家而言,《老子》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2](1)的说法,对此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12](1)。这表明,道家之“道”不可以被言语指称,属于超言绝相的存在。虽然道不可说,但《老子》的任务却是对其进行言说,此为“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12](33)。那么,如何言说道呢?《老子》中有“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12](31),“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12](10),“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12](10),“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2](20)等说法,这些说法以比喻、模拟性的命题来象征“道”,看似实有所指,但却并非对“道”的直接指称,这反而使人产生“道”不可被命题说明的印象,因此,这些命题便在间接、否定的意义上,破除了人们的执著,展现了“道”的超言绝相性。对此,冯先生曾言“先秦道家,如《老》《庄》,所谓无,系指其所谓道”[2](24),其实,不仅道家如此,魏晋玄学亦然。可见,以“无”称“道”的否定性说法,也正说明“道”不可言说。
就禅宗而言,自唐惠能、神会始,以不立文字、顿悟为尚的南禅宗崛起,而其所悟之道,实为自心,因“能见性的是我此心。故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13]。但真如本性不可被直接言说,因而在接引大众,启人开悟时,禅师们创造了四宾主、四料简、五位君臣旨诀等方法。这些方法均是在接引大众时,禅师针对具体的机缘、提问而进行开示的方法。例如,冯先生在谈及曹洞宗“五位君臣旨诀”中的“偏中正”时指出,“此种表显第一义的方法,可以说是有语中无语。禅宗中底大师,如有以佛法中底基本问题相问者,则多与一无头脑不相干底答案。”[6](225)如“僧问首山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曰:‘镇州萝葡重三斤。’问:‘万法归于一体时如何?’曰:‘三斗吃不足。’僧云:‘毕竟归于何处?’曰:‘二斗却有余。’”[6](225)可见,禅师虽对提问以实有所指的命题回应,但该命题内容并非所问之答案。在冯先生看来,“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无论怎样答,其答总是胡说,故直以胡说答之。这些答案,都是虽有说,而并未说什么”[6](226)。从冯先生的论述中可知,禅宗在揭示“第一义”时,与道家、玄学类似,也未予以直接、正面的说明,而是以明显错误答案使人知其不是什么,从而打破人的执著,使人对“第一义”有所知,即无知之知,此为禅宗的方法。
道家与禅宗的方法为新理学“负的方法”提供了启示。负的方法不直接指明新理学中的性与天道智慧,而是借助一些实有所指的命题在以间接或否定的方式来显示之,使人获得“无知之知”[6](228)。对此,冯先生曾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画月”进行具体解读。画家画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以线条画出“月”本身,另一种方法是“只在纸上烘云,予所烘云中留一圆底或半圆底空白,其空自即是月”[6](150),此为烘云托月。与此类似,新理学中超言绝相的性与天道如同所画之月,而与正的方法直接说明所指称的对象不同,负的方法的“烘云”是指以逻辑分析命题说明性与天道不是什么。由于性与天道本身的不可分析性,因而以否定命题说明其不是什么,恰是负的方法表显性与天道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在说明它不是什么时,会使它的“边界”被呈现出来。每当负的方法使用一次否定命题,性与天道的“边界”则会被进一步呈现,使人可以借助这些否定命题间接地感受到性与天道本身,对性与天道有所知,此为“托月”,正如画家“所画之月,正在他所未画底地方”[6](150)。在此,可以看出负的方法揭示性与天道的过程:新理学中性与天道的“不可说”,使负的方法转向其可被否定命题呈现或言说的“边界”;“边界”呈现的同时,使得性与天道随之被逻辑分析间接地揭示出来。
由此看来,冯先生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建构新理学体系,以期接着传统的理学讲,但有学者指出“逻辑并非他所谓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14](65)。的确,在新理学中,逻辑分析除建构新理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外,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引导中国人追求更高实在的探索性工具”[14](68-69),即探索性与天道的主要途径。性与天道的超言绝相性,使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只能以个体化的体验、直觉的方式通达,但因个人资质、机缘差异之故,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触及此性与天道的智慧。而在新理学中,冯先生以逻辑化的负的方法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通达传统哲学智慧的公共途径。可见,创立新理学这一现代哲学体系的冯先生,并未放弃对传统哲学智慧的追寻。对此,有学者表示,“在冯先生的描述中,超验领域正是人类存在的升华,是所有中国圣贤追求的顶峰与希冀的愿望”[15](101)。
四、“负的方法”能否真正呈现“性与天道”?
冯先生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性与天道智慧,并试图将其呈现于具有现代形而上学背景的新理学体系中。为此,冯先生吸收道家与禅宗的方法,结合西方逻辑分析传统,创立了“负的方法”,并以之作为呈现“性与天道”的方法。众所周知,“性与天道”在传统哲学中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智慧,但在新理学逻辑化的背景中,冯先生借助负的方法呈现的并非具有直觉、体验内涵的性与天道,而是一种理性、逻辑穷至其极之后的不可思议言说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能否被视为传统的性与天道的现代传承呢?也就是说,在新理学中,负的方法虽可以间接地呈现性与天道智慧,但其所呈现的与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是否相契呢?
对此问题,学界已有学者明确表示质疑。牟宗三先生率先发难,他认为以新实在论对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的解析是错误的,进而批评冯先生“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16]。继而,陈荣捷、蒙培元、郭齐勇、郑家栋等学者均指出,冯先生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呈现中国哲学之最高境界是徒劳无益的,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的智慧是直觉体验型的智慧,与逻辑分析的理性知识完全不同。例如,蒙培元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固然有认识意义,但更重要的则是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是整体综合的,不是逻辑分析的。心灵境界的实现,除概念认识和直觉,还必须有体知、体会、体味、体察、体验。这既是自我实现的存在体验,也是自我超越的本体体验”[17]。郑家栋教授指出,“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哲学恰恰不只是一种‘纯思’的活动,也不能完全归结为‘以名言说出之者’,它应该引导人们去体悟真善统一、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这一境界虽不排斥理智的作用,但它的最终实现须诉之于非逻辑的、动态的、超越于理智分析和语言概念的、与人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直觉体认”[18]。学者们的批评虽然说法不一,但殊途同归,都是在批评负的方法乃至新理学的逻辑分析形式不能契入、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性与天道智慧。对此,郭齐勇教授有一简洁明确的概括:“形式化、逻辑化不能承担‘贞元六书’为人生境界作形上学论 证的任务。此任务实是由中国自身的体验方法完成的。”[5](341)
不可否认,以上诸学者的批评确有道理,中国传统哲学的性与天道智慧,无论是朱子的“格物致知”以至“豁然贯通”,阳明的“良知”,道家的“道”、玄学的“无”,佛教的“佛性”“觉悟”等,确实只有通过人们亲身的直觉、体验才能通达,并非仅靠逻辑分析这种理性主义方法即可获得。因此,胡伟希先生才提出“假如说哲学思维中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的话,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到底能否‘言说’形而上 学”[19]的疑问。在此,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若新理学中所要呈现的是体验直觉型的“性与天道”,就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性而言,不得不说,冯先生借助负的方法做出的相关努力是不成功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在承续传统的性与天道的智慧时,有一个前提,即西方形而上学背景。冯先生坦言,新理学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2](4),这一“接著讲”表明冯先生并不只是传统哲学的叙述者,而是将传统哲学与当时最前沿的西方形而上学融合创新的哲学家。当时维也纳学派主张“取消形上学”运动,他们以逻辑分析为方法,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综合命题,但又无可验证,因而是无意义的命题,应予以取消。留美归来的冯先生对此派理论颇为重视,认为此派给予西方形而上学以重大打击。因此,如何在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下重建形而上学,便成为冯先生思考的问题之一。这样,传统哲学中性与天道智慧的承续与重建形而上学,这两个任务便成为新理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冯先生明白,若要不受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新底形上学,须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底”[4](126),因而他在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4](126)。
也就是说,为在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下重建形而上学,冯先生必须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形式;而在吸收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承续性与天道的智慧时,又必须空掉传统哲学中的直觉、体验,仅保留其逻辑形式。否则这些直觉、体验既涉及实际的内容,又不能被客观验证,在现代哲学领域,正落于维也纳学派的批判范围之内。不过,在冯先生看来,这一做法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为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4](127),是不受维也纳学派的真正的形上学。由此可见,虽然新理学的逻辑分析方式脱离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直觉、体验的轨范,但却将性与天道智慧由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带入现代的世界哲学领域,并以负的方法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对此智慧有所认知。这样便为哲学家们将来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恢复直觉、体验的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奠定了逻辑框架,打下了基础。从这一角度看,负的方法以逻辑分析呈现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的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兼通中西哲学的冯友兰先生撰写了《新理学》等六部著作,创立了新理学这一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是对中西哲学的综合创新、深度推进。但新理学也引起学界很多争议,质疑的核心在于逻辑分析法与中国哲学的直觉、体验精神并不相契,所谓“接著讲”不能呈现传统哲学性与天道的智慧。那么,新理学到底能否呈现性与天道的智慧呢?在此,我们分析了用以呈现此智慧的负的方法的内涵,及其具体的呈现方式。若从直觉、体验的角度看,负的方法的逻辑性并不能完全呈现性与天道的智慧。但若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冯先生吸收中国道家、禅宗的方法,与西方逻辑分析法相结合所创立的负的方法,虽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体验不相契合,但却将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带入现代哲学领域,并使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
当然,学界对冯先生的批评确有见地。不过,这些批评所指出的新理学的不足之处,正是冯先生将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融合创新,这一初步尝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状况。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新实在论是否就是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的最好方式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冯先生的努力仍然值得称道。他至少做到了构筑成他的新理学的一个完整体系,使后人能够清楚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或者清楚地看到他的失误。他所以自称自己建树的新理学为有异于宋明理学的‘新统’,也是以西方逻辑学批判中国旧的形而上学的结果。他事实上是为几乎所有的在他之后企图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的老师宿儒打开了一条新路”[20]。
冯先生开辟的这条“新路”具体是指什么呢?既然负的方法不能完全呈现传统的性与天道智慧,那么,如何更好地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呈现此智慧,正是后继学者“接著”冯先生新理学“讲”的新路所在,也是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新路所在。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新路正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21]。
[1] 冯契. “新理学”的理性精神[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 冯友兰. 新理学[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4] 冯友兰. 新原道[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5] 郭齐勇. 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类意境的哲学——论冯友兰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6] 冯友兰. 新知言[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7] 陈荣捷. 冯友兰的新理学[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83.
[8] 陈来.论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 李景林. 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冯友兰哲学方法论引发之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6): 66−79.
[10] 涂又光. 新理学: 理论与方法[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1] 冯友兰. 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C]// 冯友兰. 哲学文集(上).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08.
[12] [魏]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3] 钱穆.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C]//张曼涛.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192.
[14] Lin, Xiaoqing Diana. Feng Youlan a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M]. Leiden: Brill, 2016.
[15] Richard C. K. Lee. Comparing Søren Kierkegaard and Feng Youlan on the Search for the True Self [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13, 40 (1):87-105.
[16] 牟宗三.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0.
[17] 蒙培元.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87.
[18] 郑家栋. 冯友兰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新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限制[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98.
[19] 胡伟希.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的言道方式[C]// 胡军. 反思与境界——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国际研讨会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90.
[20] 李慎之.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我们向冯友兰学习什么[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56.
[21]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C]// 郑家栋, 陈鹏. 解析冯友兰.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
Covering and discovering of the Nature and Tao: On Feng Youlan’s Negative Method
DAI Yum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hen Feng Youlan found the Neo-Li teaching to develop the Li teaching of Song and Ming Neo-Confucianism, the wisdom of Nature and Tao was preserved in it. In order to discover this wisdom, Mr. Feng created the Negative Method with logical analysis as its basic form and with discovering metaphysical and mysterious object as its metaphysical approach. In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Nature and Tao, the Negative Method, borrows from Daoism and Confucianism,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boundary between Nature and Tao through negative proposition so as to acknowledge people of Nature and Tao. Actually, the logical form of the Negative Metho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ence being unable to discover fully the Nature and Tao.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hilosophy, Mr. Feng has, through Negative Method, taken the traditional wisdom of Nature and Tao into modern metaphysics, and has discovered the wisdom of Nature and Tao to some extent.
Feng Youlan; Negative Method; Nature and Tao; Daoism; Zen Buddhism
[编辑: 谭晓萍]
2017−06−11;
2017−09−07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代玉民(1989−),男,河北涿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017−2018),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国哲学
B261
A
1672-3104(2017)06−0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