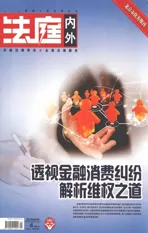淘宝地址送达法律文书侵犯隐私吗
2016-12-12文/石岩
文/石 岩
淘宝地址送达法律文书侵犯隐私吗
文/石 岩

2015年11月24日,澎湃新闻一则题为《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浙高院与阿里合作,直接寄到淘宝收货地址》的新闻迅速传播,在朋友圈刷屏。
消息一出,顿时舆论哗然,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拍砖吐槽。纵观各类评论,质疑之声多在于此举是否侵犯个人隐私,支持者则多认为有利于解决送达难、惩治“老赖”等社会不诚信行为,且相关言论似乎依身份不同,形成两大阵营,质疑者多为一般公众,而支持者多为深切了解基层司法现状的法律工作者。
时隔一周,当喧哗之声日渐平息,我们的眼球已被新的热点占据时,作为一名原基层法官、现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笔者却想更为冷静、深入而审慎地思考相关问题。
“淘宝”提供商业大数据≠侵犯隐私
首先,对于那些盲目质疑的声音,我想先来谈谈关于隐私保护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这则新闻最大的质疑即在于此。
淘宝购物形成的个人信息、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甚至是资产情况,毋庸置疑,当然的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但是,任何“私”权利都是有界限的,当面对更多人的“公共”利益时就要让步。
在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同样掌握着客户信息和更多个人资产信息的银行。作为金
融机构,银行对于客户信息的保密义务不可谓不高,这在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当公安司法机关因刑事、民事、执行等各类案件的办理需要,依法需查询、冻结甚至是直接扣划客户银行存款时,作为负有协助调查和执行义务的机关,银行也必须给予配合,提供客户信息、资金状况、冻结存款、甚至直接扣划资金。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等法律法规中均可找到依据。试想如果任何“私”的权利,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都不能“触碰”的话,社会将无公平可言,社会更将是“老赖”的天下。
那么,银行尚且如此,更何况“淘宝”呢?相对于银行而言,它更多地还是一个商品交易平台,尽管“淘宝”已经集合了众多投资理财的金融功能,但其掌握的客户资产毕竟有限。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因为“淘宝”将客户信息、资产状况提供给了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就简单地认为其已构成对隐私的侵犯,关于浙江省高级法院与淘宝之间“战略合作”的相关举措是否合理、是否适当,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以浙江省高级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正在转变常规思路,积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主动破解审判和执行工作中的难题,对这一态度、思维、创新及魄力,即应首先点赞。
任何改革和尝试受到质疑,都是正常的。只有在质疑声中,改革才能不断完善,也更加科学。澎湃新闻选择将淘宝收货地址用于法院送达这一点作为了这则报道的标题,实际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则新闻,就会发现浙江省高级法院与淘宝之间的合作绝非仅限于此,双方合作涉及送达、执行多个程序,同时也不是淘宝单向的输出,实则还涉及法院审判数据的利用问题。下面,我们就针对不同问题,一一分析和思考。

国家权力机关使用商业数据的规则亟待明确
淘宝与浙江省高级法院的此次合作,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是国家权力机关与商业运营主体之间的一次“联姻”。因此,国家权力机关使用商业应用形成的大数据,应适用何种规则,如何才能构成合法使用,做到既保护个人隐私不被随意侵犯,又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是首先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随着商业交易模式的变革,大数据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这些商业应用过程中形成的包括用户基本信息、消费习惯、资产状况等在内的信息,当然属于个人隐私。那么,当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类国家权力机关、甚至是其他商业主体需要使用这些信息时,在何种情况下、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和程序才能获取,又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基于何种目的才能使用、如何使用,这些问题目前均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空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在哪里,亟需明确。
商事主体获取国家权力机关数据的范围应以社会公众的公开为限
仔细阅读浙江省高级法院与淘宝之间的合作,不难发现,双方的战略合作并非单方的淘宝数据向法院开放,还包括法院审判数据对于淘宝的开放。
文中提到“法院的数据——案例资源如何利用起来?这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运行在阿里云平台的法院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正在搭建。简单地说,浙江各级法院的案例资源将进行电子化存储,通过阿里的多维度分析、数据可视化、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相似案例比对服务’。”文中描绘此“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将开发和实现法官审判经验共享、司法资源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功能,并进行审
判偏离度分析、预警。”
这一做法显然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审判公正。借助成熟商业主体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手段,辅助国家司法机关裁判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国家权力机关与商业主体之间的合作同样存在一个界限问题,基于这种合作而取得的数据,商业机构能否保守秘密、会否将数据用于其他商业用途,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法院裁判数据同样涉及当事人隐私,同时还涉及审判秘密。笔者认为,为避免上述问题,法院裁判数据对商业平台的开放程度与范围,应以司法向社会公众的公开为限。
刑事侦查、执行程序商业大数据大有可为
如前所述,当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两个法益相冲突时,个人隐私即应让步。因此,在刑事侦查及执行程序中,使用商业平台大数据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即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符合现行法律的。
与民事案件的办理不同,因刑事侦查需要,或者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国家生效法律文书,国家公权力机关即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执行人的个人基本信息、通讯地址、联系方式、资产状况等进行调查,并根据这些信息及案件办理的需要,采取抓捕、拘留、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正如浙江省高级法院与淘宝的合作一样,通过淘宝商业平台提供的数据,可以对涉诉人员绘制“画像”,以实现更准确地打击犯罪、更有力地惩治“老赖”,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可以说,在刑事侦查和执行领域,商业大数据大有可为。
送达程序使用商业大数据需谨慎
由于澎湃新闻在报道中将淘宝收货地址作为法院送达地址作为新闻的标题,因此关于送达程序使用商业平台大数据个人信息的正当性问题,是讨论最多的话题。
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法院,曾经从事民事审判5年的“法官”,我深知法院送达之难、法官送达之苦。但是对于这一做法,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的诉讼法,已经就送达问题进行了制度设计,在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设立了公告送达程序。在一般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只不过是一个私纠纷的中立裁判者,其调查权应有一定的限度,而不应无限扩大。在送达、举证责任分配、证据规则等制度设计的帮助下,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仅仅是出于缩短案件审理期限、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另一方当事人诉累等角度,就如此使用个人隐私信息,似有不妥。
首先,关于查找不到被告的情形,笔者认为,提供被告准确信息的责任还首先应由原告一方来承担,而不应由司法机关越俎代庖,因为这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交易的过程中应尽的注意义务,也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的商业社会更加成熟,交易主体的风险意识得到提高。
其次,关于送达难带来的诉讼周期长、当事人诉讼成本高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建立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当事人必须承担的交易成本。
再次,关于很多支持者提出的,原告故意提供被告虚假地址、被告故意隐匿等情形,笔者认为现有制度完全可以解决。关于原告故意提供虚假地址、联系方式的情况,法院诉讼程序中在确认了被告身份的情况下,可以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如进入执行程序,查找到被告,被告认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以提供证据、申请再审以维护自身权益,而故意提供虚假地址的一方当事人,如能查证属实,亦会面临法律的制裁。关于被告故意隐匿的情形,亦是如此,在诉讼程序中通过公告送达、举证责任分配等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做出判决,在判决的执行阶段,如前所述,我们大可运用商业大数据为其“画像”,查找到其下落、执行其财产,并对其故意隐匿、拒不执行的行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大数据所有权归属及使用规则亟待建立
随着商业交易模式的变换、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商业平台应用过程中形成的大数据越来越炙手可热。大数据资源的价值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同。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应用日趋广泛,甚至大数据交易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大数据的所有权到底归属于谁,究竟是消费者还是商业平台?大数据信息应如何合理、合法地使用?数据信息披露使用的规则和法律底线到底在哪儿?这些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尚没有结论,甚至很少被涉及。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大背景下,这一课题涉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利益,亟待深入研究探讨并适时规范。
责任编辑/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