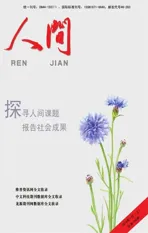伊格尔顿文本意识批判方法论的生成条件(一)
2016-11-28薄海
薄海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00)
伊格尔顿文本意识批判方法论的生成条件(一)
薄海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00)
摘要:第二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衰落后,霍尔与伊格尔顿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领域中被突显出来,霍尔在方法论上将结构主义的方法演绎成结构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且在总结右派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也拓展了自己的差异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在霍尔的研究视域中,他更强调对非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从而在差异文化的发展中找到人的身份认同,而在霍尔之后的伊格尔顿则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了左派威廉斯,即他的老师的理论基础之上,又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上开拓了霍尔的差异文化研究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文本意识批判的研究路径,在当代英国文学和政治领域为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伊格尔顿;文本意识批判;生成条件
伊格尔顿在进行理论创作之前就意识到了现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政治理论的在社会理论中的退却,这种退却不是理论本身的倒退和消失,而是当代这些重要的理论家们都逐渐的离开他们的学术理论的创作。就像罗兰·巴特在意外中死于车祸,米歇尔·福柯因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无药可救,路易·阿尔都塞因为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精神病意愿,自己的老师威廉斯和布尔迪厄因为年岁已高,也不能在进行马克思理论的创生工作。除此之外,在老一辈理论家们的离去之后,新一代理论家始终没有哪位杰出的学者可以弥补这些理论创作中的缺失;在当下的社会中,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一些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思维与方法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广泛地被学者们吹捧,这种以往的经典政治思想和思想者们在当下的社会中都纷纷退场,这种退场所导致了理论创作的缺失就是伊格尔顿所担心的政治的遗失。不过伊格尔顿也总结了当下社会理论的新兴苗头,首先,当下的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变得丰满,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着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几个部分上,但是在当下的学术理论研究中,在日常生活中与社会主体紧密联系,时常交往的对象已经被广泛的认同为学术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者的眼光逐渐从沉重的书堆中开始关照日常流行的文化题材,比如音乐,时尚,性爱等。这些新的苗头在现如今都可以成为正统文化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切入点,从此可以看出,个人的生活在当代的理论创作中变得鲜活和丰满,人的人性与人格都被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另外一个进展性的现象就是大众文化被当代的理论家和社会中的实践主体所重视,这种大众的文化不仅表现出日常流行题材被引入了学术的视野,更重要的表现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距离缩短了,当下批判的新形势就是这种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批判已经具有即时的效应和功能;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在第一时间被阅读者思考后,相关的评论就会被大众媒体所公开。伊格尔顿总结了这些新的学术现象认为学术研究与日常偏好的结合使得个人的研究兴趣得到满足,让个体的学术研究与自身的兴趣相互结合,整个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都变得丰满,个人的愉悦在严肃和乐趣的平衡中得到了实现;而后者的大众文化的历史距离的减缩使得群体的愉悦情感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下成为了可能,所有的文化题材在当下都可以找到鲜活的,日常的,即时的素材;以往的现代性的纯粹理性的政治和文化的逻辑已经在历史时间中被溶解,个体性的生活愉悦已经逐渐被社会和大众传媒所宣扬,教条形式的限定虽然没有死去,但是不同领域的多种教条形式的同时呈现让当代的理论研究者们和日常生活的主体们有了选择权,人们没有抛弃教条,也没有淹没纯粹理性在历史,政治和文化中的规约逻辑,但是人们选择了与自我愉悦相互联系的理论范式,研究的框架,或者说是生活的一种枷锁;但不论如何,当下的人对现实的个体的愉悦和大众群体的愉悦的关照已经远超过以往对现代性,纯粹理性的社会结构,政治叙事和文化逻辑的关涉。人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变得具有人格,当下的社会主体对愉悦的追求中,人性被个体和大众的社会实践所实现和呈现。伊格尔顿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主体性需求对社会呈现的过程史,而不单纯的只是理论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批判,他认为人的需求从远古历史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着,后来随着私有制的蔓延,社会主体之间产生了差距,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各种阶级和阶层逐渐产生并且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后一代的社会人总是在批判前一代的社会精神,诋毁前一代的社会贡献,但是不论如何发展,主体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的需求从来没有改变过,社会主体总是千方百计的按照自己设想的幸福生活的计划而奋斗着,但以往的主体行为在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目的并不是关照自己的需求和理想,而是关照了他人,虽然主体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被他人利用的行为过程,可是主体人的社会实践在革命历史的记载中从来都失去了自我的意愿。不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抑或是以往社会种族之间的互相残杀,这些暴力行为的背后所要依靠的精神和灵魂并不来源于行为主体,而是来源于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也已规定为一种社会意识或者是霸权意识。在社会革命中,人们无一例外的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对另一些种族和人民实行了暴力行为。伊格尔顿总结了霸权意识逻辑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的普适性;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还是在从古到今的一次次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会在自己占领的领域中宣扬自己政治意识的高尚价值,不仅使得这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存在于发展的需求,也可以同时满足被占领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需求;但是不论人们选择了哪一种政治政策和经济制度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社会主体永远都受到外来的意识和精神所影响和控制。①伊格尔顿如同福柯和德里达一样,对这些意识形态的精神入侵充满了排斥,不过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交往的主体能够摆脱这种意识思维的干扰。但是伊格尔顿并没有完全像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和具有规约性质的社会条文抱有怀恨的情感。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缺失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但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架构与社会规范和各种契约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意识形态的完全抛弃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与社会契约产生了距离,最后社会道德的评价将会失去制度性的保证,整个后现代的政治意识的结构只能给现代性的法治体系造成困扰。分析了这些重要的现代性的现象和问题后,伊格尔顿提出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理论的发展困境,那就是如何才能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产生的自由发展的干扰和如何解决毁灭意识形态后社会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中道德与信仰的崩溃。伊格尔顿在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君主与原始部落的土地斗争中,失败的部落和种族所失去的并不都是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多种族部落的人在外来的入侵者的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都能存活下来,但是所的存活下来的种族和部落群体们无一例外都成为了新时期的,新阶段的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失去了领土的所有权,但是仍然有权利使用所在领土的任何自然财物,他们可能失去了斗争前所公认的部落首领,但是他们依然在本部落应有的或者是新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社会的实践活动。当古代君王的权利在资产革命的胜利中削弱和消失后,所保留下来的王室成员必定是一个新阶段的王室的继承人,他们可能依然保留着自己高贵的心态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吸收了新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知识。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中,不论是哪一方获胜,哪一方失败,处于劣势的阶级和社会群体必定要与获胜者的精神追求相一致。在君王统领下,仍然会有持续发展的,以前彼此抗争过的宗族和部落;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体制下,新的君主和王室成员仍然可以高雅的生活在自己的领土上,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后,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所有的社会公民都有着让自己生活更加美好的权利和希望。在这些社会历史现象的演变中,政治结构对社会公民的思想控制没有改变过,经济资本的社会集聚也没有发生过改变;文化仍旧延绵不断的按照历史进程的演变而发展。可是在这所有的线性流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在潜移默化中被遮蔽了,那就是传统。③伊格尔顿的历史发展中的传统的被遗忘主要指的就是国家意识传统的被遗忘。伊格尔顿分析了当代这种意识形态传统的被遗忘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重要的实践主体在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中迷失了方向,变成了具有惰性的社会工具。在二战中磨练过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战后的传媒中塑造的明星政治家们,在虚夸设想中化成了泡沫,这些有着生命力的中产阶级好比原本生活在海洋里的鱼类,而现在被政治家们放在了透明的玻璃缸中,虽然这个透明的玻璃钢仍然沉浸在海水之中,生活在这个玻璃钢中的生物们仍然看得到海洋中发生的一切,但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与透明玻璃钢之外任何生物交往和接触。④伊格尔顿认为,中产阶级的这种被透明玻璃的介入和阻碍是受到中产阶级自己对自身地位的认同所造成的。大众传媒带给中产阶级者们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意识思维理念,更不可能是积极的社会建构的思维逻辑,大众传媒所带给整个世界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们是一种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伊格尔顿认为在当下的社会,带着礼貌和穿着礼服的人们已经逐渐退场了,那些喜欢在战场上厮杀夺命的武士们也低调地在法制社会中谋生;而发展最为迅速的,地位提高最明显的是那些影视界的明星们,还有那些证券公司的总裁们,在金融市场的波动中,他们跟随者资本的起落而起落,而多数的社会大众也将这些新时代的明星赋予了资本生命的象征,也随着这些人的欢喜而欢喜,悲痛而悲痛;社会大众的人格被当下的明星们占用了,而这些明星们的人格又被金融市场占用了。整体的人群的性格特征都在资本和金融的波动中徘徊不定;人失去了自我在社会中的原有身份,这种身份的缺失使得大众群体们失去了以往的各种“主义”和信仰,在生活的矛盾中,这些大众群体已经没有以往的革命性的精神了,因为他们自我的身份已经难以确定,矛盾双方的对象性质也难以辨别,反抗谁,依靠谁都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迷幻联想。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伊格尔顿认为当下一个严峻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让社会大众在文化霸权之中重新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的社会特性,重新找回自我存在和发展的信仰与精神。⑤
注释:
①Terry Eagleton: The truth about the Irish, Dublin: New Island books, 1999, p.61.
②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e and Society;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78.
③Terry Eagleton,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6.
④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e and Society;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120.
⑤Terry Eagleton,The truth about the Irish, Dublin: New Island books, 1999, p.48.
参考文献:
[1]Terry Eagleton: The truth about the Irish, Dublin: New Island books, 1999.
[2]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e and Society;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3]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9.
[6]Terry Eagleton,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4.
[7]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