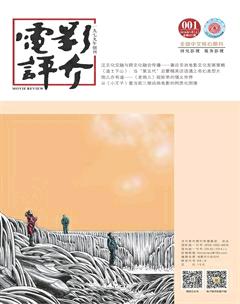大卫·芬奇电影创作中的“黑色”元素研究
2016-06-06史丽萍
史丽萍
大卫·芬奇电影创作中的“黑色”元素研究
史丽萍
“黑色电影(filmnoir)”是法国影视评论家尼诺·法兰克(Nino Frank)基于“黑色小说”一词的启发针对《马耳他之鹰》(1941)、《劳拉》(1944)、《双重赔偿》(1944)等影片的评论于1946年在《法国银幕》杂志上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它作为一个“电影类型”在美国好莱坞等地盛行至今。从内容上看,“黑色电影”一般指借助悲观、低沉、阴郁的调子以城市昏暗街道为背景,通过对社会犯罪和世界堕落场面的关注,来表现愤世嫉俗和人性危机的主题思想。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黑色电影”影响了诸多电影创作者,其中大卫·芬奇(David Finch)就是一个颇具“黑色”风格的电影导演。大卫·芬奇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垮掉一代”文化风靡一时的美国,他不仅对战后光怪陆离、庸俗不堪的美国社会现实充满不满之情,而且选择了特立独行的“脱俗”方式表达着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从1992年执导《异形3》以来,大卫·芬奇先后完成了《七宗罪》(1995)、《心理游戏》(1997)、《搏击俱乐部》(1999)、《战栗空间》(2002)、《十二宫》(2007)、《返老还童》(2008)、《社交网络》(2010)、《龙纹身的女孩》(2011)、《消失的爱人》(2014)等影片。这些电影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鲜明的“黑色”元素,不仅呈现出浮华社会阴暗暴力的一面,而且揭示出人们被空虚、焦虑、恐惧所笼罩的复杂心理状态。

电影《消失的爱人》海报
一、大卫·芬奇电影创作文本中的“黑色”元素
电影的文本主要包括叙述手法、故事题材、人物形象、思想主题等元素,就美国黑色电影来说,它一般采用多元混合的叙事手法,以凸显宿命感和时间流逝感的形式对美国社会中的暴力进行观照,主要通过对具有双重道德人格、不满社会现状、孤独绝望等一系列叛逆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现转型阶段社会异化和人性堕落的思想主题。大卫·芬奇的电影在以“幽暗”的视角延续美国传统“黑色电影”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反讽、平实冷处理等新颖手段呈现出一个别样的“黑色”影像世界。
(一)多元混合的叙事手法
大卫·芬奇之所以能把充满“黑色”元素的故事跌宕起伏地展示出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独到的叙事手法。首先,他在电影创作中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叙事主体,而是通过多重叙事主体或者无叙事主体来展开故事。他早期的电影《异形3》《七宗罪》《战栗空间》以及近年之作《龙纹身的女孩》等完全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以“他”的形式客观冷静地讲述了故事内容,属于典型的“无叙事主体”;《心理游戏》和《搏击俱乐部》通过第一人称的形式分别让主人公尼古拉斯和杰克以“回忆”的形式进行“真实”的故事告白,这是“单一叙事主体”;《返老还童》《社交网络》和《消失的爱人》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的形式构建出多个叙事主体,比如《返老还童》中虽然是由女儿以“我”的形式阅读日记,但是声音却是本杰明的第一人称形式完成的,而《社交网络》则让马克、文克莱沃斯兄弟和学校三方作为叙事主体讲述一个“各执一词”的故事。其次,大卫·芬奇没有使用单一的线性时空叙事模式,而是频频使用非线性时空叙事,让一个个故事在保持完整统一的前提下显得错综复杂而又环环相扣。《搏击俱乐部》堪称大卫·芬奇非线性时空风格电影的扛鼎之作,影片一开始就把“杰克被绑在椅子上”的结局展现出来,然后直接通过杰克展开倒叙回忆。在倒叙过程中,大卫·芬奇会在不经意或突然之间穿插一些“关联不大”的幻想内容,使得原本就“无序”的故事显得更加“突兀”,这正是黑色电影的一个典型特征。另一部作品《返老还童》则是把非线性叙事时空的模式又推进了一步:通过奇幻文学的形式把“倒叙的过去”和“正叙的现在”交融起来,让“本杰明·巴顿一生”这个原本简单的线性时空故事变得变幻莫测。而2014年的新作《消失的爱人》同样运用倒叙和插叙交织的形式通过丈夫尼克和妻子艾米两个叙事主体把一个陷入崩溃的婚姻故事编织得“引人入胜、惊险刺激”。
(二)“不一而论”的人物形象
为了契合幽暗低沉的“黑色”基调,大卫·芬奇在电影创作中往往把人物塑造成内敛沉稳的性格类型。这些人物形象一般都是处在社会边缘化地位,拥有特殊的经历、背景或精神状态。虽然都是社会非主流人物,但是他们没有完全像传统黑色电影中的人物一样以消极悲观、颓废无奈的态度面对黑暗的世界,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奋起反抗。正是大卫·芬奇对传统黑色电影的创新,使得其电影文本中的人物性格更为复杂多样,也使得人们难以用传统的善恶好坏标准来衡量。在《七宗罪》中,杜·约翰是一个冷酷无比的连环杀手,但是他内心却流露着深刻的“惩恶扬善”情怀,并以此作为准则行事做人。当被问到“你是说你做的是上帝的善事”时,他的面孔上显现出一副玩世不恭却又古怪难测的神情,同时他认为“罪恶就在我们周围,只是在混乱败坏的当下社会里,我所杀掉的人才被称之为无辜”。可见,杜·约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内心对理想化社会是非常向往的,而且也渴望通过一些从善行为去感化世人,但是现实的残酷无情却逼迫他通过极端的方式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道德救赎。善与恶之间原本就在一念之差,人们就是在善恶选择方面陷入了困惑而造就了多面性人格。影片中的警探米尔斯也是一个“不一而论”的人物,他本来站在善良一方,但是妻子的遇害彻底激起了其愤怒的神经,进而犯下了“罪恶”,他也就成了一个两面性的人物。在影片《社交网络》中,主人公马克虽然具有出众的才华和极高的智商,但在情商方面却表现得形同白痴,关键是他的性格有着相当阴暗的一面。纵观他的成功历程,不难发现他是通过对别人的欺骗而实现的,其中欺骗对象包括其唯一要好的朋友。听证会上马克目空无人,恣意妄为的行为更是彰显了其阴险多变的性格特征。
(三)“难以言尽”的思想主题
大卫·芬奇的电影很多都以开放式结尾收场,给观众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引发出“难以言尽”的多重主题。虽然作品的主题极具开放性,但基本上表达了对当下社会、人生与人性的质疑、嘲讽和批判。大卫·芬奇在《七宗罪》中虚构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环杀人狂,通过极其暴力恐怖的场面隐喻出当下社会的蜕变。现实社会中虽然找不到一个像杜·约翰这样的杀手,但是在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变态凶杀案件中不难找到他的部分身影,比如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的破坏行为以及吉姆·琼斯、邮包连环杀手大卫·卡钦斯基等案件就是参照,因此,杜·约翰等行为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下社会土壤“正常”出现的,这就是大卫·芬奇通过这种“黑色”风格电影揭露和批判社会异化的表现。《搏击俱乐部》则是通过“暴力”和“死亡”描绘了社会边缘青年的生活状态,隐喻出现代社会中边缘群体虚无幻灭感和自我麻醉的精神世界。搏击会更像一个医院,而暴力是药,搏击是精神疗法。[1]在这里,人们都上了瘾一样迷恋上了暴力,因为他们相信“暴力可以解脱奴役”,殊不知他们已经走进了另外一种更为残酷的“精神奴役”,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悲剧。大卫·芬奇期望通过这样一部暴力十足的“黑色”电影来引导人们反思造成种种暴力的根源,进而从文化上实现自省和拯救。电影《社交网络》虽然没有太多暴力元素,但却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人类社会的滑稽怪诞和人性的难测。大卫·芬奇不仅揭示出在网络等高科技横行背景下人们追逐利益的乱象,而且控诉了人们深陷精神囹圄而自我浑然不知的悲剧状态。
二、大卫·芬奇电影视听语言中的“黑色”元素
如果说文本是大卫·芬奇“黑色”电影创作灵魂的话,那么镜视听语言则是其“黑色”电影创作的框架,当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大卫·芬奇在电影创作中通过场景设计、光影效果、镜头运用等视听语言形式营造出奇特的“黑色”影像效果,与作品的“黑色”主题风格保持高度一致。
(一)黑暗场景的独特设计
大卫·芬奇在电影创作中一般把场景设定在夜晚的城市、黑暗的街道、荒废的破屋子、偏远的郊区车站、幽暗无比的酒吧、夜总会、阁楼等空间,营造出阴郁的氛围。在《七宗罪》中故事大部分发生在雨天泥泞不堪的昏暗街道中,而内景也是侧重对昏暗角落的描绘,甚至连屋子里陈设的道具都专门进行了消色处理,使其显得格外低沉,特别是案发现场被设置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消失的爱人》中,不管是尼克与妻子艾米的暧昧亲密,还是尼克与妹妹、警方的交谈,抑或艾米对情人的谋杀,基本都发生在灯光昏暗的室内,尤其是艾米伪造“强奸现场”谋杀情人的场景把“黑暗”的影像空间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多变光影效果的运用
为了突出影片的“黑色”风格,大卫·芬奇充分利用了光线的反差和阴影的设置,这在日间戏和夜间戏、内景和外景、人物造型和环境造型方面都有具体体现。在《返老还童》中,大卫·芬奇为本杰明与黛西的第一次相遇设定了一个唯美的自然环境,即通过自然光的正常显示描绘了美好的爱情,而在其它较为阴郁的环境中,大卫·芬奇有意通过人造布光降低了自然光的作用,比如在老年黛西的病房里,窗纱的白色、柔和日光灯的白色以及黛西苍老的妆容和护工的衣服的白色都很好营造出冷峻肃穆的氛围,体现了较强的悲剧色彩。《七宗罪》虽然是一个彩色电影,但是大卫·芬奇却使用大量不饱和的色彩孕育出颓废清冷的色调,即使是光天化日之下他也运用绿色和蓝色来烘托污浊冰冷的气氛,展现出人类阴暗的内心世界。
(三)多种镜头的交错使用
大卫·芬奇拍摄电影时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让镜头跟着自己无穷的想象力行进:可大可小、可高可低、可远可近、可直可弯,从而让画面带给观众以超强的视觉冲击力。在《十二宫》中,大卫·芬奇使用了诸多运动镜头突出了作品的现实色彩。镜头从“十二宫”杀手坐上一辆黄色出租车开始,紧跟着来了一个俯拍镜头,交代了周围的环境,随后镜头以出租车的行进轨迹为拍摄路径,并通过叠化将镜头逐渐推近,直到出租车停止,而当镜头恢复到正常机位时,命案开始发生:杀手从后座射杀了司机。这组运动镜头不仅交代了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而且充分展示了杀手的凶残性。[2]在《七宗罪》中,大卫·芬奇则是使用了大量静态镜头,以客观冷峻的形式向观众展现了犯罪现场的各种情况。这种镜头运用虽然没有给观众刻意灌输什么,但是起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把观众带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增强了画面的艺术张力。
结语
总的来说,大卫·芬奇不仅在电影创作文本和视听语言中均融入了“黑色”元素,但是他的作品没有一味继承传统“黑色电影”的风格,而是通过反讽、冷处理等手段实现了革新,从而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别致深邃的“黑色”影像世界。作为一个笃信“艺术至上”的导演,大卫·芬奇通过“黑色”元素不仅展现出现实社会的浮躁无味,而且从深层次揭示出人类细腻而深刻的精神世界,无怪乎人们称之为一个充满哲思意味的“鬼才导演”。
参考文献:
[1]栾鹏.从《搏击会》《七宗罪》看大卫•芬奇电影的道德与暴力[J].时代文学,2010(8):225-226.
[2]张立群.大卫•芬奇电影艺术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1(6):25.
【作者简介】史丽萍,女,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英语教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