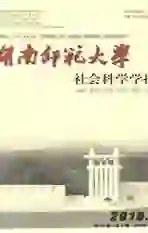航业团体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关系初探
2016-05-14刘利民
刘利民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的兴起、发展与航业团体有密切关系。由于航业团体与航权存在切身利害关系,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他们就一直呼吁收回航权,这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没有航业团体的呼吁,南京国民政府收回航权态度不会那么积极。在收回航权的过程中,航业团体也一直呼吁和提出建议,在中日修约、航政会议、中关中英修约交涉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航业团体积极活动的身影。这既为政府收回航权提供了有利后盾,支持了政府的外交活动,当然也对政府决策形成了压力,使之不敢在收回航权问题上过多妥协。航业团体在收回航权问题上的态度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两者在收回航权的具体主张和步骤方面有一定差距。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航业团体;收回航权运动;领水
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发起了收回国权运动,其中恢复航权是重要内容之一。航业团体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27年,航海界资深人士金月石等筹备成立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其宗旨定为“维护航权,收回引水权,发展航海技术,联络同仁感情”。该会一直为收回航权奔走呼号。1925年11月1日,航业大佬虞洽卿联络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政记轮船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北方航业公司、宁绍轮船公司、恒安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丰安轮船公司、招商内河轮船公司10家公司筹组上海航业公会,因时局等原因,至1927年7月2日正式成立(1931年改称上海航业同业公会,1934年改称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该公会成立后,为航权收回提出了诸多建议。各地航业团体亦非常活跃。他们通过电报、宣言、信函、集会、请愿、谈话、演讲等形式,推动收回航权运动发展。具体来说,在中日修约交涉、航政会议、中美与中英修约交涉等事件中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日修约交涉与航业团体的态度
在中日修约交涉中,航权问题成为焦点。而该问题正是航业团体关注的问题,因此他们在这场交涉中态度积极。
从1928年7月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宣布废止中日通商旧约开始,中日围绕旧约是否有效问题发生长时间争持,修约交涉并未进入实际程序。但这并不影响航业团体的积极行动。1929年1月,航业界专家陈天骏拟具收回航权意见书,分呈立法院、行政院,请求在法理上取消外人航行特权。他认为,挽回航权,根本之道在于立法,进行恃外交,补救办理在交通部。陈天骏还致函上海航业公会,希望注意该问题。
因闻悉日本新任公使将来华商订新约,9月7日下午,上海航业公会特开临时全体会员大会进行讨论,力争收回航行权。会议结果,决定分为五步:一,推定代表,谒王正廷,询问政府有关中日商约收回航权内容;二,推定三北公司虞洽卿、招商局洪雁宾、南华公司刘石荪、政记公司王伯芬、宁绍公司胡泳骥、大通公司沈竹贤、航业分会陈伯刚7人组织收回航权委员会,专办此案;三,电请国民党党部、国府暨院部,务达目的;四,必要时派代表晋京请愿;五,以后办法暂缓宣布。9月9日,刘石荪、沈竹贤、陈伯刚三人赴上海外交部办事处面询王正廷,有关中日商约中收回航权一部分内容。王正廷回答了代表们所提问题,称:“外轮行驶我国沿海及内河,系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协定之一,此次改订商约,政府当然贯彻主义,一律收回,鄙人遵守政府既定方针,可以坚决表示,明白答复,请转告航业界勿加忧虑。”航业代表就外间各种传说,及日本新造船之赶造,揣测两国当局似曾有所接触等问题进行询问。王正廷表示,并无任何接洽,并称国民政府办理外交“以国权为前提”,“断不肯自相矛盾,行不符言”。航业代表对于此次会谈“认为满意”。
9月10日,收回航权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推举虞洽卿为主席,因其丁忧,遂举陈伯刚为临时主席。会议决议,电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立法院、行政院、外交部、交通部。11日,上海航业公会发出上述电报,同时致函上海及各地航业团体三十余处,请于中日商约时力争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上海航业公会要求政府与日交涉保持警惕,并称航商愿作政府外交后盾。16日,行政院要求外交、交通两部处置。19日,交通部表示“此后与外国续订商约,自当详细审议,会同外交部据理力争,以保航权而副舆望。”
10月初,日本新任公使佐分利来华,中日修约交涉有了转机。9日,王正廷与佐分利会谈,约定一个月后进行修约谈判。在此前后,社会上传言,日本在改订条约时将取得我国沿海、沿江及内河各线之航运权,而中方以互惠为条件答应日方要求。上海航业界对此很敏感。“沪上各航商得讯,咸认为中国存亡关键,且为断送全国航权于外人,急召集七十五家轮船公司开紧急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代表均认为航权“互惠”对中国有大害。会议决定,“先派代表至交通部长王伯群处质询交部有无主张中日互相开放门户之事,是否将不平等条约中之航运权,主张不收回。如果王伯群无满意答复,即由各公司互派代表到国府请愿,非达到取消此项主张不止。”陈伯刚、洪雁宾等随即拜会交通部长王伯群。王伯群表示:“国府对于不平等条约上所产生之事实,力谋铲除。国府系有主义的政府,对于外交上有一定之政策。即交通部于航权之收回,及于新约上之请外部撤废外轮在内地行驶,乃当然之举。日人所传之言,不可偏信。”并表示政府绝不轻弃航权。各代表表示满意,遂中止请愿活动。
但是,上海航业公会仍担心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接受“互惠”协定。他们从各种渠道获悉日商早就在为“互惠”实施作准备。7月份,交通部曾训令上海航商,调查航行日本内地手续及装货情形。日商以为中国已经允可航权互换,于是着手组织一大轮公司。当时盛传日商拓展中国航路计划分为三步,先从南北洋、长江着手,然后及于内河线扩充,最终完成中国全航路。对此,上海航商“认为生死关头,一再会议,公决挽救之策,面谒王外长吁请于中日商约改订时,必须实行收回航权。”对于航商们的焦虑,王正廷表示理解。19日晚,他抵达上海宴请航业公会各委员,称:“对日订约,航权以不互惠为原则,航界前所表示,出自误会。”虞洽卿致函王正廷,“请照中波商约规定,沿海内河航行,均限本国人民,请察之以明,持之以坚,不达目的不止”。此后,航商代表又多次向政府表达类似态度。如10月25日下午,收回航权委员会成员陈伯刚、洪雁宾、胡泳骐、刘石荪、王伯芬等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收回航权方法,决定致电王正廷,请其据理力争@。
在中国航业界要求政府拒绝航权互惠时,日本航商也在运动,“其当局且协助经营”。日本驻沪领事署海事官员漏岛正明专赴芜、浔、大冶、汉口、长沙等地调查日商在长江航业现状,帮助其发展计划。日本众议员中谷贞赖等十一人组团视察中国政治、经济、交通、航政等事。这些消息引起航商不安。10月15日,上海航业公会在各大报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航权互惠,请求政府力争纠正而挽救,若政府不听,航商将“一律停航歇业”。
宣言引起了各方关注。如日轮公司“亦在积极力争,坚持保守内河航行特惠权利”。10月19日,这些公司领袖在上海宴请佐分利,“请愿力争”,同时推定日商会长米里纹吉作为代表回国,“向外务省继续请愿”。外交部也注意到了宣言的发表。16日,上海交涉员徐叔谟将此电告外交部,王正廷当天电复,要求疏解:“上海航业公会对于本部主张似有误会,航权收回,系改订条约五点之一,始终贯彻,尤于中波条约明显表示,载有沿海及内河航权,均各限于本国人民,本部所指相互平等即在此也,请速声明。”虞洽卿对外交部表态表示赞赏,但指出:“开议以后,难保不多方诱惑,百计要挟。察之倘或不明,持之倘或不坚,仍恐铸成大错。盖对方之环境,及需要与其国势,并其视为已得权利之观念,均非波兰国所可同日而语,对付自较困难。”他希望外交部不要退缩。除外交部外,交通部也颇为关注。该部航政司致函航业公会称:“贵会于收回航权所发的宣言,对于平等互惠之旨,阐发无遗,名言谠论,钦佩良深。”航政司同时就收回航权后的补充运输办法征询航业公会的意见。社会各界也广泛关注。“今自中日修约之声传遍全国后,国人皆以为收回航权,此为惟一之机会。上海航业公会大声疾呼,愿为政府后盾,故收回航权一事,已引起全国人士之注意。”宣言发出后,“各地援应之文电,纷至沓来”。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通电称赞航业公会,表示愿意为其后盾,同时于10月17日致电外交部声援航业公会。外交部不得不再次表态将取消外人在华航权。19日,王正廷在上海发表谈话,称:“收回航权,系改订条约五点之一,对中日新约尤为注意,内河及沿海航行权,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但是,外交部的声明无法消除疑虑,各团体依然致电政府。10月30日,重庆市各民众团体召开收回内河航权运动大会,成立四川省收回内河航权运动大会。11月22日,大会通电国民党党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报馆,对外人侵我航权表示不满。大会发表《四川省收回内河航权运动宣言》,指出收回航权刻不容缓,民众应该觉悟起来,收回航权,反对互惠。11月6日,江苏妇女协会整理委员会致电中央政治会议,要求容纳上海航业公会意见④。10月下旬,中华海员工业联总会对于日方谋求航权阴谋予以揭露,要求政府注意。1930年初,仍有团体发表函电。行政院要求外交部等汇案办理。
对于这些建议或质疑,外交部不得不多次表态,表示将收回航权,保障航务。由于此事未进入实行阶段,政府仍不时收到催促收回航权提案。1930年建设委员会大会上,湖南省建设厅厅长宋鹤庚提议取缔外人内河航权案,得到大会通过。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人杰)呈请行政院核夺,指出:“该当然委员所陈办法一方禁止外人航行,一方奖励国内航业,洵为当今急要之图。”行政院据此转饬交通部会同外交部办理。交通部意见是,收回内河航权一案已由收回航权会议决议,至于奖励本国航业一节,“本部现已拟有航业奖励法及造船奖励法草案,不日呈送立法院审议。”
在各方一再催促下,国民政府着手实施收回航权计划。交通部、外交部均行动起来。“收回航权,与反对中日互惠通航,为上海华航商之最大的愿望,历经发布宣言,及推举代表,向交、外两部,提出要求,外部亦曾表示,决不允外轮取得沿海及内河之航行权,而交通部更派航政司来沪,与上海各华轮磋商收回航权之预备计划,如增添航路,加造船舶,组织新轮公司等等,以备施行撤废外轮之时,可免华轮之缺班断航,妨碍交通,及阻滞商运等情。”
外交部实际上已将收回航权确定为1930年的主要工作之一。该年开始向英美等提起了收回航权问题。而中日航权交涉也在5月6日关税协定签订后进人实际阶段。人们期望关税问题解决后即解决航权问题。5月20日,上海航业公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执行委员会等致电外交部,对于中日关税协定部分条款提出质疑,要求外交部明定交涉方针,宣示收回航权步骤。此电文同时在《申报》、《海事》等报纸杂志上刊登,产生广泛影响。
正在航业公会呼吁当局取消日本在华航权时,日商亦在积极运动,力图在新约中保留航行特权。这引起上海航业公会警觉。12月初,该公会通电要求“务以收回已失航行权为主旨,毅力坚持,誓达目的而后已。”通电得到了舆论支持,如《益世报》发表社论予以积极回应。
对于航业公会的一再呼吁,交通部、外交部先后表态。交通部表示:电陈各节“实与本部之旨相同”,将请外交部“予以注意”。外交部于12月19日发表声明:“现在本部仍本取消外人在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之既定方针,积极进行。”两部的表态暂时安抚了航业团体。随后,中日关税协定签字后,日方一再拖延磋商商约问题,又因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修约交涉中断。
二、航业及航政会议召开与航业团体的建议
九一八事变暂时中断了收回航权交涉,但各界并未放弃努力,采取了经济绝交方式。经济绝交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在华航运势力,舆论欢呼为收回航权的良机。“此次举国抗日,上下一致,其素以为经济侵略大本营之扬子江日轮,首先打倒,在上月十五起,至现在止,停班之轮,已达十二艘,其他未曾停业之日船,亦皆有名无实,往来空驶。今更一步,沿海日轮亦因生意毫无,自十二日起,开始停班。从此江海各线之已失航权,我国正可乘机收回矣。”
但是,经济绝交迫使外轮停航只是暂时的。问题的根本仍是取消外人在华航权。国民政府及航业界等亦仍在为此而努力。如1932年5月间,交通部训令上海航政局,要求为收回航权作准备。交通部、外交部筹划通过修约收回航权。交通部希望先期废止内港行轮章程,同时表示,既然收回航权已经决定,则自营航业亦亟谋发展。外交部答复:“查本部对于收回航权一案,业经定有步骤,准备进行,除于本部最近所订中捷、中波商约内明白规定外人在中国领土内不得享有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权外,拟随时与关系各国分别磋议。”但是,外交部此时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交通部于1934年初举行促进航业讨论会及航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收回航权运动的发展。汉口航政局局长王洗在两年前就建议召开此种会议,交通部采纳其建议,但因一·二八事变而“中辍”。随着形势稳定,交通部于1934年3月20日至24日召开会议。20日上午,全国促进航业讨论会开幕,会议由交通部长朱家骅主持,行政院长汪精卫到会,此外参谋本部代表及交通部次长张道藩、各有关主管长官、各航政局局长、航政办事处主任和有关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正式代表50人,列席代表10余人。代表产生办法是:“(一)航业同业公会之已呈部核准备案者,或已呈准地方政府备案,只因时间关系,呈文尚未到部,但有党政机关证明者,得派代表一人出席。其未呈准备案或未改组之航业公会,而呈通融准予参加者,得派代表一人或二人列席。(二)航业公司其船舶有三千吨以上,或请求参加水陆联运之公司,而其船舶有二千吨以上,并有码头栈房设备者,得派代表一人出席。其船舶不满二千吨,但在一千吨以上,并呈请通融准予参加会议者,得派代表一人或二人列席。其余除参谋本部派有代表外,均有本部及所属各局处代表。”接到交通部的通知后,航业界意识到“此次会议关系航商至为重大,且又值中英、中美通商行船条约续订届满之期,乘此时期,正可实行收回航权,得以解除历年来束缚之痛苦”。因此,他们均十分重视,派出了航业界精英,包括三北公司虞洽卿、政记公司王伯芬、宁绍公司庐于阳、肇兴公司冯又新、华商公司叶传芳、民生公司张树霖、同德公司闵辛吾、大达公司杨管北、大通公司陆稳耕、大通公司周子安、华通公司汪子刚、联安公司陈巳生、中威公司魏文翰、崇明公司陆才甫、达兴公司周平衡、中太公司李志一、合丰公司朱盎声、大振公司冯振铎、恒安公司张国华、上海航业公会主任陈伯刚等。
按照交通部的设想,会议主要讨论航业发展问题。促进航业在当时实际上是收回航权的重要步骤,且航商在会上直接提出了与收回航权有关的议案,因此会议与收回航权关系密切。会议前,上海航商就预备向交通部提出收回航权案。“上海市航业公会认为欲发展我国航业,首宜收回航权,今中英、中美商约,行将期满,正拟续订之际,已由秘书长陈伯刚拟稿,定日内呈请交通部,咨外交部于修订中英、中美商约时,对于我国航权力争收回”。正式会议时,上海航商提出了收回航权议案。招商局总船主沈际云向记者展示了航业促进会议议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回航权案。
会议开幕式上,汪精卫致辞,要求为收回航权认真准备:“内河航权收回,外部进行甚久,而阻碍繁多,一时殊不易谈。内河航权不收回,则海外贸易无由发展,所关于航业者至巨。吾人虽遭遇困难,亦惟有竭力筹思,先期预备,或能得到机会,否则纵有机会,亦难期达到目的。”虞洽卿在演说中亦表示:“至于收回航权,不能不讲,盖非通商口岸,实可实行,此事说起来,类似高调,然对外不能不唱。”
当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航政司长高廷梓主持,讨论开辟远洋航线案及航业统制案。从20日下午开始至21日下午,共举行三次大会,讨论提案90件,其中收回航权案六件。此次会议各案均经详细讨论,“拟具办法,由本部主持,分别采择施行”。这些议案在后来有些予以实现。如议定上海国营民营各轮公司实现航业合作。“其主张在保障航线,调剂供求,永泯争端,而根本则在团集实力,达到收回航权之目的。”在交通部指导下,成立航业合作委员会,设于上海广东路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内,参加公司五十余家。
23日、24日,交通部又举行航政讨论会,由主管长官、各航政局长及航政办事处主任、特聘专家数人一起讨论航政问题。会议三次,讨论包括改革航政机关组织、载重线法案等在内的提案40件。
上述会议并非专门针对收回航权问题,但与此关系密切,尤其是促进航业讨论会直接讨论了收回航权提案。会后,交通部根据决议致函外交部,希望采纳。显然,航业及航政会议的召开,得到了航业团体的积极响应。它们在会上提出了诸多相关建议,对政府收回航权、发展民族航业决策起了积极作用。
三、中英、中美修约交涉与航业团体的努力
在交通部及航业界的一再呼吁下,外交部亦在寻找机会进行收回航权交涉,此次交涉机会就是中英、中美商约到期。
早在1933年10月,顾维钧就提议与英美进行修约,因1902年中英通商续约及1903年中美通商续约均已到期。该两约是英美在华条约权利的总汇,亦与航权关系甚大。“查英美两国在华之各种条约权利,大致曾经一九〇二年以前所订各条约分别规定,此次限期届满之两约,可称为前此各约之续编,将各片面条款总括而汇合之,未臻妥善者修改之,未经包括者增补之而已。”经过讨论,外交部决定向英、美提出修约交涉。12月23日,分别照会英、美驻华使馆,“正式提出修约之议”。美使詹森于1934年1月13日回复,美国愿意在可能范围内磋商修约,并要求中国将修约的具体时间、地点、形式及中国的意旨、提议等预先通知美方。18日,中方告知美使,中国希望全面修改,尤其提到领事裁判权、航权“于中国主权损失极大,应予撤废”。从照会内容看,收回航权是此次修约的重点内容之一。但是,美方不愿意全面修约。4月10日,美使答复已向本国政府请训,此后就一再拖延。英国更不愿意全面修约,直至5月19日才表示愿意“在可行的和适当的范围实施条约修改”。
当然,英美并没有拒绝修约。因此,外交部就如何修约进行了准备。外交部秘书谭绍华于1934年5月15日专门提出了修约方案,包括五项内容:一是撤销领事裁判权,二是收回航权问题,三是最惠国待遇、第三国待遇、互惠待遇等问题,四是准许外人在内地居留问题,五是外人设厂办理工商制造各业问题。关于航权问题,谭绍华专门提出《收回沿海贸易(航行)与内河航行权办法初步报告书》。他主张应将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一并收回,但他又信心不足,“收回航权虽系我国重要外交政策,然事实上恐未易实现。”一是各国在华享有航权由来已久,“恐不肯立即放弃”。“即使于原则上认可放弃,亦必提出各项附带条件,将现有在华各国之船舶及公司财产妥为处置”。二是中国“万难一时自备船只,扩充航业”,且不能将现有外轮公司船舶与产业评估收买。第一项困难应从外交人手,草拟适当条文,且能被外人所接受,为此需要“筹划一种过渡办法”。所谓过渡办法,就是设置过渡时期,根据收回航权原则,对外轮实施适当管辖,一俟时机成熟再完全收回。谭绍华在报告中提到,此次修约有几个困难:一是形势不利,中国国际地位“远不如东北事变之前”,此时急需英美等国声援,不可能迫其修约。二是根据条约约文,“英美对我方之要求未克表示同意,则不患无词以对也”。三是日本可能离间阻挠。因此,修约并无把握。
果如其所料,此次修约无疾而终。不过,它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就收回航权而言,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讨论的小高潮。2月13日,虞洽卿代表上海航业公会致电外交部、交通部,“请力争收回我国航权,乘英美日商约续订机会,跻国家主权于完整之列”。其电文力证收回航权的重要,称为修约的焦点。电文历述该会以前收回航权的努力,希望政府抓住修约机会,收回航权,“现悉中英、中美续订通商行船条约,又届修改之期,而中日新约则迄未续订,乘续订修约之机会,复我国已失之航权,钧部自能遵总理之遗训,解民众之痛苦也。”航业公会提醒当局不能允许航权互惠,指出,“改订互惠条约,于我国主权仍未完全,于我国航业更绝对有害无利,设或不察,则又铸成大错,历劫不复矣。”为打消当局顾虑,航业公会针对立时收回航权将造成困难的说法予以批驳,指出:“航权果能收回,沿海及内港各航线,只许我国商轮行驶,则营业发达,左券可操,全国商人,以有利可图,其投资以营航业也,自必接踵而起,则已有之公司,既易扩充,未来之商航,亦自日多,必能应国内运输之需要。即就目前而论,国人轮船,亦已可支配补充,勉敷供求,此无庸鳃鳃过虑者也。”收到电报后,交通部长朱家骅当即转请外交部办理。
此外,中华海员工会、上海市内河轮船业同业公会等亦纷纷致电政府,请求乘修约之机收回航权。3月6日,中华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致电各省市党部、各级政府、各法团、各报馆,呼吁一致主张收回内河航权:“兹值中英中美通商行船条约,已告届满,亟应乘时将内河航权收回,取消以前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敝会除已呈请交通部准派代表参加航业会议,以便贡献意见外,尚盼国人戮力同心,一致主张,督促政府,严厉交涉,务达收回目的,以挽回我国航业厄运,国家前途,实利赖之。”上海市内河轮船业同业公会根据五年来创办内河航业的经验,指出,“深知欲挽救我国内河航业之衰颓,而达到国人自办之目的,自非取消国际间不平等条约,收回我国内河航权不可”。该公会致函上海市商会,要求将意见转呈交通、外交两部。航业团体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收回航权的进行。
四、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的兴起、发展与航业团体有密切关系。显然,航业团体推动了政府收回航权运动的进行。南京国民政府在统治前期积极制定了收回航权的政策和应对方针,并在一定程度将其付诸实施。交通部从国内行政人手,通过统一航政,筹办国营航运,促进民营航运发展,实施航业统制,奖励造船业,开办商船学校,明令公物由国轮装载,号召国人乘坐国轮等措施,增强了航运势力,为收回航权奠定了一定基础。交通部不仅积极发展本国航业,亦着力推动外交部进行修约交涉。除多次函商外交部,制定收回航权节略,讨论收回航权办法等外,交通部还不时向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力争航权。外交部亦积极开展了修约交涉,试图与列强进行谈判而收回航权。外交部为废除条约特权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步骤,收回航权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其中。为此,外交部在交通部等推动和协助下,还专门制定了收回航权方略。外交部向日、美、英等正式提出新订商约的要求,其中明确提到取消外人在华航权问题。
政府的上述态度和努力,与航业团体的呼吁、督促有直接关系。由于航业团体与航权存在切身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一直在呼吁收回航权,这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没有航业团体的呼吁,南京国民政府收回航权态度不会那么积极。在收回航权的过程中,航业团体也一直呼吁和提出建议,在中日修约、航政会议、中美中英修约交涉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积极身影。这既为政府收回航权提供了有利后盾,支持了政府的外交活动,当然也对政府决策形成了压力,使之在收回航权问题上不敢过多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虽未能实现目标,但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不啻为一场航权教育运动。而这场运动发起者正是上海航业公会,并得到了各地航业团体的响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声援。通过集会、请愿、函电等形式,航业团体唤醒了民众对航权的重视。“中国收回沿海及内河航权的运动是最近一件重要事情。”“此种运动已引起大多数国人的注意”。此外,这次收回航权运动还在实际上产生了效果。此次运动不仅仅呼吁全国同胞注意航权,有的地方如四川还呼吁民众“以经济绝交不与合作,以为消极的抵制,而制其死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轮营业。更重要的是,此次呼吁亦对国民政府形成了较大压力。如四川收回内河航权运动大会就提出要“催促政府,为强有力外交,不妥协,不让步,务取消净尽此不平等条约而后已”。上海航业界更多次向政府施压。在这些团体的压力下,外交部不得不多次表态收回航权。可以说,这场运动推动了政府收回航权的进程。显然,航业团体等民众力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调收回航权的有利支撑。
当然亦应指出,在航业团体等推动下,政府对收回航权积极表态,反过来亦对民众起了鼓舞作用,民众因此纷纷觉悟起来,为积极收回航权而努力。如《益世报》发表社论指出:“自政府宣告收回航权,为时未久,而上海商业团体,遂有委员会之组织,一方表示国民之同心协力以为政府后援,一方亦实欲研究收回之手续,与将来振兴航业之方法,不可谓非吾人之大觉悟……”民众与政府在此问题上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一定分歧。在必须收回航权这一点上,民众与政府存在共识,至于如何收回航权则存在一定分歧。但不管怎样,民众与政府的共鸣使收回航权运动走向了高潮。民众推动了政府收回航权活动的进行,而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又时刻引起民众的关注,收回航权运动持续不断与此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亦是中国社会收回航权运动的高潮时期。报刊、著作、电报、宣言、各种会议等密集关注航权问题,这与国民政府积极从事收回航权活动有关。这种从政府到民间持续不断的活动加深了民众对航权、领水主权的理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积极充当政府收回航权活动的后盾,政府亦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吸收民众意见,寻求民众支持,如交通部主动征求航业界的意见。至于民众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亦能得到反馈,尤其是上海航业界的意见常直达国民党中央及政府有关部门,甚至有时直达党政要人。上海航业界对于收回航权非常注意,“迭将此情沥陈当局,希将此项要案,迅速解决”。通过这些机关或要人的转达,对外交部形成了一定压力。对政府外交而言,民众的力量既是后盾,又是压力。外交部在对外展开收回航权交涉时,不得不考虑这种因素。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收回航权问题上,比其前辈更积极,产生的影响亦更大。而这部分得益于以航业团体为代表的民众势力的贡献。当然,亦应注意的是,航业团体在收回航权问题上的态度与政府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两者在收回航权的具体主张和步骤方面有一定差距。
(责任编校: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