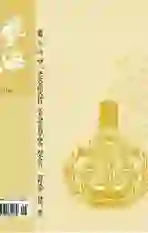一出戏,两种江湖
2016-05-14汤晨光
汤晨光
〔摘要〕新编巴陵戏《远在江湖》的剧作评论。
〔关键词〕巴陵戏编剧剧作
《远在江湖》,剧名化自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剧情大抵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演绎,搬演的就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故事。“谪”“守”为两个关键词,其中,“守”字铺展成戏剧情节,即滕子京治理巴陵郡的过程和业绩;“谪”字则是全部情节发生的背景和条件,滕子京是以贬官的身份领导巴陵郡并取得不俗业绩的。也就是说,“守”为剧之表,“谪”为剧之里,两者互为依托映照,而尤以“谪”字为全剧的焦点。
和庙堂相对的“江湖”是民间,是偏远之地,滕子京的“远在江湖”就是遭贬谪的境遇。被贬谪到偏远的洞庭湖畔,按情理,当事人该是灰头土脸抑郁自卑的,巴陵郡的下层官员就在等待这样一个贬官的到来。然而,从高处摔跌到他们面前的的滕子京却是神采焕发,没有一丝落魄的愁容,这出戏的戏剧性和主题正是从此处生发出来。滕子京就是这样出人意料,他不“忧谗畏讥”,也“不以己悲”,完全不气馁于逆境,不就缚于世俗逻辑。他是自信自尊地走马上任的。到任后则是毫不畏葸,雷厉风行,一年过去,凋敝颓败的巴陵郡就面目一新,破败的名胜岳阳楼也扩建重修了。
《岳阳楼记》所写滕子京的政绩,资料想必是其本人提供的。嘱朋友为他重修的岳阳楼作记,也难免意在借其生花妙笔宣传自己。范仲淹没有辜负朋友的嘱托,开篇就亮出其“百废具兴”的功绩,但这显然不是全文的重点,范仲淹更感兴趣的是支撑滕子京取得如此成绩的精神状态,且进一步借岳阳楼的视野想像整个文人处境和心态,并将滕子京标举为文人的精神典范。那就是,即使遭受贬谪,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不为所困,照旧甚至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不是心灰意冷,自惭形秽,缩手缩脚。这一思想的提炼虽是范仲淹对朋友嘱托的超越,但仍局限在政治视野中的文人群体。陈亚先的《远在江湖》则对此作出了又一步的升华,将它推向更普遍的人生层面,剧本的“题记”所引《黄果树大瀑布》的歌词点明了这一点:“人从高处跌下,往往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下,偏偏神采飞扬!……原来水可以成为人的榜样!”这就使该剧不仅给沉浮中的官僚文人,而且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思想的启迪。多数观众并不是官,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像成“迁客骚人”并不容易,“进亦忧,退亦忧”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缥缈的豪言壮语。但若将该剧作为“逆境对策”的人生故事来看,人们都容易贴近主人公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了,因为是人都会跌落,都有陷入灰暗的时刻,在此人生江湖上,滕子京的策略是最可取的。所以,《远在江湖》是滕子京外传,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励志故事。
从《远在江湖》全剧看,对滕子京“不以己悲”的积极处世态度的赞赏仍是较为浅在的,其更为深潜的题旨是,在固有的权力阶梯上,权力等级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权力专横地分配着人的尊严和意志,决定着两者的份额,横扫一切其他关系及其价值。这一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心和权力的本质。与此相关的情节构成该剧的骨架,贯穿其始终,成为其思想最硬的部分,而此处的“江湖”就成了以官场为主的整个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员自然都镶嵌在权力结构的相应位置上,平民大众更逃不脱权力的威压。这一主题就表现在滕子京和王钧第的关系中,尽管滕子京的性格和上述“江湖处世主题”也在其中得以表现。
为表现这一权力主题,剧本特别设计了滕子京和王钧第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原有师生之谊,年轻却为滕子京上级的湖广镇抚使王钧第是他当年的学生,前者是后者的恩师。在科举时代,恩师等于举子的赏识者和擢拔者,可以说他的官位就是恩师给的,对举人具有极大的恩情,对恩师应该敬重是不言而喻的。而恩师对于即使是处于上位的学生也是不需要特别恭敬的。这正是一般的情理和推论,滕子京也持此观念。但这种观念和权力的本性并不吻合,两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远在江湖》更激烈的戏剧性和更深刻的主题就表现在这一冲突中。
虽然滕子京是王钧第的恩师,后者是他的“贤契”,但这贤契却比恩师的官位高,是恩师的上司,而恩师不仅处于权力的下级,且是遭到贬谪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权力欲望说了算还是师恩说了算?权力意志处于人的本能的顶端,拥有权力的人不会放弃享受权力,也不会容易这种享受被打折扣,它刚性地要求与之匹配的尊重和仰视,要求下级表现出应有的惶惧和卑抑,不管这下级是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人伦位置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没有附加条件的,王钧第不会因为滕子京是他的恩师就不想要他的崇敬了。下级对上级如果没有相应的臣服的表现,本身就构成一种挑战,上级是不会不在意的。权力的本性如此,偏偏遇上滕子京的自尊自傲,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滕子京到巴陵郡上任,内心其实是害怕僚属的冷眼和慢待的,至少他会预感到这种可能性。他到达时诸下属正准备去给湖广镇抚史王钧第拜寿,确实把他的到来不当回事,不仅因为他是贬官,还因为和王钧第相比他是小官。他因此才强硬地予以阻止,其实是要求下属对他的尊重。这也是出于心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本人就更是不去巴结“贤契”了。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的恩师身份看得很重,不但不去拜寿,反倒在王钧第已经很不高兴的情况下不知趣地去告贷。他没意识到或故意不在乎他所怠慢和与之较劲的已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上司,一个比他权高位重的人。后来王钧第到岳阳检查工作,滕子京竟又把这上司放在客舍里晾了三天而不闻不问。受到如此轻慢和冒犯的王钧第怎么能心平气和!王钧第的要求不过是和人性共谋的权位的要求,就是要求权力下级的服从和尊重,巴结和仰视。而滕子京表现出的却是冷淡和对抗,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权力本性的挑战,他挑战了权力江湖上的规矩。这又和他的不以现实处境为意、无视各种潜规则、未被现实驯化的性情相联系。
《远在江湖》的“权力主题”可能不是作家有意识要优先表达的,而只是附带地藏身在“江湖处世”这一主题下面的,但却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这一主题中的滕子京也可能是更受观众欢迎,更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因为,生活中的每个人,即使是官位很高的人,也必然受到上位权力的压抑和侵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委屈,都有对上位权力扬眉吐气的需求,都有反抗的冲动,而付诸实施的毕竟少之又少,当看到滕子京那样任性勇敢地开罪上级,观众会感到是压在自己心头的一块石头被掀掉,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在幻想中获得解放和翻身的快意。因此,权力主题角度上的《远在江湖》也会很有观众缘的。
滕子京解决巴陵郡各项积弊时采用的是“雷霆手段”,其含义是打破常规,敢作敢为,其中关键的一招是帮助商人逼还被长期拖欠的债款。滕子京通过这一措施和众债主达成协议,催还的款项一半归公,填充空虚的府库,而还不上欠账的人则被官府拘押。这几乎成了他突围财政困境的绝招。但是,剧本在对相关细节的描写上出现浮泛不明确之处:一,滕子京对王钧第对他滥用刑罚的指控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辩护,没有论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差不多等于他无言以对甚至认罪了,而这是要接受处分的,但滕子京却用赢得圣旨御批成功脱逃,无法被继续追究。这样的情节是足以损害正面主人公形象的,又很像是作者曲意回护滕子京。二,与此相关,第五第六场在时间上已是一年以后,巴陵已经“百废具兴”,而且要修岳阳楼了,怎么还有大量的欠账人被关押?这局面不仅不能算“政通人和”,而且,既然是仍被关押,那就是还没有还账,官府还没有拿到那一半的债款,兴办各项公共事业的资金也就还没有筹足,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无法做到“百废具兴”,怎么还要来重修耗资巨大而并不急需的岳阳楼来了?还有,既然被关一年都没有交出欠款,那就说明欠债人真的没钱,那么,这些人将被关押到何时,关押他们还有什么意义?这其中的用意和道理都是费解的,让人困惑的。(责任编辑:蒋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