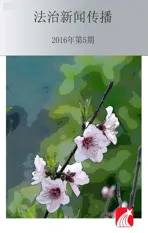新闻是硬的,文学是软的
2016-04-16孟红梅
■孟红梅
新闻是硬的,文学是软的
■孟红梅
“姓名?”
“苗苗。”
“报大名!”
“苗苗!”
“你姓啥?”
“苗。”
“你叫啥?”
“苗苗。”
“那你应该叫苗苗苗!”
当苗苗讲起这段关于自己名字的趣事时,大伙儿都笑了,苗苗也跟着笑。两只明亮的大眼睛微弯,呈半月状,可爱又妩媚。我忍不住问苗苗的年龄。她调皮地让我猜。我说20。因为毕竟参加工作了,不可能再小。再小就是中学生了。
“太夸张了。”大伙再次大笑起来。看来我是猜错了,且错得不轻。不由流露出茫然的表情。苗苗不忍我为难,便自报 “家门”:35岁,孩子10岁,上小学四年级。
这是今年6月1日到洛阳市检察院采访该院公诉处干警苗苗的一个 “微场景”。
2015年10月,苗苗受洛阳市院党组委派,来到了洛阳市检察院对口扶贫帮扶单位栾川县合峪镇马丢村担任 “第一书记”。短短8个月,她不仅为村里修了路,引进了黑猪养殖、种植日本甜柿子等脱贫致富项目,还一个人帮扶了8户贫困户,将 “第一书记”当得有声有色,受到村民们的交口称赞。
那天的 “访谈”很顺利,接下来就该到苗苗任职的马丢村进行 “田野调查”了。这是采访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整个采访计划中的关键一步。在我近十年的工作中,每次采访,我都喜欢列出个计划。到哪里采访?采访谁?分几个环节完成?每个环节采访什么?尽可能详细地了然于心,并坚决执行。我十分赞同著名新闻人、作家梁衡所说,采访如同采药。一个经验丰富的采药人从不盲目上山,他会根据自己所需,结合以往采药经历,选择地点,明确目标。通盘考虑,目光放远。既可收到预期效果,又省时节力,事半功倍。而那些没有计划,背上药篓就上山,忽而山巅,忽而沟底,漫无目的到处跑,撞到什么采什么的采药人,往往难以如愿。也许凭运气会采到一些珍贵药材,但运气毕竟是靠不住的。
夜里,下起了大雨。早晨7点多钟,天色依然晦暗不明。驱车走在通往栾川县城的高速公路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不是数人同车,说不定真要 “独怆然而泪下”了。路面积水渐深,车轮碾压,发出刺耳的 “嘶啦”声。隔着车窗望去,山峦如涛,云遮雾罩,穿山越岭蜿蜒盘旋的山间公路上,只有我们的车在雨中奔驰。难道这就是像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
连接马丢村与山外世界的是一条沙石土路。连续多日下雨,路边的山崖被雨水浸泡,不时有土石滑落,挤占了本就狭窄的路面。我们小心翼翼地开着车,缓慢通过。
“以前这条路比现在还窄,遇到顶头车,错都错不开,两车顶到那儿,上不来,下不去,弄不好就翻到沟里去了。”马丢村村委会支部委员任海药说,“不过,现在这个路宽多了,错个车啥的,一点儿不作难。”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别说在这条路上错车了,就是开个车也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如果再来个急转弯,那可真得崩溃。正担心着,一个又急又陡的弯道赫然惊现。还是个大 “S”弯!无奈,我们只得下车,以减轻车辆的负载量。尽管没有一个胖子,可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司机外,所有人都被赶下了车。
那一刻,不由得有些气馁,开始怀疑此行的必要性。因为通过昨天一天的采访,完成一篇新闻报道已没问题。到马丢村进行 “田野调查”,无非是增加一些感性认识,观察一些细节,在写新闻稿子中,多少用点细节描写等文学表现手法,增强新闻形象性,从而使稿件具有一定的文学气息。
这是我多年形成的一个习惯。近十年的写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新闻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是通过叙述达到目的。梁衡认为关于新闻写作是以叙述为主的文体。叙述是新闻的基本功;有果的叙述更可信;带情的叙述才动人;含理的叙述更深刻。而这四个方面,在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是文学的基本要求,新闻写作中也不可忽视,这样可以让新闻更具吸引力。先后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霍默·比加特在描写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时,就是通过文学手法,对现场细节进行精心描绘,真实再现历史场景,使重光葵无奈、恐慌、无助的复杂心理跃然纸上,才给读者带来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我们终于顺利到达马丢村。
马丢村位于栾川县城东南方向的深山区,距洛阳市区178公里。全村860多口人,220多户,分布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战乱年代,这里无疑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饥荒之年,山果野菜则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保障。改革开放之初,丰富的林业资源,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了温饱生活。“八十年代,光俺村就有六十多个万元户。”马丢村村委会主任郝科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马丢村靠山吃山,砍树致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人们重新回到那几块儿靠天收的土地上。当山外的人脱贫致富,奔走在小康路上时,他们仍然处在贫困线上。“马丢村,马丢村,马都能弄丢,还指望啥过上好光景?”贫困的人们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村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栾川被划为国家级贫困县,马丢村由此搭上国家扶贫的快速列车。
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山里气温本就比山下低,一遇连阴雨,气温就更低了。虽已初夏,西沟李大娘还穿着小棉袄。李大娘年近九十,与丈夫住在三间老土屋里。土屋阴暗潮湿,坐不住人。为了省钱,老两口连灯泡都舍不得用,实在不行了,就生一个火盆,既能取暖,又可照明。
见有人来,老夫妻扶着门框,站在门口迎接。当接过大伙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必需品时,老人混浊的眼里泛起了泪光,一遍遍地说着:“感谢党!感谢政府!”
相对于李大娘老两口,魏海夫妇要年轻得多,六十来岁。但他们的家庭状况却好不到哪里去。魏海长年患病,每年为治病都要花去两三万元。而这些钱全部借的是外债。尽管通过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但剩下的医药费对魏海夫妇来说,仍然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还债,魏海的妻子到矿山找活干,和男矿工干同样的活。但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问题。了解到这种情况,苗苗多次到魏海家看望他们夫妻俩,尽己所能地帮他们。
“你看俺扎的鞋垫咋样?”魏海妻子拿出一双自己做的鞋垫往苗苗手里塞,“俺也没啥回报,这是俺给你纳的鞋垫,你要是不嫌弃,就收下吧。”
苗苗以鞋垫不合自己的脚为由,婉转地拒绝了魏海妻子的好意。
离开时,魏海妻子送我们出门。她家的花狗也欢天喜地跟着,帮主人送客。过了门前的独木桥,穿过一片土豆田,魏海妻子仍没有回去的意思。我就回头劝她留步。她却突然拉住我的手,神秘地说:“村里人都说你待俺好,可眼气了。”
“咱俩可是头回见面啊!”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苗书记,你忘性咋恁大嘞?你对俺的好,俺一辈子都忘不了。”魏海妻子盯着我,动情地说。苗苗站在她身后,只是抿嘴笑。大伙儿对魏海妻子的 “健忘”也习以为常,谁也不去说破。
夜宿栾川,灯下整理采访记录。翻看着一张张生动鲜活的图片,回忆着一张张或喜或忧的面孔,体味着一句句朴实厚道的 “土言土语”,对这篇人物通讯充满了期待和信心。无需 “别出心裁”,无需 “匠心独运”,只需用点文学表现手法,如实道来就可。但这绝不是华丽词藻的渲染,更不是文过饰非的煽情。而是在深入采访过程中,通过细心观察、认真总结、全情投入,在抓住事物本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适当“软化”而已。相对而言,新闻是“硬”的,文学是“软”的。但不管“软”“硬”,都要讲究一个度。尤其在检察新闻报道过程中,“软”要建立在 “硬”之上,要为“硬”服务。新闻报道的落脚点是新闻,而不是文学。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运用文学化语言,才会产生真正好的新闻作品。
第二天,雨住天晴,空气清新得透明,漫山遍野青翠欲滴。村民魏老三一大早去割猪草,我们在村委会门口遇见了他。当时他正背着一大捆野水芹往家走。我迎了上去,讨来一根品尝,汁甜味浓,爽脆可口。这个滋味,就如同这次采访,都是令我难忘。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驻河南记者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