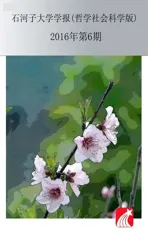西部农民生存写照和乡土文化的坚守
——刘亮程散文中的狗意象解读
2016-04-04卢军
卢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西部农民生存写照和乡土文化的坚守
——刘亮程散文中的狗意象解读
卢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有众多意蕴丰富的动物意象。其中狗意象的建构是基于作者生存体验和哲理思索之上的。他将狗与人的生存境遇、生存哲学两相观照,揭示了西部农民安命隐忍的人生态度,隐含着他对生命的苦难、孤独和脆弱的深刻体悟;对个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究;也寄寓着他对文化乡土的守护和皈依灵魂家园的渴盼,富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哲理意义。
刘亮程;狗意象;生存哲学;乡土文化
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构建了众多独具特色的乡村动物意象。在人畜共居的乡村世界里,刘亮程将狗、马、驴、牛等置于与人平等的位置,视其为人们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彼此生活的旁观者、介入者”。通过动物意象的构建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堪称一部“生存哲学”文本。已有数篇论文阐述其散文中的驴意象,而内涵丰富的狗意象却鲜有论及。狗意象隐含着刘亮程对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的关注和反思,包含了他对苦难、孤独、死亡、精神皈依等命题的独特感悟。因此,把握刘亮程散文中的狗意象,对理解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安命的生存哲学
安命是刘亮程笔下的狗意象最显著的特征。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第一篇就是《狗这一辈子》,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狗多舛命运、生存艰难的无奈与叹息:“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厉害不行,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善解人意了均不行。总之,稍一马虎便会被人剥了皮炖了肉。狗本是看家守院的,更多时候却连自己都看守不住”。在刘亮程的眼里,狗唯有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顺天安命、随遇而安,才能换取可怜的生存权。
狗被要求牺牲自己的个性,无条件地服从主人,“一条称职的好狗,不得与其他任何一个外人混熟。在它的狗眼里,除主人之外的任何面孔都必须是陌生的、危险的”。狗连谈情说爱的权利也被主人无情地剥夺,“人养了狗,狗就必须把所有的爱和忠诚奉献给人,而不应该给另一条狗。狗这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没人知道狗是带着什么使命来到人世”,一种生命的虚无感充斥笔端。总之,一条狗每天的生活就是小心翼翼地履行职责。它们必须屈服于命运的安排,随时准备承受一切,而无力改变什么。
只有到活到一把年纪,狗命才相对安全了,因为此时它的皮毛和肉体在人眼中已毫无价值。文中用一个“熬”字浓缩了狗一生的艰辛,辛苦一辈子,年老体衰了才少了些被肉身皮毛的危险,但已来日无多,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等到无人再需要它看家护院时,“在这众狗的夜晚,肯定有一条老狗,默不作声。它是黑夜的一部分。它在一个村庄转悠到老,是村庄的一部分。它再无人可咬,因而也是人的一部分。这是条终于可以冥然入睡的狗,在人们久不再去的僻远路途、废弃多年的荒宅旧院,这条狗来回地走动,眼中满是人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狗这一辈子》)。垂垂老矣的狗唯有与孤独寂寥为伴,靠回忆尘封的往事度日,令人感慨良多。
然而狗的命运何尝不是人的命运的写照?不正是刘亮程对西部乡村农民命运的感叹吗?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以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一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的人事变迁为背景。地理环境造成的荒凉和封闭是黄沙梁最显著的特征。刘亮程笔下的乡村是模糊了具体时间概念的乡村,他有意淡化时代背景,外界风云变幻对黄沙梁村的人们的生活几无影响,黄沙梁人的生存方式是封闭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如同宿命一般轮回。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态度是无可奈何和安命顺命。
刘亮程在青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繁重单调的田间劳作对人的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折磨,“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在一村庄人的一生里,劳动是件荒凉的事情”(《黄沙梁》)。单调乏味、周而复始的劳动,让身在其中的人无可奈何。农民们在对饥荒的恐惧、对来年年景收成的不可知的担忧中痛苦地煎熬,“一年一年的种地生涯对他来说,就像一幕一幕的相同梦景。你眼巴巴地看着庄稼青了黄,黄了青,你的心境随着季节转了一圈原回到那种老叹息、老欣喜、老失望之中。你跳不出这个圈子。尽管每个春天你都那样满怀憧憬,耕耘播种。每个夏天你都那样鼓足干劲,信心十足。每个秋天你都那样充满丰收的喜庆。但这一切只是一场徒劳。到了第二年春天,你的全部收获又原原本本投入到土地中,你又变成了穷光蛋,两手空空,拥有的只是那一年比一年遥远的憧憬,一年不如一年的信心和干劲,一年淡似一年的丰收喜庆”(《家园荒芜》)。田耕生活给农民带来的不是劳动的满足和喜悦,而是对生命的销蚀。同样是描写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柳青小说《土地的儿子》中有了自己土地的老汉李老三觉得“而今在天堂上过日子”,那种洋溢着幸福感的劳动和对土地的痴迷在刘亮程笔下的农民身上已荡然无存。
除了劳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如《永远一样的黄昏》描写了一家人吃晚饭的场景:“全是一样的黄昏。一样简单的晚饭使劳累一天的家人聚在一起——面条、馍馍、白菜,父亲靠着椅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土块和木头上,吃空的碗放在地上,没有收拾。一家人静静呆着,天渐渐黑了,谁也看不见谁了,还静静呆着。油灯在屋子里,没人去点着,也没人说一句话”。《树会记住许多事》写了在早春青黄不接的时节,家里的白面早就吃完了,苞谷面也所余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还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家人间没有交流、没有嬉闹,沉静得让人心悸,与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瑞典画家兼作家卡尔·拉松笔下安适温馨、其乐融融的乡村家庭生活场面大相径庭。在黄沙梁,生存的艰辛早已把人们对生活情趣、亲情表达的热情都消磨殆尽。《寒风吹彻》中的“寒风”已不仅仅是寒冷季节的体现,更多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和心境的象征,象征着生命的无尽的荒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字里行间渗透着难以言尽的悲凉。
相比对黄沙梁生活环境的恶劣的描写,作者更着力表现的是西部农民对艰辛生活的顺从和适应。面对人生的苦难,黄沙梁农民们并未怨天尤人,他们用平淡得近于木然的生活态度默默地承受苦难,“我投生到僻远荒凉的黄沙梁,就是为了从头到尾看完一村人漫长一生的寂寞演出”(《冯四》)。家徒四壁的光棍冯四赤手空拳对付了一生,他只有一间借以栖身的光线黑暗的矮土屋,在那里孤独地打发走每一天。一些村民的土房子破旧不堪,“那些人家的生活,简直过不下去的生活,也都一天天的过下去了。房子依旧破烂地撑着。人依旧贫困地活着。房子、人、草木和牲畜,都在无望中苦挨苦等”(《有人死了》)。在作者看似冷静的描述中隐藏着刘亮程对黄沙梁人悲凉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包含对西部农民坚强隐忍性格的肯定。
有论者认为刘亮程的散文过于美化乡村,忽视了农村生活的的艰难和闭塞落后,“他逃离了生活现场的残酷,在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只是一味进行想象性的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反思”[1]140。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刘亮程描述的乡村生活绝非“京派”作家笔下平和冲淡、富足安逸的文人理想化的“乡村中国”图景,翻阅《一个人的村庄》,文中随处可见生命的苦痛、焦虑、荒凉、孤寂、死亡。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刘亮程从未刻意回避农村生活的苦难,他说:“农村的苦和难是我们国家的最大问题,谁能够回避?但生活在苦难中的农民,千百年来却以自己独具的方式消解着苦难。那种恬淡、不争、无求,正是消解苦难的方式之一。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我的文字关注的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心境。……我们的农民早已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到我们不知道的自在和快乐”①参见何桂贤:乡村的欢乐与哀愁:刘亮程及其《一个人的村庄》[EB/OL].http://www.china-review.com/caf.asp?id=15167.。他欣赏的是西部农民面对苦难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借助于狗意象,刘亮程对生活在黄沙梁的西部农民的生存哲学进行了反思。他以深深的悲悯情怀,几近原生态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农民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贫瘠挤压下的挣扎、无奈与安命,并表达了对这种生存方式的理解和同情。
二、卑微个体底层境遇的写照
在刘亮程笔下,狗是卑微无助的弱势群体的象征,“狗”意象隐喻着受压迫的弱小生命个体。《两条狗》中的黑狗因胆小、不够凶猛、院子里来了生人也不敢扑过去咬,被“我”的父亲所厌弃。父亲乘着去外地卖皮子时把黑狗装进麻袋,连同三十七张皮子一起卖给皮货店,毫无丝毫怜悯之意。回来后父亲又带回一条机灵的小黄狗,家人很快就把黑狗忘掉,仿佛它从来不曾在这个家里存在过。一个多月后的某天傍晚,当全家人在院子里吃晚饭时,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黑狗突然出现在院门口,可怜地哭叫着却不敢进门。唤它进来后,它“一头钻进父亲的腿中间,两只前爪抱住父亲的脚,汪汪地叫个不停,叫得人难受”。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从皮货店死里逃生,又怎么从五十公里之外的柳湖地找回来。然而被卖掉的黑狗历尽艰辛返回家里的举动并没有改变家人对它的冷漠态度,虽然留下了它,但对它明显缺乏应有的怜悯和关爱。几年后,黑狗死在了窝里,“我想它是饿死的,或者寂寞死的。它常不出来,我们一忙起来有时也忘了给它喂食。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完全体味那条黑狗的晚年心境。我对它的死,尤其是临死前那两年的生活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两条狗》)。临死前的一个黄昏,黑狗曾与主人同在一个墙根晒太阳,背靠着墙享受着同一缕阳光的场景恐怕是黑狗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了吧。可见,人和狗的情感付出很多时候是不对等的,虽然狗对主人的态度始终都是温顺驯服的,但人类给予它的却更多的是欺压和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融洽而是对立紧张的。
在黄沙梁,尽管众多牲畜共同生活在同一农家大院里,待遇却差别甚大。家里刚买回的黄牛任性耍脾气,又踢又叫,但父亲并没鞭打它,因为爱惜它那身光亮的皮毛;家里的黑猫懒得捉老鼠,任凭老鼠在眼皮底下走过也不搭理,还偷吃饭菜,但家人却没有惩罚既懒又馋的猫,原因很简单,“猫打急了会跑掉,三五天不回家,还得人去找。有时在别人家屋里找见,已经不认你了。不像狗,对它再不好也不会跑到别人家去”(《共同的家》)。狗是满院的牲畜里最忠于职守的,每到秋天丰收的季节,院子里堆满了苞谷、黄豆、甜菜,如有胆大的羊或猪趁人不注意叼一个苞谷棒子什么的,“狗马上追咬过去,夺回来原放在粮堆”。而人们对温顺忠诚的狗却缺乏应有的怜爱和耐心。狗是人们宣泄情绪的对象,狗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被主人错怪或当替罪羊也是家常便饭,人们对狗的关爱、同情远不及其他牲畜。命运最悲惨的要属被离开故土的主人抛弃的狗,“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条穷狗,会为一根干骨头走村串巷,挨家乞讨,备受人世冷暖,最后变得世故,低声下气”(《一个人的村庄》)。它会感激给过它丁点吃食的人,感激没用土块碎石打过它的人,即使心里有些许怨恨也不吠叫。每日毫无目的地在村中游荡一圈后回到空荡荡的窝中,终日陷入无休止的对主人的回忆,何其可怜可叹。
“狗”意象的设置对照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的境遇和生活状态,刘亮程用狗的卑微来象征社会生活中人的被压迫。看家护院的狗首先要弄清哪些人不能咬,“狗不咬村长,村长到谁家去,都不提棒子。狗能闻出谁是村长。村长身上酒和羊肉味最重。有些年玉素甫身上的酒味羊肉味比村长还重,狗好多年前就把玉素甫记住了。这个人也不能咬。有关谁能咬谁不能咬的信息,早被大狗传授给小狗,代代相传。不认识村长和玉素甫的狗早被打死了”(《杨树·黑狗》),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批判意识。狗用性命换来的生存之道又何尝不是底层农民的生存法则,在封闭的乡村世界里,作为乡村政权代言人的村长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村民对其只有无条件的臣服。人微言轻的农民既是不合理的乡村秩序的受压迫者,又充当了权力秩序的自觉维护者,鲜有反抗的勇气。这使我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在刘亮程散文中相对于生命的强大他更关注于生命的脆弱与弱小”[2]56-68,衣衫褴褛的老汉被冻死在雪夜中;年老多病、天一冷便足不出户抱着火炉期盼春天来临的姑妈最终还是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有七个儿女的陈林宽一家人挤在两间矮小的破房子里,他一年到头忙着给孩子弄吃弄穿,在四十岁那年被一堵意外倒塌的墙压死了,撇下孤儿寡母,最大的儿子十五岁,最小的儿子还在母亲怀里抱着……刘亮程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倾注了深深的悲悯同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刘亮程从不认为村民们因为一个鸡蛋而与邻居反目、为半截麻绳大打出手是鸡零狗碎的斤斤计较之举。他们对邻人家事的关心多集中在王家腌了几缸咸菜喂了几头驴,李家粮仓里还有几担麦子。刘亮程对此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对生活在荒远乡村的农民来说,举凡东欧局势、香港回归等天下大事远不及牛啃了他们的庄稼、地里的麦子要旱死了重要,因为这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刘亮程善用平淡的文笔描述那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平淡琐碎的小事和感受。如他数次提及买了他家旧宅院的冯三,光棍冯三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害怕死后无人掩埋,“人家有儿女的人,后事有儿女准备,自己不用着急。我得自己料理”,因此,村里有人亡故时他常去帮着打理尸体脱换寿衣,这样自己死时会有替他们家人料理过后事的人来帮忙。冯三平日里生活寒素至极,待客的饭就是米饭和炒白菜。他对返乡的刘亮程坦言了自己的心事:烧饭的锅底一时半会还不会烧通,门窗也能凑合用,烟囱锈住了往灶房里倒烟也能忍受,唯一的担心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的房顶会塌陷,“它要能将就着撑几年,让我把日子熬完,我就给它磕头了”(《一顿晚饭》)。刘亮程在很多篇章里写到了人面对自然灾害、孤独、衰老和死亡时的脆弱和无助,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
在很多作家笔下,“狗”是勇敢者的象征,在受到压迫时,绝不一味隐忍,而会选择反抗。杨志军小说《藏獒》中的藏獒何其英勇无畏、凛凛逼人。但刘亮程笔下的狗鲜有反抗举动,这种反抗精神反倒存在于刘亮程笔下的驴意象中,“宁肯爬着往前走绝不跪着求生存,把低贱卑微的一生活得一样自在、风流且亢奋,而且并不压低嗓门,低声下气,用激扬的鸣叫压过沸沸人生”(《通驴性的人》)。刘亮程笔下的驴张扬自己的不屈与反抗性,而狗选择的则是臣服。
卑微个体的生命往往是平庸的,“一个村里出一条好狗跟出一个厉害人一样,不是件容易的事。得好多年、好几代的积累。有时好几代人和牲畜活得平平庸庸,没一个出众的,走在村里碰见尽是些傻乎乎的人、懒不兮兮的狗和连头都抬不起来的牲口。村庄的历史中大段大段都是这样的年成。但是,把好东西省下了,一个村庄一般三十年出两条厉害狗,三百年出一个攒劲人。只是一条好狗还经受不了一次磨难就彻底废掉了。一个厉害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大概正好生在这个村子的平庸年月。我小的时候觉得村里好多人都非常厉害,现在一看,一个厉害的都没有了。连一条厉害点的狗都没有了”(《坑洼地》),字里行间贯穿了知识分子式的人生思索。刘亮程通过描述庸常人生中的种种琐碎烦恼,表达了对尘世生活中小人物的灰色命运似乎永远也难以改变的无奈。
三、忠诚的乡土文化的坚守者
狗一向被视为是忠诚的化身,即使被主人误解或抛弃也对主人眷恋依旧,《两条狗》中的黑狗即是典型。狗的生命和自由皆被主人局囿在狭小的庭院里,但它们忠于职守,从不偷懒懈怠。刘亮程有次返乡时因听不到狗吠而奇怪,村民冯三告诉他:村里的狗全挣死了,每隔三年,一到竞选村长时,狗就要挣死一茬子。因为当村长可以利用职权捞好处,竞选者整夜挨家挨户敲门拉选票,闹得看家护院的狗彻夜吠叫,“许多狗挨不到村长选出来,就早早挣死了。剩下的狗叫到最后也没声了,嗓子叫坏了。狗一叫坏嗓子,不几天就急死了”(《狗全挣死了》),它们是因失声后不能为主人看家护院而急死的。狗的不善于变通的忠诚秉性从未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我觉得我和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社会变革跟它们没有一点关系,它们不参与,不打算改变自己。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自私时,它们还是原先那副憨厚样子,甚至拒绝进化。它们是一群古老的东西,身体和心灵都停留在远古。当人们抛弃一切进入现代,它们默默无闻伴前随后,保持着最质朴的品性”(《通驴性的人》)。尽管作者在文中所指的“它们”并不单指狗,但这种特质在狗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刘亮程借“狗”意象表现的是:狗比人更珍视情感,狗身上有比人类社会更有价值、更温情的东西。
刘亮程乐于向所有动物们学习生存法则。他经常用动物或昆虫的生存来观照人的生存,“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那么,刘亮程更欣赏哪种动物或虫类的生存方式呢?《人畜共居的村庄》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探讨。第一个选择是做一头驴,因为在刘亮程眼中,驴周身洋溢着一种快乐的天性,可以随性调情撒欢,活得任性潇洒,充满自豪和自信。驴虽平时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刘亮程对驴的生命态度欣赏有加,甚至自称为“通驴性的人”。第二个选择是做一条无忧无虑、乐不知死的的小虫子,尽管一生极其短暂,但也无多大遗憾。第三个选择是“做一条狗呢?”作者自问,却没有回答。但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作者的情感倾向:狗的一生背负了太多无可推卸的责任,活得太隐忍憋屈,这是刘亮程所不甘心的。
年轻时的刘亮程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方式,怀着对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他一步步离开了故土。先是把旧宅院卖掉,全家搬到县城近郊的元兴宫村,后又搬到县城,还娶了在县城一家银行工作的漂亮的妻子。但他并未满足,继而辞掉从事多年的乡农机站管理员的工作,到首府乌鲁木齐一家报社任编辑。刘亮程计划着在这个城市打好基础后,把全家在从沙湾县城搬进首府,“一户农民,只能靠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走进城市,最后彻底扔掉土地变成城市人”(《家园荒芜》)。
刘亮程努力地融入城市生活,但远去的故乡仍魂牵梦萦,他常常想起当年离开黄沙梁时,那条站在渠沿上目光忧郁的狗仿佛代表村庄和他们一家道别。“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而现在,村中那日日打鸣的红公鸡、老死窝中的黑狗、褐黄色的土壤、田野间的植株作物、带着碱味的水、傍晚的炊烟、牛哞声都成为他怀念的对象。他意识到,忘却黄沙梁,意味着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快乐、孤独等人生体验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他的精神归属仍停留在黄沙梁的田野草木之间,“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他们可以修理我的枝条,砍折我的桠枝,但无法整治我的根。他们的刀斧伸不到黄沙梁”(《留下这个村庄》)。他在《只有故土》一文中深情倾诉:“我的故乡母亲啊,当我在生命的远方消失,我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回到你这里——我没有天堂,只有故土”,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黄沙梁割舍不断的依恋。
在当下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半是老人。老人与狗相依相守的画面是许多农村生活的缩影。对狗来说,主人和院子就是它生活的全部,终其一生都要守候在这里,听从主人的召唤,看家护院。回到故宅的刘亮程掀开狗窝顶盖,“看见我的狗老死在窝里,剩下一堆白骨。它至死未离开这个窝,这座院子。它也活了一辈子”(《别人的村庄》)。狗对家园至死无悔的依恋和守候深深打动了他,刘亮程发自内心地称黑狗为“师傅”:“这一生中,我最应该把那条老死窝中的黑狗称为师傅,将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叫老师。它们教给我的,到现在我才用了十分之一”(《我受的教育》)。刘亮程笔下代表对日渐远去的乡土文化的坚守的狗意象与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农民蓝脸在精神深处有很多相通之处,蓝脸是个执拗的,或者说是一根筋式的传统农民代表,不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着土地,从未有丝毫背离土地的念头。
进城之后刘亮程又无数次地返乡。在城乡往返对照中,刘亮程认识到,城市的各种现代设施只是给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却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精神文化体系。而乡村则不同,因为那有祖坟、宗祠和祖先灵位,能妥帖地安顿人的灵魂,让人活在生命古往今来的秩序中”①参见刘亮程.城市讨好身体,乡村安顿心灵[EB/OL].http://cul.qq.com/a/20150916/055798.htm.。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让人没有来世的地方,因此,已在首府乌鲁木齐安家的刘亮程,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却重返乡间,选择了虽贫穷闭塞,但还保留着许多旧农村的风貌的木垒县菜籽沟村重新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他在那里开办了木垒书院,种菜、养鱼、垒狗窝,重拾传统农耕生活。他坦言回到农村就是想找到一个安顿身体和心灵的地方。
与贾平凹一样,刘亮程一直关注在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的乡村生活和农民命运,思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作品中展示了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命运起伏。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数亿农民将何去何从?面对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乡村文化日渐消逝,乡村精神应如何构建?贾平凹在2016年推出的新作《极花》中展示了当下农村惊人的衰败,他在《极花》后记中写道,“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农村的衰败速度极快,令人吃惊,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②参见贾平凹:贾平凹谈《极花》:农村惊人的衰败让我的心情像“失恋”[EB/OL].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6-04-14/23208 00315.shtml.。贾平凹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挽歌式的悲壮和无奈。同样,日渐凋零的家园荒芜的阴影也笼罩着刘亮程,但他虽心存焦虑,却并不过分悲观,认为中国的乡村文化体系并未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而被破坏殆尽。他相信千百年凝聚下来的乡村文化早已耳濡目染,浸淫到每个人的血液中,不是说破坏就能破坏得了的。他呼吁全社会携手传承营建乡村文化,因为我们都需要安放灵魂的地方。
刘亮程散文中构建的“狗”意象具有丰富而深邃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蕴涵。他在狗身上倾注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通过对照人与狗的生存境遇、生存哲学,表达了个体生命无法对抗无常命运和时间流逝的无奈和焦虑感。狗意象也隐含了刘亮程对乡村文化的依恋和守护皈依灵魂家园的精神追寻。从几经周折跻身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世界,到重返乡土,体现了刘亮程文化价值取向的嬗变,他放弃的是世俗名利和喧嚣繁华的物质世界,而获得的则是心灵的安宁熨贴。
[1]陈枫.矫情时代的散文秀——对刘亮程散文的另一种解读[J].社会科学论坛,2007,(2).
[2]摩罗.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J].社会科学论坛,2003,(1).
(责任编辑:任屹立)
Survival Description of Farmers in West China and Guarding of Rural Cultu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og Image in Liu Liang-cheng’s Essays
Lu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Shandong 252000,China)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rich and meaningful animal images in Liu Liang-cheng's essay collection One Person's Village.Among these im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dog imag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He contrasts 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survival philosophy between men and dogs,revealing western Chinese farmers'attitude of contenting with destiny.This is an implication of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suffering,loneliness and fragility in life,of his exploration in individual existence value and meaning and his longing for guard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for returning to soul's home.All these demonstrate insightful humanistic spirit and philosophical meaning.
Liu Liang-cheng;dog image;survival philosophy;local culture
I207.67
A
1671-0304(2016)06-0001-06
2016-09-10
时间]2015-08-31 8:10
卢军,女,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0218.1254.0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