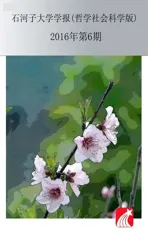论刘亮程散文中的孤独体验
2016-04-04陈红旗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新世纪散文家”专题研究】(主持人:黎保荣)
论刘亮程散文中的孤独体验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刘亮程的散文中有一个并非全部“人化”的孤独者谱系,他们是作者与世界的纠葛关系中体验最为真切、自然和随性的那类孤独感受的具化形象。孤独者最终体验的向度是死亡。在作者的心目中,不仅生者的灵魂是孤独的,甚至连死者的灵魂也是孤独的。对自然生存的思索,契合着刘亮程心灵中关于反抗孤独的主题。刘亮程散文以“命定孤独”的理路和“反抗孤独”的意识凸显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
刘亮程散文;孤独体验;反抗孤独
刘亮程的散文中充满了“历史中间物”意识。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文学行者”,他似乎总是从充满新奇、孤寂感的“行走”起始,又以沉浸在自己长梦里的“过客”[1]81式的空灵感为终。随后,“游魂”一样的“我”游走在黄沙梁边上的细节描写不断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意象和散文的意境构成了互文的关系。作为一个精神喻体,“游魂”与固着在村庄或城市的“居民”形成了二元对立。“游魂”喻指有着独立人格的不安分的灵魂,但是在一种喜欢群居、害怕被孤立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社会现实中,喜欢流浪的行者是会受到误解乃至敌视的。如此,喜欢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游荡的行者”便喻指着一种“孤独者”在中国社会中难免因被视为另类而备感孤独。刘亮程便是这样一个“游魂”,一头闯进了一个充满“陌生”语言文化的环境和世界中,失重与寂寞如影随形,直到孤独感蔓延开来,完全遮蔽了自我的精神世界。但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刘亮程又是“从容优雅”和充满喜悦的,“我的孤独不在荒野上,而在人群中”[2]42,也正是因为他在荒野中衍生出来的生命感受和艺术体验是如此丰富,以至于读者会觉得他从未因孤独而失去他所经历的一切。
一、孤独者的谱系及其与世界的间距
刘亮程的散文中有一个并非全部“人化”的孤独者谱系:“我”—贼—游魂—寻找家的影子—长梦者。长梦者是刘亮程对孤独者的最形象的演绎。的确,长梦者与“我”这个孤独者之间有着极多的相似性,“我们”都是独立的、自由的,都有着安稳的情绪,都有着厌恶甚至想灭掉统治者的意志,都是喜欢聆听虫鸣和鸟叫的灵魂,都存有可以在睡梦中接受时代消亡和伟人死去的潜意识,都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时空感……长梦者是睡在自己梦中的孤独者,没有谁能统治他们的睡眠和梦,因为所有的统治手段只能针对“人的清醒”,他们也是刘亮程与世界的纠葛关系中体验最为真切、自然和随性的那类孤独感受的具化形象,并结合着绞缠刘亮程灵魂的黄沙梁人的影子。
生与死、喧闹与荒凉、梦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刘亮程面对世界所产生的复杂情感,但在“我”或“长梦者”的内心深处,却产生了命定孤独的明显倾向。刘亮程散文所蕴含的情感的作用就在于抒写出这种倾向的延展过程。因此,刘亮程散文一直紧紧围绕着“我”或“长梦者”与故乡家园和村镇居民的双层关系。刘亮程曾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为:“我一直想撇开自己从别处开始,但每一次都原回到自己。”[2]423为此,“我”或“长梦者”与故乡家园的关系以及与村镇居民的关系便是“撇开”和“原回”两个方面。但刘亮程散文写出了民间的自在状态和衰败气象,以及时光消失背后一些被文字记录的村庄的“不幸”。当然,故乡家园与刘亮程的情感纽带是紧密的,他记录的生活真实和村庄存在意义之所在的与世界的自然关系也被其文字不断强化,尤其是后者构成了刘亮程的心灵独语,是对他心灵寂寞和恐惧的透视,因为作为一个个体,你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最后都得独自面对只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和恐惧”。这种感受使作者的深情回望充满了消解的力量,使那些不断被书写的村庄、田野、牲畜、草木都在文字背后消隐。这些寂寞和恐惧尤其是荒芜家园都促使作者的孤独感变得更加强烈,他们证明了关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图景不过是一种幻像,令作者对自己的“寻找”和“怀想”产生了浓重的怀疑,也令故土和乡情这两大情感依托最终难以落到实处。作者的“撇开”和“原回”两方面都变得艰难,他在荒芜家园中无以栖居,在都市世界中又无处回归,于是只好把不能被改变的一切深藏心中,把自己扔向一个继续寻找的困境,也把自己的臆想、伤感、黯淡和孤寂缓缓推出。
刘亮程散文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叙述在设计上有着明晰的对立统一性:一方面,故事情节和情感叙述不断强化“我”或“长梦者”与世界的离散关系,不断强化两者之间“看”与“被看”的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又让“我”或“长梦者”努力贴近黄沙梁村庄或库车老城的古老心灵,并承受着现代化浪潮裹挟下的乡村和古城衰败命运的冲击力。“我”或“长梦者”看见了那些民间生活中不会改变的东西,却无法说出它的人们整日坐在街边尘土中的“沉默不语”;“我”或“长梦者”明白他们多年不变的生活“像一种等候”,却无法说清被他们所感动的情绪,因为我们不过是这个自在世界的“一个短暂的停留者”[1]123。这种内化的哲理思辨迅速将“我”和“长梦者”等孤独者推向困境,让孤独者在无法言语的沉默中体验更深的孤独感。孤独者走过、看过库车老城、黄沙梁边上的村庄和新疆的许多地方,却最终希望那些老城、村庄和地方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因为面对它们丰富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与其妄想做它们的代言人,还不如做一个虔诚的倾听者。如此,那些看起来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情景和作者矛盾的情感,犀利地拆解了孤独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言说权利和意义,因为那些最令人动容的沉默者才是这些地方的真正主人。但作者的这种反思、独语和情节设计并不是为了批评这个世界,事实上,他意识到那些村庄的真正主人反而只能在他的叙述中沉默,这种悖论性的情节设计背后,所潜隐的是孤独者无法在他者那里实现自我认同的痛苦反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思维和宗教认同隔断了“我们”与“他们”心灵沟通的一些路径。如此,上述情节设计和情感体验的目的就明示或隐喻了孤独者与民间世界的隔膜向度。
这种自我强化的孤独体验是情节和情感推进的关节点,进而推演出孤独者的最终体验向度——死亡:“死亡是我最后的情人,在我刚出生时,她便向我张开了臂膀。最后她拥抱住的,将是我一生的快乐、幸福,还有惊恐、无助。”[2]223当然,无论是生还是死,这些向度都要通过空间的转移来设定,更要通过时间的维度来得以实现。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其实有不同的时间观念。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外来者”,“我”和“长梦者”会在自然时间之外,感受到另一种时间的存在——新疆时间。在新疆时间里,“我”和“长梦者”可以看见生长一棵树的时间、长老一个人的时间、绿洲变成沙漠的时间,可以在小说中建构一种人的永恒时间,它会让困扰我们生死的时间在“虚土庄”这里发生弯曲并生成一种可以返回的路:“它属于一个人。每个人找到的道路,都只适合一个人行走,而不适合一个村庄和一群人通过。这条道路因其狭窄而吸引单独的每个人。”[3]191这种“向后走”的脱离时间的可能性判定了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也让孤独者难以实现心灵相遇。比如“我”会感激新疆给予“我”的“智慧和生长”,“我”因此获得了“我”的目光、口音、味觉、走路的架势和文字,但必须用维汉两种语言表达的困难进一步加重了“我”的孤独感。当新疆因为地域、风俗、历史文化和伊斯兰精神而成为“中国和世界的远方”时,生活和回忆新疆黄沙梁的“我”将不得不面对更为遥远的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当意识到这种心理距离难以逾越时,“我”宁愿去和风讲述故事:“我喜欢把一些故事放在风中去讲述。风是动的,风在描述、风在呈现、风在传诵。人若听懂风声,就听懂了大地上的所有声音。文学的听懂是一种心悟,一种内心感受,是我和风之间的心照不宣。”[3]380而风给肉体带来的感受越鲜活,家乡的荒芜本相越显露,他们就越发反证着“我”和“长梦者”灵魂的孤独。这是孤独者极为真实的情感体验。
二、个体孤独的意义与限度
刘亮程散文基本上是由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在新疆尤其是黄沙梁的生活、见闻、感受和故事的,而“我”也是散文中唯一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记叙事件的独握话语权的人。这个叙述者在作者与自在的世界之间无限地接近甚至等同于作者,并对自在世界同样投入了深情的注视。叙述者在展现各种生活场面中真切而敬佩地审视着新疆人的心态,并由此主动寻求人类而非同族同教者意义上的心灵相通。随着观察的深入和展开,他看到了新疆维吾尔族人对伊斯兰教、佛教的信仰,对传统习俗(割礼、托包克游戏、把别人的祖先也当作神灵进行供奉)的沿习,对传统技艺(打铁、理发、修鞋、烤肉、烧陶、打馕等)的坚守;他了解到了蒙古族萨满的神奇之处,萨满知道在可见的世界中充满影响生物体生活的不可见的力量或者灵魂,萨满会把头伸进风里,会跟草说话,会与水对视,能看见草叶和水珠上的灵,萨满的灵能跟天上地上地下三个层面的灵交往,也能跟生前死后来世的灵对话,人可以造神,却造不了灵,而萨满都是通神的,最好的萨满可以通灵[3]170-172;此外,他还看到了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生活情态。对于这些新疆人,尤其是将死者,“我”会心疼他们在不变的生活中所耗掉的一生,但“我”说不出他们的孤独,也许在死后“我”会像《古兰经》所说的那样坐在一颗闪亮的星宿上远远地望着“我”生活过的地方和在尘土中劳忙的人们,那时“我”应该什么都能说清,“可是,那些来自天上的声音,又是多么的遥远模糊”[1]116。至此,不仅生者的灵魂是孤独的,甚至连死者的灵魂也是孤独的。
不过,叙述者“我”毕竟不是“长梦者”,相比之下,“我”要更为思绪清晰和情感细腻,善于在回忆和记叙中来化解对孤独困境的寂寞感受,也善于淡化自己的不良情绪。最重要的是,“我”的叙述“刷取”了作者的自我存在感,而这种“刷取”大多是通过感受自然事物、村民家人乃至家禽家畜的生命情态来反证的。在作者的叙述中,“我”所改变的事物——一片荒野、一把铁锹、一栋房子、一棵胡杨、一株玉米、一头牲口、一个村庄[2]6-9,永远也赶不上风所改变的东西多:风会吹弯树身,掀翻屋顶,吹散垛草,刮走时光[2]253-254;风会刮开院门,刮起父亲的脚步,刮来远远近近的声音[2]294-295;风会刮薄院墙,刮大我们,刮老父亲[2]167-169,“吹彻”亲人们的岁月和生命[2]104-105;风会改变自然,改变所有人的一生:“我们长大、长老,然后死去,刮过村庄的一场风还没有停。”[2]160具而言之,“我”与人的关系远远比不上“我”与“物”的关系密切和通透。“我”会从每个动物身上找到一点自己,“我们是彼此生活的旁观者、介入者”,当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和自私时,它们还是原先那副憨厚样子,甚至拒绝进化,“它们是一群古老的东西,身体和心灵都停留在远古”。为此,“我”努力成为一个通驴性的人,“我”知道驴是长夜里冥想大事的智者、圣者,知道人与驴相比要更加卑微:“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强大的,对驴则不然。驴不承认世界,它只相信驴圈。驴通过人和世界有了点关系,人又通过另外的人和世界相处。谁都不敢独自直面世界。但驴敢,驴的鸣叫是对世界的强烈警告。”[2]14-15“我”知道狗能活到老是件不容易的事,知道一条老狗的见识肯定会让一个走遍天下的人吃惊,因为它的眼中满是人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知道狗会把所有的爱和忠诚奉献给养它的人,更知道狗这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地践行着自己的神秘使命[2]3-5。“我”也知道家里的黑猫为什么要成为一只死心塌地的野猫,因为它的瘸腿是被人打的,这使它丧失了对“我”和他人的所有信任,它将远离它曾生活过的村子,因为它知道它干的那些事使得“村里人不会饶它”[2]180。我还知道马来到世上不仅仅是给人服务的,还肯定有它自己的事情,人们常常以为马帮自己干了一辈子活,却不知道自己也帮马操劳了一辈子,更不知道马并非被人鞭催着在奔跑,而是在自己奔逃,至于人也不过是“在借助马的速度摆脱人命中的厄运”[2]22。我更知道在深夜里鸣叫的鸟是孤独的,在黄沙梁的上空“它把孤独和寂寞叫出来了”[2]147,可人不懂鸟在叫什么,不知道鸟是会认人和对人说话的[2]343。这意味着“我”与这些动物存在着情感上的共鸣现象,它们的寂寞让“我”倍感孤独,但“我”并不想制造更多的情感波澜,“我”快意于将这些情感潜隐在叙述和故事中。这种与读者保持的距离感使得“我”在移情于“物”时,保持着物的差异性和自我的主体性,这种差异性和主体性又使得“我”与“物”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使得“我”与“物”的对话存在多种可能。
在某种意义上,“我”与“物”的对话要比“我”与“他人”的对话更为重要。这种“对话”并不仅仅是对“我”的所见所闻所感的白描,更是对游魂孤独命运的呈现,这种呈现与“我”和“物”的对话直接集合在一起。而对话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审视“物”与“人”的命运的密切关系。在作者的意识里,这些对话所概括和凝练出来的往往是彼此相关的形而上主题,他们关涉存在与虚无、实存与玄妙、入世与独守。我们总以为人比虫要高贵,但人在虫的眼中不过是更大的虫子,虫的生命简洁到了只剩快乐的程度,而我们这些自命聪明的人“却在漫长岁月中寻找痛苦和烦恼”[2]24;我们总以为自己知晓很多,却不知道真正进入一片荒野是很难的,荒野敞开它的大门让你走入,可它的细部是对你紧闭的,而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我们不知道风为什么要把人刮歪?狼的孤独是怎样的?野兔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路被人踩坏而生气?我们讲的笑话是如何把一滩草惹笑的?蚂蚁为什么不喜欢人类的帮忙?老鼠一天到晚忙出了啥意思?一只濒死的小虫在永不停息的生命喧哗中有着怎样黯淡的心境和悲哀的感知?我们无法完全体味一条狗的晚年心境,我们同样不知道时间本身并非无限,“时间再没有时间”[2]55。但这些“活物”们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它们在角落里盯着你,它们知悉你的孤独和无助,它们不会误解你的喜怒哀乐,它们其实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东西”,它们让人看清自己,而在人的灵魂中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消灭,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巨蟒大禽,在人身边活下来的人们把它们叫牲口,却不知道它们把人叫什么[2]65。或者说,我们总以为天堂、真理和道理在无尽的远方,却不知道它们就蕴含在你所生活的村庄里:“一头温顺卖力的老牛教会谁容忍。一头犟牛身上的累累鞭痕让谁体悟到不顺从者的罹难和苦痛。树上的鸟也许养育了叽叽喳喳的多舌女人。卧在墙根的猪可能教会了闲懒男人。而遍野荒草年复一年荣枯了谁的心境。一棵墙角土缝里的小草单独地教育了哪一个人。天上流云东来西去带走了谁的心。东荡西荡的风孕育了谁的性情。起伏向远的沙梁造就了谁的胸襟。谁在一声虫鸣里醒来,一声狗吠中睡去。一片叶子落下谁的一生。一粒尘土飘起谁的一世。”[4]11-12就这样,刘亮程的散文一面演绎着游魂的孤独命运,一面对“我”与“物”的关系作哲学思考,并使两者之间形成互文性阐释,进而由形而下的民间生活体验上升为形而上的诗意探寻和存在焦虑。“我”“孤独者”与叙述者,在此成为刘亮程心灵的三个侧面,折射出他对自然生存的深刻思索和对孤独灵魂的精细解剖。
对自然生存的思索,无疑契合着刘亮程心灵中关于反抗孤独的主题。对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却有宗教情怀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5]23-24,刘亮程反抗孤独的方式是不断用洞穿生命的力量去认识一个村庄的存在,去通过丰富的联想抵制孤独的侵袭:“我”知道密密麻麻的树根将大地连接在一起,“我”的耳朵贴在黄沙梁的树根上就能听见百里外的另一棵树下的动静;在别人砍树时“我”能体味到那棵树的疼痛,“我”会成为那棵树,“我”会在自己的枝干被砍断时疼得叫出声来[2]191;半夜醒来后,“我”会感知到那些小虫子在小心翼翼地挖洞,它们会在地下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2]215;在白天的阳光下,“我”能感知到村庄像一个梦境,且一直在生长[4]14;而当“我”与库车老城的那些老人坐在一起时,“我”仿佛突然就有了跟他们一样的心境与身世,仿佛坐在自己的老年岁月里,“知道人生是这样一种结局”[1]109。明了了这些,“我”会对生与死等问题释然一笑,“我”会注定回到自己行将废失的家园——黄沙梁,重新归属于她,与她的尘土、炊烟、树叶和草籽一起,成为她下一个春天的种子,重新发芽、开花,再次感知她的恩惠和生机[2]385。在作者看来,一个村民的视野当然会有局限,但谁又能不活在自己的局限之中呢?就算是鬼魂也会活在他们的局限之中,他们在村庄四周的田野上寂静地站着:“他们等着进村,他们的地和宅院全被人占了。他们乞丐一样静悄悄地恭候在村外,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地等候着。”[2]98与此同时,人的一生未必能做成什么大事,因为割草、浇地之类的小活计就可以消磨掉人的一辈子,随便一片树叶落下都能盖掉人的一辈子:“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角落落里,我们找不到的那些人,正面对着这样那样的一两件小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辈子。”[2]116显然,作者同意叙述者的观点,因此才会明确表示将持续坚守人性中对独处的心灵渴望和反抗孤独的精神诉求。
进而言之,叙述者或曰刘亮程意识到,人的孤独的生存状态“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是人为的因而可以用自我调整的方式去改变”[6]27。比如,“我”是一个村庄的游荡者,当“我”游荡时须记住自己的家,以便哪一天当“我”像鸟一样飞回来时能认出家人的面容,可当“我”真的摸回家中看见熟睡的亲人时,“我突然孤独害怕起来,觉得我不认识他们”[4]64。这意味着“我”的孤独是自己心造的,追问造成这种孤独的原因,“我”借用后父的生存状态说明了自己的问题。作为死去的亲生父亲的替代者,后父虽然与“我们”相依为命,但其实早就失去了与“我们”进行情感沟通的可能。在作者看来,在一个家里父亲之于儿女是无可替代的,儿女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女长大成人,在这个过程中儿女们会活得自在从容,会慢慢懂得老是怎么回事,可父亲在37岁就过世了,父亲死后“我”所有的童年之梦都破灭了,只剩下生存,此后“我”不但丧失了赡养亲生父亲的机会,还失去了父亲引路的可能性,“我”将不得不“在黑暗中孤独地走下去”[3]12。也是为了生存,“我们”有了后父,但“我们”和他在情感上是疏远的,在干活时是别扭的,因为“我们”总是会搅乱他在院子里的历史记忆[4]343,他留给“我们”的除了一褡裢金子的传说,此外再无什么“辉煌”的陈年旧事。作为一个家庭的后来者,后父先天地失去了与“我们”的童年一起成长的可能性,沟通不畅同样使得孤独成为他难以克服的宿命。为此,刘亮程与鲁迅一样觉得“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7]81,而要改变这种境况,除了自我去改变之外别无他法,而不去改变则孤独必将成为个体命定的生存状态。问题在于,作者在试图说服自己的同时,又对这种摆脱孤独的期望充满了怀疑,于是“命定孤独”和“反抗孤独”这两种论调都不断被诘难和质疑,以至于无法产生定论。
三、孤独之中的挣扎与反抗孤独的意识
刘亮程散文以“命定孤独”的理路和“反抗孤独”的意识凸显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我”的孤独本源于“我”的自造之门,虽然生活已经彻底攻破了“我”的现实之门,让一切东西都逼到了跟前,但“我”依然可以躲在“唯一的一道门”[2]362——心灵之门的后面。同理,“我”的反抗之于“我”自己是孤独的;而作为一种自然化的“物”的存在形态——村庄的抚慰也无法改变“我”的孤独命运。这种情形就像在荒野里,“我们”本来玩着游戏,但走着走着就剩下一个人,黑暗成了一个人的,这是无数生存游戏的结局之一,它让“我”明白,即使在一个村庄里“我”也迟早会走进那片彻底的黑暗里:“它是我一个人的漫漫长夜,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我不会在那样的黑暗中,再迎来光明。太阳永远地照耀到别处。”[4]376在这里,“抵抗”和“躲避”成为“我”反抗孤独的人生选择,但这类主体行为只会强化“我”作为一个孤独者的宿命意味,因为死亡将让“我”无处可藏。
有意味的是,刘亮程更喜欢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孤独的本质,并将其首先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加以体认。比如:在他的笔下,艾布曾是一个“月光里的贼”,他非常狡黠,他的脚印难以追踪,他明朝东跑却故意往西拐,他偷完东西就从不留脚印的柏油路上跑掉,他从路边走时会踩着驴蹄印走,有时一只脚跳着走,有时躺倒驴打滚一样滚着走,有时把自己的脚印印在别人家的门口,他还有专门偷东西时才穿的鞋,他偷过村长家的鸡、偷过临村的羊,在被四个公安追捕却蹊跷逃脱之后,他不再偷东西,但婚后的他仍然喜欢在夜里游荡,他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无人知晓,却不知道善于追踪的老村长早就知道他是村里的小偷,之所以没有抓他是怕他永远背负一个贼名生活下去,而他的妻子也一直知道他喜欢“梦游”,只是为了女儿能听见自己心上人的脚步声才点破了他的秘密,并希望他不要再在夜里游逛了[3]218-224。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很多你自以为绝密的事,他人其实是知道的,只是没有被点破而已。正所谓“人心隔肚皮”,这意味着“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8]15。
问题还在于,既然在客观世界里人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活着?刘亮程轻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相比于死的神秘莫测,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要简单得多,这个理由可能只有芝麻那么小,而这些芝麻小理并不被通常的大道所涵盖,活在大地边缘的一村人,“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大事,但不因此活得小里小气”[4]16,他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只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在民间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比生存更重要的。而关乎生存的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又无比复杂。可无论是把简单的事弄复杂,还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在民间世界里生存总是拥有优先权的,因为活着首先是为了活着,人类如此,其他生物也是如此,活着并不一定非得为了某个宏大目标或者神圣意义。当然,“有所为”而活要比“无所为”而活有力量得多。它可以使人为了做完一件或几件活计而淡化漫长岁月中的无聊之苦、冻馁之苦、劳作之苦、困顿之苦、无奈之苦、病患之苦、别离之苦、欲望之苦和放不下之苦。但这“有所为”并不一定与“反抗绝望”的生存意志相关,它们不过是一种本能行为或社会行为而已。
相比于求生意愿,死亡意志要更为强大。当一个人死后,无论是爱恨情仇还是喜怒哀乐,之于他本人都没有了意义。因此,尽管孤独不利于个体的生存,人们却偏要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失去孤独就等于失去了反抗孤独的可能性,就等于失去了某种生存意义,结果个体又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意义。这并非“我”的所愿。“我”选择这种命定孤独和坚持反抗孤独,其本身就等于某种生命态度,也等于意识到死亡和虚无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为了克服虚无,“我”选择认可孤独;为了避免绝望,“我”选择反抗绝望;为了求证生之意义,“我”选择游荡于天地之间;为了彰显个体生命的神圣性,“我”选择直面死亡这一最终结果;为了生命的未来,“我”选择用有限的生命去探究未知世界以及生命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刘亮程作为一种“主体存在”[9]40-45对生存意义的终极探寻,是对诸多形而上主题的深刻思索,是同时展开的相互问答和求证,也是他在孤独之中挣扎和有所反抗的多重呈现。
[1]刘亮程.库车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刘亮程.在新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4]刘亮程.站在黄沙梁边上[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5]王晓岚.灵魂于何处安居——刘亮程散文中的宗教情怀[J].当代文坛,2003,(3).
[6]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7).
[7]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M] //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周作人.沉默[M]//知堂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张玉瑶.一个人和他的村庄——刘亮程散文中的主体存在与村庄书写方式[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任屹立)
On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in Liu Liang-cheng’s Essays
CHEN Hong-q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Guangdong 514015,China)
There is a spectrum for lonely people that are not overall Humanization in Liu Liang-cheng's essays.The spectrum is the specified image of that kind of lonely feeling which is real,natural and casual at the same time.And this lonely feeling is derived from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entanglement with the world.The ultimate experience dimension of a lonely person is death.In his mind,not only the living soul is lonely,even the souls of the dead are also lonely.Meditation on natural existence is corresponding to Liu Liang-cheng'stheme in mind—againstloneliness.With the conceptof “destined loneliness”and the consciousness of“revolting against loneliness”,Liu Liang-cheng's essays highlight the authors'unique life experience.
Liu Liang-cheng's essays;experience of loneliness;revolting against loneliness
I207.6
A
1671-0304(2016)06-0001-06
2016-09-10
时间]2015-08-31 8:10
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项建设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优秀教学团队”(粤教高函〔2014〕97号);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粤教高函〔2015〕72号)。
陈红旗,男,吉林双辽人,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暨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