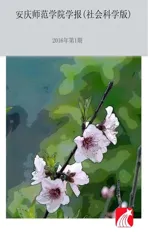白石词的色彩表现艺术
2016-03-18周媛
周 媛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白石词的色彩表现艺术
周 媛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姜夔是南宋清雅词派的开创之人,善于用大量的冷色调和精巧的构图为词作营造了空灵幽冷的氛围,并同时采取多种手法来增强颜色词的表现力。颜色词对于白诗词意象的塑造、词境的烘托以及感情的表达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姜夔;词;颜色;光
南宋词人姜夔,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全才。他能诗善词,通音律,亦有极高的书法造诣,却一生求仕无门,寄人篱下,漂泊江湖的生活给他的词作带来了惆怅沉郁的色彩。他生性耿介清高,志趣高雅,在进行创作时,善于选择清冷的色调并加以烘托、渲染。他的词作,色调优美,意境缥缈,宛如薄幕下若隐若现的青绿山水画。
对于白石词的色彩美,古今词论家都有所提及,张炎在《词源》中写道: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又云其词“真天机云锦也”,杨慎《词品》则云“槛曲萦红,檐牙飞翠……其腔皆自度者,传至今不得其调,难入管弦,只爱其句之奇丽耳。”江炳炎也认为他“笔染沧江虹月,思穿冷岫孤云”,郭麐在《灵芬馆词话》中赞白石词“一洗华靡,独标清绮”。今人陶文鹏认为姜夔擅用彩绘技法,营造出清丽疏淡的色调。而陈磊则认为,白石词如南宗画派,以淡墨渲染出迷蒙悠远的意境。笔者将跟随前辈步伐,对白石词的色彩表现艺术,作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一、冷色调的广泛使用
在词作中他常常用景物与环境的气氛烘托出冷峻而又深婉的情思,在描绘物象时,更是善于刻画它们的颜色。白石词中色彩用词出现的非常多,直接使用颜色词(包含红、绿、黄、紫等)就有61首,占了四分之三左右。他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触。陶方琦悼念姜夔时曾这样概括白石词中的常见物象:“百年心事,惟有玉阑之知;十亩梅花,不隔生香之路。抚兹一卷,契诸春秋。无声,绿尘永结。琵琶谁拨,红萼何言。”许赓飏曾曰姜夔:“正不独疏影暗香,红情绿意,属以同调,遂足方轨。”[1]在描写物象时,姜夔喜好点出它们的色彩,如“翠尊共款”(《眉妩》)、“梦逐金鞍去”(《醉吟商小品》),“红衣入桨,青灯摇浪,微凉意思”(《水龙吟》),有时甚至不出现物象具体的名字,单用颜色来代指物象,如“并刀破甘碧”(《惜红衣》),用瓜果的颜色来代指其本身,又如“我自爱红香绿舞”(《石湖仙》)并没有明写出荷花,而是用荷叶之绿,荷花之红来代指,入目即是红绿相间的绮丽之感。以及“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疏影》),用蛾绿来代指翠眉,生动而又活泼。
对于白石词的“清空”境界的塑造,色彩亦是起着极大的作用。在仔细统计白石词中的颜色词之后,发现其中绿色系词最多,共出现了52次,而且非常有层次感,较为清冷的为青(13次)、碧(5次),较为明艳的为绿(21次)、翠(13次)。红色系词共33次,淡者为粉(1次)、茜(1次),浓者为红(27次)、朱(4次)。黄色系词共11次,娇柔淡雅者为黄(4次)、缃(1次),富丽堂皇则为金(6次)。这三种颜色较为明亮,轻盈,而其他的颜色如黑色、紫色等比较厚重的颜色已经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清代笪重光《画荃》云:“墨以破用而生韵,色以清用而无痕。”是谓作画设色要轻清没有斧凿痕。明代孙鑛在《书画跋跋》提到:“作画深色最难,一色不得法即损格,若浅色则可任意,勿借口为逸品。”作画时用深色最难,难在墨色深重,画面气象容易沉闷,方法不当,画面就会显得不透气,气韵不畅,凝质含混。而姜夔的词恰恰是“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故他在使用重色时非常谨慎,作品中不过两三处。
颜色有冷暖之分,亦有轻重之分。南朝萧绎在《山水松石格》中提到:“秋毛冬骨,夏荫春英,炎绯寒碧,暖日冬星”。近代色彩学把色彩分为暖色和冷色两种,这种分法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其中绯色是红色,暖色,碧是青绿色,冷色。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有过名言:“色彩即思想”。另一位俄国画家康定斯基曾言:“纯绿色是大自然中最宁静的色彩, 它不向四方扩张, 也不具有扩张的色彩所具有的那种感染力, 不会引起欢乐、悲哀、激情, 不提出任何要求。” 绿色是姜夔所偏爱的颜色,这正与姜夔的性格相符合,作为江湖词人,一方面他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自身性格决定他即使寄人篱下也不会随波逐流,他对外界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只能坚守心中的净土,故绿色最能体现出他自身的追求。
青绿色的使用频率高于红、黄,色块也比较大,内部也有不同的分类。在姜夔的作品中多不仅“翠藤”、“绿丝”、“碧云”、“青苔”这样的物象,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绿色:“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扬州慢》),“叹芳草萋萋千里”(《翠楼吟》),为白石词平添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清冷。绿色出现的次数不仅多,运用的方式,表达的心情也是多姿多彩。姜夔对柳树有着特殊的情节,柳树其色为绿,同时代表离别,这为绿色增添哀愁怅惘之感, 如“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绿色还是生命的颜色,给人以青春活力之感,如“春浦渐生迎棹绿”(《浣溪沙》)、“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卜算子》)、“云绿峨峨千万枝,别有仙风味”(《卜算子》)等,同时也具有永恒的意味,白石也用它寄寓兴亡之感“吴唯青山,越只芳草,万古皆成灭”(《念奴娇》)。
除了个人偏好与塑造词境的需要,这也与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有着一定的关系。以绘画为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代的绘画相对于唐朝发生的很大的变化,从金碧辉煌具有装饰性的壁画转为重笔墨而轻色彩的水墨画。绘画作者也从一般的画匠转变为士大夫,他们认为应该“诗画一体”。唐代青绿山水画传到宋代,依旧有很多的继承者,南宋时仍有宗室成员绘青绿山水[2],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造,不似唐朝那般浓重艳丽,用笔纤细刻实,设色清丽不俗。纵观宋代的画作,大多数为水墨画,为数不多有颜色的,均为绿色,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荆浩的《雪山行旅图》。对于崇尚自然清丽的宋人来说,绿色是他们所偏爱的色彩。南渡之后尤甚,随着宋王朝之秋的来临,词作中的颜色风格也是“春红转眼成秋绿”,笔者在对南宋部分词人的词作颜色词统计之后,发现绿色系词均占很大的比例,特别是姜派词人,如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绿色系词的使用更是远远高于其他的颜色。
二、精妙的构图方式
姜夔对诗的写法有着很严谨的理论,《白石道人诗说》云:
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多,虽多而奚为。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屈,是不敷衍之过。
有人认为,姜夔诗作中精巧的构思来源于宋朝山水画,早在南宋时期,作者他好友潘柽称他的诗作“如图画”[3]。陶文鹏在《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这样写道:“强调诗与画的统一性,可以说是宋代普遍的美学思想倾向。”他认为:
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表现同一山水主题的不同侧面,恰似马、夏的分段长卷山水画轴。而马远和夏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们在章法构图上,大胆地采用边角取景。他们常常只在画幅上描绘出山的一角或水的一涯,留下大片空白,这种以一斑窥全豹的艺术手法,使空间感更强烈,收到了以少胜多,借有限表现无穷韵致的艺术效果。
纵观姜夔的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在茫茫背景之下展露一小片景色的方法随处可见,如“白水日以长,仅存青草芽。”又如“此时羡白鸟,飞入青山阿。”
同样的情况在词作中更是多见。夏承焘曾言:“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诗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词正复相似,也是出入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的诗来匡救晚唐温(庭筠)、韦(庄),北宋柳(永)、周(邦彦)的词风的。”从花间到北宋,走的一直是软媚绮艳的画风,姜夔一改其道,詹安泰在《宋词散论》中赞赏到他:“极力创新,力扫浮艳,运质实于清,以健笔写柔情,自成一种风格。”唐圭璋在《姜夔评传》中比较姜夔与吴文英之后,认为二者“一疏朗,一密丽,正和温飞卿、韦庄一样”。同时白石用色时追求清空明净, 疏朗的物象,清空的色调决定了白石词中颜色的使用往往比较单一、纯粹,很多时候都是用大片单一的颜色来渲染做底,即使是在喜庆绮丽的画面中,至多也不过三四种颜色,给人以疏朗之美。叶嘉莹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疏影》:“不沾滞于所写之物,都是跳起来写的。”[4]赵晓岚先生则更进一步指出,“远”、“疏”、“虚”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体现了“空”,空则疏远,空则虚灵,唯其“空灵”,才能更好地体现“清雅”[5]。
依旧是以大片的纯色作为背景,但会出现一些小块的色彩作为补色点缀,在白石词中也极为多见,如: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躜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满江红》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暗香》
《满江红》中首句“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渲染出水天一际的壮阔恢宏之感,为之后的战场描写蓄势,然而到了下阕最后又以“小红楼,帘影间”收尾。“千顷翠澜”与“小红楼”一大一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给人以万绿丛中一点红之感,既为画面做了点缀,又不会破坏画面的整体色调而显得杂乱无章。而在《暗香》中的“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一句,先著、程洪的《词洁辑评》中对此搭配有着极高的评价:“咏梅嫌纯是素色,故用‘红萼’字,此谓之破色笔。又恐突然,故先出‘翠尊’字配之;说来甚浅,然大家亦不为,此用意之妙,总使人不觉,则烹锻之功也。”词中所吟咏的梅花,以及其所处的环境中的月光、飞雪均为白色,整首词给人以清冷静谧之感,然而几种物象颜色均为纯白略显单调,质地均为柔软则显得纤弱,加之硬质的酒尊、花萼中和的画面的纤弱之感,而点出的小块颜色红与翠,更是为画面增添了色彩。
除此之外,有时会采用颜色相间的手法,画面中色彩在空间上距离近,分量比例也较为均衡,组合起来便有着鲜明的艺术效果。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相思血,都浸绿筠枝”(《小重山令》),红与绿直接组接在了一起,没有任何的颜色和空间加以缓冲和协调。于此相类似的还有“湿红恨墨浅封题”(《江梅引》),作者甚少使用黑色,此处浓重的黑与浓重的红混合在了一起,给人以透不过气的烦躁感觉,表达出强烈的离愁别恨。当然,只要在空间上拉开颜色之间的距离,选取相对的补色,相间的颜色十分适合表达出明媚绮丽的景象和热烈欢快的氛围,如“芳莲坠粉,梧桐吹绿”(《八归》)描绘出雨后的小院里的清新画面,“柏绿红椒事事新”写新年的景象。除了用形成对比的红绿色来表达喜庆绮丽的场景之外,柔和淡雅颜色相互搭配也为作者所偏爱,常见的有黄色与绿色相配如“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淡黄柳》)形象的再现出柳色之可爱,又如“翠翘光欲溜。爱著宫黄,而今时候”(《角招》)一个活泼明快的少女形象即出现在读者眼前。绿与白的搭配则更为清新雅致,“朝来碧缕挂长串,钗头挂层玉”(《好事近》)碧绿的丝线与白色的花朵相间,“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暗香》)苔枝与翠禽色相近,都是充满生机的“绿”,其间点缀白色如玉般的梅花,就更显得光彩照人。一幅色彩清新,活泼生动“双栖图”呈现在观众眼前。
三、多样的色彩渲染方式
白石词中的颜色,不仅色泽淡雅,构图精巧,同时也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渲染,既有外在光线的营造,也有内在质感的深化。
在颜色、构图方面,白石的诗词都是很相似的,意境上却有着就明显的差异,笔者认为,在这里,光起着很大的作用。色彩来源于光,描写色彩,就一定会涉及光。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曾对巴黎一天不同时刻雾气中的同一个场景进行描绘,细致地反映出光线对颜色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家们也十分热衷于在诗句中描绘光线对颜色的改变,如同莫奈的画作一般,如李白笔下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望庐山瀑布》),杜甫诗中的“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十二月一日》),王维的诗则更为细致,如“秋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木兰柴》)。曹雪芹认为:“明暗成于光,彩色别于光,远近浓淡,莫不因光而辨其殊异。”姜夔的诗词中既然多颜色自然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去描写光线,所谓“敷彩之要,光居首位”,但姜夔诗词中的光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紫盖何突兀,万里在一目,
馀峰六七十,仅如翠浪矗。
北有懒瓒岩,大石庇樵牧。
下窥半岩花,杯盂琢红玉。
飞云峰畔过,揽之不盈掬。
祝融最高绝,紫盖不足录。
俯视同仰观,苍苍万形伏。
惟馀岣嵝峰,南睇半空绿。
——《昔游诗》
摩挲紫盖峰头石,下瞰苍厓立。
玉盘动摇半厓花,花树扶疏一半白云遮。
盈盈相望无由摘,惆怅归来屐。
而今仙迹杳难寻。那日青楼曾见似花人。
——《虞美人》
从这两篇的词句大致可以看出,二者描写的是同一座山的风光,但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对衡山的景象,诗作中做了极为具体的描写,让人联想到韩愈的诗歌,而词作中山已不是主要表达的对象,下阕抒情,由山花及人,营造了一种惆怅缥缈的意境。
姜夔诗作中的关于光的描写,不仅明朗,而且具体,如:
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
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
我舟渡其中,晁晁惊我神。
朝发黄陵祠,暮至赤沙曲。
借问此何处,沧湾三十六。
青芦望不尽,明月耿如烛。
湾湾无人家,只就芦边宿。
——《昔游诗》其一
这首诗对长虹倒影在湖面上映出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作了细致的描写,把读者带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而姜夔词中的光与诗中的有着很大的差别,他笔下的光,往往是整体的,含混的。
白石词中关于光的描写并不少见,日光、月光、星光、灯光、烛光等等均有涉及。比如
空赢得,今古三星炯炯。银波相望千顷。
——《摸鱼儿》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千枝银烛舞僛僛。
——《鹧鸪天·十六夜出》
日落爱山紫。
——《水调歌头》
光与颜色融为一体,形成一背景色。即使有光线对颜色产生的变化也是比较简略,并不如诗中的那么具体,细致。
白石词中对于光与色描写最为仔细的是《卜算子·家在马城西》的上阕中的“梅雪相间不见花,月影玲珑彻”,皎洁的月光照射着梅花与白雪,这三种颜色均为白色,没有在相互作用下产生别的颜色,作者也没有细致地描写花或雪的颜色在月光的照射下是否与平时有了些许不同,只是整体上用“玲珑彻”来概括其光彩。“白石所写,实际上是一种混沌之美。”白石很喜欢透过一种阻隔物来描写的景物,在白石的自度曲中有一篇篇名为“鬲溪梅令”,所谓鬲溪梅,即是被溪水所阻隔的远处的梅花。相较于王维或李贺细致入微地描写颜色在光线下产生的不同变化,他更习惯于把光当做一种阻隔物,来描写光线下的物象。这种做法正如在华丽的丝绸衣服外面穿上一层素纱蝉衣,使衣服的颜色和图案不过分外露,显得更为庄重高雅。染上了光晕的色彩,更是给人一种缥缈梦幻之美。
近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概》中曾云:“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白石善用通感的手法来构造词境,颜色具有深厚的质感。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同时还伴随着感官上的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等。
触觉是他所注重描绘的,白石词给人冷、硬的感觉多来源于此,如“石瘦冰霜洁”(《卜算子》),洁白的冰霜覆在崚嶒的石头上,给人以冰凉,坚硬的触感。白色本属冷色,冷色调加上可以渲染出的触觉上的冷,凄清幽冷之感更甚。与此类同的还有“长记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暗香》)以及被王国维所偏爱,历代词评家所赞赏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白石词中多清冷,如果出现暖色调(多数为红色)作者常常在前面加上修饰词,用触感上的冷来中和红色在视觉上给人带来的温暖之感,如“冷红叶叶下塘秋”(《忆王孙》),“谁念我,重见冷枫红舞”(《法曲献仙音》)。
嗅觉也是白石所擅长描绘的,他笔下的颜色往往也带有各种气息,他喜爱花卉甚多,梅花、荷花、红药、牡丹、茉莉……读者在看到鲜艳花色的同时也会感受到那扑鼻而来的香气,如写茉莉“金络一团香雾”(《好事近》),写梅花“早乱落,香红千亩”(《角招》)。有时也会是视觉,嗅觉,触觉的统一,如《小重山令》中的:“东风冷,香远茜裙归”,用“茜”字点出娇艳的颜色(视觉),再用东风之冷(触觉)、香飘之远(嗅觉)来烘托意境,真可谓幽、韵、冷、香四字。
白石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较之别的词人而言,他对于声音感觉也是更为敏锐,词作中多有对声音的描写,并常与色彩融合。例如“红云低压绿玻璃,惺惚花上啼。静看楼角拂长枝,朝寒吹翠眉。”(《阮郎归》)春花成片远望如红云,西湖明净如绿玻璃,柳叶娇嫩如翠眉,比喻精巧,色彩鲜艳,加之有“低压”“拂”“吹”等动作,以及“惺惚花上啼”听觉上的渲染,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迷人湖景彩卷。有时也会省略了具体物象,直接让颜色发出声音,如“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同度可怜春”(《鹧鸪天》)。
在姜夔的词中,颜色往往也携带着情绪,如“万绿正迷人,更愁入、山阳夜笛”(《蓦山溪·题钱氏溪月》)。有时颜色词位于句首开篇即以色彩先声夺人,渲染出整体色调,如“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侧犯·咏芍药》),“银波相望千顷”(《摸鱼儿》)而且往往具有主动性,“绿杨低扫吹笙道”(《点绛唇》),“翠眉织锦,红叶浪题诗”(《蓦山溪·咏柳》),“绿野留吟屐”(《蓦山溪·题钱氏溪月》)强调颜色的动作,表达欢快的情绪,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有时颜色词置于句尾,“唯有池塘自碧”(《淡黄柳》)“石榴一树浸溪红”(《诉衷情》)“凉夜摘花钿,苒苒动摇云绿”(《好事近》),这时候强调的往往是颜色本身,表达的也是较为宁静的氛围。
结语
姜夔引诗入词,把颜色作为一个塑造意象和词境的关键,用大量的冷色调为词作营造了空灵幽冷的氛围,用精巧构图手法形成了诗词所一致的疏朗明丽的风格,对光与色的特殊把握为词作添加了其诗所没有的朦胧梦幻的色彩,形成清空骚雅的作品风貌。
文学界向来有“诗庄词媚”之说,但词至姜夔,洗去了从晚唐词产生以来的软媚纤秾的色彩。白石词,是用清冷的色彩所描绘的雅致冲淡的画卷。
参考文献:
[1]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216.
[2]贾文昭.姜夔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1:9.
[3]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25.
[4]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湖南:岳麓书社,1989:410.
[5]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292.
责任编校:汪长林
The Color Art of Ci by JIANG Kui
ZHOU 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Abstract:JIANG Kui, founder of Ci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was good at creating ethereal atmosphere by using cold colors and exquisite composition and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Ci in various ways. Color wor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images, adding effects and expressing feelings in JIANG Kui’s Ci.
Key words:JIANG Kui; Ci; color; light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15-05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04
作者简介:周媛,女,安徽当涂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3-20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