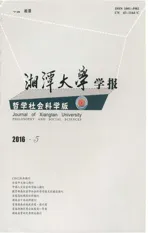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特征及现代法治意义*
2016-02-21李鼎楚
李鼎楚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特征及现代法治意义*
李鼎楚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家法族规”独特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质,至今仍具潜在和积极的影响。通过外部观察的特征描述,能更好地理解传统的“家法族规”。进而,通过全球化、中外交融、古今融通三种视角,发现传统“家法族规”在法治观念、制度架构、司法技巧三方面的中国现代法治意义。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中“封建”留毒的不利影响。
家法族规;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构
“家法族规”是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儒家宗法观为核心,而形成的区别于国家法律的社会治理规范,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特质,至今仍有潜在和积极的影响。“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因此,本文从讨论中国“本土资源”的特征入手,试图发掘传统“家法族规”之于中国现代法治的意义。
一、比较视角下“家法族规”的特征
现有文献,大多从“家法族规”的产生背景或内容构造中讨论其特征,是一种内在视角下的总结。然而,外部视角观认为,对特征的描述是为了从相似性中区分来更好地理解特定事物。所以,“家族法规”的特征,更应该从与其类似的社会规范之比较中去讨论。由此,归纳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相对国家法的公共理性,“家法族规”具有人伦私情的性质
国家法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制规范;同时,它也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1]169正因这种所谓的“公共理性”,个体的人进入国家成为“同质性”的公民,他们都被“理性”而“无差别”的国家法平等地约束着行为的自由。而“家族法规”基于血缘亲情,维护伦常秩序,尊卑长幼,嫡庶亲疏,人伦身份不同,则在家族法中地位不同。因此,它在处理纠纷时,“感性”而“差别化”的伦常私情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于是乎,对现代自由民主的法治,“家族法规”转化的范围,并非涉及到国家根本权力的安排,不应去复古“家国一体”的权力结构。当然,宪制观念意识中,可适当联接国与家的关系,进而增进人民的“国家认同”。但,转化“家法族规”,应更多地集中在对社会纠纷的规范处理之中;它涉及的领域不仅只是私法性的,还可以有公法性的,因为,那些合理转化的法规范是指向“国家治理”,而不同于根本权力安排所属于的“国家建立”范畴。换言之,这种转化主要处理“秩序效果”,而不是“权力来源”。
2.国家法具有统一体系,而“家法族规”注重各宗族自身的不同特色
一国之中,特别是在单一制的成文法体系下,“家法族规”相对于国家法,体现了明显的地域性和团体性。国家法的规范特性是统一和稳定,而“家法族规”中的规范则表现得较为多元和灵活。正因这两者的各异,“家法族规”对于法律治理才能形成有益的补充。它弥补了“形式合理性”的国家法律所造成的现代性弊端,那些理性“铁笼”[2]187下曾被忽视的个体的生命特性、价值选择和人伦关怀,得以再次受到关注。因此,这提示了不应将“家法族规”做统一模式化的过度处理;其中在观念、原则方面可以归结、提炼,但规则层面更需充分地发掘其“因地制宜”特质上的个性化可鉴资源。
3.相对“帮规”及各类“行规”,“家法族规”形式架构上更接近国家法
不同于其他强调地域性或团体性的社会规范,中国传统“家法族规”具有天然的“国家性”。从家族法产生的背景来看,国是家的扩大,家亦是国的缩小。因此,在规范的构造上,古代“家法族规”与国家法律制度有着紧密的关联:一是在制订上,参照国家立法,以“补足政府法令所不及为宗旨”,“如有与政府法令抵触时”,随即相应修改。[3]二是在执行上,可视作国家司法的前置程序。可以说,“家法族规”是“与国法大体接轨的准法律”。[4]173而“帮规”或各类“行规”,仅仅是针对不同性质的群体或行业而产生的内部性规定,往往是在多种具体利益博弈下,自发形成的规则,不像“家法族规”受到国法整体性影响之大。从本质上说,“帮规行约”是陌生人的群体规则,而“家族法规”倾向于传统熟人社会的规范。总之,“家族法规”向国家法制的转化,有着宗旨上的趋同性和路径形式上的便利;但因其受传统社会结构的限制,而在现代的社会自治及个人自由方面,却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4.和西方特色的教会法或宗教审判比较,“家法族规”不过分注重宗教式的神秘色彩。
无论中世纪教会法,还是新教改革,宗教因素对西方法治的形成不可或缺。当代学者伯尔曼甚至指出,现代法律与宗教“二者间的纽带”断裂的时候,“社会便陷于混乱”,因为“现存的制度结构和程序失却其神圣性”。[5]2如果说,教会法或宗教审判是西方法治的历史要素;那么,“家法族规”则是中国特色的法治本土资源。*“法治本土资源论”的倡导者苏力教授称,“历史中国的‘齐家’是宪制问题”,其“独具一格、自成一类”。参见苏力:《齐家: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2)。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家族法“限于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带有中国式的特色并且这种特色保持着合理性和逻辑的一贯性的东西”。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前者是西方借用宗教的神秘,支撑起对法律的信奉;而后者则用一脉相承的血缘认同与情感归属,来实现对强制规范的心理服从。因此,在缺乏宗教信仰的环境,“家法族规”可助力于发挥权威认可的传统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法治认同。
二、传统“家法族规”现代法治转化的三重意义
在上述传统“家法族规”的特征中,可以体会到“古今中西”似乎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上一个既难绕开而又纠结的理论问题;同时,“个人、家族和国家”在当下中国社会中仍构成真实的生活处境。那么,现代法治下的“家法族规”,在传统底色与现代场境间应如何合理转化呢?以下,试用全球化、中外交融、古今融通三种视角,从法治观念、制度架构、司法技巧三方面,简略地讨论传统“家法族规”的中国现代法治意义。这可为对其转化开新的细致研究和具体实践,提供一个宏观性的理解平台和理论前导。
(一)“家”的价值:促进法治观念的中国式展开
“家法族规”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宗法伦理观的典型体现。宗法伦理观在儒家思想中,被经典地表述为“亲亲”、“尊尊”。“家法族规”本于此,言治家之道,是“圣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后人知父子兄弟夫妇之道耳”。*此文字出自《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转引自陈煜斓:《家训族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效应——以江州义门陈氏“家法”为例》的“附录”,《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2)。治道缘于人道,人道始于亲性,由此体现以“家”为核心的血缘亲情是形成治理规则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法在正当理据(法为何如此)上的根本特质。正如儒家经典《论语》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2
然而,我们知道,近现代法治的核心范式,主要由西方世界逐步奠定:它是经历罗马法复兴、自然科学大发展、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等之后最终成型的。然而,其中过度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与“形式理性优越”;这也造成了所谓的一些“现代性危机”,如利益僭越了道德、现象迷失了归属等。[7]
其实,法治观念及理论被现代各国所认同,究其根本在于法治能为实现“良治善道”提供一类“最不坏”的模式。因此,法治自身并不等同于社会良景的本身。况且,不同国家、民族,各种历史传统、时代境况,其中将可能存在具体法治上“各美其美”的多样选择。
所谓法治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世界接受了西方法治的优异,也应反映“他山之石”在西方法治弊端上的世界贡献。而中国传统“家法族规”蕴涵“家”的本位与立场,这有利于克服前述法治的现代性危机。
1.“家”强调关联,能防范利益个体松散社会团结。
社会本是由个体的人通过网状关系所构成的;而“家”天然地承载了这种社会关联的核心。“家”涵括了人生完整的场境,包括任何人从生到死的各阶段。因此,传统“家法族规”包含“照管老幼要用之资,男女婚嫁之给”,故而“吉凶筵席,送迎之仪”等皆有规则施行。[8]而西方主流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它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是基于崇尚“理性”,但这种“理性”仅是正常成年人理智的标准化,并不能涵盖人生各不同阶段或特殊人的特别状态,如幼儿时期、弱智者等。因此,西方自由理性的“同质化”考虑,虽然推崇平等,但很可能因竞争而忽视了社会的扶助和团结。以此而论,“家”在社会关联性上的“真实”,告诫我们法治理念中个体利益也绝不能替代和超越社会团结。
2.“家”基于情感,能防治理性计较消解精神归属。
归属感是人们构想出存在的意义,但理性更多地是在指导行动,理性运算往往应用事物的客观规律,不一定涉及人的主观意识。所以,人生存在的意义还需通过感性来充实,因为“存在感”主要源于情感的触动。“家”是人们情感的自然“聚集地”,因而,传统“家法族规”倡明,“亲族之间,休戚漠不动念”,“三党之中,皆与我有休戚相关之谊”。这样就能激发出美好的向往,所谓“上不负祖宗,下不欺比幽独,相爱相敬,风斯古也”。[9]相反,绝对的形式理性,将可能致使冰冷的法律规则控制我们生活的丰富。故而,传统“家法族规”讲求“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并强调“倘一端偶缺,即不得为完人”。[10]职是之故,法治愿景中应当容留对家的眷恋,使我们在严格的法律下精神仍有归属。
当然,现代中国已不是传统的身份社会,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基本上解散了宗族组织。然而,传统家族观念及模式或隐或显,仍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当下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啃老族”、“老乡观念”、春节团圆、春运现象、“家族企业”、家庭“个体户”等,这些都反映中国人难以消溶的“家族式思维”及社会组织的“拟家化”。虽然,我们并不是要恢复传统的“家法族规”,但其中“家”的价值观念,不仅实存于中国当今社会,而且它是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经济的、也是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差别,因而对于西方所提供的法治模版中的弊端有所补益。因此,积极地转化开新传统“家法族规”中立基于“家”的法治价值,这也是全球化视角下法治观念的中国式展开,其必将为现代法治理论的发展输送中国贡献。滋贺秀三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家族法“由于植根于人性,所以一面含有浓厚的适用于全人类的要素”。[11]10
(二)自治“解纷”机制:完善制度架构的法治中国化
“家法族规”相比于国家法制是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治理体系中“家法”与“国法”的二元性,即“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此文字出自《中湘下砂陈氏族谱》,转引自张佩国、刘立新:《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山东法学》,1997(2)。在这二元体制中,人们通过“家法族规”了解和接受国家法律;同时,传统“家法族规”所具有的化解纠纷、和谐社会、弘扬美德的功能,又能补充正式的国家法制之不足。正所谓,“治弼周官刑章,以佐典章之用;士遵祖训家法,以辅国法之行”。[12]
其实,不同于古典的“法治国家”论,现代法治体现为一个宏观方略和综合手段。它并不排斥与国家法之外的其它治理方式相结合;或者说,现代法治立场需要法律治理与其它方式的社会治理相得益彰,为一种“确定的规则之治”提供更多可行性和有效性。就此,西方理论产生了“社会法学”和“福利国家论”;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定强调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在上述意义上,传统治理二元结构中的“家法族规”,既具有中国传统性,又暗合于法治的现代性;而在中国法治的制度层面,对此的转化开新能以扬弃中国传统而助力于去西方移殖化。换言之,它应包含“传统的现代法制化”和“现代法制的中国化”两方面,这便有利于在制度架构的中国化上完善法治。
1.良性支撑社会自治
社会自治是法治民主的基石。一方面,“家法族规”可转化促成一种“道德型自治”的中国式现代民主。如果说,“权力强制型”的传统“家法族规”可能是反现代民主理念的,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已清除了这种强制权力的源头,政府公权不再直接地支持家族之长的权威。因此,家族之长需秉公处事、或顺应人情,才能得到家族成员的认可。换言之,如今,这一乡土权威的产生,是民众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制度的民主,必然具备规则的强制。而“家法族规”转化出的“道德型自治”中,存在一种规则的强制,这是一种由民间社会博弈的胜出者所形成的实力强制。他们更多地应合了干事勤劳、思维开阔、协调能力强等社会理想人格;而那些懒惰、保守、封闭的人,在现代生活中,自然成为被强制的弱势一方。其实,适当的道德性否定以及其所形成的强制,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机理。这是“家法族规”为法治中国的社会自治所提供的活水源头,相比通过普及外来观念来建构民主法治制度,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稳定性强的制度形成路径。
2.在国家司法领域以外化解纠纷
“家法族规”是区别于国家司法体系的纠纷裁决机制。它在中国历来着极强的存在合理性。尤其,传统社会“聚族而居,偶有嫌隙,即当禀白族正,公辨是非”,而“健讼公庭”则是“蓄怒构怨”,“从中唆使,是为小人之尤”。因此,“家法族规”往往适用普遍,在许多纠纷问题上,认为“与其身试官刑,孰若治以家法”。[10]这里蕴藏着多元社会矛盾化解的中国经验。对其进行制度性的现代转化,有利于救济现代司法理论上“不可诉”的权利,如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居住权等一些社会权。另外,在宪法及法律的底线内,积极运用民间调解、和解等国家司法外的纠纷化解手段,不仅节约了司法成本,而且可避免一些司法中不必要的权利冲突和司法后所出现的“不服裁判”、“二次侵害”等负面效果。
3.实现一些国家法律无法承担的执行效果
除了“纠纷裁决机制”之外,传统“家法族规”的转化还能在“执行效果机制”上配合国家法制。特别是对中国当下一些社会性法规,它能在落实立法意图上补强国家法律的缺失。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待违反俗称为“常回家看看”义务规范的处理,可借鉴传统“家法族规”中“孝道”的规范化,在社区民约或自治公约中形成现代孝道规范,进行执法效果支持。传统“家法族规”中借助习俗、道德、情感所形成的多元制约,能有效地伸入国家法强制力不宜涉足之地。正如,有些“族规”所直言,以“补足政府法令所不及为宗旨”。[3]同样地,在私法性的家庭暴力、子女体罚、亲人财产纠纷等问题上,国家法的“刚性”处理,往往陷于权利与情感的两难问题:判定了权利,却离散了亲情,即所谓的“赢了官司,输了家庭”。在判决执行中,如何弥补或恢复情感或精神性的伤害?从“家法族规”中吸收那些立基人伦亲情的规制经验,应能实现国家法律无法起到的执行良效。
总之,转化传统“家法族规”,在上述的基础、过程和结果三方面都极具现代法治意义。具体而言,这些现代转化是将中国社会中潜行规则进行规范化,并且以这些规范化的结果支持国家法制与社会自治的区划与配合,实现法治综合治理的良效。如果说,中国化和制度化是中国法治问题的一体两面;那么,“家法族规”的这种开新,在中西交融的视角下,它为提升中国法治的制度化程度优化了主要依靠移植的路径支持。
(三)家族“执罚”经验:丰富司法技巧的中国法治实践
纵观历史,司法权的渊源形式,指向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有普遍权威的第三方解决纠纷的基本方式。从此意义而言,“家法族规”中相关“执罚”现象,*费成康主编的《中国的家法族规》中设第五章“执罚”,包括“鸣告”、“裁断”和“执行”三节。本文采用了执罚这一广义的概念。与西方宗教裁判类似,其可视为具历史传统性的中国特殊“司法”型态。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家族司法”。*李交发教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家族司法”的概念。此后,其本人以及其研究生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主要可参见李交发:《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法商研究》,2002(4);《家族司法:古代和谐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设置》,《求索》,2008(8);原美林:《明清家族司法探析》,《法学研究》,2012(3)等。
在传统中国,所谓的“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之间相互关照,不仅前者仿照后者设立,而且后者为求实效更佳,亦对前者有所吸纳,突出表现在“情判法”的特质、“以和为贵”的判决理念、裁判文书的文学化等方面。可见,“国与家无二理也,治国与治家无二法也,有国法而后家法之准以立,有家法而后国法之用以通”。*此文字出自《桐城麻溪北氏族谱》,转引自李交发:《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法商研究》,2002(4)。
当代中国,家族司法的型态已经解体。我们对传统“家法族规”转化开新,不是要建构新的“家族司法”,而是基于文化与社会的认同去寻找更有效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司法技巧。譬如,传统“家族司法”裁断的主要场所是本族的宗祠,而非家族尊长的私宅,即称为“宗堂示罚”、“集祠处断”等。这是因为在祖辈神位前作出的裁判,就像代表了先祖的意志,视为祖宗的认可。因而,各宗族祭祀祖先的宗祠,又是审判族人的“公堂”。这里蕴含着增强心理服从的裁判技巧,可具体挖掘如何利用信念和观念认同,增进司法的权威性;如同西方类似的做法,是将某些宗教仪式合理化入诉讼制度(如证人宣示),以其中神圣情感促成法治信仰。当然,如何转化以及形成中国司法中的具体技艺,这需要更为专门而细致的研究。总之,从司法接受和文化传承理论而言,文化同根同源,能让传统“家法族规”为法治实践提示更多切合中国问题的处理经验,这也体现了中国法治中古今融通的视角。
三、“家法族规”的现代局限及其“封建”流毒的不利影响
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已然解散,聚族而居的生活形式也被城市化的进程冲击得丧失了大部分“领地”。随着这些传统“家法族规”生成背景的弥散,在当下中国,留给其还有多少的“生存土壤”?虽然,现在家族性现象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之势,如兴建传统家族制度象征符号的祠堂、祖墓、庙宇以及修订族谱等;甚至,有些家族聚居地区,兴起以宗族组织制定实为一种“新家族法”的自治约定。[13]12-13但是,此时此种的兴盛往往是局部和典型意义上的,而现代的中国因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散,的确已不复能够支撑一个体系化“家法族规”的全面建构了。因此,所要转化的现代法治意义,主要并不在于一种新“家法族规”的形成。“生存土壤”的流失造成了“家法族规”的现代局限,而它影响着转化开新的方式。
相对于“整体式”的转化,因为上述现代局限,“家法族规”是以“分解式”转化的方式,为当下中国法治提供效用的。前文已述“家法族规”三个层面的法治意义,而各层面都有转化上的限制:一是,观念性转化不宜进入“国家建立”的范畴,不应处理“权力来源”的问题。二是,制度性转化仅设定在法治社会的层次上予以配合,而再不能如从前,能轻易拉通国家法制,成为规范内部的前置程序。三是,司法性转化虽能直接进入国家法制,但只是一种技术层次上的借鉴,基本不具有体系和学理的意义。其实,这些限制性的转化,是传统“家法族规”在三方面分解其整体影响的结果。换言之,它的各层面中只有某些因素或方面才能转化出现代法治意义。
需要强调,“家法族规”的现代局限并不是否定其转化意义的重要性,因为“分解式”的转化方式,并不必然降低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就如同古老的中华法律体系早已荡然崩塌,却并不能阻断“传统法律的文明因子的静悄悄的绵延”。[14]另外,特别容易误解的是,转化层次中的局限是内容范围上的限制,而这并不是在缩小“家族法规”效用上的广泛性。例如,虽已不再受法律支持,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婚嫁丧葬活动,仍然极大地受到家族性传统的影响,尤其在当代中国人上溯二三代便会归宗的乡村老家,传统的家族规范还是重要的行事规则。
对待任何事物,我们都需要反思,上述的现代局限,其实讨论的还只是一种被限制的积极方面;然而,对于现代法治的转化,“家法族规”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需要警惕传统“家法族规”中所谓的一些“封建”留毒。历史主义法学认为,任何制度皆有历史背景,因而带有时代因素。这里,并非强调“今定胜古”的历史单线进化论,但古今各异,传统中势必存在某些悖反于现代的内容,它因而可能产生类似于过期霉变的当代影响。
第一,“家法族规”对人权法治的负面影响。传统“家法族规”的惩罚中,有许多措施带有人身羞辱性质;另外,还有的基于家族利益,甚至乱用私刑,这些做法都与现代人权理念不符;况且,一旦以身份规则强化了个人权利的从属地位,制度规则的滥用可能更加严重,也必将会产生更为恶劣的人权侵犯行为。
第二,“家法族规”对法治民主的负面影响。传统“家法族规”中,突出家族之长个人的管治地位;因而,在解决纠纷时,掺杂着浓重的个人意志性。此种家长式作风,若延续到现代司法领域,易造成司法长官意志独断的倾向。这将破坏由平等而达成司法共识的可能;而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些民主性的共识是现代法治的基础。无论如何,浓烈的“人治”倾向,不利于现代司法公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武陵郭氏续修族谱·公定规约[C]//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4]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李鼎楚.权利的“方法主义”与法学的“中国建构”[J].湘潭大学学报,2014(3).
[8]西山陈氏家谱·义门家法[C]//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9]上虞雁埠章氏宗谱·家训二十四则[C]//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10]盘谷高氏贵六公房谱·盘谷新七公家训[C]//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11][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湘阴狄氏家谱·家规[C]//费成康,等.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13]李侠.家法族规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4]李双元.中国法律理念的现代化[J].法学研究,1996(3).
责任编辑:立 早
On the Characters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abou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LI Ding-chu
(SchoolofAdministrativeLaw,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family laws and regulations refle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law culture of China specially, which sti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today.The author uses three points of view,which are 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past and present, to analyze law significance of China on legal senses, construction of system and judicial skills.However,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advantages of feudalism.
the family laws and regulations; loc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 in China
2016-07-21
李鼎楚(1980-),男,湖南新邵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理论法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清末民国法理学的‘中国表达’研究”(编号:12BFX020)阶段性成果。
K892.27
A
1001-5981(2016)05-01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