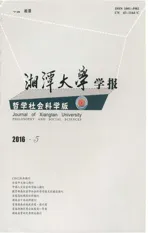行动者的鲁迅和鲁迅的行动哲学*
2016-02-21胡梅仙
胡梅仙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行动者的鲁迅和鲁迅的行动哲学*
胡梅仙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鲁迅的文字是其思想的行动,行动的艺术。鲁迅的行动性不仅包括他的活的关注现实的观点,而且包括他介入现实执着现实的一系列实践行动。鲁迅是真正把自由灌输在内心并且用行动作证的人。
鲁迅;行动;自由;行动哲学
一
文学家的柔情感性和战士的嬉笑怒骂、执戟上阵统括在独行的灵魂探索者身上,这就是用诗人、文学者的笔说战士的语言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把诗人比喻为“角剑之士”[1]102。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林语堂称之为“‘一个受了满身的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地胜利的‘武夫作家’(soldier-writer)”。[2]13增田涉把鲁迅称为“社会人”[3]149,以此与远离现实政治的其弟周作人相区别。鲁迅崇尚一种行动的语言,也就是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事务发言的权利。这种行动的语言除了反对用死的文言和不读中国书外,还表现为鲁迅一生执着的对于社会不满、永远反抗的姿势,也即是一种动的能力,一个知识分子对自我和社会能不断反省并赋予自己行动的能力。早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上就有一个署名为缪金源的写过一篇《第三段的革命》的文章,他说除了提倡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外,还应该提倡行为革命,也即是把言语、思想落实到行动。“行为革命是什么?就是务实在的事业,做实际的运动。再说一句老实话,就是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做‘跛和尚说法能说不能行’!”“若要改造社会,我们自己须得有绝俗遗世的魄力,我们须得敢于自用,我们须得不怕攻击责骂!打破了一切的旧习惯,废除了一切的假殷勤,得罪了一切的大人先生那才是我们能实现我们新思想的第一天。”[4]可以看出,对于行动的要求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呼唤。
从鲁迅的文字中,人们感到了想要行动想要参与到社会中去的欲望。应该说,必要的时候,行动是一种尊严和正义的诉求。躲在象牙塔里固然是为民族未来设计,没有现在又哪有未来;现在都朝不保夕,又何谈未来的美好前景。鲁迅是一个执着于现在,执着于地上的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5]591,如果没有烈士的流血牺牲,真会像鲁迅所说的不管是异族还是外国人都会“如入无人之境”。当代作家张承志对马尔克姆·X宝贵的血性有这样的体悟:“我镂骨铭心地觉得,若是没有这样的自尊、血性和做人的本能的话——人不如畜,无美可言。我不知人们是否接受如上的思想。我不知我们古老的中国,是否应该接受如上的思想。我只是感到,这是——自救的思想。”[6]93热血有时关乎尊严与正义,甚至比语言、优雅更重要。鲁迅从不赞成盲目的牺牲,他主张危险的时候“蛰伏”、“装死”,主张韧性的“壕堑战”,这就是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最韧性的战斗行动。
鲁迅所有的语言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启蒙。一直到1930年代,鲁迅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5]526鲁迅重视的是语言的动的能力,语言有时又会显得无力。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时代,需要一种强烈有效的行动来给一个民族灌输新鲜的活力和生机,而不是躲进实验室去。在这个时候,行动的速度会更见成效。另一方面,鲁迅希望国人摆脱死相。要表现出一幅生机民族的面孔,首先应从思想的解放开始,从外国书中寻找解放自己的思想和动力。所以,鲁迅既是愤激又无不是发自心底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7]12除了提倡少看中国书外,鲁迅一生作为一个战士的面目可以说是他行动的最好证明,而他的杂文就是一篇篇战斗的檄文,不仅是战斗的,更是深思的,文学的。甚至可以大胆地说,鲁迅的杂文的意义并不亚于他早期的小说、散文,无论是在启蒙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学审美的意义上。通读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鲁迅也说过他写文章都是熬出来的,不是灵感的一泻千里,是靠挤。是这种挤牙膏的功夫使鲁迅的文字凝练、含蓄、充满文字的质感和美感。甚至,我们从鲁迅杂文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生活的节奏和走路的声音,这是一种新的美文,战斗的又是文学的美文。鲁迅因战斗的需要创造了这种文体,除了杂文的文体意义外,鲁迅杂文表现出的文字功夫、语言美感、深刻思想构成了其杂文的永恒价值。我可以想象到,这种杂文的写作比小说诗歌更费时间和精神。鲁迅的杂文没有敷衍之作,有些名篇可以成为千古经典之作。当我每次看《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时,都会感动。诗人的真诚热血和战士的正义勇气所挟带着的鲁迅心灵实感和暴风雨一样隐晦的力量使鲁迅的大多数作品沉郁顿挫,在血和泪中,我们体会到了鲁迅的坚韧和无奈。鲁迅自陈:“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5]4当段祺瑞政府枪杀学生时,鲁迅曾震惊于“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当他看到国民党杀人的时候,他本是支持国民党的,也不得不吓得目瞪口呆了。特别是当牺牲的是他的学生、朋友、熟人时,再怎么样的道理都掩盖不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广州清党时,当时被杀的中山大学的学生毕磊就是鲁迅的学生。鲁迅自己躲在广州的白云楼上半年,趁着没人注意时才溜到上海。对于左联五烈士,鲁迅与其中几个都认识,特别是和他走路几乎是“扶住我”的柔石,鲁迅笔墨最多。在《北斗》创刊时,鲁迅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为了纪念柔石的失明的母亲悲哀地献出他的儿子的眷眷的心的。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先是赶往出事地点,继而又冒着生命危险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归来后,鲁迅沉重地写下了《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8]467杨杏佛被国民党杀害的时候,据许广平记忆,鲁迅出门参加杨的追悼大会时未带钥匙,是不准备回来的。特别是当枪炮对准自己的熟人时,鲁迅的沉痛是最深的了。这时候,任何所谓的法则、制度都无法疏解那种来自于残酷的现实的血的悲哀。所以,不管鲁迅是在当时北洋军阀手下做教育部的小官,还是后来经蔡元培的推荐拿着国民党的津贴,只要看到了蹂躏、压迫,鲁迅不会止住他的正义的呼吁呐喊。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气魄和心胸。他决不会因为几斗米而折腰,而且,在他们还未对一个政权真正地失望之前,他们认为批评政府是为了政府好。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就是因为他们反对假道学监督夏震武而集体辞职。这次“木瓜之役”胜利之后,许寿裳到了北京译学馆,鲁迅也决然回归故乡。在绍兴办《越铎日报》时,他们的主调就是骂,骂是为了革命政府好。孙伏园回忆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9]34孙伏园那时因为写了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章而得到鲁迅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评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早期对于学生关注现实、敢于发言的重视和培养。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7]279,这是一个近似真理的原则,然而生命与鲜血、自由与革命有时似乎又是对抗的。这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鲁迅,对民众生存的关注和对个体自由的彻底不妥协的追求,珍视鲜血又不肯放松的战斗意志,这些都奇妙地结合在鲁迅身上。鲁迅自己也曾说“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10]226。也许正是这样,我们由此看到了历史的曲折复杂是怎样真实地反映在鲁迅的文字和行动中。
在厦门时,鲁迅作过“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他认为多读中国书的弊病有三点:使人意志不振作;使人但求平稳,不肯冒险;使人思想模糊,是非不分。他劝大家做好事之徒,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之人,才会有改革变动,推陈出新。做好事之徒不容易,万一做不到,至少我们不能随俗加以笑骂,特别是对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讥笑轻蔑。在这里,鲁迅鼓励青年关注社会现实,不读死书,仍是把读中国书与社会行动相对立。鲁迅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改革的动的时代,青年再不能像古时的士大夫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全书”了,要投身社会实践,向社会发言。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在厦门时期,鲁迅已困倦于和章士钊的拥护者们的斗争,只想静下来好好地教书,做研究两年。没想到积习难改,在厦门的几次演讲都被校领导视为危险人物,传说学校的风潮也是因之而起。在谈到厦门的演讲时,鲁迅曾给李小峰的信中说:“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7]419可以想见,像鲁迅这种带有行动倾向的思想是决不可能为中庸保守的学校当局认可的。而鲁迅就是要做这样一个敢于搅动的人,他就像疾风暴雨,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动的时代,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唤起铁屋里沉睡的人们。1927年1月25日,在中山大学学生会的欢迎会上,鲁迅又重申:“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11]83在香港,鲁迅作了“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他鼓励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5]15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鲁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今民众的生存毫无关系,所以是无益的。他鼓励青年跨出房门,走向社会;其次是自己想想,想到就做。据何思源回忆:针对中山大学领导在校内主张蒋党的党化教育,限制学生的研究、活动、组织自由,鲁迅对朱家骅说:“‘五四’时代学生活动,是反对旧有的北洋军阀。现在学生的进步活动,则防止新的封建统治。三大政策就是防备军阀统治的再起。”[12]1651927年3月1日在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鲁迅作了关于读书与革命的演说,他要求学生一面读书,一面革命,把个人与社会命运结合起来。
二
鲁迅的文字是其思想的行动,行动的艺术。鲁迅的行动性不仅包括他的活的关注现实的观点,而且包括他介入现实执着现实的一系列实践行动。行动化入他的作品,表现为作品又呼唤着自我的挺身的战斗。特别是在鲁迅的杂文里,让人感到人是需要行动的。
行动的文字与鲁迅的自由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鲁迅是真正把自由灌输在内心并且用行动作证的人。除了内心坚韧的独立意志外,把自己的自由意志灌输在行动中来验证,更需要勇气和胆魄。这与自由主义理念要与公共领域紧密相联接近,鲁迅的思想重在要影响当时的社会、个人,不做象牙塔里的绅士或者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雅士。林语堂在《悼鲁迅》中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13]96林语堂一方面说出了鲁迅好战的一面,另一方面似乎不懂鲁迅为什么好战。不管是独战的悲哀还是横站着战斗的腹背受敌,只有鲁迅才明白他的职责就是反抗一切强权专制,并承担这一切所带来的攻击毁谤。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说:“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14]620所至与人冲突可看到鲁迅与几乎全社会的对立,这种对立是鲁迅自己的抉择。像梁实秋那样崇尚古典稳重的人是不可能理解鲁迅的不满、反抗,以致把自己推向孤身一人的境地的。何况鲁迅也并不觉得自己的反抗只有碰壁的倒霉,而没有感到,“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7]4不过鲁迅决不像梁实秋所说是没路走了才“鬻文为生”,对于是写作还是教书,鲁迅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写作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自己与实社会真正地联系起来,实现自己用文艺改造国民的思想。教书无疑会影响写作,鲁迅甚至认为写作和教书是冲突的,并且透露出自己今后决定选择写作。他在对许广平信中说,他之所以不愿到燕大教书,“只因为不愿意做教员”[15]175。在同一年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披露了同样的意思:“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15]67就像王富仁所说:“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上海的亭子间,是因为学院派关心的更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更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更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16]180鲁迅的选择和决定做某一件事其本身是一种思想的行动。鲁迅用彻底的反抗证明了他的绝对自由。人的自由是通过人的自由选择与行动、承担被赋予意义的。自称鲁迅学生的巴金曾经认为写作不是为了文学,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同样,鲁迅的写作也是为了生存、生活、斗争而写作,是为了去探究一种生活的真理、出路而写作。这样带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写作加上鲁迅天生的文学家的才能,是鲁迅作品处于一种复杂的既是政治的也是非政治的,既是文学的又并非“为文学”的状态中。这也是一些人称鲁迅为启蒙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又有一些人称鲁迅为自由主义者的原因。其实这样的界定往往有忽略历史现实复杂性的倾向,最多也是为了阐述的需要。而我们在阐述时,往往把历史简单化抽象化。历史就像文学,是感性的;也像人的品性,是有灵性的,因此是复杂的。只有把鲁迅置于历史的复杂情景中,给予鲁迅的思想、写作、行为一个历史、人性化的阐释,才能理解鲁迅的行动,理解鲁迅为什么选择了寂寞中的呐喊,后又参加了左联。一个社会需要身先士卒的人,鲁迅希望用自己的笔、自己的身躯去做这样一件关乎人的生存、尊严、自由的神圣的事业,他宁愿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到宽阔的天地中去。
有些人说鲁迅是厌世家,虚无主义者,这种说法是一种表面之谈。真正的厌世家、虚无主义者即使不像奥勃洛摩夫一样颓唐堕落、无所事事,至少也不会像鲁迅那样“拼命地做”。一个热衷于把自己投入社会中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所谓的虚无只是他所思考的形而上的问题。萨特曾说:“希望存在于行动的性质本身之中。那就是说,行动同时也是希望。”[17]102这种对于行动的渴望一方面来自于现实斗争呐喊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鲁迅的一系列无畏的行动也构成了一个诗人的鲁迅。诗人和战士,思想家和呐喊者,这在鲁迅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鲁迅希望可以通过语言来激励行动,或者让语言本身成为一种行动的力。唐弢作为一个和鲁迅有过接触的杂文家,对于周作人称鲁迅“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看来,这一转,是莫须有的。鲁迅先生相信自己,也相信中国的人民,那信心,永不动摇。只有对于另一群人,对于在这另一群人手里的中国的前途,他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论者。”[18]99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尤为推崇拜伦、雪莱、裴多菲等这些以行动践履自己思想的诗人。“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1]68鲁迅反对空谈,崇尚行动;注重作品有无激发民众行动起来的力量,注重作品本身充满的活力和行动的欲望。鲁迅也知道反抗、行动起来的人是为世人所不喜不容的,可是,鲁迅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世人所不喜的反抗者撒旦。恶魔撒旦的反抗、坚韧魔性正是鲁迅所倾心的,所以他称拜伦们为摩罗诗人。鲁迅当时之所以特别喜欢并介绍这些诗人,是因为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1]68
反抗是一种有声的有激烈动作的行动。行动本身包括一切有声无声的行为,一切有动作无动作的行为。总之,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有着动的愿望与趋势的一切文字和行动,而不是死的文字或者是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和事不关己。反抗对于鲁迅一生的行动意味着什么?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动的动作。不管是来自于内心的愤懑还是文字的表达还是行动本身的实践参与,反抗本身就喻含着行动的欲望。所以说,鲁迅一生都是动的。从日本时期参加光复会,到回国兴致勃勃地参与民国教育部各种事物,到五四的呐喊,五四落潮后的彷徨,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参加左联。可知,鲁迅的一生都是在社会的潮流中行动着的。除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后的几年,他沉浸于研佛学、抄古碑外,鲁迅的一生都是一个热血的参与社会改革实践的启蒙家。文字只是鲁迅行动的一方面,鲁迅在《新青年》上一发不可收的启蒙式的创作,办杂志《新生》《语丝》《莽原》等,维护女师大学生利益被章士钊开除,抗议章士钊的政府欺压行为和章士钊打官司,和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创造社的论争,为左联五烈士写的纪念文章以及参加左联期间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等。可看出鲁迅一生是用行动来践约着自己的文字,同时他的行动本身辉耀了他的语言或者说他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鲁迅的语言和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中表现着行动的趋势,行动中践约着他的语言的勇气和不屈。当鲁迅被通缉仍然写着揭露反抗的文字,当他不带钥匙去参加杨铨的葬礼不准备回来时,鲁迅的行为形成了对他的语言思想的高度融合,在这个时候,鲁迅的战斗的语言和他的视死如归的行为熔铸成了一篇最壮丽的诗篇。闻一多说过:“只要奇迹露一面,我即刻抛弃平凡。”奇迹就是赴死的机会,鲁迅无数次在死的危险面前仍然不屈服地动着他的那只“金不换”笔,而在一次次地逃脱危险中完成了他的不平凡。
就在鲁迅死前不久写的《这也是生活》中,他说“我有动作的欲望”,“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19]624在鲁迅感到自己即将要离这世界而去的时候,他仍有一种“动作的欲望”,可以看出行动对于鲁迅一生的意义。其远胜于诗歌、小说、杂文等文字,甚至比他的批判国民性思想更能给我们树立一个真正地身体力行的诗人和战士形象。此时,鲁迅内心的目光仍然关注的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认为都与他有关。这是一种博大的将世人容纳入心的胸怀,表现出了作为战士的鲁迅在生死一线中对于世间的无穷热爱,也即是对于光明和希望的热爱和坚信。那些他平常所说的“忽而憎人”、“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的话看来不过是愤激或者失意之时的语言。有岛武郎说:“生艺术的胎是爱。除此以外,再没有生艺术的胎了。有人以为‘真’生艺术。然而真所生的是真理。说真理即是艺术,是不行的。真得了生命而动的时候,真即变而成爱。这爱之所生的,乃是艺术。”[20]81“真得了生命而动的时候,真即变而成爱”,意即艺术要获得生命的动,才能变成爱。可知,爱与生命的动的关系。当我们赋予生命以灵性、以动感、以行动,生命才能显现出爱的意味,爱即构成了艺术,也即艺术是爱赋予生命的动态的表现。从爱到“生命而动”再到艺术的表现,这很符合鲁迅一生的创作和行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在病危之际怀念的是无穷远方和无数人们。作为战士的鲁迅,最终在他心中驻足的是人类的生存、自由、前行的脚步和与他相关的无数人的喜怒哀乐,痛苦幸福。
有的人愿意把自己更密切地与社会实践相联系,让自己的力量直接快速地散发给民众,特别是像鲁迅这样立志于终身唤醒大众的启蒙家,参与社会潮流中给民众以鼓舞和呐喊也是势在必然。有人把鲁迅后来加入左联说成是鲁迅投降了,当时的上海小报就有这样的说法*有关鲁迅投降之说,最早见于“革命文学”论争期间的创造社,1928年5月30日《流沙》半月刊第6期,登载过一篇氓(李一氓)的《游击·鲁迅投降了》。后来一些上海小报也持续传播这类说法,如1929年8月19日《真报》所载署名“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便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不是投降的意味”。左联成立后,1930年5月7日的《民国日报》亦刊登了一篇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称创造社诸人“为了要将中国文艺界,统一在共产党政治主张之下”,先对鲁迅“下总攻击”。鲁迅被创造社先打压后拉拢,同时也满足了鲁迅“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的需要。参见:张宁:《无数人们与无数远方:鲁迅与左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5页。,现在仍有这样的结论。关于鲁迅的转变和没转变之争,其实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既可以说鲁迅的信仰有转变的成分,也可以说鲁迅的反抗、为弱者贫者呐喊、争取自由的精神是一贯的。转变和没转变只是每个人看鲁迅的角度不同。信仰和精神是不同的。信仰有时显得遥远,比如鲁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精神却是内在于人的本质的,比信仰更关乎人的日常行为、现实想法。这无疑是对鲁迅一生思想轨迹的不理解。如果鲁迅不想在共产主义信仰中找到自己在现世找不到的路,鲁迅决不会加入左联。至于左联让鲁迅失望了,那是以后的事,鲁迅也以自己与左联领导的闹翻表示了自己对左联专制的不满。在一个世界性向左转的思潮中,鲁迅想去寻觅别一种的中国从未走过的路也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鲁迅一直在寻找,在用自己的行动表示着自己对现实的关切与参与。
当代学者薛毅有这样一段表述鲁迅的话:“充分估计历史和现实残酷的强度,丝毫不冲淡和减弱它,因而不认为历史和恶在现世能终结,所以他能忍受残酷现实的打击;他不认为未来一定是黄金世界,所以他身上去除了浅薄的乐观主义。总之,综合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特征,并以此洞见未来可能持续的黑暗,使他在对世界的观念上去除了现世主义,而穿透了过去和未来。”[21]148我们也可从这段话中来理解鲁迅作品的行动意义。张承志是最能体现鲁迅思想精髓的当代作家,即是强调一种融合热血、正义、切实的人生表达形式,在这种热血的流淌中,在诗意的抗争和战士的投枪中,寻找人生的尊严和不屈服。如果说文学是躺着的静静流着的河水,那么鲁迅、张承志则希望他们的文学是大海中的巨浪,巨浪中的海燕。同时,这并不表示他们的作品是浮在海面上的,正是因为有深不可测的海底,才有海面上震撼人心的巨浪。
[1]鲁迅.摩罗诗力说[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林语堂,鲁迅.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G]//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增田涉,鲁迅的印象[G]//鲁迅研究资料.杭州: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供内部参考),1977年11月.
[4]缪金源.北京大学学生周刊[J].第7号(1920-02-25).
[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张承志.清洁的精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7]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悼杨铨[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孙伏园.忆鲁迅先生[M]//子通,主编.鲁迅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10]鲁迅.关于知识阶级[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1]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讲演[M]//鲁迅演讲全集.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
[12]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情况[G]//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林语堂.悼鲁迅[J]宇宙风.第32期(1937-01-01).
[14]梁实秋.关于鲁迅[M]//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5]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G]//陈漱渝,主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17](法)让·保罗·萨特.他人就是地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8]唐弢.记鲁迅先生[G]//子通,主编.鲁迅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19]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0]有岛武郎.生艺术的胎[G]//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丸山升,著.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薛毅.无词的言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万莲姣
Lu Xun as an Actor and Lu Xun’s Philosophy of Action
HU Mei-xian
(LiteraryThoughtResearchCenter,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
Lu Xun’s words is the action of his thought and the art being created from his action.Lu Xun’action not only includes his living concern to reality ,but also includes his series of practice intervene into the reality with dedication to the actuality.Lu Xun is filled with freedom and testified for the freedom with his action.
Lu Xun; action; freedom;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
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特辑
2016-06-08
胡梅仙(1969-),女,湖北咸宁市赤壁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5FZW059)。
I210
A
1001-5981(2016)05-01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