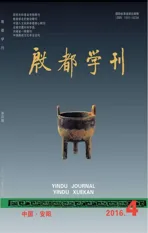《国语》诸“语”思想探析
2016-02-02仇利萍
仇利萍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国语》诸“语”思想探析
仇利萍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国语》以国别形式分述八国片段史事,每国一语,诸“语”以记言为主,有侧重地收录了各国国君、臣子或大夫间的对话或议论,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经济、礼制、哲学、宗教等问题的看法,同时也流露出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集中体现为天人观念、礼乐观念、伦理观念、经济思想及军事思想5个方面,不但反映了先秦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更重要的是后世的继承与纳新,为其后出现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国语》;诸语思想;百家争鸣
《国语》以国别形式分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8国片段史事,各部分史料来源不一、内容详略不同,时间断限也不尽一致,所以很难对其思想做出总体评价。但因《国语》诸“语”以记言为主,编撰者有选择、有侧重地收录了各国国君、臣子或大夫间的对话或议论,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经济、礼制、道德、哲学、宗教等问题的看法,同时也流露出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
在《国语》所叙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之际的数百年历史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王权由极盛逐渐走向衰微,政治制度开始出现新因素,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开始有所变动。折射到文化层面,则表现为:“天”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人的因素受到重视,礼乐制度的伦理化与政治化,人际关系与伦理制度逐渐由政治化而社会化等。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国语》诸“语”除了蕴含后来的儒家思想外,还出现了法家、道家、墨家等诸家观点的萌芽,可谓不拘一格,为之后出现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以下分别详细阐述:
一、天人观
“天”,有天道与天命两种说法,此二者的区别在于“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1]说明“天道”是指自然界中万物发展的规律,而“天命”则指上天的旨意或命令。此处涉及到的天人观特指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两者的结合来自于人君。他即是上天旨意或命令的传达者,又是人间实际的统治者,处于沟通天与人事的枢纽地位(天—人君—人事),因此要想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拥有天下,其就必须处理好天命与人事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天人观念也有所改变,不同的时代被人们赋予不同的内涵。在西周以前,天被视为最高的人格神,《尚书·泰誓》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2]可以支配和操纵人君和人事,具有至高的权威。在这一时期,天命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人们(特别是人君)对其持默认和敬畏的态度。但时至周,社会发生的剧烈变革带给了人们强烈的震撼,也冲击了他们默认的天人观念。周人开始意识到“天命靡常”,遂“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3]但人君(统治者)并不否认天命对于国家兴衰的左右,《吴语》与《越语》中“国之存亡,天命也”的思想仍有较多流露,较之殷人的进步是他们认识到人事的重要性,并开始注意调和民神关系。其作法是赋予天以道德*《吕刑》有言“惟克天德”,“天德”即上天立下的道德准则,上天以此为标准衡量君主统治的好坏,以此达到民意通神、神意通天,民神相通以顺天命。的意义,使其具有惩善罚恶、明辨是非的特性,如《周语中》单襄公云:“天道赏善而罚淫”,《晋语六》中范文子云:“天道无亲,唯德是授”。上天虽能降福祸于人事,但以人君是否有德为转移,因而能否得到上天的支援,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完全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有德。此时,“天”的神性逐渐淡化,人事的地位开始上升,人与天靠着德行统一起来,这是天至上观念转变的第一步。
此外,《国语》诸“语”中常把“民”与“天神”放在同等的位置,如《周语上》载内史过之论:“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4]当政者只有重德亲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基于这种认知,《国语》中也有较多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进行过度剥削的表述,如《楚语上》言:“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5]这种将“敬天”与“保民”思想相结合,是周人政治思想及其道德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其政治思想道德化的结果。
由上可见,“敬天”、“保民”与“修德”三者结合形成了西周初期新的天命思想,这也是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礼乐观
郭沫若先生曾提到:“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5]精辟概括了从部落氏族时代到西周时期礼乐思想的发展过程;更进一步讲,是突出了礼乐的下移及社会化,这在《国语》诸“语”中多有表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人们认识的深入,礼的功能已从祭祀天神的单一模式转型为处理个人、家庭及社会的行为规范,人们对“礼”的关注也从“形式性”转到“合理性”、“伦理性”。《国语》中的礼乐思想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正名。“名”就是名分,它反映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体现的是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强调正名是为了让人正视自己名分,达到规范人们等级意识的目的。主要包含:其一,对个人礼制行为的反思。如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知礼守礼,“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在与晚辈交谈、参加祭祀活动时,严格遵守礼法,后孔子赞其“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其二,在是非评判过程中对礼乐的阐述。如《鲁语上》关于晋人杀死晋厉公的讨论,里革认为:“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4]认为国君被杀,在于其放弃礼制,失去威仪,有其合理性。其三,对周天子、诸侯国君及卿大夫僭越礼制的劝谏。如《周语上》载密康公娶同姓女子三人,违背了礼制,其母以“小丑备物,终必亡”进行劝告,密康公不从,后被周恭王所灭。又如《鲁语下》载楚公子围以大夫之名参加虢之会,却用国君的仪卫,僭越了国君之礼。
第二,礼政。《国语》中所提到的“正名”,多是与君主、卿大夫等社会上层有关,编撰者所突出的是“礼乐”与封建统治秩序的密切关系,也即后来孔子所谓的从“正名”角度来反映治国以礼的思想,“把宗法—封建秩序合礼化的理论努力,通过这一时期的‘礼’的观念的发展而充分体现出来。”[6]如《晋语四》载负羁劝谏曹伯之语:“臣闻之:爱亲明贤,政之干也。礼宾矜穷,礼之宗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4]这就使得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发生了一种由“仪”向“义”的转变,从礼仪、礼乐到礼义、礼政的变化,强调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的意义。从而,“礼”越来越被政治化、伦理化,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一般的礼典仪式,而是把礼的要义、礼的精神揭示出来。
礼乐思想作为政治原则被有变化的保留下来,标准已经不再是僵化的了,常常会因关注现实生活而做出恰当的调整。相对而言,礼乐仪制方面渐渐衰落,所以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礼的仪节已不完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花相当大的努力来学习、搜集、研治古礼,《仪礼》的问世与此应有较大关系。
三、伦理观
在宗法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妇”五种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但春秋社会变革时代,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君臣”关系及相应的伦理秩序,这也屡见于《国语》诸“语”。
古代的伦理思想,往往是作为先王之礼、先王之制的主要内容被提出来的。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又称先王之训、先王之令、先王之教、先王之言。《国语》中在提到这类思想观念时,总是追根溯源,引据先王之礼、先王之制,侧重于伦理原则方面的阐述。例如:《晋语一》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又《晋语四》曰:“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4]强调臣事君要忠信不贰,君示臣好恶不易,君有君的原则,臣有臣的原则;若“为君不君,为臣不臣”,则“乱之本也”。这就是所谓的“君臣”之道。西周至春秋前期,君臣的秩序还较为严整。《周语上》载樊仲山父谏阻周宣王废长立少之举,多次提到“顺”*顺为顺德,表示统治—服从关系的有序和顺遂。参见陈直:《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其言:“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此外,君臣秩序的严整还体现在君对臣民的威权性上,如《晋语八》载阳毕言:“图在明训,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是遂威尔远权。”[4]
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国语》中对君臣之道的具体内容和表现也有所阐述。如《周语中》刘康公言:“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晋语九》史黯言:“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才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4]又《楚语下》员讼则言:“夫事君者,不为外内行,不为丰约举,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敌以下则有雠。非是不雠。下虐上为弒,上虐下为讨,而况君乎!君而讨臣,何雠之为?若皆雠君,则何上下之有乎?”[4]强调为君者要重民修德、知人善任、纳谏自省,而为臣者则要俭以养德、举贤任能、善于劝谏。
《国语》中虽然有不少的思想精华,但也有许多的思想糟粕。此处所宣扬的君臣关系,着力强调的是下对于上的服从和上对于下的命令,这和前文所指出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是极不合拍的,体现了在封建统治立场下对于君臣合理关系的一种追溯。
四、经济观
在《国语》一书中,除了和天人、礼乐、伦理有关的儒家思想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国语》诸“语”所反映的经济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有分工理念和尚节俭的理念。
第一,分工理念。《周语上》载内史过的分工理论:天子“教民事君”,诸侯“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与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士、商则“个守其业以共其上”。这种分工概念,和《鲁语下》所提到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一样,都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划分的,而庶人、士、工商之类的被统治阶级只能是守其业。另有,《齐语》中还记载了管仲把被统治阶级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并指出了这种分工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管仲按各阶层的专业将他们分居在固定的地区,并使职业得以世代相传,这样做的好处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而做到“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和“相陈以知贾”。管仲制定并推行的分业定居之举,不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也造就了春秋时代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现实。
第二,尚节俭的理念。提倡节俭是《国语》中所体现的重要治政思想之一。《周语中》记载周王朝卿士刘康公奉命礼聘鲁国,回国后便将自己的见闻报告给周定王,其言:“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又言“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若是则必亡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因此预言“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果然,过了八年,“鲁宣公卒。赴者未及,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
《国语》诸“语”中的分工、尚俭、反专利等经济思想,与后世的墨家思想多有谋和之处,细究可察其思想源流。
五、军事观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国语》诸“语”在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战争的一些看法,从中可以对那个时代的军事思想有所了解。
首先,《国语》中对战争是持否定态度的。《周语上》载祭公谋父之说:“先王耀德不观兵……无勤民于远”,[4]谏阻周穆王对犬戎的征伐;又《晋语九》载董安于拒绝赵简子对下邑之战战功的奖赏,言:“……及臣之长也,端委韠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与战功相比,董安于认为自己的政绩更值得嘉奖,其更视战争为“狂疾”,以战功获赏为辱。
其次,《国语》中所论多为对外战争,且以备战阶段为重,突出了发动战争的慎重性和周密性。这在《吴语》所载越王勾践与楚使申包胥的对话中有很好的体现,其中提到了勾践为和吴国作战所做的准备,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其一,安内、睦邻是进行对外战争的基础。其中,“安内”不仅是指君臣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君民的关系。如“在孤之侧者,觞酒、豆肉、箪食,未尝敢不分也。饮食不致味,听乐不尽声,求以报吴。”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让臣下甘心为君主而战,继而“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越国之中,吾宽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越国之中,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使贫富皆利之”。安富济贫,关心民众疾苦,调整为政者与国人的关系,以无后顾之忧。再者,“越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愿以此战。”[4]搞好与邻国、强国的关系。此外,爲了提高战斗力量,士卒也须经过严格筛选,凡是“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有眩瞀之疾者”、“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皆被淘汰。其二,严明军纪。在以上基础上,勾践又征求五个近臣的意见,形成“审赏”、“审罚”、“审物”、“审备”、“审声”的作战策略,并对“以环瑱通相问者”、“不从其伍之令者”、“淫逸不可禁者”进行严厉惩罚,以严格纪律。其三,选择有利的时机。《越语下》载“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成功”,古时作战讲求时机,认为只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结合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勾践灭吴的经过即是有效例证。勾践从吴国返回后的第四年就想攻打吴国雪耻,范蠡认为不具备伐吴的条件;又一年,吴王淫逸无度造成内政混乱,范蠡认为“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又一年,吴王杀死忠臣申胥,范蠡认为“天地未形”,越国还需要等待;又一年,吴国出现自然灾害,“稻蟹不遗种”,勾践想趁机出兵,但范蠡认为“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时机终于成熟,范蠡认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出兵攻打吴国。在作战过程中,范蠡仍然坚持进退有度,“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驻军三年,最终灭掉吴国。
此外,《周语中》记载了崤之战中秦军偷袭郑国的事例,王孙满观察秦军行为后作出推断:“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最终,秦军大败而归。据此,还总结出了“骄兵必败”的战争规律。
《国语》中涉及军事思想的篇幅虽然不多,但这些思想和战国时代出现的一些军事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对后来的诸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之类的兵家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尽管儒家思想萌芽占据主导,但它不是《国语》思想的全部。《国语》诸“语”所涉思想包含有后世百家思想中的部分精华,并客观地体现出来,其不但反映了先秦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更重要的是后世的继承与纳新,得以不断延伸它的影响。
[1]程颖,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
[3]孙希旦撰.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郭沫若.十批判书[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6]陈直.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郭昱]
2016-09-11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语》诸语思想探析”(2015-QN-241)的研究成果。
仇利萍,女,河南南乐县人,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与先秦史研究。
K204
A
1001-0238(2016)04-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