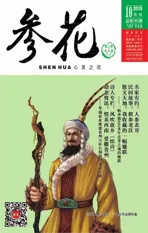从汉字“姑、舅”透视我国古代的互婚制度
2015-10-27孙永兰
◎孙永兰
从汉字“姑、舅”透视我国古代的互婚制度
◎孙永兰
从现代意义上说,“姑”“舅”二字只是单纯的亲属称谓词,但在古代汉语中,“姑”“舅”作为亲属称谓词,其意义却比现代宽泛。“姑”除指父亲的姊妹外,又为媳妇对婆婆的称呼。按照今人的观念来理解,“姑”“舅”作为亲属称谓的一名多用似乎是不合常礼的,但这恰恰是它们丰富的文化蕴涵之所在,为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探寻古代的婚姻习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婚姻习俗 互婚制度 姑 舅 媾
婚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基础,是组成家庭的必备条件。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祭丧,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关于婚姻的意义,《礼记·昏义》又说:“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一定的婚姻形式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定的制度和观念的具体表现。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婚姻。不同时期的婚姻,有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不论是群婚制、偶婚制,还是一夫一妻制,男婚女嫁都是人生经历的必要过程。汉字作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自然会记录下远古人类婚姻家庭诸方面的情况。今天,通过分析这些汉字,会使我们探寻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化信息。
从现代意义上说,“姑”“舅”二字只是单纯的亲属称谓词:“姑”指父亲的姊妹,“舅”指母亲的兄弟,这是人人皆知的。但在古代汉语中,“姑”“舅”作为亲属称谓词,其意义却比现代宽泛。“姑”除指父亲的姊妹外,又为媳妇对婆婆的称呼,《说文》:“姑,夫母也。”《尔雅·释亲》:“(妇)称夫之母曰姑”。《国语·鲁语下》:“吾闻之先姑。”韦昭注:“夫之母曰姑,殁曰先。”亦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礼记·坊记》:“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郑玄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尔雅·释亲》“妻之母为外姑。”“舅”除指母亲的兄弟外,又是媳妇对公公的称呼,《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礼记·檀弓下》:“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郑玄注:“夫之父曰舅。”《南史·徐蓠传》:“晋宋以来,初昏三日,妇拜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晚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亦为女婿对岳父的称呼。《礼记·坊记》:“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郑玄注:“舅姑,妻之父母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裴松之注:“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称之舅也。”《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舅。”
按照今人的观念来理解,“姑”“舅”作为亲属称谓的一名多用似乎是不合常礼的,但这恰恰是它们丰富的文化蕴涵之所在,为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探寻古代的婚姻习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理论上说,亲属称谓是亲属制度的产物,某种亲属称谓总体反映了某种相应的现实亲属关系。因此,“姑”“舅”一名三用的历史,似乎表明,中国古代社会曾具有这样一种常见的亲属关系:对一个丈夫来说,岳父往往就是自己的舅舅,岳母往往就是自己的姑姑;而对一个妻子来说,公公往往就是自己的舅舅,婆婆往往也是自己的姑姑。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目前还难以找到证明这种亲属关系确曾作为一种制度而普遍存在的史实依据。但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亲属关系的存在。道理很简单,亲属称谓虽然本从相应的亲属制度中产生,但其一旦形成,却可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亲属称谓并不一定同相应的亲属制度相一致。而这种差异最明显最常见的即是亲属称谓的变化往往要落后于亲属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姑”“舅”这种亲属称谓很可能反映的是中国史前先民的亲属关系。
那么,在史前古代社会中有没有可能具有由“姑”“舅”一名三用的亲属称谓所显示的亲属关系呢?综合各种情况来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在人类原始婚姻制度中,有一种很常见的婚姻形式,即原始族外婚中的固定族团互婚。所谓固定族团互婚,就是甲、乙两族男女互为通婚对象而世代相互嫁娶。这就是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所说的人类婚姻的第二阶段——伙婚制。澳洲土著人即通行这种婚姻形式,“部落都划分为两个半边,它们之间互通婚姻,而在每一个半边内部则禁止通婚。”(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国人民》,三联书店,1980年版,上册第196页)在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中,对澳洲的固定族团互婚则有更详细的介绍。我国纳西族早期亦采取此种婚姻形式,“纳西族称氏族为‘尔’,传说他们早期只有六个尔,每两尔为一组,如西与胡、牙与峨、布与搓,互为半边,彼此通婚,组成一个原始部落。”(《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而这种甲、乙两族同辈男女世代互婚的婚姻形式只需延续两代,就将导致姑为婆、婆舅为公,或姑为岳母、舅为岳父的亲属关系。
显然,从“姑”“舅”一名三用的语言遗迹,我们可以推断固定族团互婚这种较为普遍的原始婚姻形式确曾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从婚姻习俗传承角度看,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此可由“媾”字窥见。“媾”之初文为“冓”,以象征生殖的二鱼相对形象构成,后加“女”为“媾”,成为古代一种特定婚姻形式的专名,表示不同姓氏之间的交互成婚。《说文》:“媾,重婚也。”段玉裁注:“重婚者,重叠交互为婚姻。”所谓“重婚”,并非停妻再娶或私奔再嫁,而是氏族间的男女群相为婚。《左传·隐公十一年》:“惟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杜预注:“妇之父曰昏,重婚曰媾。”从文献记载来看,两姓世代交互为婚之习俗屡见不鲜,且流传长久,如西周时期姬、姜两姓即为世代交互婚娶。《宋书·后妃传》载,刘宋时,孝武帝之姑下嫁王偃,生子名藻,生女名宪源,孝武帝娶宪源为皇后,又将自己的妹妹临川长公主许配给藻。又《元史·公主表》载弘吉剌氏特薛禅父子战功卓著,皇帝发圣旨曰:“特薛禅家生女为后,生男尚主,世世不绝。”显然,正由于这种两姓交互为婚,习尚颇成气候,所以才能在语言文字中形成一个专名——媾。而“媾”所表示的这种互婚,除了互婚的单位已不是原始氏族外,几乎与前文说及的原始互婚再无相异之处。
当然,两姓交互为婚,多行于皇家贵族高门大姓之间,每每以互相勾结利用、扩充政治势力为目的。但亦有兼行于民间的类似婚姻形式。中国传统婚姻习俗崇尚所谓“亲上加亲”的“姑舅表婚”,也就是兄弟之子女与姊妹之子女之间的通婚,这种习尚在文献记载中汗牛充栋,可不赘说。“姑母作婆”“姑妈女,顺手娶”“舅舅要,隔河叫”之类的俗语正是这种习俗的反映。而这种姑舅表婚与以上我们讨论的固定族团互婚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在家庭产生以后,这种氏族间的互婚关系如延演为家庭、家族间的互婚关系,即为不折不扣的“姑舅表婚”。
当然,作为婚姻习俗的一种,“姑舅表婚”并不能排斥其他种类的婚姻形式,因而不可能造成如同固定族团互婚所导致的那种普遍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姑舅表婚”就是“姑”“舅”一名三用发生的原因。但是,“姑”“舅”一身数任的亲属称谓之所以能够在其所赖以产生的原始婚姻制度消亡后长期沿用,则当同“姑舅表婚”的长行不衰不无关系。
[1]. 何久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王立军.汉字与古代崇祖文化[J].中国教师,2008(03).
[3]. 王延林.常用古文字字典[Z].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4]. 王贵元.汉字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曦)
孙永兰,女,内蒙古赤峰学院文学院;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