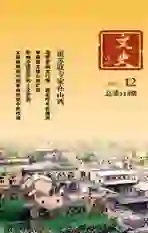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奚若
2015-09-10智效民
智效民


张奚若(1889—1973),出生于陕西朝邑的一个中医家庭,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与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有同学之谊。辛亥革命前夕,他到上海求学,遂投身革命,结识了于右任、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奔走于上海、武汉、北京、西安和日本东京等地,为购买军火、发动起义而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此外,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饶毓泰、杨杏佛、严敬斋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四十自述》83页,台湾远流版)辛亥革命后,张看到革命党人虽然是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于是他在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的同时,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张奚若文集》,第464页)起初,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需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同上,第4页),所以还是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起,张在国外度过了12个春秋。在此期间,他除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还去德国科隆大学进修,并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从而为确立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接受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最具批判精神的一个。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之后,就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打击顽固派和破坏旧秩序方面好像是孔武有力,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0页)。可见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已经有所反思。相比之下,由于因袭了那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但不能从张所提出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一运动和功过得失,就连这样一条重要的研究资料,恐怕也很少有人注意。
与胡适相比,张奚若不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一位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他除了教学、研究之外,还用通俗锐利的笔调,在报刊上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以便从学理的层面,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见解传达给普通民众。在这方面,他与当年那些深居简出,关在书斋里作学问的学究,以及时下学院大墙之内所谓的学者,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张氏著述中,我以为最值得一读的是他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分别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50期和152期(1935年5月),前者还可见于1935年5月2日的《大公报》。如所周知,1935年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候,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张为什么不讲精诚团结,不讲抗日救亡,而是要连篇累牍地谈人格问题呢?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他在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就明白了。
在前一篇文章中,张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解放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思想解放最为重要。第二,尽管个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无缺陷,但是它的优点却在于能够养成忠诚勇敢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在任何体制下都有无上的价值。第三,为立国本,为救国难,中国急需培养这样一种人格。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又以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尤为透辟。文章说:个人主义除了承认一切社会组织都应该以人为目的,其权力都来自并属于构成它的人们,以及它必须由这些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外,还必须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政府或其他。也就是说,“因为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所以举世皆以为是而我尽可以为非,或者举世皆以为非而我尽可以为是”(《张奚若文集》,第356页)。这与胡适所言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个人就不仅需要在思想和言论上有充分的自由,而且还应该有向政府提出建议、批评的义务和权利。他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服从国家才是自觉而不是被迫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感受到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以忠诚勇敢的人格去对待他的国家;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充满活力,它的国民才不至于仅仅是一种工具。
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人格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个人依附于团体的现象不仅极为严重,而且比欧美各国多了三四百年,这就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不敢抵抗,甘心屈服的“第二天性”,所以他主张应该特别提倡那种勇敢的批评精神,并保护那种不畏强暴的人格品质。就现实而言,在个人与国家的问题上,近年来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颠倒了二者的主宾关系。于是,所谓“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的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等,便为当局反复宣传,津津乐道,恨不得把它变成国人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逻辑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仿佛“全国的人最好都变成接受命令的机械,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得救”似的,这种“外国人想拿机械造人,我们偏要拿人作机械”(同上,第362页)的做法,可恶之极,也危险之至。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深刻指出:由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而只要是人,他在理智、经验和操守等方面就可能有很多缺陷,如果我们对权力不加以制约,就会使“再好的统治者,……也很难抵抗滥用(权力)的引诱”(同上)。有鉴于此,他认为把不加限制的权力托付给任何人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做为个人的集合体,任何国家都不但要营造一种宽松的舆论环境,宽容的思想氛围,还应该让掌权者懂得,在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接受批评容纳意见”是避免腐败的“有效方法中最重要的”(同上)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国民与国家的道德关系,才可以步入现代社会。
最后还应该提及的是:1949年9月,张奚若是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会上讨论国家名称的时候,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对此,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于是“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如今的国名其实是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