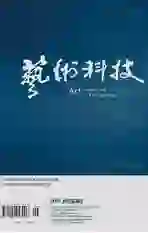“中国画”的观念形成
2015-05-30张筱膺
摘 要:中国画的概念形成并不是中国绘画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它的出现承载了一段绘画本体之外的历史内容。但这段历史又影响了后来中国绘画发展的形态。对近世中国画的概念的历史进行观照,可以为我们厘清今天中国画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全部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中国画;历史;观念
像“中国画”这样,以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名义命名艺术类型的做法,在艺术史上曾经有过。例如,波斯细密画;特别是指代一种地域风格时,这种做法更是常见。例如,荷兰风俗画、英国风景画,等等。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世界全球扩张之后,这种情况在艺术史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命名法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故意而为的民族主义的情节,像日本画、朝鲜画等等。因此,原本看似简单的名称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起来,使用时也就多了一分阐释的风险。
在谈到中国画的概念起源时,今天的很多人都会提到一段材料,借以说明“中国画”这个词最早是通过利玛窦这个西方人的嘴里说出来。[1]这段材料出自明朝万历年间金石书法家顾起元所著的史料笔记《客座赘语》。该书的卷六有一则“利玛窦”的词条,顾起元在其中写道:“利玛窦,西洋欧逻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无异也。”[2]顾起元的笔记中虽然记了一些插科打诨性质的荒诞事,但大部分仍可被看作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说来有趣,历史上“中国画”这个词最早倒不由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至少就目前的资料看是这样。
利玛窦虽然在比较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差异时说了“中国画”这样的词,但在清末以前的中国画史画论中,还很少有论家真的用到“中国画”的提法。利玛窦是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使用了“中国画”这三个字,而清末以前,虽然也有人像顾起元一样曾见过传教士带来的“天主画”,但这种进入的方式并不与足以改变中国文人对中国绘画的观念与体认,特别是不足以改变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画”、“图画”、“绘事”、“丹青”等等,仍然是论家称呼绘画的常见称谓。中国绘画仍然在一直以来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上,因循着自己的授受之道,继续发展了两百年的时间。
诚然,“中国画”概念的最早出现是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为前提的,但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播和使用,实则反映的不是中国画家对绘事本身的观念转变,而是一种刻意的文化疏离,它反映的是从文化自信到垮塌之后的自封与自保。如果我们沿着利玛窦的线索,对明清以降“中国画”做一次观念前史的还原,那我们可能会更为清晰地看出中国画在进入学院之前所承载的内涵及其文化属性上演变的痕迹。而这将会呈现为一条波浪起伏的线。
对于明末传教士带进来的宗教绘画,除了顾起元的笔记,明末清初学人姜绍书画论《无声诗史》中的“西域画”词条也是引述较多的一段文字。姜绍书所谓的西域,并不是我们理解上的亚洲中西部地区,中国人习惯上把经由西部地区来的异族人统称为西域人。姜绍书描述的对象也是利玛窦带来的圣像画,但他把当时中国画家面对异域绘画时的反应作了点睛的表述。该词条云:“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3]尤其是这最后的“中国画工,无由措手”,显然地流露出一种艳羡与惊诧。除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震惊,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也被这种传教士带来的写实性绘画所打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延揽了一批专业或非专业的传教士,作为宫廷画家专为皇帝嫔妃制像。康熙皇帝就曾经赦免了原本在张献忠的蜀军中供职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和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es)。利类思当时用透视的方法临摹了一些西方风格的风景画,送给了康熙皇帝。尽管他不是专业画家,但这种写实性的绘画在当时的皇帝面前还是新鲜事物。据《中华帝国全志》的编纂者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记载:当时“满清官员震惊了,他们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在一张纸上再现楼阁、廊台、门扇、道路及其胡同,这是如此逼真,初见时,还以为是真的。”[4]同朝的马国贤,还有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郎世宁,更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传教士宫廷画师,并有大量作品存世。除此之外,这些传教士还用西洋绘画的方法传授给一些中国的宫廷画师,像焦秉贞等在中国画史留名的中国画家就曾得到他们的指导。①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绘画在视看方式上对宫廷和文人士大夫形成了一定的视觉冲击,但这种冲击在当时看来,更多的只是猎奇层面的。很快,这种新鲜感便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朝大国心里所掩盖。即使是皇帝最被打动的时刻,他们对西式的图像也处处流露出理念上的龃龉。如乾隆皇帝曾经对郎世宁的画大加称道,称“写真世宁无过其右者”,[5]但同时也对郎世宁西式技法中不符合中国绘画、特别是宋元以来那种强调意境的格调充满微词,认为其“似则似矣逊古格”。他曾命郎世宁临摹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郎世宁画完后,乾隆认为画的很像,“许其形似”,但同时又说神韵不够,意境不到,因而“未许其神全”,郎世宁画完后仍然让“金廷標仿李公麟笔补图,希望“数理之须合中西二法”。[5]乾隆自己在其御制诗《题李公麟画三马苏轼赞真迹卷》中也曾表达类似意思,说:“奇形即命世宁传,神韵更教廷标写。”在为御诗所做的题注中对此解释道:“癸末岁,爱乌罕贡四骏,命郎世宁为之图,形极相似,但世宁擅长西洋画法,与李伯时笔意不类,且图中有马无人,因更命金廷标用公麟五马图法,用郎之奇肖李之韵,为四骏写生。”[6]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西洋绘画的技法还无法独立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传教士也只能无可奈何的采用一种“合笔画”的变通办法去迎合国人视看习惯。然而这种变通的做法尽管迎合了好奇的帝王,但是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眼里,遇到的却是一种鄙夷和不屑。
前面曾提到康熙朝受业于西洋传教士的画家焦秉贞,这是一位较早从中国人视角变通西洋画法的中国画家。他在中国画史中也因此留名。比他稍晚的清初画家张庚曾在《国朝画征录》中对他的画法有过一番点评,张庚说焦秉贞“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至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本法(海西法)也。”但张庚对这种海西之法并不称许,甚至还有明显瞧不上的意思,他认为焦秉贞这种用西画笔法画中国题材的“得其意而变通之”的合笔画,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而且“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7]同时期的邹一桂对西洋画的阐释和理解,基本上也反映了清前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看待西洋画的观点。他在《小山画谱》中对“西洋画”的解释是:“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8]邹一桂的解释有从视觉效果上对西洋绘画的客观描述,但一旦落到视觉效果之外的品评上,他立刻转变观点,认为其“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了。邹一桂的话在清初及以后中国画家定位西洋绘画的评价系统中,很有代表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清末光绪年间的画家松年在其《颐园论画》中谈道:“昨与友人谈画理,人多菲薄西洋画为匠艺之作。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9]他的这段话几乎就是邹一桂的翻版,经过了鸦片战争,经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清王朝早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了。但在看待西洋绘画的态度上,不但没有改观,甚至更加认为其“不必学、不能学”了。
对于最初见到西洋绘画的中国画家,西洋画的写实效果或许在一开始曾让他们感到震惊、感到“无由措手”,但在更深層次的精神和理念层面,这种技法和视觉上的惊诧,还不足以折服千年积淀延续下来的中国画的“道”。真正的变革,是他们在承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巨大痛楚之后,才不得已由被动到主动地做出选择之后才发生的。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画”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定性和定型之前的观念史还原,是参照着“西洋画”的观念史做出的。在利玛窦之后,从中国文人看待西洋画的观念变迁中,可以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绘画的观念演变概念。只不过,在清末之前的中国画家看来,还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画”这样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取代“画”或是“绘事”。
明末清初中国画家受到的文化冲击,在当时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冲击,是一种范围和影响有限,层次很浅的视觉刺激。在中国画的世界里,技法层面向来只被认为是浅层次的内容,而观念的交融和接纳属于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时的中国画家只是注意到了异域绘画的外在,对其建构在当时文艺复兴理性与科学基础之上的观念本源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当然,在当时来讲也不可能有深入了解的可能。当时的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之国,是天朝上国,即使是号称“中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对待异域文化的时候,也显得愚昧的可笑。他在为道光皇帝拟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一派盛气临人的口气,完全是以对待属国的口气行文,对当时已是世界头号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多以蛮夷称之。更有意思的是,在林则徐的眼中,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而外国的一切,都可有可无。他在檄文中写道:“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10]由此可见,时至清末,在中国人,甚至是所谓最开明的人的观念中,对中国之外的世界,除了想象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认知。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同样的一种观念,道光在看了林则徐的文稿后,就非常欣慰,御笔朱批:“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10]结果,这封信带来的是坚船利炮和三千年未有的近世之变。
观念的变通常常滞后于技法的变异。所以,在中西方画家最初的交往之际,中国画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对方技法方面与中国绘画的差异,而不是技法背后的理念层面,也是很正常的。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深处,中国的一切,也包括中国画,“皆利也”;外来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自然也包括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绘画,那些东西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以供玩好”的雕虫小技,绝非中国人的需要。没有对立面的存在,自然不需要也无法进行明确的自我定位。这在“中国画”的概念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840年之前,中国画家通过西洋画初步看到中西绘画技法和视看效果上的区别,但并没有太以为是。1840年之后,中国画在出于自保而被动的逐步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之后,得以确定了自我的理念认知。没有西洋画,就没有“中国画”,反之亦然。西洋画和西方文化是一面镜子,中国画只有在这面镜子中才能照见自己、确立自己的形象。但这不等于说西洋画是中国画效法的榜样,更不是像康有为说的“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11]通过明清以降“中国画”的观念史还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中国画在进入学院之前所承担的文化负载,这是今天中国画学科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画”概念是在中国画家面对西方绘画的逼拶,刻意保持一种疏离西方文化、更加深入的确立中国背景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定型和定性的。所以,中国画不仅仅是一个画种的概念,是一种绘画技法和材料上的术语,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身份认知和选择。也正是由于“中国画”的上述出身,所以它其实是“西洋画”的观念镜像,是一个虚妄的概念。中国画后世的发展,在20世纪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发展轨迹,和其由于在观念上的虚妄所导致的与其母体文化的脱节不无关系。中国画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与母体文化剥离的痛楚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牵扯中进行的。这或许不是中国画家自己的选择,但却是它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下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注释:①焦秉贞是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的门徒,受传教士影响,擅长用西化写实画法画肖像。
参考文献:
[1] 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本体学[M].第2页.刘曦林. 20世纪中国画史[M].第30页.
[2] 陆粲《庚巳编》、顾起元《客座赘语》合订本[M].中华书局,1987:193-194.
[3] 姜绍书(清).无声诗史-藏修堂从书本-第四集[M].
[4] 黄时鉴.东西交流论潭(第一册)[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13-314.转引自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Z].
[5] 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M].朗世宁条,于安澜.画史丛书[M].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
[6] 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M].
[7] 国朝画征录[M].
[8] 小山画谱[M].
[9] 松年.颐园论画[M].
[10]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M].
[11] 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M].
作者简介:张筱膺(1976—),女,辽宁鞍山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