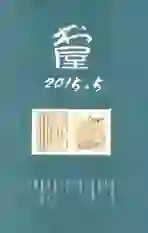魏晋玄风之缘起
2015-05-20林振岳
林振岳
读罢《世说新语·识鉴》篇,觉晋人相士之风,以及清谈之习气,“得意忘形”之学风,固有其学理之迹可循,然其与现实社会之思潮也有莫大关系。有須加注意者,略陈如下。
还是从制度谈起。于一国而言,第一重要者无疑是人才。国家取士,一般有一套固定的选拔体制。中国的取士制度,最为有名者自然是文官科举取士制。但科举取士的制度是在隋朝确立,自汉代迄隋朝,主要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所谓“孝廉”者,颜师古注释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即通过地方官员推荐乡里有令名嘉誉的人,朝廷从中选拔官吏。这也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观念盛行之结果。而作为“民之父母”,还要有廉洁之行,取“孝、廉”二德,故谓之“孝廉”。元封五年,武帝又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茂者,秀美也,“茂才”即“秀才”。举孝廉几乎全由郡、国推举,而秀才则可由众人共举,除州、郡外,还有列侯、光禄勋、御史及派员专举等,所取的为“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乃特殊之人才。举孝廉跟秀才二者皆为汉代取士之重要手段。当然,汉代取士之途除此二者之外,还有辟除法、皇帝征召、博士弟子课试等途径,但其基本的取士制度,还这种察举制度。
可见,汉代人才须由在位者察举,方可脱颖而出。故在位之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识鉴之器,方能辨识人才,材官授能。于是一时人人以伯乐自命,相士有如相马。识才鉴贤成名流专门之学,好事者亦纷纷为之专书立说,相人之书如伯乐《相马经》般纷纷呈现。刘劭的《人物志》即此类之名作。除此以外,史志著录这类书甚夥。
品识人物之书蔚然成观,可见当时风气之盛。此等风习至魏晋之时,乃至人人以识鉴自矜。《世说新语·识鉴》载谢安相人之语:“禇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禇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相士”一词,直与“相马”同类,足见时人自诩伯乐之态。又《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人物志》的作者许劭当时被目为有知人之鉴的典范,其传略称之为“以简识清浊为务”。汤用彤先生《读〈人物志〉》一文谓之:“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名成目,具有定格。”这是汉代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之风的遗习。
又识鉴已具材器者不足为奇,能见小儿潜在之质而预见者,更可矜奇伐能。故时人每见小儿有宏伟气象者,必好为之辞。如《世说新语·识鉴》篇载:
卫玠年五岁,神襟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郗超与传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在此,不禁想起《世说新语·言语》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辞,只是文书采摭,仅存其有验者,恨不得见当时人夸口而不验者也。
上流名宿各以识鉴自矜,此种风习,是科举出现之前依靠察举选贤的必然。那么,作为怀抱利器或别有用心的待选者,虽不似毛遂之自荐,但利禄诱惑之下,也不至于人人安分地坐以待选。于是窃名之士强矫姿态,以异行异闻引人注目以得举荐。如此,名与实的问题便出现了,魏晋之反叛,实自汉代开其先机。
察举者既是如此,那么作为被选之士,这种制度对其行为有何影响呢?
汉代选拔人才,虽然是选拔官吏,但却看重其德名胜过其吏治之能。又或者说,在汉人眼中,吏治之能与孝悌之行是一致的,而孝悌之行与德名又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并无区别。故取士便全凭一人的名声。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道:“汉人以名为治。”
在汉人大倡儒家孝道的同时,因为儒术为官方意志,与仕途相关,便出现了一派名不副实的状况。一些人为了仕途利禄,把这种声名视为求仕的工具。如此,礼便有徒有其名的做作意味了。礼本当称情,但汉代却已有以“善为容”而得为礼官者。《汉书·儒林传》载:“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颜师古注解释“颂读与容同”。“以颂为礼官大夫”,即是说徐生善于表演礼之容仪,以此得为大夫。而其孙徐襄不能通经,亦得“以颂为大夫”。只不过是由于容颜举止符合礼文,即便不学无术,也位列礼官。
百行孝为先,而孝道以父母三年之丧为重,所以我们不妨以三年丧来进行考察。以居丧而言,依礼是有其常制的。但汉代以后,孝子居丧往往过制,否则就不为时人所知晓。如《后汉书》称述孝行,多有“哀毁过度”、“哀毁过礼”、“哀毁骨立”、“致哀毁瘁,欧血发病”等的记载。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寑,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其实,圣人制礼,是取众人之中度,制中立节,以便世间人人可以效行。《礼记·檀弓》记录了孔门弟子这么一件事:曾子谓子思曰:“亻及 ,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但在汉人那里,因为此为声名之所征,遂人人争为孝子。若居丧不哀毁过度,则不足以彰见孝行,闻名乡里。所以,为彰显孝行,时人无所不用其极,行为便有点变样了。《颜氏家训·名实》记录了当时一个大贵人的做法:“近有大贵,孝悌著声。前后居丧,哀毁踰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以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此人或本是有孝子之心,只是觉得还不够,故特要用巴豆涂脸以显其哭毁过人。但最后却弄巧成拙,“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有孝之情实的孝子,要“清通于多士之世”,尚需如此。而那些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更是要绞尽脑汁来弄出各种奇怪的迹象,曲行阿世。有孝子居丧期间,把食物洒在墓地引来乌鸦(乌鸦被认为是孝鸟),以表彰自己的孝行天验。
以上仅仅是就居丧一事而言,而推想时人日常种种行为,其矫拂求名、故为姿态的举动,尚不知有多少。故《抱朴子·名实》谓之:“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下层之士,名不符实。上流评鉴,自然也誉不由衷。品鉴人物与利禄之门相紧系,一旦流播终成弊病。虚名假誉由是而生。对于以许劭之流的“月旦评”,《晋书·祖纳传》即已非之:“何得一月便行褒贬。”《抱朴子外篇·自述》谓之“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余嘉锡先生则谓之:“许劭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材,不过藉以植党树势,不足道也。”
好比《世说·赏誉》篇载钟会荐裴楷之事: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余嘉锡先生《笺疏》引《初学记》十一引王隐《晋书》曰:“王戎为左仆射,领吏部尚书。自戎居选,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浮沉,门调户选。”可见王戎实际并无吏治之能,徒有其名耳。余嘉锡先生評曰:“然则戎之为吏部,葺阘不才已甚。钟会复何所见?而于二十年前豫以天下无滞才期之。会之藻鉴本无足道。藉使果有此言,戎既不副所期,会为谬于赏誉,何足播为美谈。”
名不副实,一个名的世界由此崩溃。名教的崩溃,绝不是其学说内部出现了问题,而是在于现实的名不副实,即“名不正”。魏晋时人有识者,对此这种徒有其名的现实自是痛疾不已。其人的想法大概是:与其没有情实而徒有其形式,不如我有其情质而不为其形式,苟有孝之实,何必拘于俗人之名。痛恨其弊,乃持其反,于是一时避名居实,越轨放诞之行标榜于世。这可谓是“矫枉必需过正,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如《世说·德行》篇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生孝死孝,乃居名还是居实之别,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呈现,必然是“有孝道之情实而不备于礼”与“无孝道之实而备于礼”这样实质与形式的鲜明对比,在最大程度上昭显其是非。
又《世说·任诞》篇载: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籍当葬母,蒸上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为礼法,亦是因为其自矜情实之厚,若不能“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恐怕也难为世所容。
又如《世说·任诞》篇载阮籍卧侧之事:“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男女授受不亲虽为礼法,但礼法之设为防乱。苟无乱之心,亦不必拘与俗礼。这些都是避名居实的极端行为。
但是,我们也得注意,魏晋人虽然号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汤武、而非周、孔”,可其人的观念与儒家并不相悖。好比孝道、男女有别等等,他们都是避其名而居其实,实际上厌恶的是现实中名不符实的礼教,故有此愤世嫉俗之任诞行为。阮籍云:“礼教岂为我辈设”,及“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之语,其实是要有“动容周旋而中礼”的人方可以,並非人人可以效仿。阮籍越轨非礼的举动,并非是要推翻礼制观念,只不过是通过这种独立异行来痛刺现实而已。
这种重实轻名的做法,乃形成了一股社会的思潮。魏晋的玄风正由此始。而这种心态,在老庄处正有所征,乃相附成学:“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乃成一时之风气,加上佛教东渐,玄思渐起,形神、言意、名实之辨成一时风尚。魏晋人重其质,轻其文,“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玄学亦由此而起。
由此,重实质而轻形名的思潮,一变为魏晋玄风。识鉴人物则以神韵,而不拘其形貌,如魏武帝曹操“床头捉刀人”真英雄之事,刘伶形丑而不妨为名士。读书则以神会,不拘章句,如庾子嵩读《庄子》而谓了不异人意,乐令不剖析文句而以麈尾柄确几。言谈则旨指玄渺,不为实务,如传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阮籍不论时事人物,而言及玄远。汉代之清议一变而为魏晋之清谈。
汉代由孝廉举士,“以名为治”,到现实的名不副实,又到魏晋人避名居实的反叛,清玄之风的缘起由是可窥其踪迹。当然,玄风之兴起尚有学理上之内部原因,在此只是略述其社会思潮之影响。至于其内因,那就是魏晋玄学的讨论了,自是又有无穷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