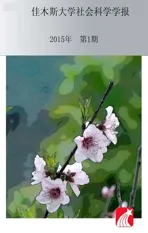广南地母文化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
2015-04-15罗杰
罗 杰
(文山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文山663000)
在当代生态审美的价值框架中,传统民族文化中的生态审美特质、民族特性往往都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基于将广南地区留存至今的宗教文化、自然崇拜、地母信仰,以及民族审美文化、建构起的生态形态都纳入到生态审美的视域中,呈现出具有边地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多元共生的特点和生态审美整体理念。广南地母文化是滇东南地区壮、汉等民族,在农历的三月初三通过祭祀地母举行驱邪纳福、祈愿丰产、风调雨顺、六畜兴旺的民俗活动,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地域环境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下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态审美文化,其中蕴含着生态审美智慧,具备了当代生态审美文化的价值与内涵,符合生态学提倡的土地伦理,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一、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
广南普千村地母庙中现存的《地母真经》中写道:“东西南北四部州,春夏秋冬母造成;庶民百姓不离母,五谷六米母长成……绫罗绸缎从母出,四季禾苗母长成”。此外地母经书还有告诫民众的训言:“敬地母,孝双亲,诵真经,行正道。可避灾劫,获常乐,得永生。”这些《地母真经》的训诫喻指生养万物的地母掌握着生养万物的神秘力量,又将其尊奉为有教化民众的美德化身,集中体现出当地民众对土地的敬畏、美德、善行、共生的道德典范。当我们把广南地母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进行探究时,应先厘清当地民众对待土地上态度来思考问题,即当地民众并不是将土地视为简单物质意义上的土地了,而是在以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作参照,敬畏地将土地尊奉为地母,自然地将五谷丰收、万物繁育、六畜兴旺都与地母的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又自由联想到对地母的信仰与农耕稻作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产生了对地母的祭祀活动,在对地母进行的祭祀活动仪式里又体现了人们对地母的敬畏和依赖情感。从生态审美文化的原初性来看,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存在关系,当人与土地之间建立起了依存关系后,人与土地的之间已经架构起一定情感纽带,广南地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民众敬畏生命和对对待土地及稻作生活的一种心理取向。同时《地母真经》中的训导彰显了地母是对自然和土地的崇拜行为,它已经将人与土地的情感提升为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指引,体现了民众对待土地的态度,意味着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非常重要的,听从地母训导和敬畏地母是将当地民众对农耕稻作生产生活中土地体验渗透到具体生活中,这种土地体验实质是当地民众特有的生态理念,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提升为整体上共生形态。
在这种共生的文化生态基础上形成了以“敬畏生命”为主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敬畏生命成为生态审美心理取向的核心是源自于与地母文化相关的原始宗教禁忌,由于地母文化的生态审美文化内涵中与广南当地多种原始宗教联系在一起,它首先体现出的是对土地的敬畏力量,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宗教禁忌约束力。地母文化的原生态特性中有将地母视为美德的化身的倾向,这种倾向本身就具有特别的圣洁性,又体现了中国神话中对地母的道德幻像,两者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生态审美心理取向的特殊性。一方面敬畏地母是一种宗教命令,人们必须绝对地遵循宗教禁令,通过禁止某些不利自然生态的行为将土地在稻作社会中的地位提到神圣位置;另一方面,敬畏地母实质上是对生命的敬畏,地母又具备教化的道德功能,强调从生产到生活都必须克制行为,又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加强了个体的道德修养,维系着整个农耕社会的群体关系和淳化社会风气。宗教禁忌上的约束力量已经被美化为一种地母崇拜的信仰仪式,在通过诵读地母真经、祭祀地母等膜拜仪式活动中,借助祈愿神灵的超然能力达到获取福祉的心理,实际上也就敬畏土地的心理表现,而这种心理倾向表征着人们合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相应的稻作生产的顺利进行及谷物丰收时,之前的祈愿得到了实现,预示着敬畏才能得到福祉,有了福祉才能完成稻作生产和丰收,最终就能实现农耕社会的正常运作和自体保存,敬畏土地实质上是人们一定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和农耕社会稻作文明体验的集中体现,其核心为敬畏生命。正是人们意识到信仰地母和敬畏生命的神圣性,地母文化才形成围绕敬畏生命的主题而创建出来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敬畏生命构成了地母文化的内核。
敬畏土地、生命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之所以会形成,既不能脱离广南地区原本存在的宗教文化、自然崇拜、地母信仰,也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宗教与土地的关系,而在于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之间所建构起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交互关系。只有这几者的协同作用,才能形成土地生态审美心理取向,地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始生态的土地是万物的始祖,地母是原始群落先民对于农耕社会中女神精神。地母开启新生、生长和养育生命,而且是一切生命的轮回成为自然隐喻,基于信仰地母而形成敬畏生命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产生的土地的生态审美心理效应,敬畏生命的生态审美心理才得以发生。“像对自己的生命意志采取敬畏生命的态度一样,对所有的生命意志也采取敬畏生命的态度。”[1]在生态审美理论中,土地与人是通过审美关系的中介才得以实现,其中生态审美心理取向是将人与土地及自然合而为一的核心,具体以敬畏生命的方式加以展现,既意味着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加深了人们的生态审美心理的体悟与感知,又深化了生态审美心理取向的内涵;敬畏生命意味着土地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在农耕社会文化上的延伸,在稻作文明上的拓展。地母被审美观照地幻化成为生命造化女神,成为一种造物神,逐渐形成了人们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和传达生态审美心理取向,敬畏生命成了生态审美心理取向的本质、核心,地母信仰以敬畏生命为启示和归属。
二、建构生命意识的生态审美理念
广南地区的族群壮族为百越后裔,是比较早的驯化野生稻的民族,被认为是地母文化留存地区的族群,拥有一定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因为他们从农耕社会和稻作生产中积累起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生态审美智慧,在长期的生产劳作生活中建立于与土地、自然的依存关系,这种地母信仰的生态审美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生态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生态智慧。地母崇拜和土地信仰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比较重要的思想,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据《淮南鸿烈集解》载:“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木啬而死为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母崇拜与土地祭祀已经成为祭祀社稷重要内容,土地信仰成为农业文明中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祭祀社稷意味着是国家存亡的重要活动。而处于农耕文明中的广南地母文化正体现了这种个体保存与种族繁衍依赖于稻作生产的心理取向,它集中地呈现出人类与土地的互相交融的特殊依赖情感,明显地表现出通过祭祀土地祈愿得到福祉回报的心态,这对地母文化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地民众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对土地进行了人化和人化等方式加以体验和诉求中的生命意味,赋予土地女性化、道德感化的审美心理内化方式,自觉地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与崇拜。
地母崇拜和土地信仰是通过建构起核心内涵生命意识的生态审美理念,具体体现为在农耕社会中稻作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使人们的生命意识有了转变,由于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和依存感加强,萌生出对土地及自然万物的生命感发,通过对土地与生命关联直观领悟的方式,把对个体生命的思考与土地的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其间产生的生命意识寄托了当地民众对地母的情感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命的关注,期许得到福祉,与土地、自然和谐相处,是人们生命意识的心理诉求,而心灵深处的重生意识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如同对土地本源、自然万物生长、四季轮回的体验等,都具有一定的原始思维,体现了人们对土地和生命的感性体悟。这种原始思维特性的生命意识建构起了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逐渐形成基于土地又超越土地、塑造地母、教化社会的核心内涵。生命意识寄托了当地民众的审美理想和道德标准,它唤醒了他们的生命意识和道德认知,督促人们在信仰上和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行动上必须遵循它,寄寓着人们的心理和道德内涵,这种生命意识体现了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和生命精神的体验,从而找到了一种通过地母崇拜和土地信仰建构起生态审美理念的、敬畏生命的审美理想。对生命的审美观照与表现,都是生命意识的体现,随着人们在农耕生产生活中与土地关系的依存性加强后,这种生命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在地母文化和其他传统文化的互动中得以深化。
广南地母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在生态审美理论中具有一种整体性,它将土地与自然融合为和谐整体,体现了广南地区的民众对土地的崇敬心理,对土地的崇敬实质上体现了稻作文明地区普遍存在的母性情结与生命感怀,通常都将人对生命的体验与地母的生育万物联系在一起思考。广南特定的自然生态地域条件和生态稻作文化、浓厚的多民族文化交融造就了其地母文化的生命意识感化模式,地母构成了生命与道德融合为一起的心理取向,象征着的是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需要遵从于地母,万物生于地母、生产生活必须顺应地母、诵真经孝敬双亲行正道等等这些关系都借助于地母的功能。“美学在其本源处,同人的生命处境与灵魂归宿息息相关,它是展现了人的对于人生意义、价值的寻求的特殊方式,它能使人从存在意义的晦暗不明之中,从存在的被遮蔽状态之中敞亮出来的本源之思,诗性之思,并在思的途中,感悟人生生命的意蕴所在,唤醒自己与他人,寻找一种生命的超越。” 正因为地母的道德感化功能及母性特质,正好契合了人们的生态审美心理取向和生命意识,才能使人们从生存的意义角度来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感悟到生命的意蕴存在。地母作为人类的生命本源,与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归属有密切关系,常常被作为自然隐喻来象征人与自然的生命精神,对于生命的感悟在人与土地、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得到了升华,人们借由地母唤起了对生命的追寻。这样广南地母文化中生命意识是为一种生态审美智慧的体现,将地母的生态审美理念提升为追寻圆满的生命意识,自然隐喻将地母幻化为与农耕生产及稻作生存维度多层面融合,现实生存处境与自然万物孕育的审美思维将生命意识从中得以提升到生态审美维度时,地母崇拜就是一种自我生命追寻的现代生态审美视域,对生命的感悟是从人与土地的基础关系、基本生存开始,对于生命的本源性探索和审美观照,超越了这些反思。正是寄寓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并在地母崇拜中追求理想生命的实现,通过宗教仪式和道德教化、感化实现自我的超越,在审美体验中追寻生命的体验与感悟,超越自身的局限而达到生命自由,并唤醒对自然永恒生命的敬畏。这种生命意识蕴含着人们对土地的崇拜和信仰,敬畏生命和尊重生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敬重。
三、深层生态学的审美反思
从广南地母留存的社会历史文化地域性来看,广南地区内的壮汉民族,崇拜地母、信仰土地、敬畏生命的生态审美理念,使广南成了在农耕文化、稻作文明传承方面区别于其他地区,从此闻名于省城乃至京城。这其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值得我们从现代生态审美视域探析,更需要与深层生态学进行整合,从此角度来审视广南地母文化,应基于生态审美的角度来进行反思,生态智慧理应是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种美学思想,在学理的范畴中生态智慧不应该只是对自然平衡的假设性分析,更多的应该是从留存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与现代生态审美精神相契合的推论和规则,如“生物中心伦理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内在价值。”[3]在广南地母文化中蕴含着是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规则的生态审美智慧,以敬畏生命和生命意识共同构建起人与自然、土地的生态审美关系,这与当代人类生态道德伦理思想和深层生态学倡导的理念是相符的,深层生态学是建立在对现代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和生存困境及因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危机等审美反思基础上的科学理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广南地母文化维系着人与自然最原初的生态平衡,蕴含着一定的生态审美智慧。
广南地母文化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人与土地关系的生态审美新维度,为我们在探讨人与土地、自然的建构的生存维度中,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提供了新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思考方向。同时它是一种基于维护土地生态环境、维系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审美智慧,是当地民众在长期的农耕稻作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调适人与土地关系的生态审美观,是人与自然、农耕社会、稻作文明相互依存地处于生态审美维度中的自然法则。在广南地母文化中,地母、土地、自然、生命相互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的共生共存规则改善了对待自然的态度,丰富了地母文化的生态审美文化内涵,提升了地母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因此,我们虽然从现代深层生态学的角度来探析其中蕴含着的生态审美智慧,但还要结合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来分析,地母文化中不仅关注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系到了人与土地的自然法则及由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教化,呈现出对土地的责任与对生命的敬畏,同时其中的生命意识是生态审美智慧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从人与土地关系的感悟,表现了关注生命的心理取向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创构,既承载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又契合于现代深层生态学理论,这是广南地母文化中值得关注的深层生态学理念。也就是说广南地母文化中的生态审美智慧表现了基于土地情感的敬畏生命和生命意识,又并未脱离具体的生态环境,又是不断地追寻生命,在数百年的地母祭祀活动、文学艺术作品中,这种生态审美智慧获得丰富的内涵,并且得以继承和遵循,形成了一个地母崇拜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广南地母文化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是一种契合深层生态学的重要规则,为地母崇拜和土地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人与生态和谐关系建构起联结。
[1]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07.
[2]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26.
[3]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