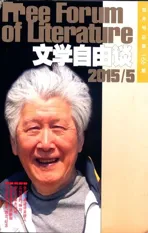一种挑战与 一种崛起
2015-03-21熊元义
●文熊元义
一种挑战与 一种崛起
●文熊元义
时下,随着自由主义无法克服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被人逐渐疏离,有人重新祭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大旗,认为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而是中国当代社会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有人则力挺批判现实主义,认为这条路在中国社会根本没有走完,仍需继续走下去。很显然,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界沉寂多年后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三个方面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的重新崛起:一,中国社会的发展绝不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共同发展,作家艺术家不能完全超越,也难以脱离这种趋势。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自主创主的阶段,而且是促进社会共同发展的巨大动力。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不少作家艺术家自觉地把主观批判和历史批判兼容并蓄,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他们不是汲汲于挖掘人民大众的保守自私、封闭狭隘的痼疾,而是在批判人民大众的不足的同时,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在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这种艺术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界的崛起。二,现实中国激烈的反腐败斗争旨在清除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艺基本上置身事外,没有出现与这场生死攸关的反腐败斗争相匹配的精品力作,甚至微弱的回声都欠缺,这种不应有的缺席和失语已令文艺蒙羞。知耻而后勇,不少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反腐败斗争将极大地推动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界的崛起。三,文艺界顽固存在的躲避崇高、向下堕落的倾向已造成文艺创作的困境,不少作品越来越低于现实生活,表现得更苍白,更干瘪,更贫乏,而且对现存冲突的解决远远滞后于现实生活自身的发展。这种躲避崇高、向下堕落的文艺创作倾向是一些作家艺术家退回内心、躲避崇高的产物。而有些作家艺术家则坚决反对其沉溺于小情趣的文艺创作,极力提倡文艺创作“要往大处写”,即“把气往大鼓,把器往大做,宁粗粝,不要玲珑。做大袍子了,不要在大袍子上追究小褶皱和花边”。他们并不反对作家表现自我,而是要求作家从“我”出发走向“我们”,而不是从“我”出发又回到“我”处。这种文艺思想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界的崛起。
其实,现实主义文艺不仅在每个时代都存在,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不是静止僵化、永恒不变的。文艺批评界既要看到作家艺术家对现实主义文艺的巨大影响,也要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现实主义文艺的积极影响。恩格斯在批评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中篇小说《城市姑娘》时,既肯定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也批评它还不够现实主义,即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不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够鲜明,而是作家没有深刻把握她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文艺理论家陈涌在比较鲁迅与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不同时认为,曾经被马克思所赞扬的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有着过多的温情,不忍让现实矛盾充分地展开,而鲁迅的现实主义则是严峻的,不让步的,总是毫不留情让现实矛盾充分地展开。陈涌认为,在中国作家中,直到现在,鲁迅还是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苦痛的一个作家。鲁迅不只看到农民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看到农民是一个革命的阶级。鲁迅是在比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活动的时代更为进步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因而在鲁迅身上,也反映了一些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所不可能有的历史特点。对于中国文艺界而言,作家艺术家对现实主义文艺的影响,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对现实主义文艺的影响是双向的,互为作用的,需要我们全面地把握它。
首先,崛起的现实主义文艺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这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当代文艺的一些弊病。有的批评家认为,这些弊病的产生主要与囿于个人经验有关,因而无法感知他人的悲欢。他们重申“清醒的现实主义”,就是强调作家艺术家突破“私人生活”、“自我经验”,走向更开阔的世界。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当代文艺的缺陷,但却囿于在重复以往现实主义文艺的基础上小补小修,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个缺陷。在推动作家艺术家走向更开阔的世界上,有的文艺理论家提出了审美超越论,认为文艺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不仅仅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仅妨碍作家艺术家深入人民创造历史活动,而且在中国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与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在时下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有根本矛盾的。这两者的差异甚至冲突只能在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否则,他们的心胸就很难成为“社会的共鸣器”。他们固然可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但是,所谓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应该是和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分不开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仅仅局限在他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缺乏超越意识,就很难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一些本质的方面。别林斯基坚决反对作家艺术家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坚决反对艺术成为一种生活在自己小天地里、同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共同点的纯粹的、与世绝缘的东西,高度肯定了那些强有力地促进俄罗斯自觉的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是人民的自觉,是我们目前还不很多的社会的内在的、精神的利益的表现”,并指出,在俄国,现在能够推动俄罗斯自觉的平庸的艺术作品比那种除了艺术却不能促进俄罗斯自觉的艺术作品要重要得多。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不少作家艺术家严格区分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这些作家在把握历史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采取较人道的形式的途径,而这种历史进步正推动着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伟大进步的变革。同时,他们还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夹杂着一些采取较残酷形式的畸形发展。人们相信,作家艺术家勇立潮头唱大风,必将创作出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
其次,崛起的现实主义文艺追求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坚决抵制和批判文艺被边缘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社会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中国文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就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边缘化发展趋势中,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分化了:有的人否认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认为中国文艺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有的人则甘居社会边缘,乐于自我矮化。其实,这种边缘化发展现象在很多时代都出现过,可怕的是有些作家艺术家随波逐流,躲避崇高,自甘堕落。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应摒弃鸵鸟心态和庸人心态,正视并批判这种文艺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自觉地承担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社会责任,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艺术创作中把这种历史进步有力地表现出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文艺作品。
最后,崛起的现实主义文艺不仅大胆直面现存冲突,而且努力解决这种现存冲突。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不少作家艺术家在是否直面并解决现存冲突上曾发生过分化。鲁迅与乃弟周作人分道扬镳,首先是正视现实、睁开眼看现实与避开现实、闭眼不看现实的分歧,是直面现存冲突与掩盖现存冲突的分歧。在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区分了“杀出血路”的小品文与“躲避时事”的“小摆设”的不同,认为这两种小品文都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但是,“躲避时事”的“小摆设”将粗犷的人心磨得平滑,即由
粗暴而变为风雅,是抚慰与麻痹,而“杀出血路”的小品文则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是休养。鲁迅不仅认为那种小巧玲珑的“小摆设”虽然是“艺术品”,与万里长城、丈八佛像等宏伟的大建筑无法相比,而且认为身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境的人所要的是坚固而伟大地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锋利而结实的匕首和投枪,而不是那种由粗暴而变为风雅的“小摆设”。这是因为“杀出血路”的小品文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是生存的小品文,而“躲避时事”的“小摆设”则是作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苟全性命的产物,是小品文的末途。本来,文艺是反映现存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形式,但是,有些文艺理论家在理论上却不彻底,只强调文艺对现存冲突的反映,却没有看到文艺对冲突的解决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降低为社会生活的直观反映。有些文艺理论家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甚至高度肯定那些无力解决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矛盾的文艺作品,他们笃信所谓的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悖论,即这种“悖论”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而且是文艺的悖论,甚至认为作家艺术家只有写出这种“悖论”,才是好的文艺作品。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生物的一种大特权是经历对立、矛盾和矛盾解决的过程。“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它就会在这矛盾上遭到毁灭。”而“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深刻反映生命的历史运动,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找对其的解决途径,而不是搁置这种现存冲突,而是通过推进对这种现存冲突的解决,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