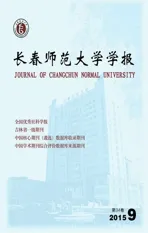中国法庭辩论中律师语用移情策略研究
2015-03-20胡锦芬
胡锦芬
(闽南理工学院英语系,福建泉州362700)
多数语境下的人际交往需要说话人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或从对方(物质、心理或情感方面的)需要出发,替别人着想,充分理解或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是一种换位思考,也是移情[1]。法庭辩论作为一种更具风险性的交际,更需要律师站在听者(尤其是法官)的立场运用语言,理解并满足法官的需求,顺应法官的思维,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接受其主张,才更可能实现胜诉的效果。语用移情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却鲜有人探讨法庭辩论中的语用移情现象。本文拟从顺应论的角度分析律师辩论中的语用移情现象,旨在发现中国法庭辩论中主要的语用移情策略,并探讨语用移情策略的选择如何作为一个动态顺应的过程,帮助律师通过换位思考达到预期的语用移情效果,从而顺利实现其交际意图。
一、语用移情
“移情”的概念起源于德国美学,意为情感的渗透,后发展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关注的重要课题。最早把“移情”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学家Kuno,他认为移情是指说话人把自己投射到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以体现他跟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2]。而“语用移情”这一概念是我国语用学专家何自然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移情在语用学上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的用意[3]。换句话说,语用移情指的是说话人能站在听话人的立场选择语言,充分理解并满足听话人的需求,而听话人也能设身处地地领会说话人的意图。庭审的胜诉除了取决于证据、法律、逻辑推理之外,往往还取决于语言策略的技巧。在庭审语境中,法官一般被认为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庭审参与者,因而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往往采用大量语用移情策略,站在法官的角度组织语言,尊重法官的感受,满足法官的需求,力求实现双方的情感趋同,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最终顺利实现其交际意图。
二、顺应论
顺应论是Verschueren于1999年提出的揭示语言使用本质特征的语言学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语言使用者不断选择语言来顺应语境、满足交际需要的过程[4]。而人们之所以能在交际过程中恰当选择语言,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三个本质特征。即是说,语言使用者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项目(变异性);选择的过程是非机械性的,需要在灵活的语用原则指导下不断协商(协商性);语言的顺应性能够让使用者在一系列不定的可能性中选择可协商的语言和策略,来顺应各种交际语境因素(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从而有效达成其交际目的。语用移情策略正是律师为满足交际需要而在一系列语言策略中进行选择商讨的结果,是律师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对语境因素作出顺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下面我们通过语料分析来具体阐释律师是如何选择语用移情策略来顺应各种交际语境因素的。
三、法庭辩论中律师语用移情策略的顺应分析
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发现在法庭辩论中律师采用了大量的语用移情策略,其中律师使用最频繁的主要有人称指示语、模糊限制语和语气系统。而这些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律师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顺应听者心理世界、律师心理动机、庭审规范等各种交际语境因素,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的过程(图1)。
(一)巧选人称指示语
人称指示语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5]。通常情况下,人称指示语是以说话人自我为中心的,即用第一人称指说话人,用第二人称指听话人,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人用第三人称指示。但在实际语境中,为了达到某些特定效果,说话人有时会有意违背自我中心这一准则,即“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把指示中心从自我转到听话人或其他听众身上,以实现说话者预期的人际及语用目的”[6]。在庭审语境中,为顺应各种交际因素,顺利达成交际目的,律师往往会消除自我主体意识,选择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这一选择反映了律师的语用移情。律师使用最多的人称指示语是用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一人称单数,第三人称指代第一、二人称。
1.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一人称单数
从语料来看,律师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不一定总是选用“我”,而是经常选用把听者也包括在内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这是因为律师沟通的语用点不是自己,而是站在听者的角度预期听者的心理世界。这样可以帮助律师缩短与听者的心理距离,引导听者顺从律师的思维而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实现心理趋同,促进交际顺利进行,顺应了律师想拉近与听者间心理距离的心理动机。
例1: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虽然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他的犯罪行为客观上并没有造成现实上的严重后果。
例2:在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对孩子弃之不管,他返回现场的目的就是不放心这个孩子能否被收养,这恰恰证明了他和一般犯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不同的,他遗弃不是抛弃,而是无奈。
在上述例子中,律师本是陈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为了让法官产生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便巧妙地选择了把听话人也包括在内的“我们”。这种指示语让律师的辩词听起来好像在与听者交换意见一样,让听者感觉自己仿佛也参与了讨论。律师从而在无形中将自己的观点悄悄渗进法官的意识中,引导法官在情感和心理上与自己取得一致。如果律师选用的是常规的“我”这一人称指示,则体现了说话者的自我中心性,可能会无形间拉大律师与法官的心理距离。
2.第三人称指代第一、二人称
律师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除了用“我们”代替“我”之外,还经常用指代第三人称的名词如“辩护人/代理人”来指代“我”。有同样用法的是当律师对听话人提出建议、请求、怀疑或反驳时,一般也不选用常规的“你/你们”,而是选用第三人称指示如“公诉人”“法庭”等来指代第二人称。
例3:结合本案的全部案件材料,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有诈骗罪证据不足。
例4:我们建议法庭在量刑时,能考虑到本案被告人诸多主观和客观的实际情况,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例3中,律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没有选用常规的“我”,而选择了第三人称“辩护人”来代替,这样做可以淡化个人色彩,突显律师职业角色,暗示听者这是从法律专业角度作出的判断,而非个人的主观臆断,充分显示了法律语言的庄严性和权威性,顺应了律师的心理动机和庭审规范。例4中,律师对听话人法官提出建议时,也没有选用常规的第二人称指示语“你/你们”,而是用第三人称名词“法庭”代替,这是因为“你们”会让人觉得咄咄逼人,可能引发听者的抵触情绪,而第三人称的使用可以缓和紧张生硬的气氛,照顾了听者的感受,也体现了法律语言的庄严性,顺应了听者的心理世界和庭审规范。
(二)善用模糊限制语
律师经常使用的另一语用移情策略是模糊限制语。语言学领域最早提出模糊限制语的Lakoff将模糊限制语定义为“有意把事情弄得更加模糊或更不模糊的词语”[7]。之后,Prince及同事以“是否改变命题的真值条件”为标准,将模糊限制语分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8]。下面分析律师如何通过选用不同类型的模糊限制语来顺应交际语境,实现语用移情效果。
1.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话语结构原意,对原话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正,或者给原话定一个变动范围[8]。律师常用的词有大约、相对、一定、某种程度上、大体说来等。在法庭上,法官判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法官更希望律师提供准确客观的案件事实。因此,当对某事的真实程度不敢完全肯定时,为了顺应法官的需求、接受心理以及庭审规范,律师就要借助这类限制语把一些接近正确又不敢完全确定的话语说得更得体一些,避免话语内容过于绝对引来听者的怀疑或反驳。其语用移情价值在于律师站在听者的角度考虑,理解法官了解案件真相的需求,同时预期了法官的接受心理,从而选择这类限制语来让话语更严谨客观,增强话语说服力。
例5:鉴于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应负一定的责任,而被告人是在一种极度气愤的心情下才实施行为的,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在量刑上能够予以从轻处罚。
例6:基于被告人能够真心悔过,且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相对轻微,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在上述例子中,律师在阐述自己理由的同时,也考虑了听者的需求和接受心理,所以选择了“一定的”“极度”“较小”“相对”等限制语,对话语作了策略修正,使话语听起来更加严谨客观,避免了与事实有太大的差距,提高了话语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如果去掉这些限制语,话语听起来会显得过于绝对,不易被听话人接受,还可能引来听者的怀疑和责难。
2.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并不改变话题内容,只是传达了说话人对话题所持的猜疑或保留态度,或是引用第三者的看法间接表达说话人的态度[8]。律师常用的词有:可能、应该、辩护人/代理人认为、众所周知、根据、证据/调查显示等。这类限制语使说话人的语气趋于缓和,让说话人在沟通中不显得咄咄逼人。它的语用移情价值在于律师在选择语言时进行了换位思考,顺应了听话人对话语的感受,使听者在心理上消除抵触情绪,让听者较为容易地接受自己的观点。
例7: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爆炸罪的犯罪形态不是未遂,而应该说是犯罪预备。
例8:众所周知,现在网络交易不一定非要知道交易对象的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因为杨某和石头有网络交易就认定杨某与石头有怎样深的勾结。
在上述两例中,律师在表述观点时选择了“辩护人认为”“应该”“众所周知”来缓和自己的绝对化声明,表明了这只是律师自己的看法或是第三方的观点,而非绝对的观点;法官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避免话语内容过于武断。如果去掉这些限制语,律师的陈述就显得咄咄逼人,可能引来听者的抵触情绪。采用移情说法则可以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营造一种融洽的交际氛围,尊重并维护听者的面子,顺应听者的感受,从而推动交际的顺利进行。
(三)善选语气系统
在功能语言学上,Halliday认为人际意义是通过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人际意义的[9]。作为人际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语气系统的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在庭审中,律师为了顺应听者的感受和自身的心理动机,说话前会预期听者的感受并选择相应的语气系统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使其积极地参与到对话中,以较好地语用移情效果。在律师话语中,实现这一效果的语气主要有疑问语气和虚拟语气。这些语气的合理选用可以帮助律师吸引听者不由自主地进入律师所说的情境中,引导听者从律师的角度解读话语,让听者在情感和心理上与律师达成一致,从而顺利达成交际意图。
1.疑问语气
在交际中,疑问语气的一般功能是听话者求取信息;但在法庭辩论中,律师运用疑问语气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用以产生特殊的语用移情效果,表达所需的人际意义。疑问语气的运用可以帮助律师吸引听者的注意,引导听者积极地融入沟通活动,无形中让听者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样听者就能站在律师这一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更好地接受律师的观点。这是律师用来引出听者移情的一种常用策略。
例9:大家可能会这样想,自己都快养不活了,你为什么还要养第二个孩子?你决定养下来,就要承担抚养义务,你养不起孩子,为什么还要养第二胎?但这就是本案的特殊性,这个婴儿的体质情况对被告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正常孩子的抚养,他的经济能力是无奈的。
例10:假如我们有个工厂生产一种美国制式的彩电,标价2000元人民币,虽然价钱不高,但由于制式不同仍不能卖出,我们能说这台彩电一块钱不值吗?能说谁偷了白偷吗?原告的作品也一样,暂时卖不出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依然存在。
例9中连续两个问句的运用,可以引起听者的注意,让听者不知不觉中也思考同样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被告人当时的处境,为被告争取减轻刑罚的可能性。例10中疑问语气的运用可以帮助听者也积极地参与到律师所述话题之中。如果听者能成功移情,去思考律师提出的疑问和推断,律师的观点就更容易被听者接受,增强了律师言论的说服力。
2.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是律师用来引出听者移情的另一种常用策略,一般由“如果”、“假设”等引出。通过虚拟假设,律师可以顺应自身的心理动机,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引导听话人参与假设的过程,让听者不经意间顺着律师的思路来思考和判断律师的言论,从而作出对律师有利的判断。
例11:普通人都知道携带假币是违法犯罪的,如果一个人身上携带数额较大的假币,肯定会藏得很严,保护得很好,更不会忘记自己携带的假币放在什么地方,而本案被告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他拿出雨披,却把假币弄掉在地上,由此可见,他对委托人给他的东西里面藏有假币是不明的。
例12:辩护人做一个反向假设的话,假想这个孩子不是早产三个月,不需要暖箱里出八万多元的高额费用,那么悲剧还会不会发生呢?辩护人认为不会,本案的情况,希望法庭可以考虑被告人的经济情况和婴儿的特殊体质完全使得被告人无法承受,这是一种无奈。
例11中,律师运用虚拟语气,引导听话人参与假设的过程。如果被告知道里面放的是假币,肯定会藏得很好,而不会出现忘记或掉在地上的情况。如果法官成功移情的话,律师提出的被告持有假币的行为主观故意不明显就能得到法官的认同,律师的心理动机就能顺利实现。例12中,律师同样采用了虚拟假设,引导法官考虑被告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婴儿的特殊体质,如果法官能理解被告当时的行为是出于无奈,而不是故意抛弃,或许会相应地减轻被告的刑罚。
四、结语
法庭辩论的成功除了取决于证据、法律之外,往往还取决于语言策略的技巧,因此律师在辩论时需要处处为听者着想,时时作换位思考,站在听者(尤其是法官)的立场选择语言。通过对律师法庭辩论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律师在法庭辩论中采用了大量的语用移情策略,其中使用较频繁的主要有人称指示语、模糊限制语和语气系统。而这些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律师为了顺应听者心理世界、律师心理动机和庭审规范等交际语境因素而作出的动态选择。它们可以帮助律师通过换位思考,预期听者的心理和需求,引导听者从律师的视角解读话语,达到预期的语用移情效果,从而拉近与听者的心理距离,实现与听者的心理趋同,顺利达成其交际意图。
[1]冉永平.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31-337.
[2]Kuno,S.Functional syntax:Anaphora,discourse and empat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何自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4):11-15.
[4]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Edward Arnold,1999:55 -56
[5]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6]Lyons J.Linguistic semantics: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7]Lakoff,G.Hedges: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J].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1973(2):458-508.
[8]Prince,E.F.,J.Frader,& C.Bosk.On hedging in physician-physician discourse[M]∥J.di Prieto[Ed.],Linguistics and the Professions.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183 -228.
[9]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