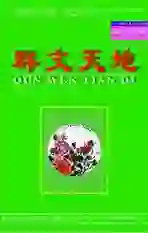张宏河作品二题
2015-03-11张宏河
张宏河
老 姨
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十几年间,我们家与同住在省委大院中的郭友芳姨姨家的关系一直处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两家既非邻居也不是对门,只是由于父亲同郭姨的丈夫同在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工作的缘故,两家的关系尤其是母亲和郭姨越走越近,越来越亲密。由于郭姨年长母亲14岁,我们姊妹都亲切地称郭姨为老姨。两家在长达近40年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虽然老姨夫妇已过世20年了,我的父母亲也于几年前相继离世,但当年两家“不是亲眷却胜似亲眷”的情谊还常常让我们感到温暖,成为我内心深处美好的记忆。
老姨是陕北米脂县艾家茆人,出生于1918年10月。1955年随丈夫来青海。老姨个子不高,微胖的身体,一副慈眉善目的面容,在我的记忆中,老姨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总有慈祥和蔼可亲的笑容。老姨和母亲一样,原来都是生活在农村大家里的操持家务,受到婆婆约束的儿媳妇;都是在解放之初参加过文化扫盲班脱盲,是新中国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受益者,也是从过去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一跃成为初具读写能力的城市居民。
老姨的丈夫何海旺,1914年2月出生,也是陕北米脂县人。1941年参加革命,1955年来青海工作,任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从1958年开始就同父亲一起共事,是父亲的领导。虽然何伯伯和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4年,但和父亲于1960年底至1963年初共赴刚察,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海北草原上参与了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创办省委农场的一段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当时我们两家与办公厅的部分干部都举家来到刚察,住的是一半在地下的“地窝子”。那时我刚满4岁初有记忆,冬季刚察草原上常常刮风,呆在“地窝子”里,就觉得狂风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出时紧时松的“呜呜”鸣叫,几乎是彻夜不停。冬季的雪天里,遍地皆白十分的刺眼。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白天要完成各自的本职工作,晚上还要轮流背上武器,顶风冒雪去场区巡视巡逻,十分辛苦。
那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有一天4岁多的我领着1岁多的妹妹去找老姨,老姨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院里养了一大群鸡,其中一只个头很大的公鸡非常凶悍,见我们两个蹒跚而至的小孩闯入它的地盘,便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一边大声喊着老姨,一边躲避着公鸡的叨啄,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老姨闻声从房子里出来,顺手捡起一把扫把赶走了那只可恶的大公鸡,把我俩领进屋里,问我们叨着没有,疼不疼。那时在我的眼里,老姨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就和我们母亲一样是最亲近的亲人。从那时起,老姨高大亲人般的形象就在我幼小的心中树立起来。
两年多的农场生活结束后,我们两家又搬回省委大院,老姨家住西一楼一楼东头的两对门,我家住在平房的一排三号。经过两年多艰苦生活的磨练,我们两家互通有无走动得更加频繁。那时侯我们放学回家见不到母亲,就会穿过东一楼的走廊去老姨家,而且十有八九就能找到母亲。何伯伯在单位上当领导,在家里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老姨常背着何伯伯向母亲诉苦说,婆婆的气不受了,老头子的气还得受,显得很是无可奈何,有时老姨与何伯伯也会斗嘴生气。母亲那时经常一人带我们四个孩子(父亲那时已去西堡公社工作)操持家务,加之母亲生活压力大又是个急性子,父母之间吵架生气也时有发生。每当谁家两口子之间闹矛盾了,对方的家里就是避风港,不是何伯伯到我家去找老姨,就是父亲到老姨家找母亲。有时老姨赌气不回去,大家就一起在我家吃饭聊天,坐的时间长了气消了,自然就风平浪静了。
我们小的时候,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的一份工资生活,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常外出干些零工,在生活的重压之下,难免心情急躁,我们姊妹犯错的时候,受到母亲严厉的责罚是常有的事。每当在这时候,只要老姨在场,总会出面护着我们,让我们尽量少受体罚。记得姐姐讲过这样一件事,她都快中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家里照明用的白炽灯泡打碎了,她怕母亲责罚,跑去找老姨帮忙,老姨说不要怕,给姐姐出钱买了一个,帮姐姐度过了难关。这件事过了很久之后母亲才知道了,让姐姐把灯泡钱还给了老姨。诸如这样的事还有许多,就像当今流行“有困难找警察”,那时侯我们是有问题就去找老姨。她就像一棵大树,没少为我们遮风避雨,提供帮助。
老姨夫妇一生没有生养,他们的儿子高良(小名),是何伯伯兄弟的孩子过继给老姨家的。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高良兄身材修长,长得十分帅气。“文革”开始的1966年的时候,老姨夫妇给高良兄娶了漂亮的媳妇瑞娟,后来就陆续有了何红、何艳、何丽三个小天使。高良夫妇及老姨养女兰兰都在国防单位221厂工作,1987年之后,221厂完成了历史使命,老姨的孩子们陆续都被安置到四川绵阳工作。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何红只有六岁多一点,十分的乖巧,有些怯生,老姨让我带她到外面去玩,她跟我寸步不离,生怕走丢了。记得那会儿还和红红在老姨家楼门前照过一张照片,后来却没有保存下来,十分遗憾。
在我的印象里,何伯伯从刚察回来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疾病,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在家养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是炎热的夏天,何伯伯都是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走路时慢慢的,何伯伯是老革命,看病是公费,但身体上受了不少痛苦折磨。那时侯也许是工作忙顾不过来,高良兄把他的小女儿何丽放在老姨家。有时何伯伯身体不舒服老姨顾不过来,就把何丽放在我家由母亲照料,整个一个学期都在我们家呆着,都快成了我家的孩子了。
我们从小和老姨在一起,可以说我们姊妹四个都是老姨看着长大的。从小听惯了老姨讲的陕北话,以至于在我走向社会之后,遇到讲陕北话的同事都有一种亲切感。记忆中老姨常说的两句陕北话是“鬼仔仔”、“圪佬佬站坷”。第一句是老姨对我们小孩子的一种亲昵的称呼。第二句是小孩子犯了错误,家长让孩子站到墙角面壁思过的意思。那时侯和我们两家走得很近的还有同去刚察办农场的田举亭叔叔周一心姨姨夫妇和路万贵夏老师夫妇及王凤贵叔叔一家,田叔叔和王凤贵叔叔两家同老姨家同住在一栋楼里。那时侯老姨家有台做陕北风格面食“饸烙”的机器,有时几家人凑在一起吃“饸烙”,那场面很是热闹,有人在揉面,有人在拉风箱烧火,有人要站在凳子上压杠子,小孩子们端着碗眼巴巴地瞅着那细细的面丝进入滚烫的锅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吃到嘴里的“饸烙”面就和其他的面食很不一样,觉得特别的有滋味。
1976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五个年头,5月份我刚从重庆培训归来,9月就到了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关口,那时我全身心地在争取这次上学的机会,终因竞争对手的父亲是单位车队队长的原因而功亏一篑。在那段争取上学的紧张的日子里,我动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一切关系。回家时见到何伯伯,就央求他助我一臂之力。伯伯知道我从小在学校是很能读书的,非常支持我的请求,立马动身出门帮我托人找关系,却没能找到要托的人。由于那天下着小雨,伯伯回到家时,外衣都有些淋湿了。第二天,伯伯又带我跑到位于韵家口的省第三毛纺厂去找他认为可以给我帮上忙的人,直到找到那个人将事情托付之后,我们才回来。(这件事在我当时的日记里面有记录,否则再好的记忆也很难把过去将近40年的事情表述得如此详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伯伯把我的事视作他孩子的一样,不顾年老体弱(那时伯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好很多了),竭尽全力帮我,对于他老人家对我的关心支持,我将终身铭记永志不能忘却。
老姨和母亲通过二三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友情友谊,已经成为彼此体谅心心相印的程度。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小舅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母亲作为大姐,颇有些长姐为母的担当,很为小舅操心。在老姨和母亲的操持下,把老姨的侄女嫁给了我小舅,让我们两家亲上加亲,更加亲近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母亲为了家庭创收,在祁连路火车站附近开了两年的食品店。由于开店需要人盯守,所以母亲那段时间很少回家。老姨许久没见母亲面很是挂念。那时老姨已经是67岁的年纪,腿脚已经不太便利,于是让我弟弟用手推车带她去铺子里见母亲。老姨到了铺子里后,母亲指着货架里的食品说,老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老姨要了一瓶杨梅罐头,和母亲聊到快天黑的时候才回去。
再后来,老姨家搬到为民巷的干休所里,我们家也搬离了省委大院,但我们两家的交往从未中断。
老姨和何伯伯的一生,虽说有些磕碰,但也是终身厮守共同生活了一辈子。1994年4月,何伯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岁。老姨在伯伯过世后,还曾对母亲讲过,伯伯“压迫”了她一辈子,现在她可要轻松地活几年。老姨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在她的潜意识里和伯伯相伴的日子过惯了,老伴走了之后内心顿感失去了依靠,在伯伯过世的第九天就随老伴而去了,让我们悲伤不已。回顾老姨和伯伯的一生,还真是做到了生生死死不离不弃,不求同生但求同归的理想境界。
老姨的一生看似很平凡,却也不乏闪光点,她正直善良,倾其一生为家庭为子孙,视我们如己出,是一位伟大母亲的光辉范例。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老姨虽已离我们远去了,但她带给我们的温暖却不会冷却,并教会了我们把这种善良和温暖传给下一代,使其发扬光大。
追寻生命之光
常言道,绿色象征着生命,象征着希望。这句话要看对什么地方的人讲,对于生活在四季皆绿的南方人来说,绿色的环境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对于生活在北方,特别是深居内陆城市的人们来说,绿色家园就是美好家园,是北方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我小时候(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记忆里,西宁就是小说中描写的典型的塞外边城,常年特别是开春的时候,寒风裹带着沙尘横扫湟川,外出回家的人们常常是灰头土脸的,那时侯几乎家家都有一把掸土的掸子,外出回家的第一件事都是要掸去一身的尘埃。那时的西宁人风趣的将身边的环境编成顺口溜:“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青海的房上能赛跑……”。身处在这样环境里,西宁人对于绿色家园的向往和渴望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候各级政府和单位年年都在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活动,我在上中学及参加工作期间和几代西宁人一样,每到开春之际,到西山到阳沟湾到泮子山及城里的道路边都曾参加过植树活动。在父亲1958~1960年的日记中让我得知,那时省级单位的员工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北山参加绿化义务劳动,主要干些平地、挖树坑、浇水等,由于条件有限,也曾出现上百人排成一字长龙传递水桶送水上山的壮观场面,也不知道一桶水到了山上还能剩下多少。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宁寿塔下的北山山头实现了引水上山的水利工程,让土楼观上的山头黄土层率先得到了真正意义的绿化。在小寺沟东侧的穆珠岭的山脊上,如今还能见到三四处当年引水上山工程的蓄水池、泵房及生铁铸管的茬头等水利工程的遗存,那个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紧张,泵房下的阶梯是用大块圆型的石英石以人工的刀劈斧砍成九十度而砌,这样的石阶在别处是绝无仅有的。保存最好的那间泵房前些年还被守山的植绿民工所利用,他们将该房屋称作“王昭房”,这说明当年西宁人为绿化家园而付出,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却没有消失在岁月的红尘之中,仍被也应该让后人所尊重和记忆。只是当年的几代西宁人为绿化家园的努力,受政治、财政能力及对绿化这项宏大的社会化生态系统工程的认识所限,实际的绿化成效也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相当长的年份里,生活在北门一带的西宁人都能看到介于大墩岭和泮子山中间北山山顶的那几棵数,因为那时的北山基本上就是荒山秃岭鲜有绿色,而且也没有空气污染,所以这几棵远在天边的山巅绿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随风舞动着枝条,向城里渴望绿色家园的人们传达绿色的信息,多少人在仰望山巅的倩影时,产生过许多美好的期盼和想象:山的尽头是不是一片大森林?为什么那么高的山上树木生长的那么茁壮而城里栽植的树苗永远长不大?山巅的那抹绿色成了几代西宁人难忘的美好记忆。
1972年初的隆冬时节,我参加工作随同100多人的大队人马奔赴山城重庆。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的远行。当列车行至天水,见到窗外绿油油的冬小麦,那生命之光让我那颗年轻的心脏很是颤抖了一回。到达成都,在隆冬季节,室外虽然不见太阳,却是满街绿树,街道边开着红色黄色烁大花朵的美人蕉,让我感觉如同置身天堂一般。给我的印象外面的世界真是很精彩。在重庆近四年的学习期间,饱览和感受了南国的青山绿水,也得知了苏东坡所描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真实内涵。从那时起的十几年间,每次东出返回家乡西宁,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从宝鸡一路向西,越走越荒凉,随着窗外绿色的减少,内心好似被抽空一般,心情难免不悲怆凄凉起来。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已到了1989年。华夏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行和不断深入,国力增强了,百姓从温饱到了奔小康的阶段。古老的高原古城也长大了,长高了,和内地的大城市一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也就是在这一年,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这意味着绿化西宁在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后,终于使建设美好绿色家园的社会化大工程驶入大干快上的高速公路。1989年3月,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实施西宁南北两山的绿化”决策,并与1990年12月出台《西宁南北两山绿化条例》,成立“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动员全社会力量,由西宁地区各部门168家机关、团体、企业、驻军参与,将117个绿化点分片承包。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两山绿化已取得丰硕成果,截至目前累计总投资7.9亿元,已完成南北山绿化总面积达24.2万亩,共栽植高规格苗木2000万株,造林成活率达到85%,保有率80%,两山草木覆盖率已达62%,森林覆盖率由7.2%增至33%。
据《西宁晚报》记者魏金玉的统计,如今南北两山现有林木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吨,每天可释放氧气4900吨。两山绿化极大的改善了西宁人的生活环境。随着南北山绿化一、二期工程及北山美丽园永久性绿地的建设实施,古城西宁的生态环境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省市绿化部门已经着手编制南北山绿化三期工程规划,延伸绿色,计划在高标准绿化南北山的基础上,通过“三川”绿化,将绿化成果扩展到三县山系。到那个时候把西宁建设成为园林生态城市的宏伟目标将初见成效,我们西宁人梦寐以求的绿色家园会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
2010年,我也加入退休赋闲的行列,鉴于十年地理教师的工作经历,及对家乡绿化建设的持续关注,我和身边的两个老伙伴制定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出行计划,通过每周一次的徒步出行,走遍了南北两山的每一座山峰,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切身体验和享受到了两山绿化的丰硕成果,见证了两山绿化事业的发展变化的点滴过程,并发挥自己文学爱好,记录了踏山巡游的所见所闻,书写了《寻访文峰塔》《初访文峰碑》《泮山秋色》《西山春色》《穿越天路》《情系大墩岭》《雾霾锁城的忧思》《两山绿化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等一些同绿化建设、环境保护、健身出行有关的文章,在描述和讴歌两山绿化事业的巨大成就及众多在两山绿化事业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事迹的同时,也反映了与之相关的问题及不尽人意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旨在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家乡的绿化事业献策出力,争当一名河湟绿化建设的守望者。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近四年每周一次的巡山出行中,在泮子山巅,在大墩岭上,穿行在郁郁葱葱的黑刺林间或云杉丛里,在尽享满山遍野绿色的时候,我们都常会朝北山两高峰中间的那处山顶张望,因为那里曾经有一抹让无数西宁人充满美好记忆和想象的绿色希冀,但是时光过去几十年,山上新绿成林,满山秀色的时候,我们印象深刻的那抹绿色却已褪去,让我们心存一些伤感和感触,就觉得保存在脑海深处的那片绿色如同报春花,又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梅花,让我们心生敬意。
为了了却存在于我们记忆之中五十多年的夙愿,2014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和我的发小涛涛及李女士专程去拜访北山之巅的那抹绿色。我们走进大寺沟,沿着山谷里工程车碾压的路面径直向北,朝着山顶的那几棵树迈进。由于是初次寻访,在不知路径也没有现成道路的情况下,奋勇攀登,坡陡之处甚至手脚并用,约用3个钟头,终于到达了我们几十年间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几棵树下。早年的时候,有人说山上的树是七棵,有人说是三棵,今日来到树下,才知是五棵,树径约为50公分左右,树种为小叶扬树,其中三棵已枯干,一棵已没了树身只剩下露出地面的树根,五棵树中只有一棵老树上,多数枝条也已干枯,却有部分枝条上仍有绿叶在摇曳。站在树下向北看到,树下的山湾里就是互助县蔡家堡乡的刘李山村,其实在2012年五月从大墩岭到泮子山的穿越之行时,就曾路过这个村子,只是从该村的北面经过,并不知这五棵树近在咫尺,与我们擦肩而过。
望着这几棵枯死的老树,再看看漫山遍野茁壮生长的新绿,让我心生无限感慨,几十年来,西宁人追寻生命之光,建设绿色家园的脚步从未停歇,从过去的举步为艰到今日的快步迅跑,见证了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进步。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我们低温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高原地区,指望着十年甚至二十年造林绿化,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现实的,需要我们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用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建成我们的绿色家园。按照目前省市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及已经形成的绿化建设模式及取得的可喜成果,我相信西宁的明天会更绿,会更美,再也不是风沙漫天的旧模样,而将是山青水秀天蓝地洁的中国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