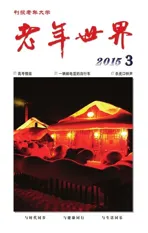银发族投资银保产品须谨慎
2015-02-23张兆利王晓芹
张兆利 王晓芹
银发族投资银保产品须谨慎
张兆利王晓芹

银保产品,实际上就是消费者通过银行柜台能够买到的保险,它最大的卖点是“保障+收益+分红”。在众多金融产品中,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销售的银保产品由于兼具人身保障及分红收益功能而受到“银发一族”的追捧。但在现实中,由于老年人经济来源有限,加上年龄、智力等方面原因,在购买银保产品时或对协议约定理解不透,或风险防范和维权意识不强,从而引发了不必要的纠纷。因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在选择理财产品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了解、理性投资、防范陷阱。
产品收益约定不能随意变更
案例:杨大妈在银行投保了一保险公司承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共计交纳保费24万元,被保险人为本人。该份保险的保险期限为3年,年回报率为5.87%。这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每年回报1万多元,3年之后应总共给付本息27万多元。可是保险合同到期后,保险公司只向杨大妈支付本息26万余元,剩余1万余元的利息没有支付。此后,老人曾多次找保险公司交涉,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底杨大妈因病去世,其丈夫及子女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利息。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已按照内部操作计算流程及产品设计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杨大妈购买的保险产品属于何种性质?
说法:本案中,杨大妈投保的险种属人身保险产品。人身保险产品的主要功用包括风险保障、长期储蓄、财务规划和投资理财等。尽管杨大妈购买的产品偏重投资功能,但本质上仍属保险产品,其经营主体为保险公司,不宜将其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应将该类保险产品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关于回报标准,本案中保险单已明确约定产品的年回报率计算标准,因此应以该标准作为年回报率的计算依据。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无论
保险公司还是杨大妈,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一方要求提高回报率,属于擅自变更合同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本案提醒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一定要仔细了解银保产品的基本知识,明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晰各方责任及相关收益约定,减少无谓支出。
合同期间内退保风险多多
案例:滕阿姨在银行办理储蓄业务时,现场工作人员向其推荐一款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保险,称该险种每年存5万元即可分红,款项有急用也可提现。如红利多,提现时会超过本金;如红利少,提现时也基本能“保本”。滕阿姨当即同意并交付了首期保金。第二年,保险公司又从滕阿姨的银行账户划款5万元。2014年初,因急于帮助儿子购房用钱,滕阿姨决定终止该保险业务,并将此前交纳的10万元取出。对此,保险公司称只能退还4万元。因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滕阿姨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解除保险合同关系并退还10万元保费。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辩称,原告在2012年8月办理业务时看了投保提示、产品说明书,亲笔填写投保单并交首期保费5万元,保险合同已生效。退保是投保人的合法权利,保险公司无异议,但依照约定不同意全额退保。
说法:本案中,滕阿姨购买的分红型保险属人身保险合同性质。对于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问题,《保险法》第47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据此,投保人在投保后有权提出解除合同。但是,解除正在履行的保险合同,投保人仅有权主张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而无权请求退还保险费。所谓现金价值,是指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保险公司为履行合同责任通常提存责任准备金,如果投保人中途退保,即以该保单的责任准备金作为给付解约的退还金。该金额的计算方法通常会在保险条款中予以载明。本案中,滕阿姨虽因事急需现金,但由于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因此只能依照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获得4万余元的退保现金。鉴于此,您在选择产品时,还应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期限及自身经济实力,避免因经济突发变故造成的财产损失。
违约之诉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案例:退休职工张先生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分红型保险合同,并依照约定向保险公司交付保险金8万元。2014年7月,张先生在一次外出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离世。事后,张先生亲属按照保险公司要求提供理赔申请及相关材料。不久,保险公司以“张先生没有告知投保前已患有高血压”为由,解除了与张先生签订的保险合同,并做出了“不予理赔”的决定,退还张先生亲属8万元。张先生的亲属认为,保险合同生效后,双方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法院确认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并支付保险金。同时,还要求保险公司支付2万元精神损失费。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说法:本案原告是基于保险公司存在合同违约行为而向法院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违约行为是指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合同纠纷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
范围。《合同法》第11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其中,精神损害非直接损失,也不是可预见性损失。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遭受损害的;个人隐私和其他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亲属关系遭受严重侵害的;死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使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犯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保险合同纠纷不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