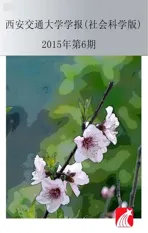丝绸之路与西方观念中的中国
2015-02-21万翔
万 翔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丝绸之路与西方观念中的中国
万 翔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回顾了近代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阐析了古代希腊、罗马学者透过丝绸之路对遥远的“丝绸之国”——中国的认识;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古代中国文明得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独立性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发展的分析,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终将使中国重现富强与繁荣,更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
丝绸之路,中国发展;东西方文明;“一带一路”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与交通路线,也是知识、思想与观念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传播的途径。对于中国文明进程而言,丝绸之路以及由之所承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保持独立性和先进性的必要条件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关研究的发展,国际史学界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即兴起于墨西哥高原与中美洲雨林的古代中美洲文明,发源于秘鲁、玻利维亚高地的古代安第斯文明,与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①两河文明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发展出来的文明,发源于公元前3 000年以前,早期代表是古巴比伦文明,晚期则是亚述文明。中国、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六大古文明。在这六大文明当中,古代印度河文明最先于公元前1 500年左右为来自中亚的印欧人建立的吠陀文明所取代,古代两河文明①则在1 000年以后被波斯帝国征服,又过了500年,已经希腊化的古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华帝国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硕果仅存的古文明,与两大美洲古文明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
中国文明的延续性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与众不同的凝聚力和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诸多城邦之间,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抑或文化观念上都是充满着强烈竞争的。而在古埃及,书吏阶层对彼岸的关注甚至要超过生活本身——宏大的金字塔和神庙,精细制作的木乃伊,与石棺上的铭文和《亡灵书》就是例证。建立在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观念滋养之上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兼具这两大古文明的竞争性与彼岸性的特征。翻开西方历史的书卷,映入眼帘的是无休止的扩张、殖民与兼并战争,以及对浪漫远行、灵魂得救、征服自然的向往。而一直受到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影响的印度次大陆,则在其文化中体现了分层的特征。原始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上的压迫,转化为种姓制度下不同种姓间的紧张。宗教势力在次大陆的根深蒂固,特别是婆罗门阶层对社会规范的控制,最终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这样的具有非暴力反抗精神的思想体系的诞生。在外来民族不断从西北方向涌入印度次大陆,给印度带来战争摧残和民族斗争苦难的同时,新的思想也不断注入,促进印度社会思想的深刻变革。然而在印度,最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没有改变,宗教的多元化和宽容也没有改变。
若与印度对比,除了保持西方与中国唯一通道的丝绸之路外,中国并未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任何实质性影响,更不必说对文明的改变和对民族的威胁了。整个古代,挑战中国文明的唯一“他者”来自北方——无论是苍凉的大漠、辽阔的草原还是东北地区的森林和山岭,与中原地区汉民族密切来往的北方民族,既为中华文明补充了新鲜血液,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因此,中华文明得以一直在欧亚大陆的东端独立发展,又以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保持着在文化、技术上与西方和亚洲各邻邦的同步。
而古代美洲两大文明却因为与东半球的长期隔绝,以及两大文明之间的彼此隔绝,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随着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而急遽瓦解,最终完全被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文明所取代。玛雅人曾拥有非凡的科学成就,印加人有复杂的政治制度,阿兹特克人国家的繁荣超过整个西欧。但在钢刀、铁骑、十字架和病菌的侵袭之下,美洲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起被西方征服者快速消灭了,数千年的文明独立发展,在十几年间戛然而止。
以地理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文明变迁的历史固然是片面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文明,以及以中华文明为主要思想文化渊源的东亚文化圈,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才得以在东半球各大文明之中,在古代和近代始终保持其文明的独立性和先进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独立性,既得益于其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又在于中国能够通过促进人员、商品和观念交流的丝绸之路,与西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与西方诸国相区别的文明自觉之基础上,保持中华文明的特性和统一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则在于中华民族通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独树一帜的精神传统,在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密切交流中萃取来自异国的优秀思想观念和满足中华文明需要的物质文化,从而以东方巨龙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并非狭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直居于世界最发达、最富饶之列的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的必要因素。
相反,正是在西方殖民者入侵远东,从海陆两端切断丝绸之路,并将西方的政治经济秩序强加于东方后的500年间,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进走向没落,又在彷徨中重拾丝绸之路时代的精神,最终通过实业自强、思想解放、人民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迈上民富国强,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转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与世界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我国首次将丝绸之路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国国际战略的自发产物,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绝不仅仅限于单纯的国际关系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而是新中国应对多极化世界挑战的战略自觉,是整个中华文明21世纪和平崛起的重要推动力。
笔者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回顾丝绸之路研究的形成,以及其研究内容当中为中国学者所不熟悉,却是西方研究丝绸之路问题基础的部分——古代西方文献中的丝绸之路与中国。正如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教育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①李希霍芬早年从事欧洲地质调查,后旅行到东亚、南亚和北美,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他的考察活动为中国的地理学和地质学发展奠定了基础。(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所说的:“正是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即西方人——笔者注)关于中国的知识。”[1]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因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终将促进东西方之间理解和信任的加深,使世界各国与中国形成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二、丝绸之路研究的缘起——西方学者的“再发现”
李希霍芬、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与黑尔曼(Albert Herrmann,1886-1945年)等人,是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倡议者。
丝绸之路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从历史角度和时代背景分析,主要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方面是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和瑞典的科学考察传统;另一方面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汉学的发展。欧洲各国科学考察的传统,源自启蒙运动时代以来欧洲逐渐流行的旅行文化。在近代以前,旅行往往伴随着商业目的——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长距离贸易,使商旅活跃于西欧、拜占庭帝国、欧亚草原、伊斯兰世界、南亚和东亚六大文明区域之间,促进了观念和文化在各个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殖民者在寻找带来丰厚利润的贸易机会之余,也深受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中世纪旅行家的影响,在东方经商、作战、殖民和传教的同时,撰写关于世界各地的旅行记录。
而大规模旅行的开始,则要到17世纪中叶英国社会开始流行的“壮游”(Grand Tour)。发源于16世纪丹麦的游学文化传统,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①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全面大规模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使包括丹麦在内的欧洲大陆各国人口锐减、经济衰退,而免受战争之苦的英国则迅速发展起来。以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崛起的英国新贵族青年前往欧洲大陆度过的重要人生经历。英国富裕家庭的青年往往由家庭教师陪同,在欧陆获取最新的科学知识,并了解欧洲各地的风俗习惯,结交上流社会的人士。
英国青年的壮游文化激发了欧洲大陆国家贵族青年的旅行热情。而在富于思辨传统的德国和瑞典,青年学者的旅行逐渐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科学考察的传统。瑞典著名的生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年)通过在欧洲大陆的旅行和考察,创立了生物的系统分类学。在林奈填补了生物学分类法的空白之后,德国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在欧洲、南北美洲和俄国的科学考察过程中,对生物的生长环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为德国的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物候学、气象学、物理学等多个领域确立了学术规范。
继承洪堡科学考察传统的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共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本人之考察经历及基于此的研究》一书。在书中,李氏指出了古代中国连接西方的四条主要交通路线:从新疆通往中亚和阿富汗的商路、从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商路、从云南通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商路,以及海上商路。广义上说,这四条商路可以统称为丝绸之路。而李氏所定义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记载的希腊商人梅斯代理人从阿富汗的巴克特拉前往中国的丝绸贸易路线[1]。这一定义基本对应前述四条路线中的第一条。
关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李希霍芬认为,张骞在公元前117年的出使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条件,而张骞逝世后,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张骞的副使到达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帝国,可算是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此后的诸多世纪间,丝绸之路一直扮演着使西方获得关于中国知识的观念之路的角色。
在李希霍芬之后,德国地理学家黑尔曼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别以文献研究和实地科学考察的方式,考证了丝绸之路的确切路线。而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则是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
法国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年)和德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年)是最早从西方与中国交往角度探讨中国古代贸易路线的学者。而英国学者裕尔(Henry Yule,1820-1889年)于1866年所著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书,将西方与中国的交往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李希霍芬之所以能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主要的历史素材来自这三位学者的论述。
李希霍芬等西方学者之所以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代指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路线,不仅由于丝绸是中国与西方进行大宗贸易的主要商品,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献记载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因丝绸贸易而为西方所知,在希腊罗马文献中被称为“赛里斯人”(Seres)的民族。“赛里斯”的词源,正是中国在罗马帝国最为人所知的商品——丝绸。
三、“丝绸之国”——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
“丝绸之路”概念的背后,是西方人对若隐若现的遥远中国的印象。若非接受了来自中国的丝绸作为服装的材料,罗马帝国的贵族阶层就无法在服饰上使自己与平民相区别。
罗马人穿着丝绸服饰的传统来自比他们更早在地中海世界崛起的希腊人。希玛纯(himation)长袍是希腊人从古风时代(公元前8-6世纪)起就一直穿着的服饰。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帕留姆长袍在希腊人建立的亚洲希腊化国家成为流行,就连当时流行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佛教造像,也以身着希腊式长袍的服饰来表现佛陀袈裟的外层——“僧伽梨”(Samghāti)。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公元5世纪起),罗马贵族和平民无论男女都穿着一种以羊毛织成的,叫做托加(toga)的繁复而宽松的长袍。但随着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希腊学者穿着的希玛纯长袍,开始为罗马平民所效仿,最终在公元前2世纪取代了托加长袍,以帕留姆(pallium)之名成为罗马男性的主要服饰。在这一时期,罗马共和国进入晚期,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贵族力图在服饰上与平民有所区别。罗马的下层平民穿着的帕留姆长袍仍是羊毛或麻质,中上层平民有的穿着从印度进口的棉质服装,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罗马的贵族开始以丝绸作为其帕留姆长袍的质料,还往往带有刺绣、金线和花边装饰。
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女性所穿着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她们不再穿托加长袍,而是以两件服饰搭配着装。在与帕留姆类似的斯托拉(stola)长袍之上,罗马妇女围着名为帕拉(palla)的大披肩,将头发包裹于其中,只露出面部。与男式服装一样,帕拉和斯托拉的质料反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丝绸,尤其是带有各种纹饰的丝质服装,是罗马贵妇人的标志性装扮。
罗马人把丝绸称为“赛里斯织物”(sericum)。这一名称与“赛里斯人”同源。虽然从语法的角度,是“赛里斯人”这一词汇,派生出了“赛里斯织物”的名称,但通过对古典时代文献材料的整理和对语言学证据的推敲,主流汉学家认为,“赛里斯人”来源于汉语的“丝”字。这一点为克拉普洛特首先提出,并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所充分论述[2]。
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作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充满离奇想象的作品当中,就出现了身高5米,长寿达200岁的赛里斯人的名字,赛里斯人和作为“丝绸之国”的赛里斯国(Serica)成为西方作家笔下的主角,还是要到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这一时期亦正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高峰期。可以说,没有发达的丝绸贸易,就没有“丝绸之国”的整体形象。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主要是以其文学发展的盛况而得名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年)和恺撒(Caesar,前102-前44年)的散文开创了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先声。但“黄金时代”的极盛期,还是伴随着公元前31年屋大维(Octavius,前63-公元14年)统治罗马,以及前27年罗马帝制的建立而开始的。活跃在屋大维统治时期的三大诗人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年)、贺拉斯(Horace,前65-前8年)和奥维德(Ovid,前43-公元18年)的诗歌悠扬婉转,蜚声于世,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文学的标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丝绸贸易开始达到空前的发达程度,以至于三大诗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赛里斯人的身影。
在黄金时代罗马诗人的笔下,赛里斯人首先被描绘成珍稀纺织品提供者的形象:维吉尔不禁发问“赛里斯人是如何从树叶上采下纤细的羊毛的呢?”[3]贺拉斯[4]提到了“赛里斯人的坐垫”;奥维德[5]则述及“赛里斯人的面纱”。同时代的诗人普罗佩提乌斯[6]76-77(Propertius,前50-前15)直接使用“赛里斯织物”(serica)来命名丝绸。四位用拉丁语写作的诗人笔下都出现了赛里斯人的纺织品,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现了新兴的罗马帝国对丝织品的巨大需求。
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中,赛里斯人还以其弓箭的锋利和战车的技术先进而著名[6]364-365。在帝国建立之后,罗马人已熟知世界各地的民族。罗马在东方的主要对手是波斯的帕提亚人。贺拉斯[7]212-213祝愿屋大维能够战胜帕提亚人,从而使赛里斯人和印度人都成为罗马的附庸,足见罗马征服整个世界的雄心。虽然路途的遥远和天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使罗马与中国终究未能直接接触,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之时,丝绸之国的鲜活形象就已充斥于罗马上层社会的观念之中。
“黄金时代”之后,罗马帝国的“白银时代”则是帝国建立后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重新确立的时代。“白银时代”的罗马作家关注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常常加以道德说教的阐发。著名的哲学家和剧作家塞涅卡(Seneca the Younger,前4-公元65年)和学者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年)是这一时期罗马文学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时期,丝绸服装已经成为罗马帝国贵族区别于普通公民的标志。塞涅卡在作品中惊呼“如果不同赛里斯人贸易,我们还能穿衣服吗?”[8]而据普林尼的估算,由于贵族中流行的奢侈风尚,每年有一亿枚罗马金币,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流入赛里斯国、印度和阿拉伯半岛[9]62-63。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中,普林尼煞有介事地声称:“赛里斯人向树木喷水,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正是因为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才能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徜徉于大庭广众之中。”[9]88-89由此可见当时罗马人对中国丝绸制作方法的无知。正是这种无知加剧了丝绸贸易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金银珠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一起,成为罗马帝国盛世之下巨大奢侈品市场上最流行的商品。象征身份和地位的丝绸,是所有奢侈品中对罗马上层社会文化改变最为剧烈的。早在塞涅卡的父亲老塞涅卡(Seneca the Elder,约前54-公元38)的时代,丝绸带来的罗马服饰风气的改变,就已使这位怀念共和国时期俭朴美德的道德家难以接受:“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丝绸衣服不能遮蔽身体,它还能不能叫衣服。少女们穿着纤薄的丝织品,以至于谁都能透过衣衫看到她们的身体。外人甚至陌生人都能随便看到少妇的身体,她们的丈夫也就能看到那么多……”[10]他忧心忡忡的描述,在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与尼禄(Nero,54-68年在位)当政的时代成为现实。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美德被上层社会和宫廷的放荡与无序完全抹煞,老塞涅卡之子小塞涅卡最终被自己的学生,皇帝尼禄赐死。
在尼禄之后不久的“五贤帝”时代(96-180年),罗马帝国进入全盛时期,领土扩张到最大。此时,帝国东部的希腊商人将贸易一直拓展到中国的边境。在著名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约100-170年)的《地理学》(Geography)中,记载有一支希腊商队从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前往赛里斯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公元100年前后。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希腊商队在经过中亚的兴都库什山区之后,来到了一处名为“石塔”的商站,这里便是赛里斯国的边界。从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的路途长达七个月之久[11]19-24。经过近代学者的考察,“石塔”的遗迹就是今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石头城”遗址,而从这个位于中国西部边陲的小镇到达中原的长安、洛阳,的确需要七个月左右的行程。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罗马帝国公民、希腊学者托勒密的记载,证明了新疆自从公元1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时代起,就是以长安、洛阳一带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的赛里斯国——中华帝国的领土。他的这一记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而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这里所指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而其国王安敦,应当是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61-180年在位)。西方学者遍寻罗马帝国时代的记载,却未发现任何遣使中国的记录,因此推断此次“来使”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中间商所冒称[12]。但在此之后不久出版的罗马帝国作家,以希腊语写作的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约110-180)的《希腊行纪》(Hellados Periegesis)中,作者颇为自信地声称,赛里斯人的织物并非如维吉尔、普林尼等人所述的那般,直接从树叶上“梳理”下来,而是通过一种名叫“赛儿”的小虫吞吃植物纤维,直到饱胀而死,赛里斯人从小虫的尸体中获得的[13]。不难猜测,上述接近丝绸生产事实的情况,正是通过发达的丝绸之路贸易——也许就是罗马帝国在延熹九年的遣使所获取的信息,在保萨尼亚斯充满想象的加工之下,介绍到了希腊罗马世界。
然而也许是读者数量有限,也许是保萨尼亚斯的记载听上去太过离奇,他的说法并未成为当时的流行。主要西方作家对丝绸生产的记载,与维吉尔和普林尼的“权威”论点并无二致。丝绸贸易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3世纪以后依然发达。虽然帝国西半部在5世纪初完全被来自北方的“蛮族”征服,在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依然保持对丝绸的巨大需求。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公元527-565年在位)即位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拜占庭帝国达到全盛时期。为了摆脱丝绸贸易完全被其东方邻国,敌对的萨珊波斯(Sassanian Persia,224-651)所垄断的不利局面,查士丁尼一世委托了解养蚕业和丝织技术的东方基督教僧侣沿丝绸之路东行,在中国西域地区取得蚕卵,并将其带回拜占庭帝国。公元553-554年返回的僧侣在竹筒之中藏着蚕卵回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从此养蚕业和丝织业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14]。由于拜占庭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丝绸不再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而“赛里斯”的名字也逐渐从西方作家的记载中淡出了。“丝绸之国”的回忆,只存在于欧洲人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再次来到中国之后,学者们引经据典的文献当中。
四、仰望与正视——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
古典西方作家对“赛里斯人”的记载,是以“高大”和“长寿”开始的。虽然希腊人有把周边各民族称为未开化的“野蛮人”(Barbaroi)的传统,在对待传说中的遥远民族时,却往往会以传奇般的幻想“神化”之。赛里斯人就是希腊人记载中典型的神化了的民族。
与常常喜欢记载远方传奇事件的希腊人不同,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即使是再离奇的故事,也有着看似理性的缘由。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对赛里斯人形象的描写,可算是西方最早的形象记录了。他记述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笔者注)的使节曾见过赛里斯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贸易关系。使团团长的父亲曾经到过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欢迎旅客们。他们的身材超过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人交谈。”关于赛里斯人的贸易方式,普林尼说,“商品对方在赛里斯人一侧的河岸上,如果商人感到价格和物品合适的话,就带走货物、留下货款。”[9]378-379无论是赛里斯人的外形,还是静默贸易的方式,都不是古代中国人形象的反映——锡兰使节无疑是到达了汉王朝统治下的西域地区,那里的许多古代绿洲国家的人民,有着与欧洲人相同的面容,并且身材高大。普林尼的记载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颇为真实可信,这一点有丰富的西方古典文献大学讨论和考古学、人类学研究证据[15-16]。
公元2世纪末以后,罗马帝国从极盛期迅速走向衰落。这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各种宣扬彼岸世界与灵魂救赎的思想,成为罗马国内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宗教作家,如巴尔德萨纳(Bardesanes,154-222)、奥利金(Origen,185-254)和索林(Solinus,公元3世纪上半叶人)都在其布道文中提及赛里斯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巴尔德萨纳及其学生对赛里斯人的描述。他们总结道:“赛里斯人的法律严禁杀人、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中,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既没有杀人犯,也没有凶杀受害者。在赛里斯人中,对祖宗之法的畏惧比对人们在其之下降生的星辰的畏惧还要强烈。……然而人们在他们之中还是发现了富人和穷人,病人和身强力壮者,统治者和附庸,因为一切都是统治者的权力机构所主宰的。”[11]56-59
在这段简短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汉代中国给西方宗教作家留下的十分具体的印象。由于佛教尚未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信仰,中国人并没有建立寺庙,崇拜偶像的习惯。国家政权和法律的权威深入人心,普天之下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段话语中流露着对于中国文化的景慕之情。然而中国社会的分层也为罗马帝国的宗教作家看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这恰恰是令人畏惧的“祖宗之法”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带来的。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宗教作家的这段描述都是极为精确的。
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以后,西方作家对遥远的“赛里斯”即中国的描述,一直停留在这一时期的印象中。由于中国陷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变乱,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直接控制,丝绸之路贸易受到很大影响。直到隋唐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丝绸之路上才恢复了往日商旅接踵而至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新知识,便在此时期出现了。一位名叫泰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公元7世纪上半叶人)的拜占庭作家,记录了名为“桃花石”(Taugast)的国度的信息:桃花石是一座著名的城市,居民非常勇敢,人丁兴旺。他们身材高大,超过世界上任何民族。桃花石人的首领被称为“天子”。这个民族崇拜偶像,法律公正,生活中充满智慧。习俗禁止男子佩戴金首饰,虽然他们拥有大量金银。桃花石以一条江为界。从前,这条江分开了隔岸相望的两大民族,一个穿着黑衣服,一个穿着红衣服。到毛里斯皇帝在位的时候(582-602年),穿黑衣的越过了大江,向穿红衣的发动了战争,最终取胜并建立了自己的霸业”[11]104-105。
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不难发现,西莫卡塔所讲的战争是隋灭陈之战(589年),而根据中国五行家学派的“五德终始说”,北方的隋朝是水德,服饰尚黑,而南方的陈为火德,服饰尚红,与西莫卡塔的说法吻合。根据上面的记载,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依然保持着“身材高大”的想象,而法律公正、充满智慧的说法,则仿佛是对罗马帝国晚期宗教作家记载的回溯。西莫卡塔的两处细节描写,桃花石人的“崇拜偶像”和“习俗禁止男子佩戴金首饰”,分别符合佛教化之后中国的信仰状况,和中国男性并不习惯佩戴首饰的事实[17]。如果说西方人在古典时代还对赛里斯人有所仰望的话,西莫卡塔的记载已经充分说明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知识有多么精确。
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同时,西亚地区崛起了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内,扩张到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将西欧与东方的联系切断。在唐代以后的丝绸之路历史上,进入黑暗中世纪的西欧逐渐退出了与东方的贸易。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征服大半个欧亚大陆之后,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旅行家才再次领略到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风采。由彼时以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逐渐意识到,中国是如此富裕、发达和文明的国度。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同一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伦敦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在这部经济学史上最经典的著作中,作者这样描述中国:“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肥沃、最文明、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中国,一切看上去都是停滞的。五百年前造访中国的马可波罗,讲述了那里的文明、富强与人口众多,而直到今天,旅行家们还用这些词汇形容中国。也许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很久,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她的法律与制度所能容许的富强状态。”[18]
正如斯密所看到的表象一样,中国的富裕、文明和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以后明清两代陷入了长久的“闭关锁国”状态,丝绸之路时代的辉煌不复存在。16世纪以来的五百多年中,中国历史从黑暗的、屈辱的篇章中渐渐走出,通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代的思想解放,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重拾胜利的自信,在建国后长期面临西方封锁的局面下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最终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之路。从本文回溯的西方印象来看,古代中国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生机的社会。丝绸之路不仅是将中国的形象传播给世界的途径,更是促成中国实现文明与富裕的文明之道。在丝绸之路关闭的明清时代,中国从昌盛走向没落,从发展走向停滞;而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往富强、文明和发展的对外交往路线,并在改革深化的“新常态”下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终将使世界侧目,使西方再度产生认识中国之伟大与繁荣的新观念。
[1]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China: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M]:Berlin:Dietrich Reimer,1877:496-507.
[2] PELLIOT PAUL.Notes on Marco Polo[M]:Paris:Imperie Nationale,1959:265-266.
[3] VIRGIL.Georgic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6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144-145.
[4] HORACE.Epode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3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292-293.
[5] OVID.Amore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4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372-373.
[6] PROPERTIUS.Elegie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1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76-77;364-365.
[7] HORACE.Ode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3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212-213;260-261.
[8] SENECA THE YOUNGER.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M].Loeb Classical Library 7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404-405.
[9] PLINY THE ELDER.Naturalis Historia[M].Loeb Classical Library 370-37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62-63;88-89;378-379.
[10] SENECA THE ELDER.Controversiae[M].Loeb Classical Library 46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10-11.
[11]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M].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J].学术集林,1998(12):188-190.
[13] PAUSANIAS.Hellados Periegesis[M].Loeb Classical Library 27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8:160-161.
[14] PROCOPIUS.De Bello Gothico[M].Loeb Classical Library 21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228-231.
[15] LIEBERMAN SAMUEL.Who Were Pliny′s Blue-Eyed Chinese[J].Classical Philology,1957,52:174-177.
[16] MAIR VICTOR H.Genes,geography,and glottochronology:The Tarim Basin during late prehistory and history[R]//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UCLA Indo-European Conference,Los Angeles:UCLA,2004:15-18,24-26.
[17] 张绪山.西摩卡塔所记中国历史风俗事物考[J].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5(1):88-93.
[18] 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祖钧,孟晋,盛之,译.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44.
(责任编辑:冯 蓉)
The Silk Road and W estern Concepts in China
WANG Xi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This paper,by reviewing the concepts of the Silk Road history put forward bymodern western scholars,interprets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cholars to China,the distant silk country,through the Silk Road,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ilk Roa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wa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western world,but also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maintain Chinese advanced nature and independence in its ancient civilization.Besides,by analyzing the Silk Road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development,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of the Silk Road,which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y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willmake Chinamor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The Silk Road;China Development;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One Belt and One Road"
G112
A
1008-245X(2015)06-0010-07
10.15896/j.xjtuskxb.201506002
2015-09-06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5M58086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万翔(1982-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