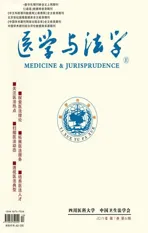“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风险探析
2015-02-12卢意光
卢意光
◆现代医学与法律
“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风险探析
卢意光
“互联网+医疗”正在不断发展,其中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医生集团等备受社会关注——它们对于解决目前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使用效率不高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亟待完善相关立法。
远程会诊;移动医疗;医生集团;法律风险;立法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去中心化等特性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提升传统行业的创新力和覆盖力。[1]自互联网技术与医疗行业结合以来,移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软件等层出不穷,“远程会诊”“移动医疗”“医生集团”“数字医疗”“网络医院“可穿戴设备”等新概念、新模式也应运而生。由于“互联网+医疗”可以缓解当前处在困境中的医患矛盾,提高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所以无论是投资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还是一般民众,对其都表示欢迎。
就在“互联网+医疗”的投资和发展处于如火如荼之际,2015年4月1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涉及医学的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医生通过网络只能作健康方面的咨询,但不能开展医疗诊治工作。某些媒体将上述言论解读为国家卫计委明确禁止“互联网+医疗”,并认为这是在阻挡新生事物、扼杀互联网时代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而进行的探索。随后,国家卫计委对此予以澄清,认为是外界的误读。
“互联网+医疗”,这个新鲜事物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可能涉及哪些法律风险?行政监管应当如何规范其行为以促进其健康发展?这些都值得我们我们认真探讨。鉴于篇幅,本文仅讨论“互联网+医疗”中的远程会诊、移动医疗和医生集团。
一、远程会诊及其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远程会诊”,是指接诊患者的主治医师利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与会诊专家进行沟通和咨询,为患者完成病历分析、病情诊断,以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或提出医学建议的医疗行为。远程会诊有力地带动了传统治疗方式的改革和进步,为医疗走向区域扩大化、服务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也为规范医疗市场、评价医疗质量标准、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交流医疗服务经验提供了新的准则和工具。
(一)目前我国有关远程会诊的法律规定
1999年1月4日,我国原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以下简作《通知》)。《通知》共八条,其中第七条指出:“会诊医师与申请会诊医师之间的关系属于医学知识的咨询关系,而申请会诊医师与患者之间则属于通常法律范围内的医患关系。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属于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若出现医疗纠纷仍由申请会诊的医疗机构负责。”
2014年8月21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以下简作《意见》),对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监督管理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并明确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含影像、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等)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所规定的其他项目”。
综上,我国目前有关远程会诊的相关法律规定,专门性立法少、所涉及的法律位阶不高、太过原则而可操作性不强,对远程会诊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行政监管等均未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二)远程会诊中会诊专家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在远程会诊中,所涉及的主体很多,包括患者、接诊医生、远程会诊专家、各方医疗机构、互联网公司等。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远程会诊是由互联网公司组织的基层接诊医师与会诊专家之间通过移动终端APP进行连接的远程会诊。因此,我们重点讨论该种情况下远程会诊所涉的法律风险,特别是会诊专家所涉的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从所涉及的法律责任角度,可以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其一,行政责任。根据《通知》及《意见》的要求,医师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应满足以下条件和要求:首先,会诊医师应当具备副高或以上职称;其次,会诊专科要对应;再次,会诊医师应履行知情同意义务,要向患者或其近亲属充分告知并取得同意,同时妥善保管有关资料;最后,远程会诊属于医学咨询,会诊意见提供给接诊医生,不能直接提供给患者。
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具体,但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包括:
一是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有严格的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因此,会诊专家一旦违反了上述《通知》或《意见》,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处罚就成了一个难题。
二是远程会诊与传统会诊的区分问题。2005年4月30日,原卫生部发布《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本规定所称医师外出会诊是指医师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为其他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而远程会诊被原卫生部认为是医学咨询,两者(远程会诊与传统会诊)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待明确。
三是会诊专家的远程会诊是否属于执业行为的问题。如果远程会诊仅仅是医学咨询,与患者之间不构成医患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远程会诊就不应当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执业活动,就无须取得会诊专家所在医疗机构的同意?笔者对此持肯定观点。
其二,民事责任。根据《通知》,会诊医师(即远程会诊专家)与申请会诊医师(即接诊医生)之间的关系属于医学知识的咨询关系,而申请会诊医师与患者之间则属于通常法律范围内的医患关系。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属于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2]若出现医疗纠纷仍由申请会诊的医疗机构负责。按照这样的规定,远程会诊专家不对医疗纠纷承担责任。但是,笔者认为,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只要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卫生部的这个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相悖。
其三,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一种惩罚性责任,只有在施行其他法律责任后仍不足以惩戒时才使用。因此,如果没有规定应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则可以不考虑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在民事、行政责任不清的情况下,是否一定可以规避刑事责任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移动医疗及其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国内尚没有关于“移动医疗”的定义。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对“移动医疗”的定义是:指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3]国内较主流的移动医疗模式包括医疗保健信息平台、可穿戴健康设备以及医药电商等。
(一)医疗保健信息平台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医疗保健信息平台是医务人员与患者通过互联网媒介的帮助,进行信息交流、沟通和咨询的平台。2009年7月1日施行的《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开办医疗卫生机构网站、预防保健知识网站或者在综合网站设立预防保健类频道向上网用户提供医疗保健信息的服务活动。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进一步明确表示,互联网上医生通过网络只能作健康方面的咨询,不能开展医疗诊治工作。笔者对其法律风险作如下讨论:
其一,行政责任。医疗保健信息平台只能进行健康咨询,不能从事诊疗活动,否则就可能遭受行政处罚。但问题是,如何准确甄别健康咨询与诊疗活动。
我国法律没有对“健康咨询”这一概念进行界定。1994年,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作《细则》)将“诊疗活动”定义为: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由于《细则》制定时,我国处在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实践中,对“诊疗活动”的理解常常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立法的时候,还没有将药物区分为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没有将医疗器械进行明确分类;但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利用非处方药、一类医疗器械等自行进行部分健康管理,而这些健康管理活动,与《细则》规定的“诊疗活动”很难区分。同理,医疗保健信息平台所进行的健康咨询,与《细则》规定的“诊疗活动”也存在界限模糊甚至重合的情形。对于构建平台的主体,就存在可能承担行政责任的法律风险。
其二,民事责任。通过医疗保健信息平台,患者可能是进行一般的健康信息咨询,也可能是对已有症状或不适体征进行针对性的问诊,这与病情的发现、处理和康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而且,在实际咨询中,医患各方对医疗问题询问和解答的尺度把握不同,医师的有些解答可能已经涉及疾病的诊断和处理。因此,即使互联网公司试图通过格式性的条款来约定咨询的免责情况,但如果医师在咨询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该咨询医师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刑事责任。医疗保健信息平台在提供医学信息咨询的过程中,不仅涉及经济利益的获取,而且还涉及广告的发布。如果这些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则主要涉及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如果情节或后果非常严重,则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二)可穿戴健康设备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没有就“可穿戴健康设备”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一般认为,“可穿戴健康设备”是指直接穿在身上或整合到用户的衣服或配件的一种便携式设备。[4]通过可穿戴健康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再利用软件支持以及数据交互、云端交互来实现人体健康数据的监测、分析和解读。举例来说,AppleWatch即为可穿戴健康设备,该设备包含了健康配件功能,如体重管理、压力管理等。
可穿戴健康设备所涉的法律风险同样可以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一般产品责任类似,行政责任则主要看可穿戴健康设备与医疗器械的联系与区别。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的效用主要是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而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辅助作用。使用医疗器械的目的是: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妊娠控制;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因此,如果可穿戴健康设备符合医疗器械的定义及上述特征,则可将其纳入医疗器械的监管范畴,对其产品的研发、注册或备案、生产、经营、使用、广告发布等方面进行监管;如果可穿戴健康设备被认定为医疗器械,但企业又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去管理,就可能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在实践中,如何对可穿戴健康设备和医疗器械进行区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然,大部分可穿戴健康设备生产厂家和经销商都不希望可穿戴健康设备被纳入医疗器械的范畴,不愿意接受CFDA严苛的监管,声称其产品的使用目的不是对疾病的管理或治疗,而是仅对人体健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三、医生集团及其所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医生集团的基本理念是医生用持有股份或签约的方式加入医生集团这一独立法人,自愿分工合作,各自用自己的优势给病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分享收益。有数据显示,美国超过80%的医生加入医生集团,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部分医生依赖医生集团执业。但是,美国的医疗体制和中国完全不同:其没有“编制”的概念,保险完全商业化,公立医院不占绝对优势,不存在放开多点执业等。因此,不能完全参考美国的情况来预测中国的医生集团如何发展。
医生集团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可能涉及以下法律问题:
(一)医生集团开展诊疗活动的前提条件
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即便医生集团的专家都是高水平的专家,但是如果医生集团没有取得行政许可(即执业许可证),其是不能擅自从事诊疗活动的。这容易理解,即医疗机构除了要有人员以外,还要有设备设施、场所场地、规章制度等,要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行政监管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为难企业,而是为了保护公众安全。一家医疗机构如果消毒措施不过关或设备简陋不符合要求,即使其医生水平再高,其手术效果也难以得到保障。
(二)医生集团与医疗机构的合作问题
医生集团的优势在于其拥有高水平的医生,但高水平的医生资源是短缺的。因此,必须要有医疗机构愿意与医生集团合作,共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平台。这种合作,可以是医生集团自己开设医疗机构、收购医疗机构,也可以是医生集团与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当前,与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更为便捷和灵活,成本也最低,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和效益;但是,需要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必将给今后工作埋下隐患(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责任,可能互相推诿,纠缠不清)。
(三)医师多点执业问题
2014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14〕86号),至目前,各地试点情况不一。如上海就没有参与试点,仍然执行2007年发布的《上海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医师外出行医管理的指导意见》(沪卫医政〔2007〕124号)。医生集团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诊疗活动,应当与当地的多点执业规定相衔接,否则,医师的诊疗活动就成了“走穴”。
医生集团的法律风险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医生集团内部如何拟定章程、医生是否有权持股、各医生的权利义务如何、机构如何正常运转等,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定,否则,也会留下隐患,成为其发展壮大的“瓶颈”。
四、关于“互联网+医疗”的立法建议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互联网+医疗”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风险有很多是由立法上的滞后导致的,故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重新定义“诊疗活动”
目前的“诊疗活动”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确定的,其当时所指,与当前的社会环境、行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有必要重新定义,并至少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其一,行业技术的不断更新。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以前看起来风险很大的事情,逐渐变得平常以及风险可控。如测量血压,随着电子血压计的不断进展,家用血压计开始普及,高血压患者可以自行或请家属代为测量血压,这样可以免除去医疗机构测量血压的舟车劳顿。因此,在对“诊疗活动”进行定义时,可以将这部分医疗器械的使用予以排除。与此类似的还有非处方药的服用、与诊疗活动互为补充的健康管理等,不必纳入诊疗活动的范畴。
其二,诊疗行为的风险评估。立法对“诊疗活动”进行定义并设定监管措施,其用意在于控制其风险,防止损害患者的生命健康。但实际上,风险无处不在,即使是使用家用温度计测量体温,也可能因测量不准而延误病情。因此,在立法时,应当对风险高低进行评估,对于风险极低的一些行为,在其收益远大于其风险时,可以不纳入诊疗活动的范畴。如利用互联网进行的轻问诊,虽然也存在一些风险,但其极大地提高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对于患者及时、便利地处理一些医疗问题提供了可能,在权衡其对整个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收益时,收益明显高于其风险,因此,可以不纳入诊疗活动的范畴。
(二)完善“互联网+医疗”的立法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医疗”的格局和边界也应当有相应的调整变化,需要通过进一步立法来加以明确。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互联网+医疗”也经历了一个从禁止到解禁、从探索到成熟的过程。此外,关于互联网远程医疗与医保的对接、网上支付、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资质认定、远程医疗纠纷的处理方法、患者权利维护与救济等,都需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技术规范和完善立法来加以保障。[5]只有这样,法律风险主体进行法律风险管理才会更有针对性,行业的健康发展才更有保障。
[1][5]潘多拉.医疗服务别赶“互联网+”时髦[J].中国卫生人才,2015(5):14-15.
[2]左秀柒.网络时代远程医疗法律问题论析[J].人民论坛,2010(12):54-55.
[3]宗文红,陈晓萍.国外移动医疗监管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2(4):340-345.
[4]郝军志.移动医疗:看病从此不再难?[J].快乐养生,2014 (11):10-13.
(责任编辑:王海容)
Discussions on Legal Risks Involved in"Internet+M edical Treatment"
Lu Yiguang
"Internet+Medical Treatment"i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among which telemedicine,mobile health and medical group have attracted much social attention,and they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balancing medical treatment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improving use efficiency in China,meanwhile,there are also some legal risks,therefore,relevant legislation should be perfected.
tele-consultation;mobile health;medical group;legal risk;legislation
卢意光,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