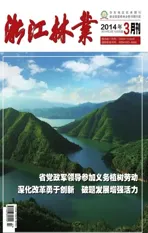印象俄罗斯
2014-04-24撰文摄影何晓玲
◆撰文摄影/何晓玲
印象俄罗斯
◆撰文摄影/何晓玲
俄罗斯是个很复杂的国家,古典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放,艺术与政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掺杂其间。这就是我对它的总体印象。
解一个心结
俄罗斯,对于中国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人来说,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情感。爱怨交加,褒贬不一,熟悉与陌生并存。这种情感自然来自于耿耿于怀的前苏联情结。从建国之初的无私援助,到关键时刻的撂挑子走人,是“苏联老大哥”培养出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趁着寒冷的秋冬季到来之前去了趟俄罗斯,也算是解了一个心结。
毕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经历过大起大落历史骤变的大国,虽然整个空气显得有些沉闷,节奏有些缓慢,神情有些灰暗,但还是可以体察到无处不在的唯我独尊、自负自大的傲气,甚至还能感受到彼得大帝、沙皇帝国的遗风。
来到莫斯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并不陌生的“莫斯科大学”。这座完全开放式的学府,曾经是多少共产主义者的摇篮,也是多少中国仁人志士成长的起点。高大雄伟的建筑,典型的苏联式风格,典雅而大气。它是斯大林年代苏联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既保留了沙皇时期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现代艺术的元素,堪称经典。
要说苏式建筑,其实在国内也早就有过接触,譬如北京展览馆、上海中苏友谊大厦,还有哈尔滨的许多老屋。那些原本就是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项目,不仅外表相似,而且内部布局、装饰、摆设也全都是苏式。记得曾经在北展的“老莫剧场”观看过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经典芭蕾《天鹅湖》,至今印象深刻。剧场不大,小巧精致且金碧辉煌,演员在台上翩翩起舞,就像是镶嵌在一幅幅流动的油画上。
虽说芭蕾是响当当的俄罗斯特产,可惜即便在当地,也只是上层人等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所以想在俄罗斯看一场原汁原味的芭蕾也只能是奢望了。好在俄罗斯可以提得起的东西很多,以至于少看一场芭蕾也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说芭蕾,自然就离不开柴可夫斯基;提到柴可夫斯基,就会联想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普希金等等。这些伟大的俄国诗人、作家、作曲家,都与一座赫赫有名的城市——圣彼得堡联系在一起。那些不朽的名字和作品,使19世纪的圣彼得堡成为一个充满芭蕾、艺术、文化、茶和鱼子酱的世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圣彼得堡人,被百姓称作是当代的彼得大帝,评价不低。
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每条街道都街灯悠悠,忽明忽暗地映射着两旁的橱窗、楼群;地面被洒上了一层薄薄的清水,倒映出朦胧的街景,极其清净;城区的建筑十分古老,几乎都是彼得大帝手上留下的产物,保存非常完好;坚实厚重的石块砌墙,整齐划一的楼层高度,还有纵横交错的市区水网,活脱脱一个翻版的威尼斯。置身于圣彼得堡的晨曦中,仿佛有一种梦回中世纪的感觉,那种只有在小说和电影里才能想象的体验。很喜欢这样的氛围,就一边慢慢地在路边小餐馆里用餐,一边尽情地享受着梦游般的美丽,静静等待圣彼得堡的天明。
要说圣彼得堡流淌在市区大街小巷水道里的支流,都来自于著名的涅瓦河,那条连接着紧靠欧洲波罗的海芬兰湾的母亲河。涅瓦河的源头有著名的彼得保罗要塞,也就是圣彼得堡的发源地,那个独特的俄罗斯双头鹰国标最早就出现在这里。据说对此设计最形象的解释是:一头望着西方,一头看着东方。要塞里还有一栋不起眼的房子——当时的俄罗斯铸币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版人民币就出自于此。
泛舟在清澈的涅瓦河上,尽享两岸风光,品尝高度的沃特加和美味的鱼子酱,和着久违的手风琴声,与俄罗斯艺人们共同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苏联老歌和中国民歌,那种亲切而复杂的情感再次被勾起。中国—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无处不在,并且相信,还会继续绵延下去,源远流长。
艺术流
俄罗斯是个拥有历史、深涵文化、充满艺术的国家。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无处不跳跃着文化与艺术的音符。那些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众若繁星的艺术作品,无论体现在建筑里、芭蕾里、诗歌里、小说里、电影里、歌曲里,都是那样经典。这些足以让他们骄傲的精神财富经久不衰。
位于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堪称是俄罗斯的艺术精粹,仅次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被列为世界第四大博物馆。但我们对冬宫的最初认识却并不在于它的艺术地位,而是来自于腥风血雨的《列宁在1918》。那个炮打冬宫的震撼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还有那艘制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洛尔号巡洋舰,仍停留在邻近的涅瓦河上。如今,当那些充满硝烟的年代渐渐远去,当历史一次次地轮回,冬宫博物馆,这座最初的沙俄女皇的宫殿,虽然历经磨难和沧桑,其艺术的光华却依然璀璨。这就印证了一句老话,唯有文化与艺术将会长存,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一入冬宫,那个电影里展现过的镜头便映入眼中:长廊、深宫、熙攘的人群,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列宁在1918》。但再往里走,这种感觉就很快渐行渐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股扑面而来的艺术流。珍珠、玛瑙、宝石、翡翠,一件件珍品令人目不暇接,但要说冬宫里最金贵的,还是那些铺天盖地、藏品繁多的油画作品,举首投足之间都能与它们相遇。镇宫之宝是两幅风格迥异的达·芬奇的油画真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排队观瞻。
冬宫博物馆的艺术性自不必说,让我们惊叹的倒是俄罗斯地铁站的华丽和精美。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地铁,享有“地下艺术殿堂”之美称。我们特意选乘了一个站点打了个来回,去感受那里“深藏不露”的艺术氛围。
真是名不虚传,其每一个站点都以不同的风格和基调装饰,廊柱上、站壁上、顶篷上到处是色彩靓丽、绘制精湛的雕塑、油画。而且地铁站分上下多层,错落有致,景深宽厚。如果从一个局部去看,简直很难想象这是人来人往、俄罗斯最为拥挤、市民行动速度最快的公共场所。难怪去俄罗斯的行程中,常常会把参观莫斯科地铁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莫斯科的地铁是全世界最古老、效率最高、入地最深的地铁,建于1935年。为了战事,修得很深,足有上百米。从站口进入扶手电梯,一眼望下去几乎看不到底,而且坡度之陡、速度之快,是我们从未体验过的,一脚踏上去多少还带有点恐惧感。而当地市民却习以为常,依然在快速运行的电梯上步履敏捷,行色匆匆地穿过习惯上留出的左半边通道,随流速上下跨步。唯有此时才一扫俄罗斯人节奏缓慢的整体形象,显现出活力来。都说俄罗斯只有“两快”,一是地铁里的行人速度快,二是马路上的车子开得快。
俄罗斯体现艺术的地方真是无所不有,就连墓地这样悲凉、肃穆的场所都可以表现得很艺术,真是佩服。我们在莫斯科参观过的新圣女陵园就是欧洲三大公墓之一,这里安葬着2.6万多个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他们中有很多熟悉的名字,赫鲁晓夫、叶利钦、卓娅、奥斯特洛夫斯基、斯大林夫人、屠格涅夫、高尔基、乌兰诺娃、乡村女教师的饰演者等等,甚至还有唯一的一对外国人——中国的王明夫妇(因离婚未葬同穴)。这里独具特色的是,每一块别致的墓碑都由著名的设计师根据逝者的生平故事来设计,几乎每件都是很好的雕塑作品。譬如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用黑白两种大理石雕刻成的一张阴阳脸,寓意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屠格涅夫的墓碑长有两个翅膀,这是为了纪念其对苏制“图系列”战机设计制造的贡献;叶利钦待遇不错,墓碑被设计成俄罗斯白蓝红三色国旗的形态,显然是一种较高的荣誉。
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逝者,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如此而言,唯有俄罗斯人最浪漫、最潇洒,即便死去,也可以进入艺术的天堂。
开放与固守
受苏联的影响,俄罗斯如今仍保留着很多固有的东西,包括刻板与官僚。但只说其守旧,那也是偏颇。
俄罗斯的开放令人惊讶,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从教条的束缚中走出来,又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很有一种叛逆心理。所以行为和观念都十分前卫,大有全世界之最的程度。
大街上,抽烟的女孩比比皆是,而且穿着时髦又大胆,成为一道风景。公共场合,醉酒的男孩常常能见,随处会有一堆堆丢弃的酒瓶。年轻人收入不多却花费大方,经常寅吃卯粮。唯有用车不讲究,除了婚礼时租用的长体礼仪车以外,马路上破车、旧车、脏车、低档车很多,只要能跑,得过且过。想起去日本时看到满世界都是的新车、靓车、豪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远眺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虽说物价较高,商品相对匮乏,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却不低。城里人大多在郊外建有自己的别墅,成片连群,多为木制,色彩艳丽,虽然不大但很温馨,去彼得夏宫的一路上就见到很多。所以大凡周末,市区的街道会明显比较空闲,车和人都少,他们全都在外出度假。
俄罗斯充满现代气息的街区很多,莫斯科就有一条著名的阿尔巴特街,浪漫诗人普希金的故居就坐落于此。小街两侧布满了咖啡屋、小酒吧、鲜花铺、礼品店。沿途还有摆卖各式油画的小摊、任人随意涂鸦的粉墙、街头艺人随性而起的悠扬琴声……这种令人身心愉悦的开放倒是大受欢迎。
此外,真正让人感到大气、开放的是他们政府部门的透明。连克里姆林宫这样的总统府要地,平时也对外开放,允许游客入内参观。但有严格的路线规定,要员行车经过的路上不能随意踏入和停留,有保安专人看管。违反规定者首次将被警告,再次就会被带离。
克里姆林宫高墙围绕,内有数座著名的教堂,平日里游人如织,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热点。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好安保工作实属不易,好在俄罗斯的克格勃很厉害,解决这点问题,小菜一碟。其他机关、校园大多没有围墙,通透性很好,给人一种敞亮的感觉。说到克格勃,车行时曾路过克格勃总部大楼,从外表看很不起眼,一栋极普通的白色建筑,只是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显得很神秘。
说开放,俄罗斯又不失有许多固守。与年轻人相反,老年人普遍比较传统,尤其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思想和行为始终信守马列主义。综观上下,虽然苏联解体已是旧事,但其遗留的痕迹依然清晰。马恩列斯像尽管不多但仍能见到,民族友谊宫、胜利纪念塔、勇士凯旋门,依然是他们心中的骄傲。特别让人感慨的是,年轻人结婚最热门的婚纱拍摄地和礼仪场所是胜利纪念广场和红场。不难看出,那种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民族的根,永远都不会枯折。在莫斯科,近年几乎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红场阅兵仪式,还常常模拟当年的战斗场面,再现苏联红军英勇不屈的顽强精神,以纪念卫国战争的胜利。
要说红场,的确是俄罗斯的象征,虽说面积不大,但人气很旺。那里有华丽宏大的古姆商场,尽管历史悠久却依然充满现代气息;有童话般美丽的建筑群,色彩斑斓,熠熠生辉;有绿树成荫的广场公园,空气清新,整天熙熙攘攘;有年轻的新郎新娘,带着喜悦,在这里举行浪漫的婚礼;有每一个整点按时进行的红场卫兵交接仪式,庄严而神圣,成为市民们争相守候的盛典;还有几经风雨的列宁墓,命运多舛,终究仍占有一席之地……固守,其实是一种血脉的延续,一种情愫的寄托,一种精神的回归。
开放与固守,让人们看到一个多元而立体的俄罗斯民族。
窄窄的上帝之门
就像去欧洲访问一样,少不了会去参观教堂。俄罗斯也有许多精美的教堂,有的还挺有名气。
俄罗斯人大都信奉东正教,所以他们的教堂也有其独特的风格,既有别于德国哥特式的尖顶设计,也有别于罗马梵蒂冈式的厚实建筑,以别具一格的圆顶“洋葱头”为标志。最著名的是位于红场南端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色彩斑斓、童话般美丽的“洋葱头”拱顶造型,不知在多少画面和镜头中出现过,也成为莫斯科地标性的建筑。
要说那些教堂顶上“洋葱头”的数量是有讲究的,通常为3头、5头、13头等单数,这个缘由想必出自于圣经故事。据说俄罗斯的大教堂中,“洋葱头”最多的达到33个,象征着耶稣在人间生活的33个月。
其实东正教特别敬奉的倒不是耶稣,而是圣母玛利亚。做弥撒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忏悔的时候,都会面对圣母像。所以,俄罗斯教堂里的圣母像特别多,千姿百态,神情各异。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东正教徒做祷告时画十字的动作与基督教有点细小的差别,基督教是上下左右,东正教则是上下右左。至于此番举动的个中原因,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俄罗斯的教堂遍布很广,大城市里尤其多,这恐怕也是西洋教区别于我们佛教的地方之一。佛教的寺院大多建在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处,佛主对众生的教诲是要超凡脱俗,六根清净,躲避尘世的烦恼;西洋教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希望人人参与,自律自主,教堂常建在市区,供教徒方便做礼拜,而且允许犯错误,但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
佛教与西洋教的诵经曲调也大不相同。中国有句老话叫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佛经诵词单调冗长、浑厚低沉;教堂里诵经则是洪亮悦耳的唱诗和音,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演唱演奏,带有很强的表演性,在俄罗斯的时候就听过好几次美妙的唱诗颂词。这与中西乐曲的特点正好相反,中国的民乐音调高扬,清脆明丽,高音区表现充分;西洋乐则雄浑圆润,大气深沉,低音区极具魅力。从外观上看,寺庙巍峨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教堂则富丽华贵,视觉美观。这也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对人对己的要求不同。
克里姆林宫周围就有好几座漂亮的大教堂,金碧辉煌,高耸入云。只是不能理解的是,每一座教堂的入口都很窄小,哪怕是正门,有的只能勉强一个人通过。所以常常在进门处拥挤不堪,或排起长队,这与其高大的外表和宽敞精致的内部厅堂很不相称。如果你注意考证一下,似乎所有的教堂门都不大,欧洲也一样。这就不得不让人想深究下去,也许这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和教诲在行事。
耶稣曾告诫他的信徒:“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导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到底还是上帝高明,看问题就是深刻,仔细想想这话还挺有哲理。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从大处出发,往往越走越小;从小处起步,却能越走越大。原来上帝洞开的小门,是为了要引导到人们的永生。